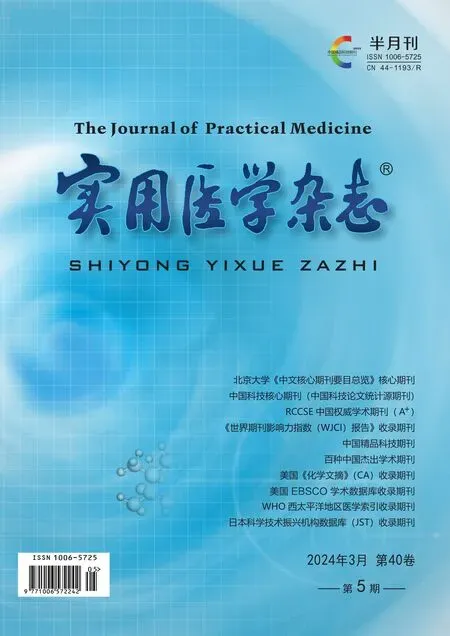基于術前磁共振小腸成像預測克羅恩病患者首次腸切除術后早期吻合口復發風險
何偉濤 申曉迪 王楊迪 杜金芳 李雪華 熊珊珊 李周雷 林少春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1放射科,2消化內科 (廣州 510080)
克羅恩病(Crohn′s disease,CD)是一種慢性復發性炎癥性腸病,常伴有腸梗阻、腸瘺或腸周膿腫形成[1-2]。約70%的CD患者在確診后因腸道并發癥或保守治療無效需要行病變腸管切除術[3]。然而,術后1年內,約25%的患者會出現臨床復發,超過50%的患者出現內鏡復發,而且大部分發生于手術吻合口區域,經常需要再次或反復的手術[4-5]。反復手術可能會導致短腸綜合征,導致患者預后不良。早期吻合口復發(early anastomotic recurrence,EAR)高風險的患者在術后積極進行早期藥物預防,可有效改善其預后[6]。因此,根據CD患者的EAR風險程度對CD患者進行分層后個體化治療,是改善其預后和避免再次手術最經濟有效的方法。
內鏡是目前監測吻合口復發的金標準,并建議在術后6 ~ 12個月內進行[3,7]。影像學對診斷CD術后復發也有較高的準確性[8-9];然而,大部分研究都聚焦于EAR的術后評估,而不是術前預測。在臨床上,超過50%的內鏡復發患者術后1年內并無明顯的臨床癥狀[5],因此患者接受及時隨訪復查的主觀意愿并不強,導致診斷延誤和治療效果下降。如果術前就能對EAR高風險患者進行準確識別,術后及時進行藥物預防[6],可降低其復發率并改善預后。
磁共振小腸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enterography,MRE)是評估CD的最重要影像學檢查技術[10-11]。結合常規MRE[12]和功能性MRE,如磁化傳遞成像(magnetization transfer imaging,MTI)[13]和擴散加權相關成像(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DWI)[14-16],可提供更全面的病理生理學信息甚至預測復發風險的工具。
本研究旨在術前眾多資料中篩查可預測EAR的有效危險因素,并構建一種用于術前預測CD患者首次腸切除術后EAR(≤ 12個月)風險度的列線圖模型。為了評估術前指標具備有效預測性,我們在研究前期也同步納入了術中和術后的可能危險因素進行分析。
1 資料與方法
1.1 患者納入和排除標準回顧性收集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經臨床、影像學、內鏡及病理綜合確診為CD的擇期手術患者的術前(臨床、實驗室指標、影像)、術中和術后(病理、藥物治療)資料。所有患者均行傳統CD腸切除術,即在切除病變腸管時,與腸緣平齊分離并保留病變腸管周圍的腸系膜[17]。納入標準:(1)經臨床、影像學、內鏡及病理綜合確診為CD;(2)術前行多參數MRE;(3)手術前后臨床等資料齊全,在術后有可探及吻合口的內鏡復查。排除標準:(1)既往有腸管切除術史;(2)合并其他腸道疾病;(3)MRE圖像質量差或MRE距離手術超過3個月;(4)圖像質量不佳;(5)術后腸鏡復查距離手術時間超過12個月。本研究經本院倫理委員會批準([2020]351;[2021]140),豁免知情同意。
1.2 術前資料收集
1.2.1 術前臨床和實驗室檢查資料由1名放射科醫生從電子病歷中收集患者術前1周內的臨床和實驗室檢查數據,包括性別、年齡、病程、身高、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吸煙史、C反應蛋白、紅細胞沉降率[6]。
1.2.2 MRE掃描方案患者在MRE檢查前進行了常規腸道準備[13]。采用3.0-T MR(Magnetom Trio;德國西門子醫療)掃描儀及多通道相控陣體線圈進行掃描,掃描范圍自肝頂至恥骨聯合,患者取仰臥位。所有患者均行MRE平掃及增強掃描、DWI和MTI檢查。掃描序列包括:(1)T2加權成像(T2-weighted imaging,T2WI);(2)DWI,后處理獲得擴散峰度成像(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和體素內不相干運動(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IVIM)成像;(3)MTI;(4)脂肪抑制三維容積內插屏氣序列(three dimensional volumetric interpolated breath-hold examination,3D-VIBE)T1WI,采用高壓注射器以2 mL/s的流速經右側肘前靜脈注射0.2 mL/kg釓噴酸葡胺注射液(Gd-DTPA,北京北陸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注射對比劑后立即以相同流速注射0.9%的生理鹽水共20 mL,于注射前及注射對比劑后第15秒、第70秒和第7分鐘采集動態對比增強圖像。
1.2.3 腸道病灶在MRE圖和手術切除標本上的匹配定位由1名具有多年腹部影像診斷經驗的放射科醫師,在知曉患者臨床資料的情況下,根據手術記錄及大體照片上的腸管解剖標志(如回盲瓣或闌尾,病灶最狹窄部位、腸粘連或腸瘺),將腸道病變最嚴重處在術前影像和手術切除標本上進行區域對區域的定位標記[13]。
1.2.4 腸道病灶及腸周脂肪的常規MRE序列分析由2名具有多年腸道影像診斷經驗的放射科醫師,在不知曉臨床、手術和病理信息的情況下,對已標記病灶的MRE圖進行獨立閱片。評價2名醫師評估結果的觀察者間一致性;然后二人再對定性變量共同討論達成一致意見,作為最終結果后續分析,定量變量以2名醫師測量平均值為最終結果。本研究同時對病變腸段及其周圍腸系膜脂肪的MRE參數進行了評估。病變腸段的常規定量參數包括:腸壁最大厚度、最狹窄處內徑、狹窄近端腸管最大處內徑、狹窄指數(狹窄腸段近端最大內徑與最狹窄處內徑之比)[18];常規定性參數包括:腸壁不對稱增厚[19]、腸壁T2WI信號強度、腸壁動脈期強化方式[12]、小腸梗阻[19]、腸管假憩室樣擴張[20]、腸黏膜假息肉樣增生[21]。病變腸段周圍腸系膜的常規MRE參數包括:腸系膜爬行脂肪指數(mesenteric creeping fat index,MCFI)、腸系膜脂肪增生[12,22]、淋巴結腫大[23]、梳狀征[24]、腹盆腔積液和穿透性病變(如膿腫/炎性包塊)。
1.2.5 腸道病灶及腸周脂肪的功能MRE序列分析此外,我們還在功能MRE上分析了病變腸道及其周圍脂肪的特征。使用MATLAB(MathWorks,Natick,MA)后處理軟件繪制感興趣區域(region of interest,ROI),分別測量DWI、DKI、IVIM和MTI的定量參數。首先選擇病變最嚴重的腸壁勾畫3個ROIs獲得相應參數值,ROI需覆蓋腸壁全層。另有3個ROI放在離切除腸壁約1 cm的腸系膜上,避開血管和淋巴結。3個ROI的平均值作為最終結果。測量DWI上的表觀擴散系數(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DKI上的非高斯分布的表觀擴散系數(apparent diffusion for non-Gaussian distribution,Dapp)和表觀擴散峰度(apparent diffusional kurtosis,Kapp),IVIM上的擴散系數(diffusion coefficient,D)、假性擴散系數(pseudodiffusion coefficient,D*)和灌注分數(perfusion fraction,f),以及病變腸壁的磁化傳遞率(magnetization transfer ratio,MTR)、病變腸壁的標準化MTR1=MTR病變腸壁/MTR肌肉和標準化MTR2=(MTR病變腸壁-MTR正常腸壁)/(MTR肌肉-MTR正常腸壁)。
1.3 手術或術中資料收集從患者手術病歷中收集手術或術中相關信息,包括手術指征、術式、切除腸段范圍。
1.4 術后資料收集
1.4.1 術后標本病理分析由一名腸道病理醫生選取腸道病變最嚴重處的病理玻片[13]并使用半定量評分系統(0 ~ 4分),在蘇木精-伊紅染色上行炎癥評分和在馬松三色染色上行纖維化評分[25]。
1.4.2 術后藥物治療信息收集患者術后早期的藥物預防策略。術后早期藥物預防定義為術后給予免疫抑制劑(如硫唑嘌呤和6-巰基嘌呤等),或抗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藥物(如英夫利昔單抗等治療);無術后早期藥物預防定義為術后未予CD相關的藥物治療,或只予常規抗生素或美沙拉嗪治療[6]。
1.5 術后吻合口復發標準由1名消化內科醫師對吻合口區域(即吻合口和吻合口以近約10 cm的腸段[8])復發進行評估。吻合口復發定義為內鏡復發或手術復發[7]。術后12個月內吻合口區域內鏡Rutgeerts評分≥ I2或需要再切除吻合口的患者定義為EAR。術后12個月內吻合區內鏡Rutgeerts評分為I0或I1且不需再切除吻合口的患者定義為無EAR。
1.6 統計學方法使用SPSS 20.0版(IBM Corp.,Armonk,NY,USA)和R 3.6.1版(http://www.rproject.org)進行統計學分析。P< 0.05認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連續變量用均數±標準差或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表示,采用Mann-WhitneyU檢驗比較組間差異。分類變量用頻數和百分比表示,有序分類變量采用Mann-WhitneyU檢驗,無序分類變量采用Fisher精確檢驗比較組間差異。采用Spearman相關分析評估EAR情況與術前中后資料之間的相關性。
先使用R的glmnet軟件包進行最小絕對值收斂和選擇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回歸實現數據降維和變量選擇。對LASSO回歸篩選出的變量進一步行多因素二分類logistic回歸分析,并采用似然比檢驗、赤池信息量準則(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及向后逐步選擇法篩選出可以預測EAR的獨立危險因素。基于篩選出的獨立危險因素,使用R的rms軟件包建立預測EAR風險的列線圖預測模型。模型預測能力是通過其區分和校準能力來評估的;其區分能力通過計算Harrell一致性指數(Harrell′s concordance index)和自舉驗證(1 000個自舉重采樣)校正的一致性指數來量化評估,一致性指數> 0.70認為區分能力中等,> 0.80認為區分能力較高[26];其校準能力通過繪制具有1 000個自舉重采樣的校準曲線以及Hosmer-Lemeshow擬合優度檢驗(P> 0.05認為模型擬合優度較高)來評估。建立列線圖預測模型后,每個患者均可計算出總分,與實際復發情況相比較,應用受試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分析,根據約登指數(Youden index,YI)最大值可以確定EAR風險分層的閾值。
2 結果
2.1 臨床資料53例CD手術患者中,排除無術前3個月內MRE資料5例,合并其他腸道病變2例(腸結核1例,組織胞漿菌病1例),既往腸管切除病史7例,圖像質量不佳3例,術后腸鏡復查超過12個月6例;其余30例患者納入本研究[男18例,女12例;年齡(28.07 ± 9.34)歲]。這30例患者中,復發組18例(60%) (內鏡復發,n= 17;手術復發,n= 1),無復發組12例(40%)。兩組患者的臨床資料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0.05)。見表1。是否發生EAR與臨床、實驗室檢查、病理等資料均無相關性(P> 0.05),見圖1A。

圖1 早期吻合口復發與臨床病理特征(A)、病變腸段MRE征象(B)、腸周腸系膜MRE征象(C)的相關性Fig.1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early anastomotic recurrence with clinico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A),preoperative MRE findings of the resected intestines(B),preoperative MRE findings of the perienteric mesentery(C) in the study

表1 無早期吻合口復發組與復發組CD患者的術前病變腸段周圍腸系膜傳統MRE參數差異Tab.1 Differences in preoperative MRE findings of the perienteric mesentery between the non-EAR and EAR groups 例(%)
2.2 術前MRE結果在無復發組與復發組之間的差異EAR與病變腸段術前MRE參數的單因素分析如圖1B所示。僅狹窄近端腸管最大處內徑有統計學意義(P= 0.014),其他影像學參數無統計學意義。復發組狹窄近端腸管最大處內徑明顯高于無復發組,復發組與狹窄近端腸管最大處內徑也有顯著相關(r= 0.456,P= 0.011)。
EAR與病變腸段周圍腸系膜MRE參數的單因素分析結果如圖1C所示。以下3個MRE參數的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MCFI(P= 0.012)、梳狀征(P= 0.008)、腹盆腔積液(P= 0.013)(表1)。復發組與MCFI(r= 0.469,P= 0.009)、梳狀征(r= 0.522,P= 0.003)、腹盆腔積液(r= 0.505,P= 0.004)也有顯著相關。
2.3 EAR預測模型的構建和性能評估LASSO回歸分析從38個臨床特征和MRE參數中篩選出3個非零系數的潛在風險預測因子(圖2):MCFI、梳狀征和腹盆腔積液。對這3個參數進一步行多因素二分類logistic回歸分析,篩選出2個可預測EAR的獨立危險因素:梳狀征(回歸系數β = 3.366;優勢比 = 28.963;95%CI:1.867 ~ 449.252,P= 0.016),MCFI(回歸系數β = 1.124;優勢比 = 3.078;95%CI:1.074 ~ 8.822;P= 0.036)。

圖2 基于LASSO回歸模型的變量選擇Fig.2 Feature selection using the LASSO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納入上述篩選出的獨立危險因素構建預測EAR風險的列線圖預測模型。模型的Harrell一致性指數和經偏差校正的一致性指數分別為0.882(95%CI:0.764 ~ 1)和0.860,表明模型區分是否發生EAR的能力較高。校準曲線顯示通過模型估算的EAR預測概率與實際概率之間有較好的一致性。Hosmer-Lemeshow擬合優度檢驗表明擬合良好(P= 0.640)。
該基于術前MRE的列線圖預測模型預測CD手術患者為EAR低風險還是高風險的閾值約為64分,將患者分為EAR低風險組和高風險組(圖3),靈敏度為66.67%,特異度為91.67%,陽性預測值為92.31%,陰性預測值為64.71%。

圖3 基于術前MRE的列線圖預測CD患者為早期吻合口復發高風險Fig.3 Identify of high-risk CD patient for EAR based on preoperative MRE nomogram
3 討 論
本研究開發并驗證了術前預測EAR的列線圖預測模型,從38個臨床特征、實驗室指標、組織學分析和MRE參數中,篩選出了2個能預測首次行腸切除術CD患者術后EAR的獨立危險因素:MCFI和梳狀征。基于這2個術前MRE參數的列線圖預測性能良好,Harrell一致性指數為0.882,模型總分≥ 64分的CD患者在首次腸切除術后的EAR風險高,建議術后早期藥物干預。
腸切除術后12個月內,超過50%的CD患者出現內鏡復發,只有約25%的患者在復發早期出現臨床癥狀[5]。術后早期的藥物干預有利于預防CD的復發和進展,但考慮到藥物副作用和經濟因素,并不建議所有患者在術后早期接受藥物預防。因此,在術前對術后EAR發生風險進行評估,可為CD患者提供個體化治療策略。
MRE已成為CD患者術前評估的常規成像方式[19],在評價深部小腸及腸周改變方面優于內鏡。本研究開發的列線圖模型包含了兩個常見的術前MRE參數,預測的EAR結果與實際觀測之間具有較強的一致性。為臨床醫生設計完整的術前個體化治療策略、術后早期醫療預防提供參考;以降低CD患者EAR發生率、減少不可逆腸道損傷和再次腸道手術的風險。根據本研究的結果,列線圖評分≥64的CD患者往往是EAR的高危人群。建議預測EAR高風險的患者接受早期藥物預防,如硫唑嘌呤或抗TNF-α藥物治療;而低風險組的患者可不接受藥物輔助,或僅接受抗生素或美沙拉嗪治療,根據術后6 ~ 12個月內鏡復查的結果調整治療策略[6]。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病變腸段的MRE參數,病變腸段周圍的腸系膜異常改變在術前預測EAR方面可能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在本研究中,病變腸段的術前MRE參數與是否發生EAR無相關性,而病變腸段周圍腸系膜的MRE參數(梳狀征、MCFI)卻被選為可預測EAR的獨立危險因素并納入模型中。梳狀征是CD的一種特征性影像表現,常提示存在活動性疾病,需要更積極地治療[27-28]。我們的結果顯示與其他研究[23,29]一致,術前MRE顯示病變腸管周圍存在梳狀征的患者,術后吻合口復發的風險較高。MCFI是一種新近報道的非侵入性表征CD爬行脂肪的半定量影像學指標,它描述了腸周腸系膜小血管包裹腸道的程度,間接提示了爬行脂肪包裹病變腸管的程度。爬行脂肪是CD的特有表現,并與疾病進展相關[17,30]。HOLT等[31]報道內臟脂肪過多是CD術后內鏡復發的獨立危險因素。同樣,本研究結果顯示隨著術前MRE中手術切除腸段的MCFI評分增高,患者在術后發生EAR的風險增加[31]。
相對于術前腸壁改變,腸系膜異常改變在預測EAR中起著更重要的作用。可能是因為本研究中的患者均行傳統的CD腸切除術,即在切除病變腸管時,與腸緣平齊分離并保留病變腸管周圍的腸系膜,這也是目前多數醫院所采用的手術方式,以減少出血等手術并發癥。因此,殘存的腸周腸系膜組織的慢性炎性病變仍可能對吻合口產生影響,從而導致吻合口復發。COFFEY等[17]的研究間接證實了這一假設:在切除CD病變腸管的同時切除病變周圍腸系膜可降低術后手術復發率。另一個影像學預測CD患者EAR的研究結果[32]也支持了我們的結論。在該研究中,腸系膜CT影像組學的預測價值稍高于腸道CT影像組學(風險比:2.19vs.2.17),提示腸系膜在EAR中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此外,雖然該研究采用影像組學聯合臨床影像等多維度信息構建模型預測EAR可指導CD術后個性化治療策略[32]。但影像組學分析需要專業的代碼或軟件操作,限制了其臨床推廣性。而本研究基于常規MRE影像即可評估EAR風險,具有更好的臨床實用性。
本研究尚有一定局限性。(1)本研究的納入和排除標準要求嚴格,而只有30例患者符合分析條件,且未進行外部驗證。預測模型的效能值得在后續研究中進行外部驗證。(2)本研究對CD患者腸切除術后早期用藥類型進行了分析,組間無明顯差異;但是沒有分析具體的方案和藥物治療過程,這可能會影響CD患者吻合口預后情況。
綜上所述,本研究基于術前MRE的列線圖預測模型可用于CD首次腸切除術后EAR高風險患者的篩選,為其術后早期個體化藥物輔助治療方案的制定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