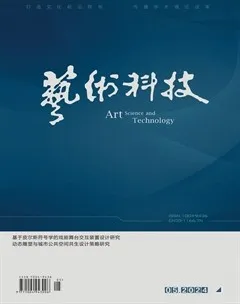基于皮爾斯符號學的戲劇舞臺交互裝置設計研究
蔡欣怡 李棟寧
摘要:目的:在立體主義、實驗戲劇等藝術思潮的影響下,戲劇舞臺設計往往過于重視數字技術和感官刺激,而忽略了戲劇的本質,沖擊著戲劇的戲劇性。在“炫技”或“炫目”的浪潮中,設計師應當如何以系統性方法構建戲劇舞臺交互裝置,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文章以皮爾斯符號學為視角,創新戲劇舞臺交互裝置美學理論,旨在為當代戲劇舞臺交互裝置的體系構建研究貢獻綿薄之力。方法:文章基于皮爾斯符號學視域,以交互裝置為研究對象,明晰戲劇文本、裝置場域范疇,在“戲劇文本—交互裝置—角色互動”坐標軸中構建其設計體系。戲劇舞臺交互裝置設計師基于戲劇符號文本解碼戲劇主題與情感;預設戲劇場域元語言和演員、觀眾情感;再基于設計師知覺意向,搭建質料載體、創作內置影像、外延互動形態,填充裝置之“形、身、韻”,并結合演員動作空間對符號的傳達,共同編織設計數字交互裝置符碼本體。結果:當代數字交互裝置對傳統戲劇舞臺而言是創新也是挑戰,技術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只有以戲劇的戲劇性為內核,借由符號構思、場域預設到本體創作,人、物、場共同審視,戲劇舞臺交互裝置最終才得以落地與“敞開”,構建其符號學設計體系。結論:數字交互裝置延展了戲劇舞臺空間,活化了傳統戲劇布景式舞臺,讓戲劇舞臺歷久彌新。
關鍵詞:皮爾斯符號學;戲劇舞臺;數字交互裝置;戲劇性
中圖分類號:J8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4)05-0-03
0 引言
從透視布景到約瑟夫·斯沃博達對光影的注重,迪克·黑根斯對“互動媒介”的宣揚,乃至數字交互裝置的介入,擁有百余年歷史的舞臺美術在當代戲劇舞臺創作中呈多元化、科技化、革新化等態勢。在立體主義、后戲劇思潮下,不少設計師在舞臺設計中拘泥于數字技術和感官刺激,忽略了戲劇的本質。戲劇舞臺交互裝置是戲劇場域中質料、情感、角色和數字的有機組合。1917年馬塞爾·杜尚的裝置《泉》,顯露出藝術可由物象之形抽象出符號。1940年維爾特魯斯基及布拉格學派稱“舞臺上的一切都是記號”,舞臺的假定性、戲曲的“一桌二椅”,無一不體現戲劇舞臺的符號性。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的“再現體、對象、解釋項”是符號顯現的過程,設計師只有先剖析預判符號對象、解釋項,方可更妥實地構建舞臺交互裝置符號。在符號學視域下,作為戲劇符號可感知的再現體,舞臺交互裝置是對傳統物性的創造,對表意的延伸,設計師應基于“戲劇文本—交互裝置—角色互動”的坐標軸構建舞臺交互裝置。
1 戲劇文本:舞臺交互裝置符號對象的解碼
戲劇文本即劇本,作為戲劇藝術的一種伴隨文本,是設計師構建舞臺交互裝置的基石、原點與核心[1]。戲劇文本作為舞臺交互裝置符號的指示對象,牽動著裝置敘事與情感,而裝置對戲劇文本的模仿和再現,能夠凸顯戲劇的戲劇性,這也是舞臺交互裝置區別于一般數字交互裝置的要素之一。劇本解碼,是舞臺交互裝置設計師對戲劇劇本不斷甄別、解讀和剖析的過程。設計師通過解碼以對白為主的戲劇劇本,研析其戲劇動作、戲劇沖突、戲劇情境等戲劇性符號文本,便可知曉戲中角色對話、情節敘事、戲劇動作、環境氛圍、思想情感、文化內涵等信息,筑牢舞臺交互裝置的構建基礎。無論是正劇、喜劇、音樂劇、實驗劇、兒童劇還是舞劇,多幕劇還是獨幕劇,設計師首先都要對戲劇文本進行解碼,揣度角色在舞臺空間中的行動路徑,預設其與數字交互裝置的互動。進而通曉戲劇語境,提煉其主題思想,以此構建數字交互裝置的情感原點。再依據戲劇語句文本、語義文本、語境文本,籌劃數字交互裝置中的戲劇情感。
2 戲劇場域:舞臺交互裝置元語言的詮釋
場域,指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型[2]。舞臺交互裝置場域,是數字交互裝置、戲劇角色互動、舞臺布景之間“在場”的關系網。裝置元語言的詮釋,即戲劇場域的表意,也是設計師預設戲劇演出呈現、裝置與場域融合的一種延伸與外化。皮爾斯理論認為,一個符號只有被解釋成符號才能成為符號[3],舞臺交互裝置符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因可詮釋的意義而得以飽滿呈現。“言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舞臺交互裝置元語言,即戲劇場域的預設,關聯著其整體構建。
當代舞臺交互裝置打破了以模仿和再現為主的傳統戲劇模式,為意向符號敞開了空間。在舞臺交互裝置元語言的象外之象中,設計師預設的表意顯露。數字交互裝置的戲劇價值,不在于還原出多絢麗的影像或現實復制品,而在于一種經過設計師編碼、演員傳遞符碼、觀眾解讀后的情感,升華出戲劇的情緒與意義。設計師將自己的知覺意向和情感預設,借舞臺交互裝置作品進行可視化呈現,促成演員和觀眾的直觀感受[4]。通過預設舞臺交互裝置場域、元語言,深入戲劇內部結構,參與戲劇敘事,延伸出其審美符號,具有審美價值。
3 舞臺交互裝置:戲劇符號再現體的設計
3.1 裝置親歷者的在場動作
鏡框式舞臺中,數字交互裝置從輔助性布景轉為極具能動性的戲劇元素,從傳統影像的獨立呈現到裝置與角色的協作。數字交互裝置與舞臺美術具有契合性,皆是四維時空的表現藝術,都注重人的“在場”、場域及互動。
數字交互裝置處于劇場性四維時空場域中,裝置動作隨時間而影響戲劇敘事和戲劇環境,戲劇動作的在場也體現著戲劇的戲劇性。角色演員是戲劇符號的親歷者和傳遞者,是裝置構建的一部分。若不考慮角色在場的戲劇動作,就無法想象角色具身的活動空間,更無法準確預設數字交互裝置環境。因此舞臺交互裝置的構建需要共同審視場域中的角色動作、交互裝置、空間環境,即人、物、場。
戲劇舞臺交互裝置動作以戲劇文本為模仿基礎,角色親歷敘事、在場動作和生成情感都深受戲劇文本的指導。設計師預設角色區域、支點、路線等行動路徑,依據主次、方位、范圍劃分裝置所占區域,設置前后、左右、側區,中心區、主副演區、過渡區等,建立角色在數字交互裝置空間中的行動區域,完成角色的在場互動。
數字交互裝置因角色在場動作而“活”起來,以全息、激光、虛擬現實、多感官交互、機械數控等多種數字交互裝置再現于角色面前,演員以觸、摸、移等在場動作介入裝置,裝置因介入而有響應,生成新的數字影像虛擬符號,二者呼應。演員結合自己的舞臺經驗、感受構想,形成自己的知覺意向,與戲中角色共情。實體舞臺上,演員真實“具身”于戲劇空間內;數字交互裝置世界中,形成與演員對應的虛擬“在場”身份,實體身份與虛擬身份實時相互反應,設計師預設的“空白”被不斷填補完善。數字交互裝置消弭了傳統藝術作品“看與被看”的二元對立界限,而舞臺交互裝置的互動彌合了傳統舞臺布景與角色之間“遠觀”的罅隙[5]。
3.2 裝置空間的審美還原
數字交互裝置可通過質料載體、內置影像、形態互動等方式營造出設計師預設的戲劇情感,但其本身并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戲劇空間,單獨的數字交互裝置在劇場中展出便會顯得“無戲”。相反,數字交互裝置與舞臺臺面、布景、燈光等舞美元素相嵌合,共同營造整個戲劇氛圍,才能達到“有戲”的效果。
舞臺交互裝置空間既不是簡單靜置的布景,又不是符號堆砌的容器,應該與其他舞美手段結合,共同呈現戲劇符號,還原戲劇舞臺審美意象。數字交互裝置設計師借助自己的知覺意向,編碼再現交互裝置符號,調控舞臺交互裝置空間內點、線、面、體的形狀分布,二維、立體的肌理質感,以及動態的舞臺燈光等視覺元素,將演員、裝置、場域在動作、時間、空間、情感中達成統一[6]。經組合、分解、再組合,編碼與解構,在形狀與色彩、光與影、材料與質感、活動與節奏等創造的符號性意向空間中,呈現沉浸式戲劇舞臺交互裝置。
3.3 裝置本體的創作建構
置身于當代藝術語境和戲劇舞臺場域,舞臺交互裝置因此具有當代數字性、多元綜合性、實時互動性等特征。如科幻或歷史類戲劇中,裝置視覺特效和虛實轉換的顯現,或音樂劇,或舞劇中,裝置與演員肢體的互動,以多重數字媒介的拼貼,構建科幻與現實交融的多元化舞臺空間,呈現出奇幻的舞臺效果。從最初的幻燈機、投影儀、LED電子顯示屏,到全息、激光、VR、AR、3D Mapping、無人機等技術的應用,舞臺交互裝置不斷迭代更新。
2017年懸疑探險劇《摸金玦》中,3D Mapping、投影等裝置與三維場景的影像內容共同呈現100余個盜墓場景,再現墓穴探險中地上與地下的驚險世界,真實角色與數字虛擬內容在舞臺上共同創造逼真生動的感知效果。
在戲劇舞臺場域,設計師深度解碼、提煉出戲劇敘事和情感觀念,融合自身創作經驗,當下敘事文本、戲劇情感,以及對舞臺場域、角色介入的期許預設。將這些知覺意向進行重組與編碼,進而抽象塑造出裝置的質料、圖像、聲音、光影、互動符號性意象,以此構建舞臺交互裝置的符號再現載體。2017年張藝謀執導的國家大劇院版《對話·寓言2047》中,現代舞與激光交互裝置、碗碗腔與全息投影交互裝置、提線木偶與機械臂、笙演奏與無人機……對傳統文化符號文本進行解構,結合設計師審美的知覺意向符號,最終蘊含、消解在各類舞臺交互裝置的符號性意象中,突出“科技與人,何往何至”之哲學思考。
舞臺交互裝置的構建離不開質料載體的搭建、內置影像的呈現以及外延形態的互動。裝置的質料載體是可以被感知或操作的實體材料,有傳統繪畫、雕塑材料、合成材料之類布景可塑材料,亦有如LCD、LED之類可顯質料,還有如投影幕布、全息膜之類可轉化呈現的材料等。譬如2022年順義大劇院版舞劇《南苑秋風》的設計師以全息影像將角色動作實時投射到全息幕布上,同時結合昏暗舞臺燈光以隱藏全息幕布本體,裸眼3D影像懸浮于空中,觀眾即使多角度觀看也能獲得虛實難分的視覺震撼。因此,設計師可依據可靠性、靈敏度、耐用性等因素來選擇適配度較高的質料,以錯置、懸空、分割、集合、疊加等設計手法重構,勾勒裝置符號之“形”。
隨后通過設計內置影像,填充裝置符號之“身”。裝置影像符號元素有三種類型。“質符性”影像,即與戲劇符號文本有直接相關性的符號,如代表冬季的飛雪畫面。“單符性”元素,是與戲劇符號文本有因果關系或時間先后關系的符號元素,如暗示戰爭發生的烽火影像。而“型符性”元素,是與戲劇符號文本之間沒有任何因果關系的符號元素,如非線性敘事影像、抽象的實驗動畫。設計師由知覺意向勾勒出線性或非線性的文本敘事,抽象或具象的畫面風格,圖形或視頻的動靜狀態,二維或三維的場景空間,實景、動畫或CG特效……設計師在裝置影像的數字空間中編碼,渲染情感與戲劇氛圍。
實時投影、數字虛擬人物、數字實時生成或動態捕捉等都可與演員產生互動行為,這種互動是裝置的一種外延形態,活化了戲劇舞臺數字交互裝置,是裝置符號之“韻”。而依據角色演員動作實時生成的數字交互裝置,借Kinect傳感器、紅外LED燈管發射器等設備,跟蹤、采集角色演員的骨骼和動作數據,實時傳輸至感應處理器系統,計算渲染可視畫面并實時或延時性投射至舞臺上。如皇家莎士比亞劇團版《暴風雨》,設計師在愛麗兒的內層服裝中固定傳感器,采用VFX和實時動畫來綁定、捕捉演員的表情和動作,采集傳感追蹤數據,編碼生成虛擬角色愛麗兒精靈,角色的運動軌跡可傳輸到虛擬空間內對應的虛擬身份上,現場演員表演和數字虛擬精靈互為動作,在舞臺交互裝置中交織綻放。
4 結語
舞臺交互裝置的融合突破了傳統戲劇中僅作單獨背景的舞臺美術桎梏,增強了戲劇舞臺的互動與默契,突破了戲劇時空、材料、觀念的限制,活化了傳統戲劇布景式舞臺,為當代戲劇舞臺注入了新鮮血液。基于戲劇的戲劇性,舞臺交互裝置在“戲劇文本—交互裝置—角色互動”的坐標軸中構建,設計師解碼戲劇符號文本,提煉裝置符號所指對象與戲劇主題與情感;借助觀眾和角色演員的審美感受,預設詮釋舞臺交互裝置場域,在戲劇情感世界與戲劇共情;以其質料、影像、互動形式再現戲劇符號,共同編織裝置符碼。一味追求炫目與炫技都不可取,若只顧追求技術新奇和視覺盛宴,會導致戲劇情感缺失,甚至讓舞臺交互裝置藝術失去獨立性。因此,舞臺交互裝置的構建觀念尤為重要,技術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只有在此觀念的指導下歷史悠久的戲劇藝術才能再創舞臺奇觀。
參考文獻:
[1] 潘健華,潘天.慎思“后戲劇”膜拜下的舞臺美術革新:兼評2019布拉格國際舞美展[J].戲劇,2019(6):46-53.
[2] 布爾迪厄,華康德.反思社會學導引[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22.
[3] 皮爾斯.皮爾斯:論符號[M].趙星植,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165.
[4] 李棟寧.觸發與激活:影像藝術敘事理論的機制建構[J].藝術百家,2020,36(4):156-162.
[5] 李棟寧.數字媒體藝術之美[M].南京: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23:142.
[6] 胡妙勝.閱讀空間:舞臺設計美學[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33-35.
作者簡介:蔡欣怡(1999—),女,湖北武漢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數字媒體藝術。
李棟寧(1971—),男,江蘇南京人,博士,教授,研究方
向:數字媒體藝術設計及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