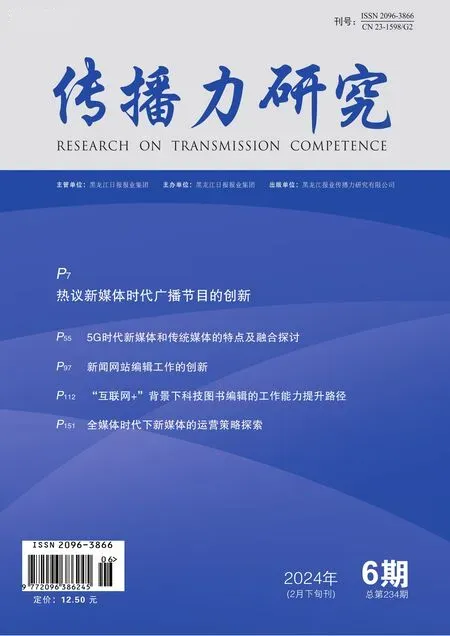電視紀錄片的故事化創作
◎宋麗娟 伍楚娟
(廣西廣播電視臺,廣西 南寧 530022)
隨著文化產業的高速發展與傳播媒介的不斷融合,受眾的審美觀念與審美理解逐漸發生了轉變,促使電視紀錄片的紀實風格與表達方式也發生了變化,結合時代發展與市場需求變化,電視紀錄片的風格、類型、流派呈現出多元化發展趨勢。而在電視紀錄片產業發展過程中,故事化創作在業內取得了不同凡響的成績,在社會中得到了更多受眾的青睞,逐漸成為電視紀錄片發展的主流。該形式的創作,兼顧傳統紀錄片的真實性,還兼具故事化創作的戲劇性效果,其感染力更強,讓受眾在觀看的過程中能時刻保持對其的吸引力。
一、新媒體時代背景下電視紀錄片故事化創作的發展趨勢
新媒體時代的到來,為電視紀錄片的創新發展提供了更加豐富的素材資源與創作靈感,也為其帶來了更加嚴峻的挑戰。隨著媒介的不斷融合,文化產業間的競爭越發激烈,電視紀錄片要想獲得更好的發展前景以及更多的受眾群體,就必須秉持與時俱進的原則,不斷革新創作理念,結合時代發展背景創新創作方式。在此背景下,故事化創作逐漸取代傳統電視紀錄片的敘事方式,并成為未來電視紀錄片創作的主流形式。故事化創作更加符合當今時代受眾審美觀念與消費需求,通過將虛擬與真實相融合,使受眾在觀看的過程中既能領略故事內容的戲劇性與趣味性,還能感受到事件的真實性,滿足他們的幻想[1]。
(一)故事化創作方式更易被受眾所接受
在新媒介環境下,受眾獲取信息資訊的途徑愈發多元化,并隨著節目內容的增多,對節目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此,電視紀錄片要想獲得更多的受眾,就必須注重敘事形式的創新與優化。文似看山不喜平,故事要避免平鋪直敘帶來的乏味感,就要在故事中將情節設置得一波三折,使故事峰回路轉,波瀾迭起,才能達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使受眾在觀看電視紀錄片的過程中時刻保持新鮮感。對此,紀錄片制作人員要了解受眾的觀看喜好與觀看需求和方式,合理運用構思能力、想象能力、語言組織能力,設置故事的敘述方式,讓其曲折有趣,高潮迭起,進而促進電視紀實行業的健康發展。
(二)故事創作理念更加多元化
在新媒介環境下,受眾獲得資訊的渠道與方法日益多樣化,而電視紀錄片的創意觀念也隨之發生很大的變化。這就要求創作人員要根據時代的發展需要,革新敘事觀念、創新敘述方式,既能滿足受眾對敘事內容的需要,又能給敘事節目帶來新的生機。在敘事結構、敘事語言和敘事視角上,要遵循真實性、典型性和紀實性等原則,使故事與實際生活相融合[2]。除此之外,創作者還可以以主題和內容需求為依據,選取適當的故事化創作語言和角度,讓受眾體會到故事化的內容所帶來的沖擊。同時,在新媒介條件下,電視紀錄片的創作也必須符合其自身的發展規律,符合其美學需求。在新媒介環境中,隨著人們獲得資訊的途徑日益多樣化,電視紀錄片的創作者必須選擇受眾喜歡的形式去進行紀錄片的創作。比如,可以針對當前的社會熱點問題展開敘事,運用新媒體技術,對當前的社會熱點問題進行深入闡釋。2023年初,廣西衛視推出全媒體紀實節目《我們的新征程》,圍繞“中國式現代化”的主題,用紀實手法和平實視角捕捉鮮活故事,以“第一人稱”講述的方式,生動書寫新時代、新征程、新生活,讓普通中國人與新時代發展同頻共振,激發觀眾共鳴共情共奮進,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此外,還可以對某些典型的人物、事件等做深度訪談,使其成為一個“故事”,運用一種以敘事為中心、具有敘事功能的敘事方式。《我們的新征程》的主角既有基層的二十大代表、先進人物,也有心懷國之大者、為實現中國夢踔厲奮發的普通人。節目采用紀實手法,以“第一人稱”講述,以平視視角捕捉鮮活故事,形成“我們”與“新征程”的同頻共振,彰顯出主流媒體的時代使命和價值引領力。
二、故事化創作在電視紀錄片中的作用
(一)有助于增強電視紀錄片的真實性
電視紀錄片之所以能經久不衰并在文化產業中長期占據重要地位,主要原因便是其高度的真實性與紀實性,而故事化創作不僅保留其獨特屬性,而且還利用全新的敘事手法使受眾在觀看的過程中獲得全新的體驗[3]。例如,在人物創作中,創作者結合歷史背景,將人物的生平事跡以講故事的形式敘述出來,并搭配真實形象的電視畫面與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使該人物形象在敘述的過程中越發真實、生動,仿佛該人物就在受眾的身邊。而在歷史文化的講解中,廣西文化精品欄目《廣西故事》將歷史文化故事化,不僅滿足了受眾的好奇心,而且也方便受眾更好地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廣西故事》遵循“讓文物說話”的原則,走進博物館,運用鏡頭語言,多角度呈現珍貴的歷史文物,追尋歷史背后的故事;面對專家觀點,遵循實事求是原則,還原故事與歷史的真實面貌;將手中的素材與歷史資料結合,深入淺出描繪出生動的歷史故事,并在環境、音效的渲染下引發受眾情感上的共鳴,從而學會辯證地看待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力求挖掘好廣西故事、為受眾講好廣西故事,并在繼承中弘揚我國優秀的歷史文化、傳統文化。
(二)有助于增強電視紀錄片的感染力
故事化本身存在一定的虛擬性,將故事化創作與電視紀錄片相融合,主要是對電視紀錄片內容的豐富與拓展。故事化創作主要抓住人們對新奇事物的好奇心理,以其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滿足受眾心中對美好事物的幻想。因此,故事化創作有利于提高電視紀錄片的藝術感染力。例如,在人物傳記類紀錄片的創作中,要想實現故事化創作,需要作者對該人物展開詳細調查,深入挖掘該人物所代表的精神價值。在《我們的新征程》系列紀錄片中,除了先進典型、行業先鋒,欄目也把鏡頭對準在平凡崗位上不懈進取的普通人。第五期節目《在希望的田野上》講述的是原本在浙江、上海金融圈打拼的“85 后”青年,出于對袁隆平先生“禾下乘涼夢”的追尋,放棄高薪回到小縣城做農民。他將經濟學知識運用于種糧事業,應用現代農業機械設備,從育秧到收割實行全程機械化,打造了一支專業的新型職業農民隊伍。主人公用變革性實踐,高度契合響應了黨和政府的號召,實現了“金融男”到“種田郎”的人生轉變。故事化創作并非將虛擬的事物強加到紀錄片中,而是將紀錄片內容以講故事的形式展現出來,從而使整個紀錄片更具藝術感染力,彰顯電視紀錄片作為藝術創作的價值。
三、電視紀錄片故事化創作需要注意的問題
電視紀錄片的“故事化敘事”就是把發生在真實世界中的具有新聞價值的事件再創造,以敘事的方式展現出來,從而與受眾形成感情上的共振。通過對其進行敘事,可以為其注入新的活力,但是要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還需要注意以下兩方面的問題。
其一,保證紀錄片的真實性。紀錄片的實質是為受眾展現事件中最為真實的一面,并以獨特的敘事手法呈現在受眾眼前。但實際情況是所謂的真實事件并非完全是真的,在實際創作過程中,“編創”的內容占據了主導地位,“真實性”則成為輔助,這也導致受眾在觀看電視紀錄片的過程中產生了錯誤的理解。
其二,紀錄片內容過度渲染。現階段,部分電視紀錄片創作者為增強紀錄片內容的真實性與還原性,存在利用特效技術過度渲染的情況。這就導致故事化創作內容過于刻意,受眾在觀看的過程中完全沉浸在特效技術所帶來的視聽體驗中,對紀錄片內容本身并未過多留意。這種舍本逐末的創作方式,雖然會給受眾帶來更加新奇的觀看體驗,但是這并不符合電視紀錄片創作的初衷。
四、電視紀錄片故事化創作策略
電視紀錄片故事化創作的初衷是將具有報道價值的真實事件以全新的形式展現出來,而非是作為一檔娛樂節目來滿足受眾的視聽享受。為避免舍本逐末情況的發生,創作者應更加注重故事化敘事方式的使用,依托真實事件重新設計故事情節,靈活設置敘述懸念,強化真實事件的主導地位。此外,創作者可借助新媒體技術的發展優勢與傳播特征,利用互聯網技術搜集更多與創作內容相關的資料信息,并在完成信息真實性的核驗后,將其與內容創作相融合,從而使電視紀錄片內容更加豐滿,故事內容更加真實。
(一)注重故事情節設計,增強觀眾的代入感
電視紀錄片故事化創作的關鍵在于故事情節的設計,依托真實事件設計的故事情節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調動受眾的情緒。在創作過程中,創作者需要對現階段受眾的審美特點與心理需求進行系統的調查與分析,總結故事化創作與電視紀錄片的共同特征,在不斷地探索中嘗試將二者深度融合,使受眾在觀看的過程中能將自身的情感帶入到故事情節當中[4]。同時,部分電視紀錄片還具有較強的地域性色彩,尤其是地理題材的紀錄片,不僅包括對不同地區地理環境與地質條件的介紹,而且還包括對當地民族特色的分析。這就需要創作者本身具有較深的文化底蘊,在保證故事完整性的同時彰顯地域特色。
(二)合理安排敘事結構,增強故事的吸引力
合理安排敘事結構是增強電視紀錄片吸引力與故事內容真實性的重要基礎。敘事結構是對整體紀錄片內容的把控,包括各片段與故事情節的聯系、時間線索的安排、空間架構的組合,以及邏輯順序的調整。此外,敘事結構能將事件中最具報道價值的內涵披露出來,使受眾在觀看的過程中進入更深層次的思考,從而完全被故事內容所吸引[5]。
以《長江之歌》為例,它的敘述框架很具有代表性。《長江之歌》是一部從多個視角,圍繞“我與長江”的長江故事的傳記。該紀錄片以長江自然生態為主線,以不同地區的風俗民情、自然風貌及風俗習慣為主要表現對象,展示了長江地區的民俗風情。創作者為進一步增強電視紀錄片的吸引力,選取四個不同的敘述角度,分別為“長江、自然、人、社會”。該紀錄片總共六集。
第一集主要講述“我”與“長江”之間的關系,水作為萬物生長的源頭,對人類文明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長江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其在推動中國文明發展過程中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創作者利用鏡頭語言敘述長江的故事,為受眾詳細講述長江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第二至第三集則為受眾展現“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第二集的開篇為受眾介紹依靠長江建立的生態系統,并展現近年來長江流域附近生態環境的變化情況。第三集是將長江與社會發展相關聯,展現出自古至今依托長江發展的文明與文化,其中作者花費了大量的篇幅對包含長江元素的古文物與傳統技藝進行介紹,通過一個又一個的小故事為受眾展現獨屬于中國人的長江情感。
第四至第五集主要為受眾展示“長江”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在第四集作者以獨特的敘事結構,先為受眾展示長江對沿江地區經濟發展的幫助,再借助自然災害為受眾展現長江母親河的另一面。通過對比的形式,為受眾分別展示母親河溫柔美麗與暴戾之氣,進而引發受眾的反思,主動參與到母親河的保護工作當中。第五集為受眾展現可持續發展理念下,人們開始注重對長江生態環境的保護,作者利用獨特的語言藝術為受眾詳細介紹我國為保護與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所做出的努力。
在第六集中,作者借助典型故事極為細致地為受眾講述我國是如何在漫長的發展進程中,依托長江開拓出全新的發展路徑,其中包含了中國特色、持續發展、生態環境與人類發展共存。
(三)靈活運用視聽語言,增強故事的感染力
在電視紀錄片的故事化創作中,故事情節設計與敘事結構的使用主要是增強紀錄片的吸引力,使受眾在觀看的過程中能更加注重事件本身。而視聽語言則是從感官上給予受眾全方位的刺激,從而將自身的情感更好地帶入到故事情節中。該類表現方式在紀實類電視節目中有著較為廣泛的應用,尤其是在社會事件的報道中,創作者將音樂與畫面巧妙地集合,引發受眾情感強烈的共鳴。
《廣西故事》的《追尋·弘揚偉大建黨精神》系列紀錄片,選取梧州、南寧、桂林、北海、河池、百色六個城市,總共6 期節目,每期節目由黨史專家作為黨史講解人走訪革命遺址、紀念館等,通過介紹革命文物、尋訪先烈遺屬、歷史事件見證者和守護者、探尋革命遺址等方式講述黨史故事,并探訪當代廣西各地深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習近平總書記對廣西工作系列重要指示,全方位、深層次地展示八桂人民對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傳承與發揚。
在第三集《桂林篇》中央紅軍搶渡湘江的過程中,作者所搭配的音樂,或急促、或沉重、或凄婉、或悲壯,使受眾的情感隨著音樂的起伏,感受正面戰場的慘烈,紅軍戰士英勇犧牲的大無畏精神隨著音樂的變化溢出屏幕,使紀錄片的主題“追尋偉大建黨精神”更加突出。
(四)設置敘事懸念,調動受眾的情感
在電視紀錄片故事創作中,具有一定的懸念的劇情總會引起受眾的關注,同時也會調動受眾的期望和焦慮等情緒。因此,創作者要想使得受眾能被故事情節所吸引,全身心投入到紀錄片的觀看中,就需要在故事情節設計中巧設懸念內容。然而,在敘述懸念的設定中,編導必須遵循真實性,不可違背真實事件,以一種故事化的形式,與紀錄片的真實性相互補充、相互協調。
(五)通過鏡頭語言敘事,強化蒙太奇效應
蒙太奇是電影語言,其定義為鏡頭的剪切與組接。紀錄片鏡頭承擔的任務主要有兩點,即在敘事段落用鏡頭與文字搭配,展示事件的來龍去脈;在論證階段用鏡頭承擔敘事、抒情功用。紀錄片受其自身特征與屬性的影響,整體節奏相對緩慢,且由于紀實性較強,受眾在觀看的過程中很難保持高漲的熱情與足夠的興趣。對此,在電視紀錄片中鏡頭敘事的作用尤為明顯,通過鏡頭語言將原本枯燥乏味的事情,轉變為更符合受眾觀看需要與情感體驗的故事內容,從而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和藝術效果。例如,在紀錄片中為了體現故事情節的緊張感,制作者往往用鏡頭的拉伸,通過多組鏡頭的相互配合,渲染緊張的氛圍,為受眾呈現更加生動、立體的故事,以此展現事件的重大或緊迫,引發受眾的情感共鳴。
五、結語
綜上所述,隨著媒體行業的不斷發展與新媒體技術的誕生,面對受眾日益增長的需求,電視紀錄片只有通過不斷地創新與變革,才能取得更大的發展。“講故事”要符合紀實的原則,不能做假的“講故事”,更不能因為追求“講故事”,而忽略了對“真”材料的選擇與篩選。因此,要使電視紀實節目更具感染力,更具藝術價值,在創作過程中要注重各種創作方式與藝術表現形式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