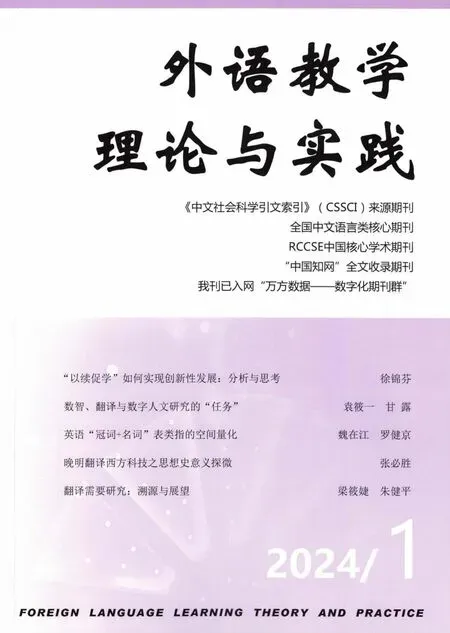中國文化術語外譯的規范性與術語性*
上海外國語大學語料庫研究院 韓子滿
提 要:“太極拳”這一術語目前存在多種不同的英語譯文,譯文不僅混亂,有些還存在明顯問題。英美圖書館藏書的書名和學術論文數據庫中論文的標題顯示,解釋性的譯名均未形成有效傳播,其他譯名的傳播效果很不平衡。原因在于“太極拳”的英語譯名未能實現規范化,多數譯名的術語性也不明顯。從太極拳及太極文化國際傳播的實際需求出發,結合英語術語的構詞規范,taijiquan應該作為“太極拳”規范的英語譯文。
1. 引言
術語外譯的傳播與接受近年來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在相關研究中,有兩個問題經常被提及。一是規范性,也就是標準化,即如何為漢語術語確定一個為受眾普遍接受的統一的外語譯名,避免出現多個不同的外語譯名,或是縮短多個外語譯名共存的時間。有學者在論述文學術語外譯的時候指出,“文學術語的翻譯要想做到規范化,最理想、最有效的是采取標準化(standardization) 的辦法” (仇蓓玲,2017: 25)。二是術語性,也就是外語譯名在外語中是否具有術語的特質,比如是否是由術語學者提出的。有學者發現,我國一些重要政治術語翻譯為外語后,“并沒有相應地轉變為對方語言中的概念”,也就是沒有變成對方語言中的術語(楊雪冬,2016: 15)。
不過,對于這兩個問題,迄今尚沒有專門的研究。學者們要么在討論其他問題時順便提及,要么只研究了其中一個問題,尤其是規范性問題,未能將二者聯系起來進行討論。現有的研究大多針對政治術語,少數結合文學術語展開分析,結合中醫、武術等海外傳播更為活躍的文化領域來考察的還比較少。鑒于這些領域在海外受眾較多,甚至已形成體系化的術語譯名,規范性和術語性的問題更加突出,我們擬以“太極拳”這一典型的武術術語為例,結合其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接受情況對術語外譯的規范性和術語性進行探討。
2. “太極拳”英譯
太極拳在我國的對外文化交流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已然成為普遍被國際認可的‘世界語’”(黎慧,2019)。可以預見,隨著2020年太極拳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目錄,太極拳及太極文化的國際影響將持續擴大。在此過程中,包括“太極拳”在內的太極文化術語的外譯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只有翻譯為外語,尤其是英語,世界各國的太極拳愛好者才能更好地了解并參與這一運動。畢竟,針對非漢語人士推廣太極拳,直接使用漢語的情況還不是主流,翻譯才是太極拳國際傳播的主要手段。不過,正如很多學者注意到的那樣,太極拳相關翻譯目前存在許多不足。有學者注意到,太極拳的相關英譯主要有兩方面的問題: 一是譯文不準確,對太極拳拳架和拳理的理解有誤;二是譯文錯誤導致理解錯誤,主要表現為“譯文不規范”(秦琴,2020)。也有學者認為,太極拳翻譯存在“一詞多譯”、“詞不達意”和“表達方式多種多樣”等三種問題(申夢悅、代梧佑,2021)。學者們所說的主要是術語翻譯問題。由于這些太極拳術語極具中國文化特色,這些問題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國文化術語外譯的普遍問題。
在論述太極拳翻譯問題的時候,學者們往往會分析“云手”等太極拳招式的譯法,都是一些只有專業人士才會接觸到的表達法。實際上,即便是“太極拳”這一大眾化的術語,目前的英譯也存在許多問題。有學者發現,這一術語目前有taijiquan、traditional Chinese Taiji、Traditional Chinese Boxing、Taiji boxing、Tai Chi Boxing、Tai Chi Fist、Tai Chi Quan、shadow boxing和hexagram boxing 等九種譯名(張明璽,2014: 90)。我們發現,這種一詞多譯的現象在詞典和教科書中同樣存在。首先,不同詞典或教科書給出的譯名不同。比如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詞典組編寫的詞典中給出的譯名是taijiquan,并給出了長達29個詞的解釋(1995: 973)。《武術-漢英對照》給出的則是Tai Chi Quan,并在括號里給出了另一個譯名Tai Chi Fist Fighting(蔣劍民、黃一棉,2014: 86)。吳冰主編(2004: 24)的口譯教程則把“太極拳”譯為shadow boxing;其次,多數漢英詞典在解釋“太極拳”時都給出了多個英語譯名,比如《現代漢語詞典》漢英雙語版對“太極拳”的解釋就是 “taijiquan; shadow boxing; school of popular traditional martial art marked for slow and graceful movements that are designed to attack or counterattack, keep fit, prevent and treat disease”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2002: 1853), taijiquan和“shadow boxing”都是譯名。《新世紀漢英大詞典》的解釋是“tai chi; taichi chuan; shadow boxing [ system of physical exercises consisting of slow balanced circular movement, chiefly for attaining bodily or mental control and also for self defence]” (杜瑞清,2016: 1619),“tai chi”、“taichi chuan”和“shadow boxing”也都是譯名;再次,一些武術或文化詞典也給出了多個譯名。如《英漢漢英武術常用詞匯》給出了“Taiji boxing”和“Taiji Quan”兩個譯名(解守德、李文英,1989: 185), 《英漢漢英武術詞典》則給出了Taijiquan、Shadow Boxing、Chinese Shadow Boxing、traditional Chinese Taijiquan等四個譯名(段平、鄭守志,2006: 10)。日本學者編著的《漢英中華文化圖解詞典》給出了shadow boxing和taijiquan兩個譯名(興水優等,2000: 270)。
這些譯名的翻譯方法可分為音譯、意譯和解釋三類。Taijiquan和taichi chuan是音譯,分別采用了漢語拼音寫法和威妥瑪式拼法,而Tai Chi Quan則組合了漢語拼音和威妥瑪式拼法。“太極拳”作為一個詞還是拆解為多個詞,不同音譯的處理方式也不同。Taijiquan是一個詞,taiji quan是兩個詞,Tai Chi Quan則成了三個詞。是否翻譯“拳”字,不同的詞典也不一致,tai chi和tai chi chuan明顯不同。在不翻譯“拳”的音譯中,又有是否添加送氣符的不同,tai chi和t’ai chi也不一樣。意譯主要體現在shadow boxing這一譯名上,用英語中的術語進行對譯,有一定的解釋成分,但和不計篇幅的解釋還是有所區別。解釋的篇幅過長,已經喪失了術語的特點。上面提到的兩種長句段就是典型的解釋,不過由于前面有譯名,這兩處解釋還不能算作譯名。但也有少數詞典不提供術語式的譯名,只給出解釋。比如在《漢英中國文化詞典》中,“太極拳”的釋義就只有“a system of physical exercises and an art of self-defence”這個句段(思馬得學校,2005: 361)。有些譯名不局限于一種譯法,而是混合使用多種譯法。Tai Chi Fist Fighting就是音譯和解釋的混合,Chinese Shadow Boxing混合了意譯和解釋。
這些譯名有問題,不僅僅在于不統一,還在于有些譯名本身就不準確,或者畫蛇添足,不像是術語。Shadow boxing這個譯名流傳很廣,尤其是在英語教材中曾一度廣泛使用,但這是拳擊術語。有專業健身網站給出的解釋是“一種與想象的對手搏斗的訓練方式” (Knight,2020),英文維基百科將其寫作一個詞shadowboxing,解釋是“向想象中的對手擊拳的格斗練習”,國內拳擊界已有通行的譯法,叫作“影子拳練習”,和太極拳完全不同。即便是在前面加上Chinese,形成Chinese shadow boxing這種表達,英語讀者估計也會將其理解為某種拳擊。shadow boxing及其派生表達法shadow boxer還廣泛用于文學表達,亞馬遜上可以找到多部以shadow boxing為題的小說。在其中一部小說中,shadow指的是主人公感受到的感情陰影,shadow boxing則表示為走出這種陰影而進行的掙扎(Pesesorski, 2009)。用boxing來翻譯“太極拳”中的“拳”本身就是個錯誤。太極拳是一種拳術,而 “拳術”的意思是“徒手的武術”(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2016: 1084),和西方的拳擊明顯不同。Tai chi fist fighting中的fist fighting也沒有表達出“拳”的意思,太極拳的招式并不都是用拳頭去擊打對手。traditional Chinese Taijiquan雖然不至于讓讀者產生誤解,但traditional和Chinese畫蛇添足。如果讀者對太極拳一無所知,traditional和Chinese對他們不會有實質性的幫助。上述這些譯法歸根結底都是解釋,都想降低目標讀者的理解難度,只是由于這些譯法存在先天不足,結果很有可能事與愿違。
3. 太極拳英譯國際傳播
混亂甚至有問題的譯名在國際傳播中也的確產生了一些問題。這在英美國家的相關圖書和國際學術論文中有明顯表現。我們僅從書名或標題就可以對“太極拳”不同英語譯名的國際傳播有一個比較準確的了解。如果國外的作家或學者以某個譯名作為自己著作或論文的標題,那就說明他們接受了這個譯名。他們采用最多的譯名,自然也就是國際傳播最成功的譯名。即便這些圖書或論文是國內作家及學者用英語完成的,既然被英美等國的圖書館收藏,或者在國際期刊上發表,又或者是被學位論文數據庫收錄,其采用的譯名自然也受到了這些圖書館、期刊及數據庫的認可。
最能反映圖書館藏書情況的,當然是各國的版權圖書館。我們以美國國會圖書館和英國大英圖書館作為研究對象,考察其藏書的書名中“太極拳”英譯名的使用情況。先來看美國國會圖書館。通過檢索該館書目可知,上述解釋性的太極拳英語譯名,在書名中都沒有出現。《漢英中國文化詞典》中那個句段式譯名沒有出現在書名中不難理解,因為字數太多無法作為書名。“Tai Chi fist Fighting”、“traditional Chinese Taijiquan”、“Traditional Chinese Boxing”、“Tai Chi Boxing”和“hexagram boxing”等譯法雖然并不長,但也未在任何書名中出現。僅有“taiji boxing”和“Chinese Shadow Boxing”這兩種譯法在書名中各出現了一次,但都只在副標題中出現,正標題中都有taijiquan的字樣。不加任何修飾成分的Shadow boxing只在五個書名中出現,且都不表示“太極拳”。音譯taichi出現得也比較少,只在三個書名中出現。書名中出現比較多的主要是taiji、taijiquan、tai chi、tai chi chuan、t’ai chi和t’ai chi chuan六種譯名,主要區別在于是否用拼音,“拳”字是否翻譯。不用拼音,采用威妥瑪式拼寫的,又有是否添加送氣符之分。以十年為單位,這六種譯名出現次數見表1。

表1.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書書名中包含“太極拳”英語譯名情況
六種譯名共出現316次,taiji和taijiquan在六本書中同時出現,實際對應的是310本書。其中taiji出現27次,taijiquan出現34次,tai chi出現129次,tai chi chuan出現52次,t’ai chi出現40次,t’ai chi chuan出現37次。威妥瑪式寫法占了絕大多數,其中不加送氣符的又占了絕大多數。加送氣符的t’ai chi chuan出現得最早,在1947年就出現了。20世紀60年代又有三本書的書名包含了t’ai chi或t’ai chi chuan;不加送氣符的tai chi于1963年開始出現在書名中,新世紀之后呈爆發之勢;taiji和taijiquan都是遲至20世紀80年代之后才出現,大多出現在中國大陸、香港及新加坡出版的英文原創著作或譯作中。
解釋性譯名在大英圖書館的藏書書名中也沒有出現。“shadow boxing”在六本書的書名中出現,同樣無一表示“太極拳”。Taichi也只在三個書名中出現。taiji、taijiquan、tai chi、tai chi chuan、t’ai chi和t’ai chi chuan出現的情況見表2。

表2. 英國大英圖書館藏書書名中包含“太極拳”英語譯名情況
六種譯名總共出現了235次,未發現taiji和taijiquan同時出現的情況。taiji出現15次,taijiquan出現18次,tai chi出現106次,tai chi chuan出現28次,t’ai chi出現40次,t’ai chi chuan出現28次。威妥瑪式寫法同樣占了絕大多數,且不加送氣符的居多。加送氣符的t’ai chi chuan同樣出現得最早,在1947年已出現,和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是同一本書。此后包含送氣符的t’ai chi和t’ai chi chuan出現的次數一直略多于不含送氣符的tai chi和tai chi chuan。直到2000年之后,后者才明顯爆發,大幅領先,但t’ai chi chuan的出現頻率仍然略高于tai chi chuan,但2020年之后再未出現在書名中。taiji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出現在中國學者出版的英文著作中,新世紀前十年有個小高潮,之后又陷入低潮;taijiquan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書名中出現,主要是在大陸及香港出版的英文著作或中譯英著作中,也在新世紀初出現高潮,之后又陷入低潮。書名包含taiji和taijiquan的著作譯著都占了一定比例,其中包含taiji的15部書中有3部是譯著,包含taijiquan的18部書中有7部是譯著。
國際學術期刊論文可以從Web of Science數據庫入手來考察。解釋性的譯名在論文標題中都未出現。Shadow boxing在10篇論文的標題中出現,但只在1篇中國學者的論文標題中表示“太極拳”的意思。(Zheng et al, 2015)taichi未見于任何論文標題中。以五年為單位,taiji、taijiquan、tai chi、tai chi chuan、t’ai chi和t’ai chi chuan出現的情況見表3。

表3. Web of Science數據庫中論文標題包含“太極拳”英語譯名情況
與圖書館藏書的書名相比,六個譯名在期刊論文標題中出現的情況明顯不同。首先是出現的次數嚴重不平衡,tai chi占了絕大多數。六個譯名總共在論文標題中出現了962次,tai chi就占了765次,t’ai chi chuan只出現了一次,有送氣符的t’ai chi及t’ai chi chuan在每個時間段都要少于沒有送氣符的tai chi和tai chi chuan。其次是出現時間比較晚,taiji、taijiquan、tai chi、tai chi chuan、t’ai chi和t’ai chi chuan在論文標題中首次出現的年份分別為2006年、2004年、2001年、2002年、2005年和2007年,比圖書標題晚了五十多年。再次是除個別譯名外,其他譯名出現的次數呈穩步增多趨勢,近幾年增長態勢明顯,2022年甚至已經發表了兩篇標題中含有tai chi的論文。此外,標題中包含這些譯名的論文多數都發表于醫學健康類期刊,內容主要與醫學,尤其是運動醫學或傷病防治有關。
學位論文我們通過ProQuest學位論文數據庫來考察。解釋性的譯名均未在論文標題中出現。只有4篇論文的標題中包含shadow boxing,但都不是太極拳的意思。taiji、taijiquan、tai chi、tai chi chuan、t’ai chi和t’ai chi chuan出現的次數略多一些,具體次數見表4。

表4. ProQuest學位論文數據庫中論文標題包含“太極拳”英語譯名情況
題目中包含這幾個譯名的學位論文數量不多,總共才70篇。最早出現的同樣是T’ai chi chuan,1972年就出現了,但之后出現得一直很少。標題中含有tai chi的有44篇,超過了六成,出現的時間也比較晚。除t’ai chi chuan之外的其他五種譯名分別于1991年、1988年、1986年、2003年和1986年才開始出現。但此類論文2010年之后數量不及新世紀前十年。和期刊論文一樣,此類學位論文多數也討論醫學、健康與護理問題。
可見,包括shadow boxing在內的解釋性譯名,還沒有真正走出國門。國際受眾普遍接受的譯名是威妥瑪拼法的tai chi和tai chi chuan以及包含送氣符的t’ai chi和t’ai chi chuan,不含送氣符的越來越成為主流。拼音形式的taiji及taijiquan為國際受眾采用的時間較短,但正被越來越多的圖書和學術論文采用。期刊論文和學術論文對譯名的接受與圖書采用的情況有所不同。從期刊論文和學術論文來看,現有譯名的接受主要集中在醫學、保健和護理等領域。從圖書標題來看,對譯名的接受則集中在體育領域,尤其是武術領域。值得注意的是,雖然tai chi和tai chi chuan在圖書書名和論文標題中出現的次數都最多,但并沒有一統天下,拼音形式的taiji和taijiquan一直與之并存。
4. 太極拳英語譯名的規范性與術語性
無論是國內詞典和教科書上的英譯,還是海外圖書和國際論文中的實際應用,“太極拳”的英語譯名都沒有到達規范性的要求,有些譯名也不具備術語性特征。這對于太極拳文化的國際傳播,乃至于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都是非常不利的。
其實國內各界對于術語的規范化歷來高度重視。“中國的譯名研究比任何歐美國家都復雜;學者在統一譯名上花的精力遠遠超過西方同行。”(朱志瑜、黃立波,2013: 2)在自然科學領域,國家還于1985年成立了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負責各類科技術語的統一,特別是外語科技術語漢語譯名的統一。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沒有專門的政府機構,但學者們對術語的規范化一直高度重視,外語術語漢語譯名的統一更是學界聚焦的重點。本世紀初有學者在編選《西方文論關鍵詞》時就聲稱,“西方文論內容繁雜,譯介口徑不一……這就使得我國學者在傳播與應用過程中,屢屢碰到術語與概念不統一、不明確甚至不可解的障礙。”(趙一凡2006: ii)術語不統一成了“障礙”,解決的辦法則是“……盡量統一關鍵詞譯名” (同上: iii)。西方學界對術語也有類似的要求,大多都會提到術語應該標準化,有人甚至認為,一般的語言研究和術語學的區別之一就是術語學不排斥人為的規定性,將制定標準術語作為目標(Cabré,1998: 34)。
不過,對于漢語術語外譯的規范性,無論是政府機構還是學者,重視程度似乎都弱很多。對于這一問題,直到最近幾年才有少數學者開始關注,迄今也沒有專門負責此事的政府機構,只有少數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如“中華思想文化傳播工程”和“中國關鍵詞”等,不斷推出外語譯名,客觀上起到了規范譯名的作用。這兩項工程的相關研究者也注意到譯名不規范的危害。“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傳播工程”的負責學者就注意到,“過去,……不同的譯者在對術語內涵的理解上有差異,所以同一個術語往往有二三種甚至更多譯法,這極大地影響了外國受眾對中華思想文化術語的準確理解,也影響了術語國際傳播的質量。”(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傳播工程秘書處/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21: 24)這樣的研究項目數量目前還太少,整理的術語也不多。之所以如此,可能與學界及政府部門對術語規范化的認識有關。術語規范性與標準化,歷來是語言規劃的重要內容,具有一定的約束力甚至是強制性。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推出的外語術語譯名,國內新聞界和出版界就必須采用,具有強制性。經學界討論而形成的外語術語譯名,也具有強大的影響力。至于漢語術語的外譯,我國政府和學界推動的規范性和標準化約束力和強制性肯定都要大打折扣,畢竟對于目標語的語言規劃我國政府和學界都沒有發言權。
不僅如此,詞典和教科書在翻譯文化術語時往往還不注意譯名的術語性,重心放在了對術語含義的解釋上,特別重視譯名的準確性,對于譯名是否具有術語的特質卻不在意。就連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在翻譯中國文化術語時也是如此。“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傳播工程”推出的術語英譯許多都是解釋性的,完全不具備英語術語的特點。這在動詞性術語和詞組性術語中尤為突出,如“安貧樂道”被譯成了“Be content with a simple but virtuous life”。即便是名詞性術語,也大多只是解釋了含義,如把“八卦”譯成了“eight trigrams”,“二柄”譯成了“two handles”。對于源自其他語言的音譯術語,雖然給出了原來語言對應的音譯,但往往也給出一個普通詞匯的解釋,讓讀者以為普通詞匯也是該術語的譯名,同樣失去了術語的特征。比如“般若”的譯名是Prajna/wisdom(《中華思想文化術語》編委會,2021: 12-13),雖然給出了Prajna這個對應的梵語形式,卻又加了斜杠,給出了wisdom這一普通詞匯作為譯名。這樣的譯名雖然意思準確,可能也方便了讀者的理解,卻很難作為術語在英語中廣泛傳播。“Tai Chi fist Fighting”、“traditional Chinese Taijiquan”、“Traditional Chinese Boxing”等在英美圖書館藏書的書名和國際論文標題中從未出現,就是證明。此外,從術語傳播的效果來看,哪怕是借用現有英語術語的解釋性翻譯,也不是理想的譯名,shadow boxing在書名和論文標題中的使用情況說明了這一點。
當然,規范性本身也是術語應有的特質。馮志偉(2011: 35)列出的術語定名十一條原則中,第三條就是“單義性”:“……同一個概念只用一個術語來表達,不能有歧義。”有西方學者列出了術語構成的12種要求,其中有四種是: 術語不該有同義詞、術語不該有詞形變體形式、術語不該有同音或同形異義詞、術語內容應該精確且意思與其他術語沒有重疊。”(Sager, 1990: 89)雖然沒有用規范或標準之類的字眼,但包含了這一層意思。術語的單義性還要求“至少在一個學科內,一個術語只能表述一個概念”。shadow boxing在英語中已經有固定的含義,用來表述“太極拳”這一概念顯然違反了這一原則。不過,規范性畢竟是人為的,不完全是術語的內在屬性。本文所說的術語性主要指詞匯之所以成為術語的其他三個相對內在的屬性,即專業性、簡明性和能產性。這三個屬性也包含在馮志偉列出的術語定名原則之內。專業性指術語用來“表達或限定專業概念”,含義和“日常生活的常識”有所不同(馮志偉,2011: 32-33)。以這個屬性來衡量,wisdom顯然算不上術語,因為在對“般若”詞條的解釋中,wisdom并沒有別的特殊含義,只是對該詞條漢語解釋中的“智慧”一詞的英譯。簡明性指“術語定名要易懂、易記、易讀、簡潔,使用方便,避免生僻用字” (同上: 37),或者是“在不犧牲精確性的前提下,術語應簡潔,不包含不必要的信息”(Sager, 1990: 89),也就是國際標準化組織所提出的“語言經濟原則”(ISO, 2009: 40)。“Tai Chi fist Fighting”等解釋性譯名顯然不具有這種屬性。能產性指的是術語確定以后,可根據“構詞法或詞組構成的方法”,產生新的譯法(馮志偉,2011: 38),也就是西方學者和國際標準化組織所說的派生原則(derivability)(Sager, 1990: 89; ISO, 2009: 40)。解釋性的譯文往往不夠簡潔,無法派生其他術語。
因此,要解決“太極拳”英譯面臨的問題,不僅要實現學者們呼吁的規范性,同時還要確保譯名的單義性、專業性、簡明性和能產性,以確保譯名在英語中也是術語,具備應有的國際傳播力。這樣一來,包括shadow boxing在內的解釋性譯文都可以排除。只有taiji、taijiquan、tai chi、tai chi chuan、t’ai chi和 t’ai chi chuan符合要求。規范化譯名理應從中產生,因為術語還需要遵守約定俗成性的原則,即對于“對應面較廣,使用已久,已為大家接受的術語,即使科學性不強,也應保留,不要輕易改動。”(馮志偉,2011: 34)嚴格按照這一點來要求,“太極拳”的規范性譯名無疑應該是tai chi,因為這種譯名傳播最廣,在圖書和論文中均出現次數最多。不過,“約定俗成”也不是絕對的。國際標準化組織在其術語命名規則中提出了一個前提條件,即如果要改變已經流傳開來的術語,“要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且確保新的術語可作為完全的替代術語被接受” (ISO, 2009: 56)。基于這一點,taiji和taijiquan也可以作為規范化的譯名。令人信服的理由是中國文化術語海外傳播越來越多地以拼音書寫的形式進行,且正為越來越多的英語國家受眾所接受。國家外文局的一項調研考察了中國術語拼音外譯在英語國家傳播的情況,發現整體情況較好(中國外文局,2018)。依據術語系統性的原則,“太極拳”的英語譯名應該與整個中國文化的英譯系統保持一致。至于能否作為替代術語被接受,外文局的調研還發現,“太極”在英語國家民眾對中國話語認知度TOP100總榜單中位列第十七,且被劃分到“武術功夫”類詞匯中。(同上: 33)上文統計的圖書書名和論文標題中,taiji和taijiquan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與此發現一致。至于t’ai chi和t’ai chi chuan,由于送氣符在當代英語書寫中已基本消失,這樣的寫法已不符合英語的構詞規則,因而也不符合術語的“約定俗成性”,不宜作為“太極拳”的規范性譯名。
也就是說,“太極拳”的規范性英語譯名應該是taiji或taijiquan。二者的區別在于是否翻譯“拳”字。從上文考察的情況來看,無論是圖書作者還是論文作者,在使用taiji時,都包含了“太極拳”的意思,使用“tai chi”或“t’ai chi”時,也是如此。在實際的國際傳播中,“拳”的作用并不大。其實,在“太極拳”這個術語中,“拳”是中心概念詞,表示“太極”的類屬,整個術語采用的是王寅所說的“屬加種差”構詞法(王寅,2010)。將這種“屬加種差”詞翻譯為英語時,沒有必要把概念詞翻譯出來。但如果不譯“拳”字,采用taiji這種譯名的話,又容易與表示哲學思想的“太極”混淆。《中國思想文化術語(哲學卷)》就收錄了“太極”一詞,給出的都是哲學上的解釋,給出的英語譯文就是taiji(《中華思想文化術語》編委會, 2021: 240)。為了避免混淆,還是以taijiquan作為規范性的譯名比較好。我國在“太極拳”申遺時用的就是taijiquan這個譯名,看來有關方面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同時,隨著這一譯名進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目錄,其國際傳播力也將大幅增強,必將為更多的國際受眾所接受。
5. 結語
《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報告2018》發現,“中餐、中醫藥、武術仍是海外受訪者認為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元素” (辛聞,2019)。太極拳既是武術,又廣泛用于養生,海外傳播也多見于醫學健康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說,“太極拳”這一術語橫跨了中醫藥和武術兩個領域,對于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具有重要意義,我們沒有理由不為其確定一個合理的譯名。拼音形式的taijiquan最符合術語的各項特征,術語性最強,理應作為規范化的標準英語譯名,相關部門以這個譯名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非常有遠見的。
確定taijiquan這樣一個標準的英語譯名,并非僅僅是對英美受眾接受習慣的迎合,而是對術語構詞規范性的尊重,也是對術語譯名術語性的回歸。從翻譯研究和術語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尊重與回歸并沒有多少新意。尤其是考慮到國內學界和政府部門對術語外譯漢的討論與管理,這樣的尊重與回歸似乎更沒有創意了。但在社會各界都在大力推動中國話語國際傳播的今天,這種尊重與回歸卻有著明顯的現實意義。解釋性的譯名大行其道,包括上述“中華思想文化傳播工程”和“中國關鍵詞”工程對解釋性譯名的偏愛,實質是對傳播效果的過度擔憂,反映了對話語外譯傳播效果的控制意圖。這種意圖當然是必要的,但傳播要產生效果,首先必須要傳播出去。要傳播出去,規范性和術語性就是必備特質。從本文的研究來看,規范性和術語性并未影響術語外譯傳播的效果,沒有產生不良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過度追求解釋性,漠視規范性與術語性,反而是對術語外譯與傳播規律的背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