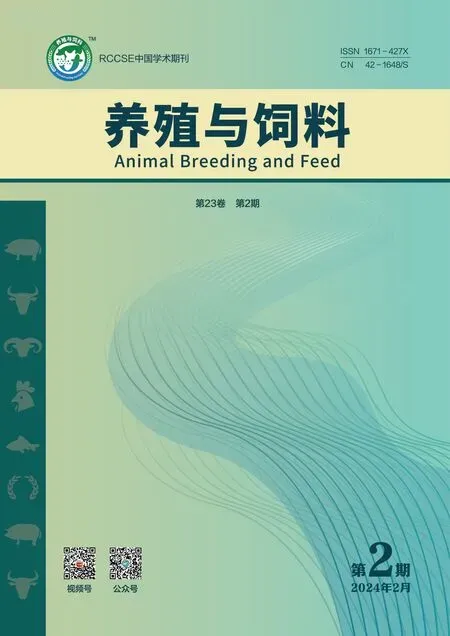淺談我國畜牧業綠色發展的策略
李月英,李同
1.成都農業科技職業學院,四川成都 611130;
2.中國農業科學院都市農業研究所,四川成都 610200
近年來,隨著畜牧業的快速發展,不同規模的養殖場不斷涌現,由此引發的環境污染和食品安全問題已成為行業關注的重點,其中環境問題涉及污水排放、臭氣治理等,食品安全問題涉及人們關注的肉、奶、蛋等畜禽產品的質量保障和瘦肉精、抗生素濫用等關鍵性問題。隨著人們環保意識的增強,人們對環境污染和食品安全質量的要求也在逐步提高,如何科學有效地提升產品的質量,依然是行業的焦點。然而大規模集約化養殖場又是我國今后發展畜牧業的方向,因此養殖場的環境污染控制及食品安全的把控關系到畜牧業能否可持續發展。在當前農村產業結構不斷調整,畜牧業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掌握生態平衡原理至關重要,畜牧業綠色發展將關系到產業未來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對社會經濟發展及未來畜牧業產生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強畜牧業生態保護,發展高質量安全型畜牧經濟,不僅提高畜產品的品質及附加值,同時能夠實現生態保護、畜牧業生產、農牧民增收的和諧發展。
1 加強源頭管控,突出精準減排
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提出:要深入推進環境污染防治,持續深入打好藍天、碧水、凈土保衛戰,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氣,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體,加強土壤污染源頭防控,提升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推進城鄉人居環境整治。隨著畜牧業集約化的發展,污染物的量開始呈集中式增長變化,糞污減排必然成為畜牧業健康發展的一個關鍵舉措。糞污減排需要從源頭飼料抓起,過程中經歷了源頭節水、糞污清除及深度處理等環節,是一個細長的減排鏈條。
1.1 提高飼料利用效率,降低源頭污染排放
飼料生產利用效率低,不僅會增加養殖動物的生產代謝負擔,而且會導致飼料中的大部分營養成分無法得到有效降解排出體外,給周邊環境及生產環節帶來較大的環境影響,進而成為畜牧業發展的一項重大問題。
根據《畜禽養殖業污染防治技術規范》(HJ/T 81―2001)中要求,畜禽養殖生產過程中,飼喂的飼料應采用科學合理的配方,來提高營養物質吸收率,減少未降解養分排放量和糞便的生產量。
目前行業內通過一些先進手段,例如品種改良、環境治理、營養配方配施等技術來逐步降低單位動物的飼料用量,同時根據各地區氣候差異、養殖動物不同生產階段的養分需求等來針對性提供不同階段的營養元素,進而有效提高飼料利用率,大大減少了污染物的排放和舍內惡臭氣體的產生[1]。
1.2 加強設施設備智能化,持續提升工藝科學化水平
隨著養殖業規模化、集約化程度不斷提升,產生糞污的集中度也隨之驟升。因此,在養殖過程中,舍內設施設備智能化及工藝設計科學化的改造及提升是至關重要的,例如舍內飲水設施可以由水嘴改造成水碗的形式,舍內糞溝及欄位清洗設施由傳統的清洗方式逐步迭代為高壓清洗模式,可以降低50%以上的沖洗水排放;同時在舍內可根據生產環節的節奏,彈性減少沖欄頻率,尤其是高密度生豬養殖,清糞方式逐漸由傳統的水沖糞、水泡糞等升級為干清糞或者機械清糞的方式,可以降低30%以上的排污量。
舍外做好雨污分離、干濕分離等[2],使得糞污收集量明顯減少,同時在畜禽舍和糞污處理池建設過程中要做好防滲工作,防止地下水或者雨水倒灌;尤其是南方地下水系及雨水頻繁的區域,地下水、雨水等復雜混合物會導致污染物容量大增,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凈化處理及存儲難度,糞污資源化利用效率低下。
2 強化糞污督導,實施科學處理
目前規模化畜禽場建設已經相對比較標準化,但針對環保處理的建設及運營需要因地制宜去進行布局規劃。土地承載量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2018 年農業農村部信息中心曾發布了《畜禽糞污土地承載力測算指南》,土地配套相對比較充足的區域,可以進行糞污資源化利用的深度推廣,例如東北三省、內蒙、甘肅等省份,土地面積開闊,適宜資源化利用的推廣,這些區域可以配套采用沼氣工程+沼液還田的模式[3]。厭氧技術可以選擇CSTR 模式或者黑膜沼氣,CSTR 發酵周期維持在14 d,黑膜沼氣發酵周期維持在40 d,使得病原微生物可以進行有效的殺滅來實現無害化處理的過程[4]。
沼液還田技術可以通過多種形式,如通過深耕施肥機械可精準定量還田,施肥作業均勻,節省人工勞動投入,但前期投入成本及運營成本相對較高;如通過噴灑的模式,根據區域種植的差異,在作物種植之前15~20 d 進行噴灑施肥,后續對土地進行翻耕處理。
針對土地配套不充足的區域,環保處理方式需要進行調整,首先源頭上必須進行徹底減排,清糞模式需要采用干清糞,可有效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時降低液體污染物的負荷;污水處理工藝建議采用深度處理模式,例如厭氧+兩級A/O 的處理方式,將污水處理到農田灌溉標準,再進行農田灌溉使用,這樣可以有效降低糞污消納所需要的土地配套量,緩解還田壓力。厭氧處理技術可以采用UASB 厭氧反應器,發酵周期維持在4~5 d,可有效降解污水中的COD,好氧深度處理選擇A/O 法,停留時間維持在3~4 d,利用硝化反硝化脫氮作用,可有效降解污水中的氨氮,從而達到農田灌溉的標準[5]。
固體糞便采用好氧堆肥發酵技術,目前行業更多采用槽式發酵模式,但槽式發酵占地面積較大,需要大量的基建投資,運營過程中發酵周期較長,需要大量的輔料作為碳源,整體過程自動化程度較低。目前行業引用了立式發酵技術,通過配套立式發酵罐,進行局部好氧堆肥發酵,發酵周期維持在7~10 d,發酵溫度可以實現60~70 ℃,能夠有效實現無害化處理;同時立式發酵占地面積較小,單臺罐體占地面積25 m2,日處理可實現6~8 m3固體糞便,整個過程可以完全實現自動化。
3 加強飼料獸藥企業監管,健全獸藥安全生產體系
首先針對大型飼料企業,全面開展飼料原料營養價值評定,建立行業內的飼料原料大數據庫,規范飼料行業飼料添加劑正確使用問題,從源頭上加強監管。建立并健全獸藥標準體系,加強國家科研機構及高校同企業之間的聯系,共建科學合理的獸藥研發體系及推廣體系,加強國家及地方對獸藥及藥殘的檢測及檢驗機質,組織開展檢測檢驗能力體系建設。進而,開展飼料產品非法添加專項整治行動,實施獸藥質量監督抽檢和市場整治,嚴厲打擊飼料環節非法添加藥物和違禁物質、銷售假劣獸藥等違法行為[6]。
4 強化病死畜禽無害化處理體系建設,建立健全無害化處理長效機制
針對大型規模化養殖企業,要在規劃建設生產基地期間,配套獨有的死畜禽無害化處理設施,實行病死禽就地無害化處理,同時可將污染范圍降到最低,防止病原微生物在不同場區及不同區域的交叉感染[7];對于中小企業及養殖合同戶,需要同當地集約化的死畜禽處理中心進行統一處理,提高集中處理效率,同時要把污染范圍降到最低。
加強地方政府屬地管理責任和生產經營者主體責任,在不同區域推動制定合理化的補助標準,優化健全無害化處理體系及標準;在不同區域不同生物安全情況下,制定專業的無害化處理生物安全技術規范,推進病死畜禽無害化處理信息化及渠道監管,防止出現監管疏漏,及時完善好病死禽保險聯動機制[8]。
5 強化企業及地方政府對接,完善疫病監測與流行病學調查預警機制
對于養殖企業及合同養殖戶要及時追蹤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下疫病暴發情況,及時獲取并分析流行病暴發原因,一旦發現疫病,杜絕疫情蔓延是至關重要的工作。因此需要聯合企業、各級高校及地方政府專家積極開展常規流調工作,制定專門流行病學調查工作方案;專門成立工作小組,到養殖場戶進行實地調研并采集樣品,重點對豬群、肉雞群、蛋雞群、牛羊群開展相關疫病的流調工作,形成流調報告為相關疫病監測流調計劃做決策參考;定期進行大數據的分析研討,摸清主要畜禽物種動物疫病流行狀況及規律[9]。
6 加快推進動物疫病區域化管理,增強疫病防控體系建設
實施動物疫病區域化管理,能夠在突發疫情狀況下,快速有效控制和撲滅重大動物疫情,減少因疫情擴散帶來的巨大損失。我國跨越了寒溫帶、中溫帶、暖溫帶、亞熱帶、熱帶、高原氣候區等不同溫度帶,不僅從北到南生態環境差異較大,且各地經濟水平、動物衛生和疫病狀況、動物疫病防控水平以及畜牧業養殖情況等差異較大,無法做到統一疫病管理防控模式,特別需要進行區域化管理和防控。
按照《動物防疫法》規定,要求對動物疫病實行區域化管理,這是我國動物疫病預防、控制和撲滅的基本措施,也是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基本做法。自2018年發生非洲豬瘟以來,國家及地方政府不斷推進非洲豬瘟等動物疫病無疫區建設,各大企業及養殖戶均在積極響應。在建設期間鼓勵不斷修訂和完善動物疫病防控技術標準體系,推進規模養殖場疫病防控的可持續性[10]。
7 加強屠宰行業監管力度,構建產品質量安全監管長效機制
對生豬屠宰場設立嚴格的準入原則,堅決關閉或者撤銷不符合法定條件的生豬屠宰企業。應當對屠宰企業的準入進行嚴格的把控,避免具有違規企圖的個人或者企業進入,從屠宰源頭上進行掌控。
地方政府及企業應及時聯合完善修訂屠宰肉品品質檢驗的相關規程,加強屠宰過程標準的管控。鼓勵并引導大型屠宰企業通過入股、合作、收購等方式兼并、重組小型屠宰場點,從根本上解決生豬散養收購和肉品供應問題。引導大型屠宰企業建立科學合理的屠宰質量標準體系,引入先進的屠宰管理理念及先進的質量控制技術,通過升級改造實現屠宰流程自動化、標準化和智能化操作,同時做好副產品綜合利用和無害化處理管控,防止環境污染。在行動管控上,建議采取開展聯合執法行動,嚴厲打擊非法屠宰病死豬、私屠濫宰、非法使用瘦肉精等違法行為,一旦發現從嚴查處企業及相關個人。
8 結 語
綜上所述,畜牧業發展的可持續性是畜牧業綠色發展的關鍵所在,畜牧養殖業已經成為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產業。推動生態良好型畜牧業的發展,構建完整的生態畜牧業科技支撐體系,旨在解決我國在現代畜牧業生產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環保、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關系民生的重大問題。為此,我們只有不斷提升飼料與屠宰行業的生產加工水平,強化病死畜禽與糞污無害化處理,加強對飼料獸藥企業的監管,完善疫病監測機制和增強疫病防控體系建設等,才能實現我國畜牧業高質量、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