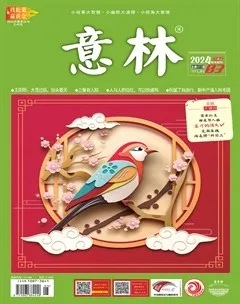客廳的消失
夏明浩

當代人還需要客廳這個東西嗎?
翻一翻豆瓣和知乎,你會發(fā)現(xiàn)就在前一陣子,有許多人都在討論同一個有趣然而卻小之又小的問題:為什么現(xiàn)在很多年輕人都反感家里來客人了?
有人說是因為過年時七大姑八大姨來串門,給自己留下了心理陰影;有人說,“高度社恐癥患者”沒有朋友,家里來客的話一定是刺客;有人說,客隨主便,作為主人我的原則只有一個,就是別進門。
但是一定要說的話,當代青年更關(guān)心的是另一件事:客人來了,有地方招待嗎?
你一定有過這樣的經(jīng)歷:搬到這所新房子以后,來過幾次(臨時)朋友,進門以后只能說:“我只有一把椅子,你坐,我躺床上吧。”聽起來像是一場反客為主的心理治療。
所以今天,我們就跟大家聊一聊待客空間的歷史。
客廳不是一天建成的
起初,客廳的名字叫作“parlor”,中文譯為待客廳。如果聽到這個詞你腦海中沒有浮出畫面的話,可以參考一下《唐頓莊園》。在唐頓莊園里,紳士和太太們端著酒杯在會客廳,或來回踱步,或安坐沙發(fā),談論著家長里短或者國際形勢。
事實上,這就是會客廳作為一個“家庭空間產(chǎn)品”最初的應用場景:城市文明的發(fā)展,導致了有閑有錢的士紳階級形成,他們需要開辟這樣一塊空間,承擔新的娛樂功能。所謂娛樂,主要就是一件事:說話。
轉(zhuǎn)眼到了20世紀初。一戰(zhàn)以后,西班牙大流感橫行,流感時期人們不敢去別人家做客,待客廳當然就成為空房間。《唐頓莊園》里也有類似的情節(jié):格蘭瑟姆伯爵夫人染上了惡疾,無法待客。不過,劇中的夫人痊愈了,真實的狀況卻慘烈許多。堆積的遺體來不及一一下葬,只能堆在包括待客廳在內(nèi)的、通常沒有人居住的閑置空間里。當時的“parlor”也因此有了一個新名字:the death room(死亡之室)。
然而當萬物復蘇的時候,會客室里又有了歡聲笑語,再叫“the death room”就有些不合時宜了。于是,人們又為這塊地盤起了一個新的名字“the living room(起居室)”,這個改稱就沿用到了現(xiàn)在。
莊園制度會沒落,城堡終有一天要變成景點。奢侈的“會客廳”,在生活方式的演變中,逐漸變成了每個公寓里必不可少的“客廳”。城市空間要容納更多的人,逐漸變得更集約緊縮,客廳要承擔的功能也隨之增加。不僅是待客,日常的生活情景也會發(fā)生于此,它便成了名副其實的“起居室”。
也許正是因為生活空間和待客空間的混淆,才讓現(xiàn)代人意識到了“隱私”的重要性。在現(xiàn)代化進程飛快的中國社會,對隱私的不同體驗,就像是人們思想上被拉傷的一根韌帶。父母輩還保留著城市化之前鄰里共融的傳統(tǒng),順理成章地邀請親戚朋友來家聚聚;而子女輩卻在這種陌生的際遇間,感知到了日常的生活空間,在偶爾成為待客空間時的不適感。
講話難,陪人講話更難
一件有點像悖論的事情是:我們說不想再讓別人進入自己的隱私空間,可是在電子時代,我們的隱私被泄露得還不夠全面嗎?
打字比發(fā)語音更加省時省力,圖片比音頻更易點擊查看。在網(wǎng)絡世界里,視覺是最重要的“第一性”,聽覺是第二性。這種基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視覺暴政,是當代生活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對語言來說,言談又是第一性,文字才是第二性,因為文字并不是信息的全部,它丟失了言談中所具有的語氣和溫度。這種矛盾導致了當下網(wǎng)絡世界的誤解橫生,即便在網(wǎng)絡技術(shù)的加持下,即時通信再怎么流行,也很難單純用文字讓兩個終端產(chǎn)生鮮活的交互。
類似“談話版會客廳”的Clubhouse風靡一時,就是在對這種視覺第一性的挑戰(zhàn)。在以言談為主的平臺上,我們會發(fā)現(xiàn),真正有價值的討論的確更可能發(fā)生——不過,使用語音聊天室終究是小眾的。對習慣了打字聊天的我們來說,言談終究還是可有可無的。
言談場景的消失,可能才是客廳不再待客的本質(zhì)。因為言談也是一門技藝,不常常用就會生疏。一旦生疏,做客和請客都會變得索然無味。網(wǎng)絡上的人們聚集在一個個量身定制的興趣話題下,逐步形成信息繭房。很少有人會愿意走出舒適區(qū),挑戰(zhàn)自己和他人的觀念與知識,因為一言不合就不必再言。這種習慣被我們帶到了現(xiàn)實生活中,自然就終止了一系列交流的由頭。
我們真正需要的,可能跟臥床已久的病人一樣,是一場復健,重新開始說話的復健。
客廳可有可無了,待客之道會消失嗎
對當代年輕人來說,客廳似乎已經(jīng)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空間,在一二線城市租下小小一居室的空巢青年們,屋子只要有一張桌子一張床,就能完成吃飯睡覺看劇乃至邊刷手機邊處理工作等人類基本生存活動,有朋友來了直接出去找個地方就行,有沒有所謂的待客空間,又有什么要緊?
所以,不進行物理接觸,在網(wǎng)絡上交朋友,變成了一個更好的選項。待客與起居之間的張力消失了,這片空間將確然地成為私人領(lǐng)域。尤其是,在許多科技巨頭聲稱的愿景里,《頭號玩家》里那種切膚的交互,將會很快成為可能。到了那一天,待客還有什么必要呢?
可是,卡在上一個物理時代和下一個虛擬時代中間的我們,如何應對這個失語時代?“好客”曾經(jīng)是一種美好的品質(zhì),它在都市行色匆匆的景觀里格格不入。對來客的反感,既是人們主觀的感受,又根植于我們所困在的系統(tǒng)里。鄉(xiāng)野、村落、農(nóng)家、串門,這些有溫度(但同時也意味著麻煩)的詞語,被逐漸擠出日常,只能存在于生活之外的遠方,或者李子柒的視頻里。
說多了,都是時代的眼淚。對你我而言,不管再怎么感慨萬千,即便知道日后間或有人到訪,恐怕也不會費力去添置第二把椅子。畢竟,上門的朋友再怎么合你心意,終究沒有必要擠在本就不太寬敞的空間促膝而談——畢竟你也知道,在對方的家里同樣有一張形單影只的單人床和一把煢煢孑立的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