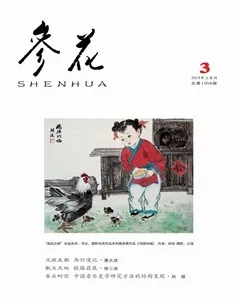淺析5G時代沉浸式藝術的發展路徑
于祉祺 牟磊
沉浸式藝術的核心為“沉浸”,指藝術家在特定空間內,采用聲、光、電等元素,為受眾營造一個有別于現實的場景,從而使受眾在獲得感官體驗的同時與作品產生互動,進而引發共鳴。隨著5G 時代的到來,沉浸式藝術作為藝術與科技結合的新型產物,漸漸融入大眾的生活。沉浸式藝術結合了多種技術手段,作為多感官并具有互動性的藝術呈現形式,可以將受眾的體驗延伸,從而吸引更多人走入沉浸式展廳親身體驗。隨著科技的發展,沉浸式藝術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一、沉浸式藝術的起源與發展
“沉浸”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心理學家米哈里·希斯贊特米哈伊提出的,指當人們全身心地投入當前的情境活動,忽視時間的流逝和環境的因素,從而達到一種忘我的沉浸狀態。沉浸的理念可運用于多個領域,其在藝術領域中的發展尤為矚目。隨著沉浸式藝術的興起和發展,追溯沉浸式藝術最早的作品形態與表達方式,同時利用新型科技手段不斷創作出具有鮮明時代特點、色彩豐富且能吸引受眾注意的藝術作品具有重要意義。
早期的沉浸式藝術展,是利用看似很簡單的裝置,打造出一個無限的、并不真實存在的空間。藝術家將它當作一個向世界發問的工具,使受眾沉浸其中尋找答案。
最早的沉浸式藝術萌發在18 世紀初期,當時的藝術家已經開始思考如何將受眾帶入作品的情景之中,利用實驗電影帶給受眾沉浸感。湯姆·岡寧在《吸引力電影:早期電影及其觀眾與先鋒派》中強調:吸引力電影應對觀眾產生視覺沖擊,將戲劇性的視覺效果凌駕于敘事之上,用電影手段強調畫面新奇性,使觀眾受到沖擊,直接吸引觀眾的注意力,使之沉迷其中。而后,受到這種新的表現手法的影響,同時期的電影導演也借鑒了類似的電影剪輯手法,來增強畫面的運動感。包豪斯學派藝術家在設計建筑本身結構的同時,還考慮了利用色、光、影來增強建筑物的氛圍,這也為沉浸式藝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創造了18 世紀的輝煌成就后,西方藝術的發展似乎陷入了短暫的停滯,這使藝術家產生了新的思考:想要做出革命性的改變,就必須有新的風格誕生。1917 年,杜尚在獨立藝術家協會展覽上展出了一個小便器實物,稱之為《泉》,這為藝術開創了更多的可能性,影響了后來的概念藝術、裝置藝術等形式的發展,并為沉浸式藝術做了鋪墊。
中國最早的沉浸式展覽是2010 年的《感覺即真實》,由中國建筑師馬巖松與丹麥藝術家奧拉維爾·埃利亞松合作舉辦。該展覽創造了一個虛幻的光譜空間,使受眾仿佛置身于迷幻世界,分不清現實和虛擬的界限。
Ramus 藝術團隊是澳大利亞的一家多學科設計工作室。2019 年,其在悉尼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個永久性沉浸式藝術作品——TheStar 沉浸式體驗空間。它將光、水及交互式藝術畫廊融為一體,呈現出一個精美的沉浸式藝術空間。該項目的創作總監、藝術導演布魯斯·拉姆斯表示:“我希望連接不同的元素,使整個空間環境在視覺上形成一個同步的整體,從而創造出與建筑空間相交融的數字藝術作品。其最終的目的是讓人的體驗變得更加完整和豐富。”
以裝置藝術為基礎的沉浸式藝術展在隨后的幾年中有了極大的發展,未來,隨著人們精神層面需求的不斷增長,沉浸式藝術展也將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二、沉浸式體驗的特征
(一)互動性
在傳統的展覽中,藝術作品以靜態的形式呈現,無法與受眾進行互動交流,可以很明確地感受到兩者之間的距離,不論是心理上還是空間上,都有一些疏離感。在日新月異的藝術環境中,傳統的藝術欣賞方式已經滿足不了受眾的需求,取而代之的是更新鮮、更有趣的體驗藝術方式。在科技的帶動下,沉浸式藝術融合了生物學、物理學、光學等多種學科的知識,動態地呈現藝術作品,將人、空間與藝術作品巧妙地融合,重視受眾的心理感受與生理體驗,加強了人與藝術作品之間的互動和溝通。
(二)故事性
每一次的沉浸式體驗,都是對一個實體化故事的欣賞,受眾可以真切感受藝術家的設計理念或文學作品中的故事情節。位于天津西青區社會山文旅港內的民國物語博物館,融合技術、藝術和情感,將游人代入沉浸式的互動體驗中,使其自然而然感受到“傳統與現代”“西洋與東方”“復古與潮流”的多元藝術碰撞,“故事性”十足的新場景受到游人追捧。
(三)角色化
受眾在參與沉浸式藝術展覽的過程中,可以通過沉浸式體驗找到自己的角色,從而提升個人自我認同感。沉浸式藝術在給予受眾更廣泛想象空間的同時,將受眾融為藝術作品的一部分。高士明在《我們是改變的力量》這篇文章中提出:“藝術的作用不只是生產出供觀看者欣賞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要讓受眾成為作者,讓每個人都成為藝術家。成為藝術家并不是獲得一種身份,而是意味著進入‘藝術時刻。在‘藝術時刻中,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是有所創造的人。”[1]
三、5G 時代科技在沉浸式藝術中的深度應用
5G 時代藝術作品利用全息投影技術、虛擬現實技術等,將受眾拉入沉浸式藝術作品的內部世界,真正做到全方位地為受眾傳遞信息。
(一)全息投影技術的應用
在我們的認知中科學是嚴謹的,富有連貫性與邏輯性,而藝術是充滿想象的。沉浸式藝術非常巧妙地將科學和藝術融合在一起。隨著5G 時代的到來,沉浸式藝術也在逐漸走向成熟,通過科技成果的加持,真正地形成了新業態,它包含了眾多的前沿科技成果,例如全息投影技術、增強現實技術等。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著名畫卷之一。為了讓文物“活起來”并吸引更多的人了解中國文化,故宮博物院舉辦了《清明上河圖3.0》沉浸互動藝術展,挖掘文物藏品的內涵,連接歷史與現實,打造出真人與虛擬交織、人在畫中的沉浸式體驗,使歷經歲月變遷的國寶再次熠熠生輝。這次展覽采用360°全息投影技術、虛擬現實技術、增強現實技術及真實造景,使《清明上河圖》數字化呈現。在繪畫中打造真假交織、人畫合一的身臨其境的體驗,是博物館展覽的一次顛覆性創新。受眾不僅可以通過高清動態的長卷世界研究舟船樓宇的精妙結構,感受北宋汴京的先進與發達,在孫羊店沉浸劇場中看窗外流動的街市風物,還能在4D 動感的虹橋球幕影院“坐”上宋代的大船,親歷汴河的繁忙與兩岸的綺麗。展覽消除了歷史長河古今相隔的距離感,使受眾完全沉浸在宋代的風土人情之中,帶給其感官、行為與心理上的沉浸式體驗。
(二)虛擬現實技術的應用
虛擬現實是沉浸式藝術中最具代表性的技術之一,主要應用于沉浸式虛擬現實系統。沉浸式虛擬現實系統可使用戶完全融入并感知虛擬環境,從而獲得存在感。一般有兩種途徑實現虛擬現實系統的功能,即洞穴自動虛擬環境和頭戴式顯示器,同時配備運動傳感器以協助自然交互的進行。2018 年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期間,被譽為“行為藝術之母”的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所創作的《RISING》將體驗者帶至洶涌上升的海平面之前,旨在點出現代世界不容忽視的全球變暖危機。體驗者戴上沉浸感強的Vive 頭盔,便可走入藝術家創造的虛擬私人空間之中,親眼看見漸漸升起的海平面從藝術家的腰際直升到脖子,親耳聽見被困在玻璃水艙中的藝術家的聲聲呼喚。
四、5G 時代沉浸式藝術的發展路徑
盡管沉浸式藝術憑借其強調多重感官體驗的特點贏得了人們的熱捧與關注,但隨之而來對其精神內涵提出質疑的人也不在少數。策展人和藝術家不能一味追求感官刺激,而應該在策展和藝術作品創作時,注重科技對藝術作品故事性的加持,將受眾帶入作品中,引導其感悟藝術作品背后的內涵。
(一)增強趣味性,拉近受眾與藝術的距離
5G 時代,隨著人工智能等技術的飛速發展,展覽作品與展廳環境的結合更加緊密,這就模糊了現實與虛擬的邊界感,增強了藝術作品展覽的趣味性,拉近了受眾與作品、展廳空間的距離。
2023 年4 月,《遇見凡·高 沉浸光影藝術展》中國首展,在遇見博物館·上海靜安館開幕。該展覽以凡·高的《星月夜》《向日葵》等149 幅經典作品為創作背景,運用數字多媒體技術進行渲染,打造出流光溢彩的動畫視覺效果,使凡·高作品的筆觸、色彩更加鮮明,讓藝術展覽更具趣味性。該展覽重點展示了凡·高的人生軌跡和創作歷程,用光影的視覺線貫穿凡·高的一生,為展覽加以故事性與敘事性,并結合聲音、色彩的精湛呈現,打造了一個占地600 平方米的沉浸式光影藝術空間,將受眾帶入奇幻的畫境之中。在這個畫境中,受眾可以感受到凡·高內心對于藝術的無限熱情和追求。同時,該展覽還展示了凡·高的浪漫情懷,通過細膩的色彩和溫暖的音樂,讓受眾感受到凡·高對自然和生命的贊美和熱愛。受眾可以沉浸在凡·高的藝術世界中感受其作品的詩意、獨特的藝術語言和表達方式所帶來的想象力。整個展覽空間仿佛成為凡·高內心世界的延伸,受眾可以在其中自由探索,感受藝術的魅力。
5G 時代,科技的融入讓受眾身臨其境地感受藝術作品,增強了藝術展覽的趣味性和受眾的感官體驗。受眾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欣賞藝術作品,感受到藝術作品中的更多細節。在科技手段的加持下,凡·高的藝術創作與受眾之間產生了更強烈的共鳴。
(二)增強互動性,注重受眾的主觀體驗
為了豐富個人的精神世界,越來越多的人接受、認可甚至向往沉浸式藝術帶來的完美體驗。這種“沉浸”不僅表現為客觀環境的沉浸,也反映在人們的主觀感受。因此,沉浸式藝術既要注重營造客觀環境,又要關注受眾的主觀體驗。受眾不再是游覽式地觀看藝術作品,而是融入展陳空間去感受藝術作品,打破其與藝術作品之間的距離感。展廳中的藝術世界因以多媒體的形式呈現而更加生動有趣,反饋性與交互性更強,使受眾與作品之間的信息傳遞由單向變成雙向。
《遇見敦煌光影藝術展》在北京、上海、成都等相繼落地巡展。敦煌莫高窟宛如絲綢之路上的璀璨明珠,不同的民族與文化在這里交會、碰撞,形成了敦煌特有的美學。如今,敦煌藝術文化跨越一千多年的歷史,以數字藝術的形式與我們見面。《遇見敦煌光影藝術展》運用了燈光、投影、音效等多種表現形式360°沉浸式地將受眾引入敦煌壁畫中,通過運用3D 光雕技術和數十臺超清投影設備,將敦煌壁畫作品中的經典元素作為千年文化的“領路人”,為受眾創造出全新的視聽交互體驗,彰顯了古老文明的魅力。在“九色鹿王”與“敦煌舞樂”互動展區,受眾可以成為情節中的角色,更好地詮釋了“受眾亦是表演者”這一沉浸式藝術的觀點。在該藝術展中,受眾能夠欣賞到石窟建筑、彩塑造像和絕美壁畫等,全方位地體驗敦煌文化藝術數字化發展的最新成果,感受敦煌的文化藝術之美。
五、結語
隨著社會不斷發展,科學技術不斷進步,藝術作品的展示與欣賞方式不斷迎來創新。沉浸式藝術作為當今世界流行的藝術傳播方式之一,成為人們欣賞藝術的重要方式。5G時代,多維度、多元化的沉浸式藝術已經逐漸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文化中,使受眾也成為沉浸式藝術作品的一部分。雖然沉浸式藝術展覽在廣泛多元的藝術環境與數字科技元素的共同作用下,呈現出豐富多彩的視覺效果,但不可否認,當下沉浸式藝術展覽良莠不齊,存在著科技含量不高、藝術氛圍不濃、沉浸體驗不佳等各種問題。很多沉浸式藝術展覽一味追求科技手段、強調感官體驗,顛倒了藝術與科技的主次關系,最終失去了藝術的內核,使受眾在感官體驗的影響下,主觀能動性受到限制,審美受到影響。因此,沉浸式藝術除了依靠虛擬場景和技術手段,更要打造有文化內涵的藝術展覽,對于策展人和藝術家而言,不僅要調動藝術與科技的手段,更要平衡二者之間的關系。
(作者簡介:于祉祺,女,碩士研究生在讀,魯迅美術學院中英數字媒體< 數字媒體> 藝術學院,研究方向:思維的物化形態與觀念轉換;牟磊,碩士研究生,魯迅美術學院中英數字媒體< 數字媒體> 藝術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畫筆墨造型)
(責任編輯 劉月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