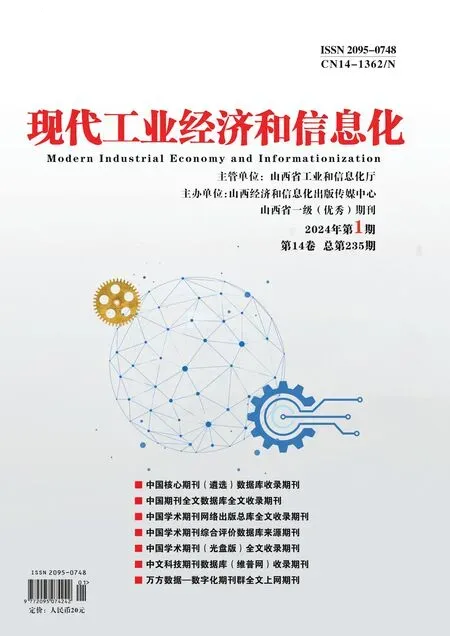碳達峰背景下安徽省工業碳排放與經濟脫鉤研究★
李睿奇
(安徽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0 引言
20 世紀以來,以CO2為主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迅速增加,溫室效應對人類生存環境構成嚴峻威脅。我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高度重視全球氣候變暖問題。 “十四五” 規劃中,我國提出要努力在2030 年前碳達峰、2060 年前碳中和的 “雙碳” 目標。安徽省位于長三角區域,連接國內多個重要經濟板塊,在發展中形成以消耗傳統化石能源為主的產業結構及能源消費結構,碳排放強度較高。工業部門生產消耗能源產生的CO2是碳排放的重要來源[1]。如何在保證工業經濟能夠持續增長的同時,順利完成降碳減排的目標,成為政府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目前,大量學者在分析行業能源消耗與國民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中,脫鉤理論運用較為普遍。徐玥等[2]基于Tapio 脫鉤模型分析了徐州市農業碳排放總量、強度和結構與農業經濟發展間的脫鉤關系,研究表明,徐州市農業碳排放與經濟發展呈現出 “弱脫鉤—強負脫鉤—擴張負脫鉤—強脫鉤” 的變化歷程,且 “十三五” 以來主要表現為強脫鉤。鞏小曼等[3]運用Tapio 脫鉤模型對新疆紡織工業藍水足跡、灰水足跡、水足跡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結果表明,藍水足跡、灰水足跡與經濟增長之間總體上均呈現弱脫鉤,水足跡則呈現成水量型弱脫鉤,三種水足跡與經濟增長之間均未達到穩定理想的脫鉤狀態。He T等通過構建Tapio 脫鉤模型和LMDI 模型,研究黑龍江省畜牧業經濟與碳排放的脫鉤狀態,研究結果表明,2000—2020 年,黑龍江省畜牧業碳排放量總體呈現小幅上升態勢,而畜牧業經濟增長與碳排放量之間的聯系主要體現為弱脫鉤。Guan Qifan 通過脫鉤理論和LMDI 模型,分析2005—2019 年京津翼地區與能源活動相關的碳排放量影響因素及各影響因素的貢獻度,結果表明,北京、天津相繼實現強脫鉤,河北保持弱脫鉤,創新因素在脫鉤中作用重大,不可忽視。Cui Shengnan 等選取中國28 個工業行業的隱含碳排放增量數據,使用Tapio 脫鉤模型研究其與經濟增長的脫鉤狀態,結果發現,2005—2020 年實現強脫鉤的產業部門數量顯著增加,但重點產業部門以擴張性負脫鉤為主。能源效率對強脫鉤有促進作用,需求規模對脫鉤的抑制作用更為顯著。戴勝利等[4]使用Tapio 脫鉤模型結合LMDI 模型,探索中部六省工業能源碳排放與工業經濟的發展關系,結果表明,中部六省碳排放量增速減緩,工業經濟增長趨于平穩,脫鉤關系呈現出由弱脫鉤向強脫鉤轉變的趨勢。張翼等[5]使用 “脫鉤” 原理構建煤炭工業碳排放與行業發展、行業發展與經濟發展等脫鉤指數,研究中國煤炭工業碳排放與工業經濟發展的脫鉤關系,研究表明,二者間脫鉤關系由增長負脫鉤向絕對脫鉤轉變,理想脫鉤狀態與行業碳排放控制力度和政策實施的連續性密切相關。
現有研究多聚焦于國家層面或特定區域的研究,對省際范圍工業行業整體進行研究相對較少。本研究在針對安徽省工業構建碳排放測算體系的基礎之上,對2007—2021 年安徽省工業能源消耗及碳排放總量進行詳盡測算,并構建Tapio 脫鉤模型對安徽省工業碳排放和經濟發展間的動態關系進行明確。同時,探究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成因,并為安徽省及其周圍省份工業科學綠色高質量發展以及實現經濟健康可持續增長提供理論與數據參考。
1 研究方法及數據來源
1.1 碳排放量的核算方法
本文參考IPCC 并使用《省級溫室氣體清單編制指南》中的相關參數,主要選取原煤、焦炭、焦爐煤氣、原油、柴油、汽油、燃料油和天然氣等8 種能源對安徽省工業碳排放量WC排放進行計算。
式中:i為消耗能源的種類;Ei為消費的能源量;CVi為能源的平均低位發熱值;CCFi為能源含碳量;COFi為能源燃燒時碳氧化率[6];44/12 為碳氣化系數。參照《省級溫室氣體清單編制指南》,計算得出相關能源的排放因子,如表1 所示。

表1 相關能源碳排放因子
1.2 脫鉤分析方法
脫鉤理論早期應用于物理學研究領域,用于分析兩個聯系密切的變量逐漸脫離相互影響的過程,現廣泛用于分析資源消耗或環境壓力與經濟變化的關系。通過使用彈性系數,Tapio 脫鉤模型能夠動態展示2個觀察對象變化的離散關系,即本文中工業碳排放量的變化與經濟發展間的關系。若工業碳排放增速為負或小于經濟發展增速,則存在一定程度的脫鉤。不同的脫鉤彈性可分為負脫鉤、脫鉤和連接,表2 為脫鉤狀態的8 種判別范圍[7]。脫鉤彈性系數D測算公式如下:

表2 Tapio 脫鉤類別及狀態
式中:D為脫鉤彈性;ΔCE、ΔPGD分別為CO2、GDP在某一單位時段的變化。
1.3 數據來源
安徽省工業的能源消耗量來源于2007—2021《安徽省統計年鑒》,碳排放系數來源《IPCC 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指南》,各能源折合標準煤系數來源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及《省級溫室氣體清單編制指南》。
2 結果與分析
2.1 安徽省工業碳排放總量特征
根據式1 測算,安徽省工業2007—2021 年碳排放總量如表3 所示。安徽省工業碳排放總量呈 “快速上升—波動下降—緩慢上升” 變化趨勢,碳排放總量在15 年間增長了102.53%。

表3 2007—2021 年安徽省工業主要能源消耗碳排放量表 單位:萬t
1)2007—2010 年為第一階段,安徽省工業碳排放總量快速上升,年均增幅為2 090.6 萬t,年均增率為12.48%。在早期,由于安徽省工業技術發展相對緩慢,且未形成清晰明確的節能減碳意識,導致安徽省工業形成了消耗大量的原煤、原油和焦炭等傳統化石能源的發展模式,快速的工業發展及能源消耗使安徽省工業碳排放呈現出快速上升的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天然氣在能源消費占比不斷增長,說明期間安徽省工業開始著手優化能源消費結構,在往綠色清潔能源方向上進行探索。
2)2011—2015 年為第二階段,安徽省工業碳排放總量處于波動下降期,年均增幅為483.85 萬t,年均增率為2.19%。為落實 “十二五規劃” 提出的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工作,安徽省轉變以早期工業主導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降低生產中能源浪費率,使碳排放增長速度不斷下降且出現負增長。除2012 年為突破第二產業生產總值萬億元大關,工業碳排放增速較高外,其余年份安徽省工業碳排放增長速率均低于4%,且在2014—2015 年連續兩年實現負增長,安徽省工業碳排放在控制下呈現出波動下降的趨勢。
3)2016—2021 年為第三階段,安徽省工業碳排放總量緩慢上升,年均增幅為714.19 萬t,年均增率為2.76%,且連續5 年增長率低于5%。 “綠色” 的新發展規劃已指明中國未來發展的道路,2017 年,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高質量發展的新表述,安徽省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進行產業升級轉型,經濟發展出現放緩。 “中國聲谷” 等高新科技產業園的順利啟用,使安徽省工業碳排放即使在疫情導致的經濟下行時期仍未出現大幅增長,安徽省工業碳排放呈現緩慢上升的趨勢。
2.2 安徽省工業碳排放與經濟發展脫鉤效應
通過使用Tapio 脫鉤公式對2007—2021 年安徽省工業碳排放與經濟發展進行測算,歷年脫鉤彈性系數D及脫鉤狀況如表4 所示。

表4 2007—2021 年安徽省工業碳排放與經濟發展脫鉤情況
由表4 可知,15 年間,安徽省工業碳排放與經濟發展間基本處于未脫鉤的狀態。總體上看,安徽省工業碳排放和經濟發展大致經歷了 “增長連接—弱脫鉤—強脫鉤—弱脫鉤” 的變化歷程,雖然自 “十二五” 以來表現出由弱脫鉤向強脫鉤發展的趨勢,受疫情經濟下行的影響而出現放緩。但在溫室氣體排放受控的情況下,隨著經濟的發展,仍可表現出積極的發展趨勢。
1)2007—2010 年為第一階段,2007—2008 年表現為增長連接,2009—2010 年表現為弱脫鉤。由于生產發展需要,開始大量使用化石能源。雖然綠色生產理念仍在摸索階段,但初期階段經濟產值仍然是連年增長。由于逐漸下降的碳排放增量以及迅速增長的生產總值,導致后續年份表現出弱脫鉤甚至強脫鉤。
2)2011—2015 年為第二階段,安徽省工業碳排放脫鉤態度轉變積極。除2012—2013 年表現為增長連接,其余表現為由弱脫鉤到強脫鉤的變化趨勢。隨著 “十二五” 提出降低17%CO2排放量的目標,安徽省做出包括調整產業結構、抑制或淘汰高耗能高排放企業等在內的改變。同時,由于該階段大量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導致經濟發展出現放緩,也使得工業碳排放脫鉤狀態出現放緩。
3)2016—2021 年為第三個階段,伴隨著工業產業結構調整及經濟產出累積效應的影響,除2017 年表現為強脫鉤,其余年份均表現為弱脫鉤。這可能是由于該階段碳排放總量低速增長,且經濟產出受高質量發展理念指導下的產業優化以及工業技術升級創新出現阻力的影響,2018—2019 年,經濟增長相對減緩,工業碳排放與經濟發展的脫鉤進程也逐漸放慢。為繼續順利實現降碳減排,安徽省出臺《安徽省 “十三五” 工業技術創新發展規劃》《五大發展美好安徽省行動計劃》等文件,鼓勵工業技術創新,促進產業升級,以期在未來向更積極的脫鉤態勢轉變。
3 結論與建議
3.1 結論
本研究在針對安徽省工業構建碳排放測算體系的基礎之上,詳細測算了2007—2021 年安徽省工業能源消耗及碳排放總量,并構建Tapio 脫鉤模型,明確安徽省工業碳排放和經濟發展間的動態關系,同時,探究其背后存在的原因,得出如下結論:
安徽省工業碳排放總體呈 “快速上升—波動下降—緩慢上升” 變化趨勢,由2007 年的13 999.06 萬t上升至2021 年的28 351.67 萬t,年均增幅5.33%。其中,2007—2010 年,安徽省工業碳排放增幅較大,主要是由于安徽省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導致碳排放總量增長迅速。 “十二五” 和 “十三五” 期間,伴隨著節能減碳降排的綠色理念不斷深入,工業碳排放總量首次出現下降,且工業碳排放增幅均低于5%,而后保持緩慢增長。
得益于 “十二五” 和 “十三五” 規劃對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規劃不斷清晰完善,安徽省工業碳排放和經濟發展間脫鉤狀態總體呈 “增長連接—弱脫鉤—強脫鉤—弱脫鉤” 的變化歷程,且在 “十二五” 期間大體表現為強脫鉤,脫鉤彈性系數介于-0.35~0.82 之間。 “十三五” 期間,受大規模投入基礎設施建設、高質量發展規劃指導進行產業優化升級以及疫情影響導致經濟增長放緩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工業碳排放與經濟發展的脫鉤狀態受阻,從強脫鉤放緩為弱脫鉤。15年間,安徽省工業碳排放增長量總體呈下降趨勢。因此,安徽省出臺《安徽省促進工業經濟平穩增長行動方案》,以解決經濟發展卡點、放緩的問題,預計 “十四五” 期間,安徽省工業碳排放與經濟發展脫鉤狀態仍可向積極方向發展。
3.2 建議
本文測算結果顯示,安徽省工業碳排放與經濟發展脫鉤仍處于弱脫鉤的范圍,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間。為進一步控制工業碳排放總量,在實現 “2030 年碳達峰” 目標的同時,保持與經濟發展的脫鉤狀態,提出如下具體建議:
1)工業碳減排是降碳基礎。針對煤炭等傳統化石能源這一主要碳源,要充分結合本省資源及技術優勢,提升資源有效利用率、優化能源消耗結構。同時,要積極開發非化石能源,提升光伏發電、風電及生物質發電等清潔綠色能源在能源消費結構的比重,制定切合實際的生產計劃,消除生產過剩和資源浪費。
2)產業優化調整為減排助力。積極構建低碳產業體系,完善綠色節能供應鏈。對鋼鐵、建材、有色等高能耗高排放產業進行降碳技術升級改造,以高新適用性科技助力行業降碳減排,依法淘汰產能落后或資源浪費。同時,應注意加強供給側改革,提升產業附加值,權衡好經濟發展與降低工業碳排放的關系。
3)構建碳排放交易市場是可行之策。對現行的溫室氣體排放報告制度查漏補缺,使報告結果更為精準,便于政府和企業更加規范、科學地監管碳排放數據。安徽省未來可聯合長三角經濟區共同建立并發布工業碳排放年度統計公報,以實際數據為工業減碳降排明確方向。可參照浙江省成立 “工業碳效評價與改革創新中心” ,通過收取部分碳稅來彌補高碳排放區域造成的污染,促進工業生產和碳交易產品的相互轉化,實現工業碳排放逐步降低和經濟穩定持續增長的雙贏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