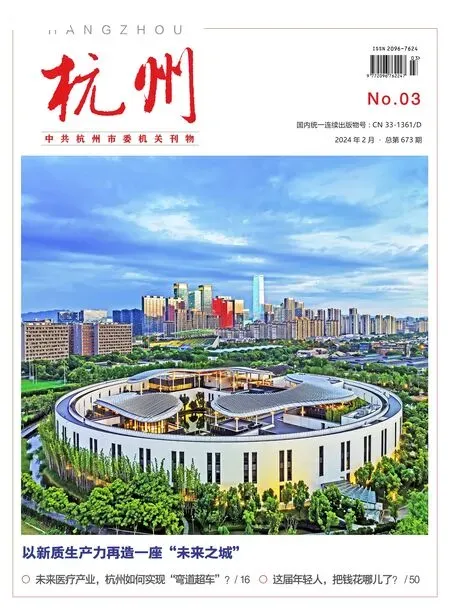當代小說中的“杭州”一窺

如果要用文學體裁來比擬杭州,散文或詩歌一定會被提起,比如說,杭州是一首詩,美而不艷,雅而不俗,讓人回味無窮;杭州也是一篇散文,淡淡幾筆,萬象俱生,惹得人們心旌搖曳。然而,鮮少有人會用小說來形容杭州。的確,縱觀整個中國文學史,杭州與小說的緣分確實也淺。
文學與城市之間、作家與城市之間一直存在著非常迷人的聯系。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我們熟知老舍的北京、巴金的成都、張愛玲的香港、王安憶的上海、池莉的武漢……似乎,唯獨缺了杭州。當然,許多作家寫過杭州,特別是在現代文人的作品中,杭州的景與物、人與事常常成為描摹的對象或情感的寄托。但是,這些作品中的“杭州”常以山水特別是西湖美景出鏡,而這些作品的體裁也常是散文或詩歌,能納入文學史的大作、力作并不多。因此,有人說,杭州是現當代文學史上的“失蹤者”。
“失蹤者”的說法值得商榷,但是,在小說的語境中,杭州的確如害羞的姑娘,鮮少露出真容。不過,仍然可以在部分當代作家的小說中發現杭州的存在。
與杭州情感聯系最密切的當代作家非王旭烽莫屬了。從《南方有嘉木》到《望江南》,再到以西湖十景為題的十部愛情小說,王旭烽以壯闊的筆觸和細膩的描寫,一次次讓杭州成為小說世界的主角。
《茶人四部曲》以茶葉世家幾代人跌宕起伏的命運為主線,描繪了一首有關茶人精神的交響曲,杭州這座城市始終立于文字之中。在王旭烽的妙筆之下,人事起起伏伏,往事山回路轉,留下的是一個人的一生,一個家族的過往,也是一座城市的命運和一個民族的歷史。王旭烽的精妙之處在于,她把對杭州的理解和經年累積起來的感情全部投入到了書寫之中。因此,閱讀她的小說,仿佛打開了杭城某個家族的相冊,每一幀的相片都在無聲地講述著悲欣、變遷與榮光。在《望江南》中,王旭烽對杭州的炙熱情感達到了頂峰,她以對人物的細致刻畫和對事件的戲劇化設置,把茶人茶事與蕩氣回腸的大時代緊密相連,她的茶盞中,倒映著杭州的山水、古典的文墨和時代的風度。
城市文學不是寫城市,而是寫“我”的城市。寫作者長期居于某座城市,是書寫城市的情感基礎。著名作家艾偉長居寧波數年,他早年的小說多以“永城”為背景——此處的“永”與寧波的簡稱“甬”同音。2015 年,艾偉遷居杭州,經年之后,“杭州”出現在了他最新的長篇小說《鏡中》之中。書中,莊潤生的妻兒發生車禍的地點在“虎跑路進入錢塘江大橋的拐彎處”,莊潤生與情人約會的地點是龍井村附近的一處茶莊,莊潤生的建筑事務所位于錢塘江邊的文化創意園區,莊潤生妻子易蓉的老宅在運河邊……帶著杭州符號的生活場域頻頻出現,城市成為了作家感官體驗與心靈活動的特殊寄放場所。在尋訪、徘徊、失落之中,作家與城市相視一笑,精神世界與現實世界也達成了和解。艾偉自述,這是他在小說中首次書寫杭州,《鏡中》是一部獻給杭州的贊美詩。
作家葛亮在他的“中國三部曲”第二部《北鳶》中也對杭州著墨頗多。葛亮的爺爺葛康俞先生早年就讀于國立杭州藝專,這部以家族史為背景的長篇小說自然地無法離開青春故土杭州了。《北鳶》的寫作氣勢磅礴,場景輾轉大半個中國,杭州故事的出現仿佛清風拂面,為大時代的鳴唱帶來了溫柔又明亮的注腳。讀者也能在葛亮的敘事間領略一百年前杭州的風采。文學中的城市以“再現”的方式隱秘地透露著知識、歷史與文化的昨天,因為文學的力量,城市開始呈現自己的意義與價值。
不過,在小說中滲透進一座城市的空間符號與時間標記,是不是就能創造獨屬于這座城市的文學?假設,很多小說抽離了這些有關城市的符號,城市與文學的關系是否成立?細想,小說的內容依然成立,但是,情感指向上可能就有了偏差。當然,如此理解小說與城市的關系,未免苛刻,畢竟,文學與城市的關系始終多元。
然而,讀老舍的《駱駝祥子》,立刻知道這寫的是北平的故事,讀金宇澄的《繁花》,馬上便知這是一部上海小說。可見,文學的要素以外,語言的運用也在成就文學與城市的永生。如今,更年輕的寫作者開始了這樣的嘗試。2018 年,杭州青年作家張哲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是夢》,介紹里說,這部小說“描寫了20 世紀80 年代至今中國市民社會的一段歷史,也再現了杭州曾經的風物、山水、方言和舊的生活方式。”在文學式微的當下,這部小說并未引起過多的重視,當然,其中一定有作者寫作意識與文本內容的原因,也有宣發力度的問題。但是,這部小說仍然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閱讀杭州的方式。小說中,邁著小碎步般地夾雜著杭州方言的語言,無處不在的杭州地名與民俗,似乎都在提醒我們,這里的一切屬于杭州。作者張哲是土生土長的杭州人,他見證了熟悉的逼仄的城市一點點壯大直到陌生,也見識了人情冷暖的變遷與世事無常的無奈,他的寫作是一種自發的“為杭州書寫”。
當“為杭州書寫”成為本能,一定會有更多生活于此的作家和寫作者創作更多屬于杭州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作品。城市承載著我們的過去、現實與未來,以無聲無息的方式延續自己的風華,而文學則將以想象與創造的方式永固這種風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