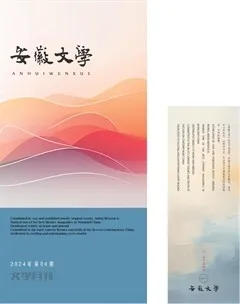果園
范懷智
女 人
他琢磨星星。
真奇了怪了,這些天,天里憑空冒出一顆星星。
夜黑透,河川靜寡寡地靜,就在果園西頭抵近小河水的上空,冒出了一盞蛋黃樣的星星,明嶄嶄的像盛開的金針花一樣,黃燦燦的老沖他笑。
整個午后,他都在果園收拾雜草。按理說噴施些農藥,就省得用鋤頭去一下一下刮草。他是生怕農藥傷了青果,殃及果樹。反正到了農閑,用不著進城去務工。
說及不務工,不是他要躺平。六十好幾的人啦,他進了工地能咋樣,搞安檢的人來看身份證,還不得清退他。與其這樣子,不如窩在河川,侍弄這衰舊的果園。他是這么琢磨,日月平緩,如靜水深流,他只要手頭有個零錢,不給兒子添累就成。
麥收畢,沒多少人家種玉米,田地消停下來。
好些年了,每次收種完畢,他都跟河川里的匠人們一同外出,待到收種時又急慌慌往回趕,慌急得真像個趕麥黃的候鳥。日子如車輪,飛轉不停,即便是個機器,也得有個歇緩的時候,他們卻是除了陰雨日整天都在忙亂。前幾年,果園由女人侍弄,每到開春和收種結束,他就得背起女人漿洗過的被褥進城,真像那趕麥黃的鳥兒。
每到出走前的晚上,女人會問他:“果園咋弄?”
他說:“能咋弄,能拾幾個就拾幾個。拾不著果子了,不長草也成。”
女人是明知故問,女人知道他顧不上果園,知道他仍舊要那么答復,可女人還是要有所依賴地問問。
女人來侍弄果園,確實有些力不從心,可這能有啥法子!風要把樹葉子吹黃,樹能有個啥法子。河水要將河槽改道,河槽能有啥法子。再說羊娃子,來到這河灘上,還不是個挨宰的命,可羊娃子能有個啥法子!
村里的好幾家果園,都由各家的女人來侍弄。再說果園一般沒啥好收成。果子成了時,滿河川的果子都成了,哪能賣出個好價錢。要是果子歉收,都歉收了嘛!原本想著多少能賣個好價錢,往往是外地的果子又擠進來。一年勞累,哪年的果園都沒能賺到盆滿缽滿。因此他對果園有期盼沒要求,故且隨了女人去侍弄。這兩年,河川地的承包費每畝七百,兩畝地的果園,女人每年能收回一千五也成。既然他都這么說了,女人只管鋤凈雜草,到中秋前后,果汁廠的人來收果子時,可依據河川里的行情,不論多少,轉手就成。
女人說:“不管咋說,比麥子的收成要好些。一畝麥子除收割、耕地、播種、化肥、農藥、種子,還不算人工,撐死了能落下五百塊。現今不論咋說,一畝果園,閉著眼都能賣出個三兩千元來。”
他說:“這不就成了嘛,管個水電費,夠你開銷就成。”
女人說:“這開銷是個啥,菜自家種,糧食自家地里打,只要不生病,這日月還不是往前紅火著過哩!”
他說:“兒子要成婚哩!”
女人說:“這個你管,我不管!”
雖說不管,他外出的日子,女人除了料理果園,還在河川打個零工。
還未入伏,太陽落進河西原畔,通紅的晚霞登時熏染川原,天即刻清涼。
跟往常勞作一樣,他操持大杈耙,把鋪展在地的雜草攏成堆,待它們在風日里干透,再碼堆到庵房南側的草棚子下。大草棚間散養著八只羊,干草留給羊過冬,羊吃剩的草柯子,平日用來燒火和煨炕。
初夏羊群的數目不只是八只。到深秋,到白霜浸染了小河川,到了羊長到胖壯的季節,羊販子們一上門,他準要挑揀著留下八只羊。其余的羊,清點過數目,讓羊販子統統帶走。有人問他養了幾只羊。不論啥時候他都說八只羊,他管每只羊都叫八只羊,這稱呼合心意,這稱呼有些富足的意味。
羊性情綿柔,像壇陳酒,是種靈醒畜類,愛干凈,只吃頭茬草,只吃掛了露水珠的青草。到冬天,青草沒了,羊只顧吃那干草的前半部分,前半部分蓄了草香,可剩下的后半部分,成了草柯,揪撒得滿地都是,他只好將散亂的草柯跟黑金似的羊糞蛋子,攏到庵房前的空場上晾曬,摻和了羊糞蛋的草柯煨就的火炕火燙得緊,耐久得很,歷時一晝夜,照舊燙烘烘的熨帖。待到白雪落白川原,他就躺在庵房的火炕上,捂進被窩,看門洞外頭的厚雪,新棉被一樣蓬松的雪。這時的川原臃腫富泰。
庵 房
在小河川,村人把蓋在果園地頭的小瓦房,用來避雨、休憩、放農具的小房子統稱庵房。栽種果樹時,他期望地東頭的緩坡上能有座小庵房。
他說:“有個小庵房好,有個小庵房,閑時可來坐坐。再者,要叫你推趕到屋門外頭,也能有個去處。”
女人說:“你是匠人你不會蓋?看你說下的話,兩口子過日子,咋能不慪個氣,慪個氣就慪個氣嘛,咋舍得趕你到門外。”
話是這么說下了,果樹見天瘋長,從一棵小樹秧子長成大樹,長到青果子壓彎枝丫,這小庵房呢還沒蓋成。直到兒子成婚,女人不能下地的日子,她還惦念個小庵房。
“你看你看,多少年了,凈是謊話兒,咋還沒見你起蓋!”
“忙嘛,哪能抽出點空閑。”
“要說忙,凈是忙。要說不忙,看似要緊的活兒,說放下也就放下了。我是說,你往后也好有個去處。”
“凈瞎想,想得多能頂個啥?往后的事往后了再說!”
女人盈盈地笑,他跟著女人笑。女人笑得疲累得很,女人的笑瘦瘦的,一天比一天瘦。似乎就在女人盈盈的一笑間,一眨眼竟過了兩年。總覺著,年少的日月長得望不到頭,人活到了一定年歲,日月竟短到沒了頭緒,稍不留神,一年就白嘩嘩地淌遠了。
照他的話說,一年能有多長,三百六十五日,還不是晃晃悠悠的一場夢境。
上回進城,背著條汗腥腥的被褥換過幾個工地,還不是沒干幾天活就回了河川。這一回呢,緊巴巴的日子忽地開闊,開闊得又曠又遠,日子一下子閑散到有些闊綽,有些乏味。他攥著鐮刀,掮著鋤頭去果園,果園不只生滿雜草,新生的枝杈和雜草的藤蔓把樹冠銹結得不成樣子,真像個頭發蓬亂毛頭毛臉的野人。
鋤草的間歇,他有意看過女人說過的起蓋庵房的地頭,地緊挨原坡,斜緩的坡面長滿洋槐高草,地頭和原坡銜接的塄坎下女人栽種了一根竹,土是好的,一根竹已經長成一叢竹,竹叢長得青蔥歪斜,一副頭重腳輕的樣子。他明白女人的用意,竹東的坡面,地勢高過田地,是起蓋庵房合宜的處所。這地頭的不遠處,有眼砌了井臺的機井。前幾年有人要承包這片地,承包地前必須通路、通電、通水。路本來就是通的,修葺過機井,農用電拉到井前,承包的事宜反倒沒了下文。
很明顯的,女人肯定修整過竹東的地頭,雖則又長滿了雜草。他剔除掉高聳的茅草,在這片空地上,他從傍晚一直圪蹴到夜黑,他靜靜地守著果園,腳前是他捏碎的一捧土,細若粉面的黃土。
河川飄起暮靄,潮蒙蒙的月亮升上來。恰好,青竹后的這掛緩坡上曾有一座庵觀,庵觀里有五眼窯,上下兩層,底層三眼,頂層兩眼。底窯住人,頂窯的窯壁跟窯頂畫滿彩。在頂窯的頂上還有一方磚砌的平臺,平臺上建有一座鐘樓,飛檐翹角四面透風的鐘樓,其實是座簡易的能吊起銅鐘的亭臺。這口古鐘每天清晨、傍晚都會撞醒,嗡噌渾闊的聲響直貫百里,順著彎彎繞繞的河水,響徹河川。可惜他沒見到過它,他出生以前,一場纏綿兩月的陰雨,滑塌了整座庵坡,那座有彩繪和古鐘的庵觀埋進了土,原本陡峭的拾級而上的庵坡趨于斜緩。有人說,在庵坡的坡面上,夜深人靜時,可以看見一只金馬駒子在林子和草叢間跑跑停停,它脖頸下綴了紅纓子的串鈴,叮當叮當地響。
說及起蓋庵房,女人問他:“說是到了夜靜,能聽到那丁零響的鈴鐺聲。”
他說:“說是有口古鐘。”
夜靜得深了,女人躺在他身側,靜靜地聽。瘦削的女人還在悄悄地瘦。女人靜得比夜深還靜……
起蓋庵房時,他在地頭挖出過銹蝕的鐵鍋,挖出過破碎的陶罐,還有一架完整的狗骨,輕輕一碰,它就融進了土中。大約此前,此處曾有過院舍。
庵房蓋起后,他沒想過盤火炕,可他又盤了火炕。火炕干透,傍晚他和了泥巴,糊抹了炕面上的煙縫,窗下的炕洞散出柴煙,他在溫熱的炕坯上靜靜睡過一宿,睡得跟瘦削的女人一樣靜。一根竹子,它沒想到過,它會長成竹叢。一粒麥籽,它沒想到過,它會長成遍野的麥子。一塊地頭,它沒想到過,它的軀體上還會升起煙火。不知是只啥鳥,它在水井旁的洋槐樹上筑巢了。
火炕盤起,他沒想過要住進庵房,可他住進了庵房。起初一個月住不了幾天,到果子收獲全倒賣掉的初冬,他白天坐到庵房前的樹墩上曬暖暖,曬到迷昏的瞌睡襲漫全身,他歪垂著頭扯起了鼾。晚晌爐膛間生了火,看那苗條的火焰擰扭腰身,他索性臥進燒燙的炕頭,聽那轟吼的青煙鉆出煙囪,繚繞上房頂,四散進庵坡和果園。苗條的紅火映紅庵房,映紅農具跟鍋碗,映紅炕頭和窗,映紅臉,映出臉上星光樣的微笑。
杏 嬋
入了冬,杏嬋有陣子還往果園送飯。杏嬋懷里抱著的是他的孫女,這孫女一點都不親近他。他說叫爺,孫女畏怯地把頭臉窩進杏嬋的胸脯上去。
杏嬋有了身孕才從西安回到了河川,兒子仍在西安打工。兒子準備在縣城租一套房子,等到杏嬋生下二胎,孫女開春入學,他們往后的日月都要在縣城里磨纏下去。
放落手鋸,取下別在褲腰上的剪枝刀,他上了地頭。地頭的陽光分外旺,明凈和暖,獨有鉆過果園的風,挾裹著颼颼的清冷。
他說:“抱個娃娃,跑這么遠做啥!”
他說:“有爐子,有鍋灶呢,隨便弄個吃食就成。”
杏嬋說:“咋成哩。”
跟他一樣,杏嬋不咋說話。杏嬋靦腆,是個通情理的孩子。她笑笑,抱著女兒,笨拙地走進果園,走到一棵兩棵的果樹后頭去。
杏嬋的父親跟他同齡,他倆去務工,樓體外的架板脫落,砸傷了兩個人,摔死了杏嬋的父親。她母親改嫁,走時杏嬋不到五歲。杏嬋入了學,他每次務工回來都去看她,給些接濟。他還讓女人給杏嬋買過書包,買過衣襖。女人說過,干脆接過來,當咱閨女養。他說看你說下的話,不光要咱愿意,還得杏嬋爺跟杏嬋婆愿意呢,兩個老人咋舍得?!杏嬋十七歲時奶奶病故。他愿意供給小閨女上高中,杏嬋不想上,要去打工。杏嬋二十歲,有人托他去提親。杏嬋說還不急。杏嬋二十三歲,正月里回了屋,他給過杏嬋壓歲錢,還是幫人提親。
杏嬋問:“叔,你家祺正訂了婚?”
他說:“沒,到了年歲,他反倒不讓催逼。”
杏嬋說:“那你給我電話,我給他提個親!”
他說:“成。”
他愿意,女人愿意。兒子順從了他,兒子同杏嬋訂了婚。
他說:“祺正,杏嬋比你大一歲,但你可得把她當妹妹。”
女人說:“這話用得著你說!兩口子過日子,窮富是個啥,兩個人一起開心,一起歡喜才有個好日子。”
沒想養羊,卻在庵房的南側起了個大草棚,養了羊。就像井臺旁的洋槐樹,沒想過要長成啥樣子,卻在風日里偏長成那樣。那口隱在深土里的水,也根本沒想過它會成為井水。
深冬季,河川空靜。風隔會兒撩一段黃塵,穿過果園,嬉鬧般地在綠沉沉的大麥田奔跑。高天里的鷂鷹像粒黑豆,在松散的白云下凝滯。每次去打水,他總往槐樹下的水洼倒些清水,鴉雀們隔陣子撲棱棱落下來,落進淺淺的水洼,聒噪著汲水。它們每汲一口水,就擰頭沖著井南的庵房叫,它們沖著庵房說謝謝你,謝謝你。大晌午,身體笨重的杏嬋拖拽著女兒,拎著小半袋面粉鉆過果園,要是粉白和粉紅的花朵們綻放在枝頭該有多好!羊們咩咩叫,像在告知他,閨女來了,閨女來了。
他提拎回一桶水,杏嬋和面,孩子坐在庵房前的干草上玩貝殼,是他從果園的沙土里刨出來的貝殼。杏嬋餳面。他燒旺了爐火,架上鐵鍋。
杏嬋說:“爸,想問你個事哩。”
他說:“你問。”
杏嬋說:“我媽想來認我!”
他說:“你咋想的?”
杏嬋沉靜地擇菜,杏嬋說:“我有三個姑姑,就不認了吧!”
他看著孫女,說:“姑是姑,媽是媽,還是認了好!”
杏嬋的飯做得細致,可他吃不出他想吃的味兒。
臘月,天上堆起陰云,祺正回來了。
夜,燒紅爐火,擠在庵房里吃過一頓飽飯,是杏嬋和祺正做的揪面片子,湯火里煮進燴炒過的洋芋疙瘩。他一日兩餐,果園里的早飯在十點左右,晚飯要吃到飽脹才能安睡。
夜靜,拖著哨音的風撲過果園,撲上斜緩的坡面,搖晃風中的枝梢,掀起嗚嗚的林濤,如沙的細雪打上窗戶,趁雪還未下旺,趁風還未冷硬,他要祺正摟抱了孩子和杏嬋回屋院去。兒子不回,杏嬋笑瞇瞇地上火炕,他燒到燙烘烘的火炕。八只羊躲在大草棚下藏進干草垛后咩咩喚叫,它們在欣喜地喚雪。冷風卷裹著不急不緩的雪,零星的雪粒隨意飄灑,慵懶的,有一搭沒一搭的,雪像白紙樣彌漫了河川。
雪忽爾又停了,風還搖著樹梢和門窗,門環咣當地拍響木門。挪了新窩的孩子,在溫煦的紅火中,在綿軟的炕頭上蹦跳。在紅燦燦的火光中,一家人擁上炕頭。此夜當然說到了房子,西安的房子太貴,祺正想都不敢想,現今若想買房,最好的選擇在縣城,若交首付,手頭還沒有那么多的積蓄。眼下杏嬋還得生孩子,光是奶粉錢,幾年下來,都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只可惜,這兩年的收入,他貼補了家用,前兩年的收入還了債。再者即便有一身純熟的手藝,可沒了能使喚手藝的地方。
“這個,你得聽聽杏嬋的主意!”他說。
他攏抱孩子,綿軟的孩子從他懷里爬出,爬往窗臺,去摸窗臺上的油燈。杏嬋拉拽孩子,孩子鉆進被窩。杏嬋能有啥主意,她從不催逼祺正,過日子嘛,能過成個啥樣就過成個啥樣,啥是好日子,平安就是好日子,一家人和氣就是好光景。
“只要盡了力,都說那個人本事大哩,人能有多大本事,他能叫日頭直端端地停在頭頂上,一直是白天,一直不讓天黑?”杏嬋說這話時,滿臉噙著笑,她雙眼彎彎,彎成兩枚新月牙兒,“有房子也好,沒房子也好,在城里有房子,大冬天有暖氣,沒房子,咱住到咱爸修成的屋院里來,咱還有咱的大火爐子哩!”
祺正說:“到縣城里得有房子,孩娃們好上學!”
杏嬋說:“幼兒園,紫藍鎮上有兩所。鎮上有小學,有初中,校車每天來接送,孩娃咋就上不了學了。”
“我是說,縣城的教學質量高!”
“看你說下的話,只要孩娃們都不虧孝、不邪淫、愛惜物命,他長大了干啥都成!”
祺正看著手機,房子他還是決定要買。吃了頓飽飯,坐進燙烘烘的炕頭,眼睛澀澀的,腦子昏沉到擠滿了瞌睡。
杏嬋問他:“爸,你說我說得對不對?”
他說:“對、對!”
他聽見杏嬋說:“每天一睜眼,還能看到窗外頭的天,看到院里的光影一寸一寸地往窯窗跟前移,心里就有莫大的幸福感,我還能深深地吸口氣,還能勻勻地吐出去。”
杏嬋說到這兒,深深地吸氣,祺正跟著吸氣。杏嬋勻勻地吐出去,祺正跟著勻勻地吐出去。他在不經意間,也跟著吸氣吐氣。好似這一輩子,他才體味到他鼻子前頭原來就布滿空氣,沒顏色沒味道卻能嘗出香甜的空氣。
杏嬋說:“我三十一,我爸到我這年歲就沒了,這世上,跟我爸同樣年歲就沒了的人有多少?再有就是跟我在西安的電子廠打工的玲萍,她比我大兩歲,大前年,身體不適,還以為懷了孕,到醫院一檢查,是白血病,一年后玲萍沒了,我給她打電話,先是關機,后來欠費,再后來成了空號,她的微信還在,微信的名字叫溫馨之馨,可微信里沒了聲息。這世上如玲萍的人又不知有多少。爸,你說我說得對不對?”
他眨巴眨巴眼,緊忙說:“對,對的哩!”
孩子從他懷里爬出,爬向祺正,祺正狠狠地親一口,再親一口,孩子笑出聲,笑聲分外脆,跟咬進口里的冰糖一樣脆。
他突然想問杏嬋一句話,瞇著眼打過一個哈欠,卻忘了要問啥。
爐火疲軟了些,映在庵房里的影子不再厚實,忽而有些虛飄。祺正下炕去,挑揀了結實的槐木疙瘩塞進爐膛,萎縮的紅火煥發了神氣,猶似一列高鐵竄出山洞。涌騰的青煙飛馳過鐵皮的煙囪,并從煙囪口噴涌出去,隱有轟吼。冷硬的夜風愈發冰冷,干草垛后的八只羊咩咩地叫喚,云團壓上果園,壓上低矮的庵房頂。若窗里沒光亮,紅潤潤的光亮,夜比禁錮在鉛錠里還黑。
靜 聽
祺正坐到爐火前看手機,瀏覽房價。孩子偎趴到杏嬋的胸前,打過一個小巧的哈欠,瞌睡說來就來。孩子偎蹭杏嬋,瞑了眼,杏嬋輕輕地拍撫她,孩子睡著了。
杏嬋問他:“爸,我爺說庵房這地方有兩口古鐘。”
他迷迷昏昏地說:“對,有一口。”
“是兩口。一口是先前鑄下的,一口是第二回鑄下的。先前的那口埋進了坡地,后一回的那口掛上了鐘亭,就是每天早晚都敲響的那口。”
“是一口,都說是一口。”
“是兩口,都是從山東來的鑄鐘匠鑄下的鐘,鑄鐘匠還是個瘸子呢,拄了根油光溜溜的手杖,住進了庵坡窯。他住下來到各村各戶去化銅,紅銅、黃銅、青銅都化呢。”
真的困倦了,眼皮子輕輕彈動,眼睛似睜似瞑,是杏嬋給他講述,是他給身側悄悄消瘦的女人講述。夜那么靜,燈昏黃著。
預期兩年。兩年里鑄鐘匠能化多少銅,就鑄多大的鐘。化到第二年開春,鑄鐘匠走進河川的一戶人家。女人晌午剛跟男人吵過架,坐在院場的杏樹下奶孩娃呢,女人還在氣頭上,他就上了院場。他剛給女人恭敬地打過躬,女人就隨口拋給他一句話,要銅沒有,若非要化,就把我家娃娃化了嘛,還能頂不了幾兩廢銅?氣恨恨的,女人的頭別到一邊去了嘛!他哀嘆一聲,走了。到冬天女人家吃奶的娃娃得病,沒了嘛!
到年底,熔銅鑄鐘。正月十五元宵節那天,一口背簍大的銅鐘鑄成,幾十人抬著厚墩墩的銅鐘掛上起先修好的鐘亭。他說不忙敲,等過了二月二再敲。他拄著油光溜溜的拐杖走了。過了二月二,村人想敲,有人阻攔,還怕等不到三月三嗎?
過了三月三,草長鶯飛的日子,浸潤過了雨水,滿河川的綠,清凈的小河在大太陽底下明晃晃地晃眼哩!鐘亭里的銅鐘撞響了,沒曾想到的事嘛!轟嗡的鐘聲里咋有孩娃驚詫詫的哭聲?就是這口鐘,敲過幾天后,孩娃的哭聲愈發地緊,就像天里壓了厚厚的云。這往后嘛沒人敢敲。鐘懸在鐘亭,自然廢棄。
過了麥收,村人往秋田里培肥的時節,拄著拐的鑄鐘匠回來了,夜里還住到庵坡窯。村人去看他。他說坐馬車快到北京了,聽到鐘敲響了,鐘聲里咋有孩娃的哭聲,就回來了嘛!唉——!
猶如夜幕降臨,彌漫的瞌睡濃霧樣塞實他的腦海。他的嘴里含混地說:“對,對就一口鐘。”
祺正沒聽杏嬋說啥,他攥著手機,往爐膛里塞了塊槐木疙瘩。
杏嬋說:“爸,你說的那口鐘,該不是他回來后,鑄下的第二口鐘,就是掛進鐘樓,后來早晚敲響的那鐘?”
風撩拋雪,雪撲灑上窯窗。雪在玻璃上沙沙響,就是庵房里的這個鐵爐,他曾在窯垴間燜著一汪紅火,徐徐散著溫熱,窯門頂的煙筒口,浮散出絲縷的煤煙。
女人悄悄問:“鑄鐘匠回來了?”
他說:“回來了!”
女人靜靜地聽,窯窗外的雪花也在聽。
白天忙農活,夜黑了,一伙子人借著一盞油燈光,問鑄鐘匠咋辦。他說還能咋辦,吊在鐘亭里的鐘,很明顯是廢掉了嘛,還能咋辦,挖個深坑埋了,趕明日再化兩年鐵,再鑄一口。
天一明,他拄了油光溜溜的拐杖,到各村各戶去化銅,破舊的銅鍋、銅壺、銅勺、銅盞子都化取,包括地底下挖出的破爛的朽脆的銹銅也化取。能化多少銅就鑄多大的鐘吧。兩年后的冬天,一堆破銅堆在庵坡窯的院子里。
冬至前,沸銅濾去殘渣,熔成了銅錠。冬至后重新制模,到開春的正月十五日,鑄成的第二口鐘掛上了鐘亭。正月十六,是個吉祥圓滿的好日子,他要走了,他還是叮囑,等過了二月二再敲,最好是過了三月三敲。他背個背簍就走了。
鑄鐘的人走就走了嘛,只是這口鐘,等過正月十七,等過正月十八,正月十九日的傍晚,飛掠在河川里的鴿子們,成群的鴿子們回了庵窯,撲棱棱落上鐘,落上鐘亭的飛檐翹角,落上青瓦,轟嗡的鐘聲敲響了,河西的原畔上亮起金燦燦的祥光,漫天的紅霞在悠揚的鐘聲中褪盡。三天的焦急等待,村人終于確信,鑄鐘匠沒騙他們。他們沒在轟嗡的鐘聲間聽到異樣的聲音,叫整個河川不安的聲音。
正月二十二傍晚,鴿群落上鐘亭,西原畔上灼燒起祥瑞的金光,晚霞們急驟地被收攏進金光。鑄鐘匠回來了,在噌吰的鐘聲中,他一臉慍怒道:“親口叮囑過的嘛,等過了二月二,最好是過了三月三敲,咋剛過三天,就敲響了。”村人說:“心切得緊,只怕這鐘聲里還有不祥的聲音,你卻走遠了,走得沒了蹤影。”
鑄鐘匠往窯院里重重地頓一下拐子,長長地哀嘆一聲:“這鐘聲,我走多遠就能傳多遠,三天我走過了百里路,這鐘聲也只能在百里的路途上傳鳴!”有人說,要么重鑄。鑄鐘匠說:“是個代天地發聲的器物,怎會有三回鑄造的理,也罷吧!”夜靜靜地墨黑,天里掛著虧殘了一半的月影。
天未明,鐘未響時,鑄鐘人踩著淺淺的白霜,順著那彎折的小河走去。
他沒再含混地回應,杏嬋輕聲喊爸。他睡著了,扯著微弱又勻稱的鼾。趴在杏嬋胸脯上的孩子睡熟了。坐在紅火曛曛的鐵爐前,祺正還在撥弄手機,他在手機里看汽車、看奶粉。慌急的風揪扯枝梢,瘋癲的風在曠遠的麥田,在庵房后的坡面上扯長了呼嘯。隱在草棚、隱在干草垛后的八只羊一波一波喚叫,下雪啦下雪啦!厚重的陰云咚地砸了地,白雪紛揚地拋撒下來!堅硬的雪粒敲響蒙著苫布的窗戶,雪打在皮實的塑料紙上嚓嚓響。
原野若那水草豐茂時的綿羊,一夜間長得肥胖,長到油光水亮,雪捂肥了果園、原坡和麥田。煙囪里撲散著青煙,河川憨睡在厚重的白棉花底下,還有庵房、草棚和水井。他醒轉時,一窩麻雀和兩只斑鳩在窗外吵鬧得緊。
拉開門,掃開門前一方白雪,撒落一碗玉米,眼尖的麻雀們迅速飛來,像疾風卷了紛擾的葉片,覆蓋了白雪間的金黃。八只羊渴了,他拎了鐵桶,踩著深及膝頭的雪去打水。井口冒著白汽,一團氤氳的白汽,白汽吞沒鐵桶,麻繩猛地一松,井底回響起水面被打破的撲通聲。
雪還在飄飛,酣暢的青煙鉆出煙囪。吃過早飯,祺正摟抱著孩子,把她包裹在衣襖里,身后跟著愈顯笨拙的杏嬋。倆人走進白雪,走進果園,偶或還能聽見走遠了的說話聲,散淡的說話聲,這天地間唯一的小兩口的說話聲。他也想跟守過果園的那人說說話,天地茫茫,徒有鳥鳴。
香 云
臘月底,祺正在縣城租了房子,兩室一廳,在紫韻小區,跟杏嬋的三姑家隔了幢樓。農歷二月初五新孩出生。看來到紫韻小區租房肯定是杏嬋的主意,要么杏嬋同三姑商量好了,往后不單是讓三姑照顧她,還要三姑幫她照看孩子。三姑家的孫子已經長成,最小的上了初中,跟了表哥表嫂去寶雞,三姑成了天天擠到超市門口買低價菜的閑人。有了杏嬋,她也有了個說體己話的人。
杏嬋出了月子,祺正就去打工了,他是車工,離開工廠沒事可做。祺正走前回到河川,拉走了磨好的新面粉和新榨的菜籽油。他特意給杏嬋三姑家備妥了一桶油。家中添新人,添進了鮮活氣。他心中滋起安穩的歡喜。沒想到花白若雪海的日子,香云來找他。
他坐在白雪擁堆的果樹下劈干柴,循著空空的斧斫聲,白酥酥的花樹下鉆出香云。他著實嚇了一驚,在白晃晃的花樹間,在亮汪汪的太陽下,站著的怎會是香云。斧頭哐地落上柴禾,斷折的柴梗蹦一下,落下去。
“你咋來了?!”
“咋不能來,看我閨女杏嬋!”
去年收罷麥子,有人專門來到果園,向他提說香云。
他問:“不知人家香云咋想、咋盤算?”
來人說:“還能咋盤算嘛!是香云托了話來。”
來人留下香云的電話,順便帶走了杏嬋的號碼。
趕過秋收,種齊麥子,一轉眼節令從秋分淌入小寒。香云來了屋院看他,她為杏嬋的小閨女買了衣襖。正午的太陽真像銅鏡,從銅鏡里折下的光稍稍浸著些暖意。他淘洗菜籽,準備春節時榨取些清油。一年到頭屋院沒幾個人影,過年時偏是個吃油最旺的節日,他盼望祺正、杏嬋和那綿軟的小閨女回來,她要孩子們啥都不干,只要他們吃好睡好,既是拖了身疲累回來,那就一身輕松再走!
她說她是香云,她若不說,他真不認識她。
大晌午的陽光稠密了些,和暖溫煦。她幫他淘洗,他瀝干了油菜籽,往寬展的彩條布上晾曬。
杏云說:“以前對杏嬋有虧欠,現今你是杏嬋爸,我是杏嬋媽,以前是有家室,現今是有了自由,只想搭幫過個日月,給杏嬋一個渾全的日子,一個有媽的日子。”
他問:“那你兒子咋辦?”
“兒子在北京,結了婚,有了小孩娃!”
“那小孩娃咋辦?”
“孩娃有外婆,有外公。外婆、外公是北京人,兒媳是獨生女。”
他一下子明白了。
她笑得輕攏了一把鬢角的發絲。
他說:“你看咱河川,獨生子女的屋院也有幾十家,旁的不說,你看我只有祺正。就你好,有兒有女,真是個渾全日子,賽神仙嘛!”
她笑出聲:“年輕時沒當成個神仙,近六十歲的人了,還真成了神仙!這個神仙我不要。”
近一年的光景,他沒跟香云通話,也沒她消息。到初冬,果樹們落盡了葉子,懶洋洋的果園睡進輕薄的陽光里,杏嬋來送飯時說起過她。
他請香云進庵房,她這一次來,是給新孩縫了身新棉襖,繡了對虎頭枕頭和小憨豬的鞋子。
他說:“勞煩你了!”
她說:“有啥勞煩不勞煩,是自家親外孫。一人守個屋院,光景滿是清閑,坐在窯門口就個銅燦燦的太陽,縫縫剪剪倒也安寧,只是好些年不動針線了,針腳粗疏,手生!”
他說:“人巧了,手也巧嘛,針腳也粗疏不到哪兒去!”
大晌午。他挑水,她擇菜,他燒火,她揉面。太陽端正到果園上空,他和她坐到庵房前的木墩旁靜靜地吃飯。吃飽肚子喝飽水,散步到庵房前的八只羊臥在他倆旁側,睇了眼反芻,瞑了眼養神。不知倦怠的小羔子們,不是頂撞、跪乳,就是繞在母羊周遭跳蹦子。
隔過月余,趕足雨水的大麥田揚花孕育,果樹枝頭坐實了果子,熟知農事的香云幫他疏果。麥收畢,他耬耙過果園的雜草。雜草極其頑固,一經朝露潤澤又泛新綠。莊稼要跟雜草一樣易生易長該多好。他知曉,月余后入伏,到果樹澆水、套袋的時節香云又會來。夜影罩滿河川,一浪一浪地把河川淹進了黑。
沏碗茶,他背依房檐圪蹴到檐臺,看將滿的月亮。東起的月亮,把庵房的影子投上木墩,檐頭的影子一痕痕縮短,一痕痕朝他逼近,仰脖喝盡濃茶,他撥通了杏嬋的電話。
他問杏嬋的近況。
杏嬋說:“一天三頓都是三姑在做,晚上有三姑來照看,爸你不用操心。”
他問小閨女,問新孩。
杏嬋說:“小閨女還愛去學校,每天一大早醒來,就惦記著去學校。早上是我三姑送去,后晌是我三姑接回來,就是老愛看手機,老愛看動畫片。新孩呢,吃了凈是個睡,晚上也起不了幾回夜,十二點多喝一回奶,就一覺睡到大天明,前兩天,剛吃過糖丸,剛打過防疫針。爸,你在果園要按時吃飯,到暑假,我跟孩娃們回來幾天,你給咱抱新孩、帶小閨女,我給青果套袋子,給咱鋤草。”
他說:“果園的活絡閑散,二畝園子不用你搭手。你管好孩娃,管好自己就成。”
話到口邊,他還是冒昧地說起了香云,說香云送來了新衣襖,送來了老虎枕頭,還有繡了憨豬的小棉鞋。
他問:“你媽跟你通話了沒?”
電話那端,杏嬋不再說話。他喂喂幾聲,還是沒聽到杏嬋的回應。
星 星
電話掛斷,他吃飽了飯,肚子鼓脹、腦殼昏沉著松散地倒上炕頭。只是接連幾晚都無睡意。似睡似醒,迷瞪瞪地聽風撩撥竹葉,聽露珠從新葉上滑跌,從花蕊中滾出。新葉一扭,青果一歪,含了葉香果香的露水滴進月影,滴入闃寂。眼睛干澀得厲害,看見陽光和白粉粉的花樹,眼瞳灼刺得生痛。
隨后幾天,他到果樹下刨挖澆水的渠道。晚飯后,就著月影,他要刨挖到月夜的靜深處,他要以疲累召喚瞌睡蒞臨。這一夜,月亮升上果園,月亮鉆進一朵云,他睡著了,他做了夢。
夢在屋院的背景上鋪展,夢里的窯門上別著一盤金燦燦的葵花。夢里還有大草棚,和大草棚下的公羊。公羊的犄角長長的,走來走去,它在這只和那只母羊的尾巴下嗅聞,聞來聞去。獨獨是那臥在水桶跟前的母羊,黑蹄子的母羊。母羊額心里長了撮黑絨,它撲娑娑搖著尾巴站起。它從容又松弛地走到彎斜的竹叢下,公羊跟了過去。溫和的母羊祥和地守在那里,強悍的公羊跳一下蹶子,趴上母羊的脊背,母羊戰粟,公羊戰栗,他也戰栗。他突然聽到有個聲音在馬彥龍、馬彥龍地叫他。
他驚醒過來,睜亮眼睛靜靜聽。是青竹那邊,是公羊母羊在叫,是羊在爬羔。眼睛的干澀緩和了些,他睜亮眼睛靜聽。醒轉了的八只羊靜聽,風撩撥竹葉,竹葉一如水浪樣沙沙地響。
戰栗結束,咩叫結束,母羊跪到地上,跪到頎長的莎草上,公羊跳下母羊的脊背,它殷勤地咬噬母羊的脖頸,舔舐母羊的耳朵、臉畔、鼻頭和潮汪汪的眼睛。母親說過:“夜半聽見喚叫你的名字,你千萬別應聲。”曾在果園里疏花、疏果、澆水、施肥的女人這么說過。杏嬋這么說過,像是香云也這么說過的。“就你一人在果園,到夜靜,聽到喚你的聲音,可別回應!”
透過窗,他看到了沖他微笑的星星,燦若金針花的星星。眨眨眼,他靜靜地看它。葉子不知風要把它帶到哪里,不論落到哪里,都是注定要落到那里。月亮不知,它為何繞住地球奔跑,一經繞上去,注定再也無法偏離。
叮咚叮咚,一串清悅的鈴鐺聲,是那經年的金馬駒走在青草馥郁的坡地上。它走走停停揪食新生的槐葉兒。叮咚叮咚,鈴鐺聲比春竹還青翠。凡它揪食過的槐樹,會綻出繁碩的槐花來。
天近破曉,黎明將至。擠擁在風里的青果香來敲窗欞。風攜了結實的青果香來叩木門。
責任編輯 王子倩
創作談
像樹一樣生長
他很普通,普通如樹,在哪里發芽,就在哪里變老。他的真名叫鎖成,小說里他叫馬彥龍,文字未破壞他沉靜寂寥的性情。
妻子患大病走了,他家成了突發困難戶,幫扶干部去下戶,一連幾次院門緊鎖,以為他去打零工了。我得去看看他。一是他60多歲了,建筑工地不會要他;二是他極不愿拖累家人,即便家庭和睦。他家是河灣有果園的人家之一。
夜黑我有意照看鎖成的院場,燈火沒越過院墻。抽了空,我騎摩托車去了果園,土剛剛翻過,綿軟松散。我從地這頭走往地那頭,看到了地頭坡坎上的綿羊,看到了一簇青竹后的小庵房,放置農具和休憩用的小庵房。他在爐火上做飯。我問他,啥時候蓋起了小庵房?他說,大半年了。我問他,晚上也睡在這里?他說一個人嘛,回去弄啥!他那么靜,我不免擔心他。
晚上,我分幾次把幫扶干部帶來的米面油送給他。我坐到庵房中的爐火旁跟他聊聊天。他向我說起他妻子,還有他給妻子講述過的兩口古鐘的往事。妻子在古鐘的啼哭和回響中沒再醒來。他向我說起香云,就是兒媳的生母乃燕。她想回來,把愛帶回女兒身邊,不知女兒愿不愿意。大約兒媳愿意,不知父親允不允許!
夜來,書寫鎖成的現狀時,我不想附加現實外的因素。他們的普通本來就很大眾,本來就是民間生態的事實。只要寫出本真,又何必讓鎖成負載起作者的意愿,承擔不該有的重負。讓善終有回報,讓愛終有潤澤。讓他們像一棵曠野中的樹那樣生長,這是文字該有的樣貌。人間有暖,一伸手就能觸碰到,該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