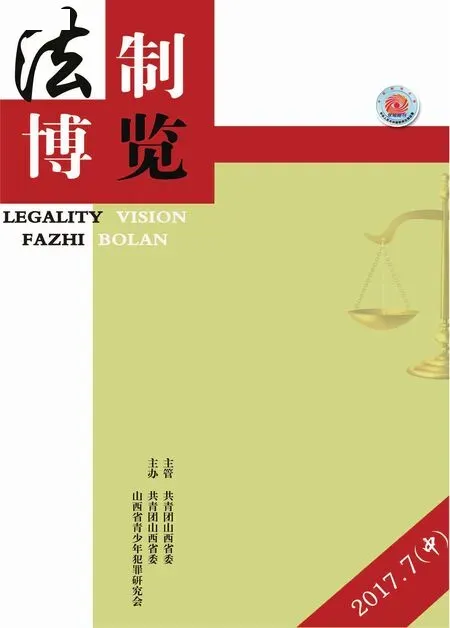淺析刑事訴訟若干證據制度
——從比較法的角度
張麗鋒
通許縣人民檢察院,河南 通許 475400
?
淺析刑事訴訟若干證據制度
——從比較法的角度
張麗鋒
通許縣人民檢察院,河南 通許 475400
證人證言作為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七種法定證據之一,在我國刑事證據體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不論是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證人證言都是應用最為廣泛、最為普遍的一種證據。基于各個國家歷史傳承社會發展經濟基礎的不同,兩大法系雖有部分相通,但是還有許多不同之處。本文以兩大法系的比較為主線,通過深入剖析兩大法系非法證據、拒絕做證權、證人宣言等制度,發現乃至于完善我國相關立法的不足之處。
美國;德國;非法證據排除;傳聞證據;拒絕作證特權;比較;借鑒
一、美德中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比較分析
(一)對非法證據認定的方式不同
1.美國對非法證據的認定方式
在美國,如果被證明口供是在被強迫的情形下取得的,那么這個證據就會被自動排除,甚至從這個違法所得的口供中得到的線索找到其他的證據,這個被稱之為“毒樹之果”的證據也要被排除。美國對非法取得口供的認定是法官就個案情況綜合考慮認定的。
2.德國對非法證據的認定方式
德國的刑事訴訟法分為兩步,第一步是用列舉的方式列舉出非法手段,第二步才是是法官認定。如果取得口供的方式被認定屬于強制手段,即使被告人同意使用也不得用作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據。德國這種列舉的方法所存在的問題是,違法取得供述的手段是不能被窮盡的,而且,像法律列舉的“欺騙”,與現實生活中警察使用的“詐術”很難區分。
(二)排除非法證據的含義和功效是不同的
在美國,排除非法證據意味著審判者,如陪審團,完全不知道這個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曾經存在過。而在德國,非法證據的排除意味著不能將其作為定案的根據。
(三)中國立法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現狀
1.理論上非法證據排除的立法缺陷
中國憲法并沒有直接規定關于反對強迫自我歸罪的權利,但是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這個法律規定表現了對強迫供述的反對態度。但還是立法的缺陷是雖然法律禁止用強迫的手段搜集但是法律沒有明確規定使這條禁止條款得以實現的具體保障。
2.實踐中由于立法缺陷造成的弊端
在實踐中,當被告人或其他辯護律師提出有刑訊逼供的證據是,法院沒有相應的程序對這種訴求進行審查,這使得有些非法取得的供述繼續作為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但是,立法也試圖彌補刑事訴訟法法的缺陷,指出;“凡經查證確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陳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這個補充的解釋完善了對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的排除規則,但是在實踐中,這個排除規則并沒有得到切實貫徹。
二、美德關于拒絕作證特權的比較分析
(一)拒絕作證特權的含義及意義
在庭審中保持沉默的權利。被告人在庭審中保持沉默的權利,它是反對強迫自我歸罪特權的結果。反對強迫自我歸罪特權也允許任何證人在作證將使其陷入受到刑事指控的風險時拒絕作證。按照美國法律,該特權僅僅保護那些被傳喚出庭作證的人,但在德國,證人也可以不回答可能使其配偶或者血親或姻親歸罪的問題。反對強迫自我歸罪的特權被家庭特權所補充。
在美國刑事訴訟中,由證人自己主張適用反對對強迫自我歸罪的特權。在德國主持庭審的法官必須告知證人享有拒絕回答問題的權利。在有些情況下,已經在庭審中出示的證據向法官表明證人可能會作出自我歸罪的回答。大多數的情況下法官在為庭審做準備而閱卷時就會知道這種問題。
(二)在婚姻和家庭關系方面的拒絕作證特權的區別
1.美國相關規定
在美國,法律認可兩種婚姻特權。配偶的拒絕作證特權允許配偶一方拒絕作證指控另一方。它排除了作證的配偶的所有不利證言。通常只有作證的配偶可以主張該特權。但是,有些州也允許作為刑事案件被告人的配偶主張該特權。第二項特權是婚姻信任特權。這一特權保護配偶之間的秘密交流。傳統上配偶的任意一方均可主張該特權。
2.德國相關規定
在德國,個人隱私受到全面更多的保護。德國的家庭成員特權不僅包括配偶,而且包括血親和姻親。例如祖父婆與外祖父母、叔叔與舅舅、姑姑與姨、堂與表兄弟姐妹、侄子與外甥和侄女與外甥女。證人可以或者拒絕任何有關婚姻或者家庭的事項進行作證。這同美國的配偶拒絕作證特權不同,美國的有些州即允許被告人也允許作證的配偶行使該特權。如德國部分所述,德國特權的理論依據是證人不應被迫在說真話與保護配偶或者親屬之間進行選擇。
如果因為證人未被適當告知拒絕作為不利于其配偶或親屬作證的特權而導致其已經作證,則該證據必須加以排除。只有證人已經作證,隨后被告知了拒絕作證特權并且同意使用其詞言作為證據時,才屬于排除的例外。
(三)在職業關系方面的拒絕作證特權的區別
更多的是從范圍上講,德國法比美國法承認更多有關職業關系的拒絕作證特權。
1.在職業范圍上美德兩國的不同處
美國刑事訴訟保護律師與其當事人之間,醫生與其患者之間以及牧師與其信徒之間的秘密交流。個別州有時還承認其他特權,例如精神治療醫師,社會工作者以及記者的特權。德國的職業特權不僅包括美國所承認的范圍,而且還擴大于藥劑師,心理醫生,有權幫助孕婦或者吸毒者的機構的咨詢人員,注冊會計師以及稅務顧問。該特權還包括這些專業人士的助手。專業人士及其助手只有在當事人已經解除其保密義務后才能出庭作證。
2.在追求法律價值方面美德兩國的相同處
德國法通過承認這么多的拒絕作證特權表明了它對隱私利益所賦予的高度。與德國的法律都從原則上要求證人親自出庭作證。但是,在某種情形下,兩國都意識到要求證人出庭作證將損害其他某種更值得保護的價值,例如夫妻之間或者醫生或患者之間的關系。在這些情形下,兩國的法律制度都選擇了不要求證人出庭作證。這種情形被稱為“拒絕作證特權”。
美國和德國的法律承認一系列拒絕作證特權。對拒絕作證特權的認可使得發現事實真相更為困難,因為相關得證據被排除出審判之外。想到發現事實真相是德國審問式訴訟的主導原則,而在美國的對抗制中對個人自由的保護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可以估計在美國發現比德國更多的拒絕特權。但是這一假設是錯誤的。與美國相比,德國在拒絕作證特權方面不但數量更多,而且執行的更嚴格。
(四)中國關于拒絕作證特權的規定
中國刑事訴訟法并沒有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有保持沉默的權利,并且在刑事訴訟法的第93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在這個規定緊跟的一句話“但是與本案無關的問題,有拒絕回答的權利。”這一表述看似保護犯罪嫌疑人的一部分隱私權,但是在現實中關鍵問題是誰來決定所提出的問題是否與本案無關。按照一般規則,應當是由犯罪嫌疑人決定所提出的問題是否屬于與本案無關的問題,但是在實踐中的情形并非如此,在一些案件的判決中,被告人不如實交待的情節被用做非法定的認罪態度不好,而加重刑罰。
三、美德關于詢問證人和證人宣誓的比較分析
(一)詢問證人
按照德國法,證人必須被賦予連貫陳述其了解得案情的機會。該陳述會被認為有助于發現事實的真相。法官可能了解他或者她通過閱卷不能了解的新事實。連貫陳述之后的詢問主要是法官和證人之間的一場非正式的對話。由于雙方當事人可以在法官詢問結束后進行補充發問,因此他們很少打斷法官的詢問。
基于閱卷所了解的情況,法官有時會得出證人提供的證言不正確或不相關的印象。而在這種情況之下,法官可能會在證人有機會全面解釋其對案情的了解之前就變得不耐煩起來,并且開始提出誘導性和刺探性的問題。這將使證人感到困惑,并且最終妨礙事實認定。在許多情況下辯護律師并不愿意反對這種過度詢問。因為辯護律師擔心法官會覺得自己受到了批評和冒犯,而且這有可能最終對定罪和量刑決定產生不利的影響。
在詢問證人被分為直接詢問和反詢問的對抗中并不存在這種問題。由于在直接訊問中一般不允許提誘導性問題,證人可以不受打擾地陳述他或者她所了解的案發情況。
但是,在美國實踐中,雙方當事人經常試圖通過嚴格地控制證據來證明自己的主張。檢察官和辯護律師傾向于從證人處得到簡要得答案。他們在反詢問時經常問一些要求證人只能回答“是”或“不是”的問題。有時候他們會試圖禁止附加任何解釋的語言。這樣的詢問,以及用來阻擾證據采納的異議,在美國的陪審團審判中經常能夠看到。它們只是美國法庭中進行的激烈對抗的另一種象征。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審問制訴訟的舉證與對抗制訴訟的舉證哪一個是認定事實的更好辦法?以前進行的心理學研究表明,對抗制的證明方法更好,因為它可能揭示更多的事實,而且可能使法官更趨于中立。但是,該研究是在實驗條件下進行的,不是以接近法庭的現實情況。重要的是,這些試驗并未考慮過美國當事人的過分對抗以及德國法官的過分審問。
(二)證人宣誓
在美國刑事訴訟中,每一個證人在作證前都必須宣誓。在大多數情況下,宣誓指的是向上帝起誓,但是如果證人愿意,他們可以作出與宗教無關的莊嚴聲明。宣誓正式提醒證人他負有某種特殊的法律義務同時也是宗教義務,按照這一義務他必須說真話。與此同時,宣誓還可以給審判增加某種莊重的因素。通常而言,只有進行了宗教宣誓或作出非宗教聲明并因此受到警告的證人才能在其說謊時以偽證罪進行處罰。
如德國部分所述,德國的證人通常不必宣誓,因為人們普遍認為宣誓并不能確保證人會說真話。但是,在德國庭審的一開始,法官會仔細地告知證人有關說真話的義務。按照德國發對證人進行的該告知與美國刑事訴訟中證人作證前所進行的宣誓有著相同的目的。二者都提醒證人不得說謊的義務。德國法與美國法所采取的不同辦法是審問制與對抗制的典型特征。在德國家長式作風的法官規勸證人說實話,而在美國,證人被要求許諾他將說“真話,完全的真話,除了真話沒有其他”。
與美國的做法相反,德國的證人可以因作出了未宣誓的虛假陳述而受到處罰。在德國證人必須宣誓的少數案件中,宣誓是在他或者她作證之后才進行。正如美國一樣,宣誓可以是宗教性質的,或者依照證人的申請,也可以是非宗教的聲明。
[1]陳光中.刑事訴訟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2]陳衛東.模范刑事訴訟法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3]陳光中.中德不起訴制度比較研究[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
[4]丘岳玲.德美證據排除規則比較-中國確立刑事證據規則之經驗借鑒[J].政法論壇,2003(3).
D
A
2095-4379-(2017)20-0108-02
張麗鋒(1969-),女,河南大學,研究生,通許縣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研究方向:訴訟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