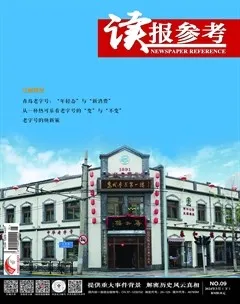中國古代所謂的“龍脈”在哪里
“古今論九州山脈,言華山為虎,泰山為龍。地理家亦僅云泰山特起東方,張左右為障,總未根究泰山之龍,于何處發脈。”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與重臣李光地就泰山龍脈的問題進行了一番討論。李光地認為泰山龍脈“大約從陜西、河南來”,康熙卻獨出心裁地提出“凡山東泰岱諸山來脈,俱從長白山來”,由此寫下《泰山龍脈自長白山來》。
康熙并未解釋什么是“龍脈”。古人缺乏定義意識,層積之下,“龍脈”成了只可意會、無法細究的詞匯。
“龍脈”源頭是“地脈”
“龍脈”說貌似悠久,但相關古籍皆偽托,中晚唐始有此論,至宋勃興。
“龍脈”出自“地脈”。據學者沈婉婷的《昆侖龍脈觀念溯源》,《史記》最早提到“地脈”:(蒙恬被秦二世賜死前)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余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司馬遷評論說,建秦直道令百姓痛苦,蒙恬“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則“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漢代王充在《論衡》中稱:“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王充認為,地養萬物,“絕地脈”即傷民生,應處死。
三人都相信“地脈”客觀存在。“地脈”是比附人體而成的觀念,視山巒為骨骼,視泥土為肌肉,視地下水為血液……人有筋脈,地亦有“地脈”。故《吳越春秋》稱:“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問之山川脈理。”
學者段志強在《經學、政治與堪輿:中國龍脈理論的形成》一文中鉤沉,中國最早地理學文獻《山海經》《禹貢》中,記錄(欠準確)了山川分布,尚無等級、尊卑之分。東漢學者馬融、王肅將《禹貢》中的大山從北至南分為三條(學者鄭玄又分南條成二列),最北為碣石,最南為衡山,即當時人們界定的華夏核心區域。
一步步走向“龍脈說”
段志強指出,唐代僧一行提出“兩戒兩河說”,是“以山川限華夷”之始。僧一行認為,“北戒”始于三危山(今甘肅省敦煌市附近)、積石山(青甘邊界祁連山支脈),沿終南山、太華山、王屋山、太行,直到濊貊、朝鮮,“所以限戎狄也”;“南戒”始于岷山、嶓冢(今甘肅省天水與禮縣之間),經商山、熊耳山、桐柏、武當山、荊山至衡山,再至閩中,“所以限蠻夷也”。
“兩戒”之間,又分“兩河”,即黃河、涇水、渭水、濟水等組成的北河;長江、漢水、淮水等組成的南河。
“兩戒”別華夷,“兩河”分華夏。
這些歸納成的“規律”不產生新知識,甚至為“合理”而扭曲事實,但通俗易懂便于記憶。“兩戒兩河說”最大的漏洞在于,唐朝首都長安竟在“北戒”外,成了“戎狄”。據段志強鉤沉,南宋唐仲友繪《唐一行山河分野圖》時,悄悄將“北戒”向北移動,以將長安收入中原。
為補僧一行的漏洞,南宋人在偽托唐人楊筠松的《撼龍經》中,將佛教的“四大部洲說”抄襲了過來,將須彌山定為天下中央,生出四條龍脈,唯“南方之龍”入中國,與長江、黃河相連。在同樣托名楊筠松的《疑龍經》中,則稱天下皆龍脈,有干龍、枝龍之別,“長作軍州短作縣,枝上節節是鄉村……凡有枝龍長百里,百里周圍作一縣”。
《撼龍經》《疑龍經》皆出自江西,是堪輿術的基礎典籍,到了明初,已是“其學盛行于今,大江以南,無不遵之”,只不過把“天下中央”從須彌山變成昆侖山。
朱熹又加了把火
堪輿術走向正統,多虧宋代的朱熹。據段志強鉤沉,朱熹喜風水學,他將客觀的地理知識“義理化”。他提出“三條說”,以鴨綠江、黃河、長江三河為根本,主張“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個風水”“河東河北皆繞太行山,堯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朱熹這么說,有反對偏安江南之意,且解釋了金國為何崛起,即“以華夷共視為中脈,蓋鴨綠江外又有大干為護”。朱熹的主張與道德理論相結合,讓地理學染上神秘色彩。
后人稱朱熹的觀點“明理”,是“探山川融結之情,引經援史,遠及方郡邑之大勢,可與識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其好處是只要懂道德原理,無需實地踏勘,即可當“地理人”。由此養成讀書人只知教條、不顧實際的陋習,貌似博學,實則“為通而通”,只會毫無意義的“通”。
朱熹的“大風水說”(實為堪輿學速成法)影響巨大,成為“意識形態”。明代朱棣遷都北京,即有碰瓷“冀都”之嫌,其實,朱熹也沒說“冀都”是北京。
“三大干龍說”
明代地理家王士性提出“三大干龍說”,即“自昔堪輿家皆云,天下山川起昆侖,分三龍入中國”,主要內容是以“天下祖山”昆侖山為始,三支山脈穿越中國,稱北干、中干和南干,即龍脈。北京在北干(最長的龍脈)上,起于昆侖山,終于天壽山(今屬昌平區)。
昆侖山上位,一是被認作天下正中;二是長江、黃河等重要水系的發源地,符合龍馭雨水的傳說。之后遂有“山之發根脈從昆侖,昆侖之脈,枝干分明”之論。
“三大干龍說”適合歷史解釋,比如,元朝興起是得北干之助;朱元璋起于鳳陽,“發自中條,王氣攸萃”;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是回歸“冀都”……可南干到橫斷山脈轉為南北向,與理想中的格局不同。此外,南干少帝王,只好解釋成:“古今王氣,中龍最先發,最盛而長,北龍次之,南龍向未發,自宋南渡始發,而久者宜其少間歇,其新發者其當坌涌何疑?”
康熙偏要講“科學”
清帝更重視宏觀的龍脈。康熙三赴泰山,行二跪六叩之禮,在《從“泰山龍脈”之爭看滿漢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一文中,學者周郢鉤沉:“康熙帝以如此隆重的禮儀親祀泰山神,這是史無先例的。”
乾隆更甚,11次至泰山,是歷代君王之最,最后一次,80歲的他三跪九叩,寫詩自道“九叩申虔謝,八旬實罕逢”。
當時的朝鮮使節不以為然,認為是“無益之費”,稱“清人之好佛,亦不讓于前明,可不懼哉”。清代北京,東岳廟香火鼎盛,朝鮮使節一邊感慨“非一兩日間可以畢覽”,一邊諷刺廟中竟供臆想的東岳大帝父母,即“殿內奉一丈夫一婦人,乃泰山神爺娘也”。
清帝重視泰山,碧霞元君雖不見于典籍,屬野神,康熙卻多次祭拜;奇怪的是,他稱碧霞元君是天妃(即媽祖)。乾隆也6次在泰山祭拜碧霞元君,以至無人再敢稱其為淫祀。
為證明泰山來自長白山,康熙派傳教士“航海測量”,《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中稱:“皇帝特遣西洋國人善解天文地理者來到鳳城,歷覽地理,圖畫山形,后轉向水上云云。”結論是,遼東半島及渤海灣諸島巖石,與山東半島相同,北京的龍脈在長白山。
龍脈本是建構而成的說法,康熙偏要拿出“科學精神”來,未免牽強。李光地等人信以為真,可能因明代遼東也屬山東布政司,長白山與泰山同省。其實,康熙的觀點的科學依據不足,但“蓋自圣祖御制《泰山龍脈論》出,而百家息啄矣”。皇權參與科學爭論,必然是既無爭論,也無科學。
(摘自《北京晚報》蔡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