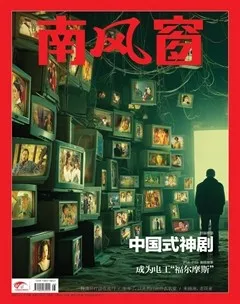哲學(xué)困境里的“士兵突擊”
姚遠(yuǎn)

首播于2006年的《士兵突擊》,至今依然是中國軍旅劇集的巔峰,地位不容動搖。
只是在我看來,將“軍旅劇集”的限定詞放置在前,對這部作品來說是一種束縛。
《士兵突擊》不該被局限于某個單一垂類題材中,它之所以動人,之所以如此廣泛且持久地抵達(dá)人心,不僅是因?yàn)橹v述了一個男孩如何成為兵王的爽文—當(dāng)然,草根逆襲的勵志情結(jié)是這部劇集扣人心弦的一部分,但僅僅是一小部分。
真正動人的,是《士兵突擊》中一群人對于“意義”的發(fā)現(xiàn)之旅。軍營只是一個舞臺,它恰好足夠封閉與純凈,可以屏蔽各種因素的干擾,讓這段故事回歸它最質(zhì)樸的樣子。
18年過去,《士兵突擊》在時間的滾滾洪流中歷久彌新。社會以驚人的速度飛馳發(fā)展,分工進(jìn)一步細(xì)化,個人被迫成為龐大機(jī)器上一顆微不足道的螺絲釘。存在主義危機(jī)下,個人價值感與意義感缺失,當(dāng)下或許是回顧《士兵突擊》的最好時機(jī)。
這部質(zhì)樸粗糲卻頗富深意的作品,是給予時代性焦慮的一針?biāo)傩ф?zhèn)靜劑。
草原五班
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流放西伯利亞,他在勞改營中發(fā)現(xiàn),世界上最殘酷的折磨,莫過于迫使人無休止地做一份沒有任何意義的工作。
制作磚塊、搬運(yùn)砂石或者壘砌一座墻體,盡管無趣又辛苦,但這些工作有用途,也有盡頭。倘若這個囚犯被迫去做的工作,是把水從一個容器倒進(jìn)另一個容器中,搗碎原本就是零碎的砂石,或者把一堆土毫無目的性地來回搬運(yùn),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道:“那么我確信,只需要幾天工夫,這名囚犯就會上吊自殺或者去犯一千種死罪。他寧死也不想忍受這種羞辱和折磨。”
當(dāng)許三多剛剛結(jié)束新兵連訓(xùn)練,被派往紅三連二排五班報到時,就面臨著這種處境。
五班,4間東倒西歪的小屋,4個千錘百煉的老兵,和一片荒無人煙的廣袤草原。去團(tuán)部5小時車程,補(bǔ)給車3天一趟,主要任務(wù)是看守輸油管道—腳下5米,深挖,全自動化操作,不用人管。
不苦也不累,五班的日子只有兩個字,“枯燥”。指導(dǎo)員拍著許三多肩膀鼓勵他,“這是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wù)”,被五班班長老馬罵道“光榮個蛋,艱巨個屁”。
這是列兵許三多從軍生涯的第一重考驗(yàn)。
其余4名老兵,早就被朔風(fēng)和時間磨去了士兵的骨頭。薛林,熱愛在草原上追趕走失的牲畜,給附近老鄉(xiāng)送回去,只圖跟五班以外的人說上話;老魏執(zhí)著于給人起外號;老馬醉心于橋牌;李夢,決心寫一部200萬字的小說,進(jìn)度始終停留在第一頁稿紙。
直到某天,混沌但平靜的生活中忽然闖進(jìn)來個許三多。他缺根筋似的保持著新兵連時的作息,出早操、練射擊,整理全宿舍的內(nèi)務(wù)。
編劇蘭曉龍擅于寫人,尤其擅于刻畫隱晦微妙的人物心理。《士兵突擊》相較于同類型題材劇集的卓越之處正在于此,它摒棄宏大敘事與英雄主義情結(jié),轉(zhuǎn)而從個人視角切入,編織士兵與士兵之間細(xì)膩的情感羈絆。
對待許三多的格格不入,蘭曉龍如此描寫其余四人的反應(yīng):他們先是極盡嘲諷、出手阻撓,而后陸續(xù)生出些許恨意—“恨”,其實(shí)是一種自我保護(hù)機(jī)制。四人恨許三多,因?yàn)樗拖褚桓蹋谒麄冏鳛檐娙说牧夹纳希囮囎魍础?/p>
再往后,恨意變成某種憐憫,一群聰明人對待一個傻子的憐憫。憐憫他忙著看不見任何意義和希望的工作,憐憫他干巴、苦澀,不懂得抓住近在咫尺的快樂。
他執(zhí)拗得近乎不真實(shí)—真實(shí)人性中的惰性與慣性,絕對不足以使人屏蔽來自伙伴的排擠與敵視并如此堅持己見,絕對不足以使任何人在顯然被拋棄的境遇中依然保有尚未死去的東西。
某種意義上,草原五班是被團(tuán)部“拋棄”的一群人。同期士兵忙著訓(xùn)練實(shí)彈射擊、駕駛裝甲戰(zhàn)車,機(jī)會在眼前,希望在前方。與此同時,五班守著荒土,等候被歲月吞噬,在黯然中擇期復(fù)員。
一群被“拋棄”的士兵,無論如何嚴(yán)格軍紀(jì)、整頓作風(fēng),誰能看見?誰會在乎?有什么意義?
五班的老兵們是這么想的,于是他們自作聰明地早早放棄,任憑自己終日沉浸在瑣碎但即時的快樂中,麻痹感官,以抵御“無意義”帶來的痛苦。任何觀眾都不會對他們苛責(zé)過多,人們深知,倘若把自己放在同等的處境中,大多數(shù)普通人都會作出與老兵們相似的選擇。
而我們在這個故事中看見了許三多的不同。他執(zhí)拗得近乎不真實(shí)—真實(shí)人性中的惰性與慣性,絕對不足以使人屏蔽來自伙伴的排擠與敵視并如此堅持己見,絕對不足以使任何人在顯然被拋棄的境遇中依然保有尚未死去的東西。
許三多個性中近乎懸浮的執(zhí)拗,塑造了《士兵突擊》整部作品精神的基底,直至今天,依然召喚著人們。
推動巨石
編劇蘭曉龍在采訪中說,他曾去軍隊(duì)基層體驗(yàn)生活,《士兵突擊》中史今、伍六一、連長、成才等角色在普通連隊(duì)中都可以找到影子,反而是主角許三多,并沒有生活中具體的原型。
許三多這個人物,“綜合了中國士兵身上很多的弱點(diǎn)甚至是缺陷”,蘭曉龍說。有些不自信,有些懦弱,與此同時,他的個性也集中了中國士兵最獨(dú)特的優(yōu)點(diǎn):踏實(shí)、吃苦、耐勞、堅韌、服從,幾近神經(jīng)質(zhì)的專注,永無止境的勁頭。
蘭曉龍把這么一份理想化中國士兵的人格樣本放進(jìn)故事,讓他與其他角色爭執(zhí)、對立,然后試圖從中得出一份答案,一份關(guān)于“活著的意義是什么”的回答。
許三多有一句基準(zhǔn)臺詞,在關(guān)鍵情節(jié)處被幾次重復(fù)。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人對他的叮囑:“要好好活。有意義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有意義的事。”
用時下流行的話來說,這是一句“廢話文學(xué)”。許三多的遲鈍只足以讓他分辨,打撲克牌和酗酒沒有意義:“我二哥就是玩牌玩得不大回家了,雖說我倒不覺得像我爸說的那樣,他變壞了。”一句話把班長老馬嘆的氣,生生噎了回去。而究竟什么是有意義的,他自己也說不清。
編劇蘭曉龍相信加繆的存在主義。由他執(zhí)筆的、于2009年播出的電視劇集《我的團(tuán)長我的團(tuán)》,其中靈魂角色團(tuán)長龍文章,“就是照著加繆《西西弗神話》的精神寫的”。而作為同一編劇時隔不久的前作《士兵突擊》,其中植有一脈相承的哲學(xué)思索。
蘭曉龍給許三多的成長設(shè)有三次重大轉(zhuǎn)折,幾乎次次都關(guān)乎個人的價值危機(jī)。進(jìn)入草原上的五班、駐守鋼七連營房、在執(zhí)行任務(wù)時親手掐死毒販,無一不在向“意義”發(fā)起質(zhì)詢。
許三多反復(fù)念叨的車轱轆話,“有意義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有意義的事”,空洞的循環(huán)論證似乎恰如加繆所相信的:“正因?yàn)樯芸赡軟]有意義,它才值得更好地活過。”
而在這本影響了編劇蘭曉龍創(chuàng)作觀念的《西西弗神話》中,加繆重寫了古希臘神話中西西弗斯觸犯眾神的傳說。諸神判罰西西弗將巖石推上山巔,巨石因?yàn)樽陨淼闹亓浚竭_(dá)山巔就會滾落。西西弗將永生永世困在這無休止的勞作中,諸神覺得,再也沒有比徒勞而沒有希望的勞動更加可怕的懲罰了。
世界被荒誕籠罩著,任何人都無法從這個世界逃離。加繆對此的解法是,反抗。人應(yīng)該在荒誕的時空中創(chuàng)造出一個獨(dú)屬于他自己的新世界,在無意義中用人類的雙手創(chuàng)造意義,義無反顧地生活下去。在反抗中,荒誕開始敗退,人性宣告勝利。
反抗,這也是許三多在草原上所做的。他決心修筑一條五米寬、可供坦克駛過的路。四處撿來石頭,砸碎,依據(jù)不同大小和顏色分門別類地擺放。深夜,老兵們跳上石堆,把它們踢得七零八落,第二天一早,許三多總會把它們撿拾回來,重新開始他的浩蕩工程。
枝枝蔓蔓
如果只能用一個詞來形容許三多,“執(zhí)拗”或許不是最恰當(dāng)?shù)摹?/p>
特種大隊(duì)隊(duì)長袁朗看中許三多的品質(zhì),邀請他參與特種兵選拔時稱贊他說:“很安心的一個兵,不焦慮,我們很多人無時無刻不在焦慮,怕沒得到,唯恐丟失。我喜歡不焦慮的人。”
劇中,這組對話發(fā)生時,許三多正在經(jīng)歷士兵生涯中第二次考驗(yàn)。依然是與“枯燥”對抗,不過,這次他只身一人。
許三多所屬的鋼七連被改編,曾經(jīng)鋼鐵般的連隊(duì)在引擎聲中煙消云散;戰(zhàn)友在軍車駛動的煙塵中,四散向整個師的各個角落。許三多被留了下來,或者說,他被忘記了。整整半年的時間,他看守房屋,打掃、維護(hù)設(shè)備,從前的偵察兵尖子,現(xiàn)在是安靜的雜務(wù)兵。
他每做好一件小事,就像救命稻草一樣抓著,后來忽然有一天,人們會發(fā)現(xiàn),他抱著的,是一棵讓人仰望的參天大樹。
“不焦慮”,是袁朗抵達(dá)空曠干凈的七連營地后,對這個雜務(wù)兵的最高評價。
與之對應(yīng),劇中最“焦慮”的兵,是成才。許三多與成才是同年的同鄉(xiāng)兵,他們在故事中經(jīng)常被視作一組精致的對照。過往的觀眾習(xí)慣評價成才“精明”“投機(jī)”,但“焦慮”二字似乎能更準(zhǔn)確地指向他行為背后的動機(jī)。
如今看來,成才的焦慮在當(dāng)下的社會中具有某種普遍性。他是一個被徹底工具理性化的人,眼睛只瞄準(zhǔn)目標(biāo)。從進(jìn)入軍營的第一刻起,他就決心在這轟轟烈烈中“出人頭地”,緊緊抓住任何一個實(shí)現(xiàn)目標(biāo)的機(jī)會,無論它使人付出怎樣的代價。
成才擔(dān)憂自己繼續(xù)留在競爭激烈的七連無法轉(zhuǎn)成士官,于是他放棄了狙擊手的夢想,甚至背叛鋼七連的誓言,成為鋼七連有史以來第一個“逃兵”,轉(zhuǎn)去其他更有機(jī)會的連隊(duì)。
他像一根電線桿,一直緊張不安、一向計算得失,把自己的枝枝蔓蔓全部砍光。然后在某一天,瞄向虛空中的準(zhǔn)心落空后,他陷進(jìn)巨大的迷失,就如特種大隊(duì)最終選拔時袁朗的質(zhì)問:“你的努力是為了什么呢?為了一個結(jié)果虛耗人生?”
因焦慮而冒進(jìn)的人,是成才;因焦慮而迷失的人們,則會變成草原五班混日子的老兵。
從特種兵選拔落選后,成才去了紅三連五班,在草原上看守輸油管道,這是許三多的來處。《士兵突擊》的故事走向終究是溫暖的,后來,成才在這片與虛無對抗的草原上,找回了自己的重心。
加繆說,世界或許是荒誕的,活著或許沒有確切的目的。但在看似無意義地推動巨石的過程中,這巨石上每一顆粒、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顆礦砂,唯有對西西弗才形成一個世界,他爬上山頂所要進(jìn)行的斗爭本身,就足以使一個人心里感到充實(shí)。
恰如許三多。他每做好一件小事,就像救命稻草一樣抓著,后來忽然有一天,人們會發(fā)現(xiàn),他抱著的,是一棵讓人仰望的參天大樹。
《士兵突擊》告訴我們,要好好活,就是像大樹一樣生長,沒有歸宿,至死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