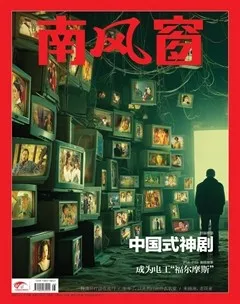“奮斗”仍是個好詞
張茜雯

在2024年,我們似乎很難想象,一部廣受年輕人追捧的電視劇會叫《奮斗》。
社會壓力讓年輕人有點“喘不上氣”的今天,人們對生活的期待變得越來越趨于現實、 近于眼前。“奮斗”這個帶著濃厚理想色彩的詞,在當下社會語境中給人的感覺,像一句漂亮的口號,帶著些許空想主義,透著點不切實際。
如今,年輕人即使還在做著“奮斗”之事,卻已經很少會表達“奮斗”之志。
而當我們回望17年前,聚焦這部以《奮斗》為題的現象級電視劇,它的朝氣活力、熱烈激情,劇中那群年輕人在自己搭建的烏托邦里喊出的青春宣言,令人酣暢,更不免讓人在今天感到悵然。
我去2007年
2007年前后,3G時代到來,中國移動互聯網發展即將迎來爆發年,電子商務、搜索引擎、社交網絡勢如破竹。土豆、優酷等視頻網站陸續成立,QQ、校內網、豆瓣、百度貼吧、天涯論壇等社交產品,侵入式地占有了人們的碎片化生活。成長在這一時期的“80后”“90后”成為主流用戶,QQ空間一時成了年輕人的精神家園,一代人正前所未有地感受時代的強勁風暴席卷而來。
《奮斗》正是乘著這場風暴誕生的。
“你得有運氣碰到一個時代,而你的夢想,也許是自然結果。”這句來自 《奮斗》主人公陸濤的“富爸爸”,房地產商徐志森的臺詞,是他對剛剛建筑學畢業的兒子設計師夢想的箴言。后來再看,更像是整部劇的預言。
《奮斗》的爆紅,像那個勢不可擋的時代一樣不由分說。開播便穩居各大衛視收視率第一,平均收視率6.3%,大結局更創下11.5%的最高收視記錄。主演們紅了,男生們學著陸濤穿POLO衫要立領,女孩們鐘情于夏琳、楊曉蕓各式各樣的吊帶、背心、熱褲和短裙。“廠房改Loft”的概念就源自這里,尚未畢業的“85后”和正值青春期的“90后”,夢想著將來也要像《奮斗》一樣,和好朋友們住在一起。
對導演趙寶剛而言,與其說是“碰上”了這樣一個時代,不如說是敏銳地嗅到了新鮮的時代氣息。他想要在這熱騰騰的新世界做點什么,首先需要轉變的,是一貫擅長的浪漫言情題材的苦情基調。
趙寶剛意識到,苦情、悲情的東西對時下人們的生活來說,是一種負擔。他想要探尋一種更“貼地”的,更能引起觀眾共鳴的影視表達,人物性格干脆、不拖泥帶水,臺詞及演繹方式更具趣味性、更幽默,能引人發笑。
他把目光投向“80后”:這代年輕人的奮斗并不是苦大仇深的,它可以是愉快的。這是趙寶剛的洞察,“長期以來,人們對奮斗這個詞印象太深了,它前邊的限定詞一般都是艱苦。但奮斗有時候也不一定是艱苦的”。編劇石康在這一點上與趙寶剛不謀而合,他認為時代不同,對奮斗的定義就不同。
滋養《奮斗》的北京土壤,與生俱來就帶有樂觀積極的文化特征。石康理解北京文化有一種趣味,那就是“事已至此”,當事人會自嘲,他們不悔恨、不仇恨、不壓抑,而是從中尋找好笑的地方,以消除內心的痛苦與不快。
因此,我們會在劇中看到每一個角色都有自己的一地雞毛,但在經歷種種之后,他們永遠有第二天一早又是新的一天的豁達,就像華子和露露喜歡的那首《水手》中唱的:“他說風雨中,那點痛算什么,擦干淚不要問為什么。”
“80后”的烏托邦
一直以來,對《奮斗》的評價都不乏批判的聲音。尤其是后來一批又一批更年輕、離劇播年代更遙遠的群體,對《奮斗》的印象基本上離不開“狗血”“毀三觀”“渣男”“作精”等關鍵詞。
《奮斗》是好劇嗎?這個問題脫離了時代背景便很難準確回答。
在人設上,主角團幾乎沒有絕對的好人。他們沖動自私、任性妄為、矛盾擰巴、不負責任,每個人都致力于把這攤渾水攪得更渾一些,甚至在道德層面,很多人或多或少都做過明顯的“惡”。
比如,陸濤、夏琳在各自都有伴侶的情況下雙雙出軌陷入熱戀,遭受背叛的其中一方是夏琳最好的朋友米萊;米萊舊情難忘,短暫出走回歸后的主要任務就是糾纏陸濤,報復夏琳,逼迫陸濤在夏琳眼皮底下與自己幽會,試圖以彼之道還施彼身;露露靠著華子實現了開店夢想,卻最終選擇了比華子更有錢、更能給她和家人可期未來的豬頭,而豬頭是華子最鐵的哥們兒;向南和楊曉蕓認識第一天就決定結婚,去領證的戶口本是偷的,辦婚禮的錢是湊的,作婚房的屋是借的,閃婚閃離又復婚,人生大事如此草率地做了一件又一件……
《奮斗》充滿了各種“不正確”,受限于時代,它的局限性也不言而喻。在那個女性自我意識尚未完全覺醒的時期,女性角色就算有自己的思考與追求,也免不了成為男性的客體。當時觀眾最喜愛的角色,是除了陸濤的愛什么都擁有,卻什么也不想要的癡情富家女米萊,而如今她是不被理解的“戀愛腦”,反而從前給人虛榮印象的露露得到了更多人的共情。
即便如此,經過不同時代價值觀的碰撞,近13萬人在豆瓣為它打出7.6分,一大批觀眾將其奉為“80后”的文化代表作,也是現實主義青春時尚劇難以超越的經典。
這代年輕人的奮斗并不是苦大仇深的,它可以是愉快的。
有人說,劇名叫《奮斗》,但這群人里到底有幾個真正在奮斗?除了華子,其他人的奮斗似乎只能稱為瞎折騰。但奮斗的維度不止對物質的追求。主人公們清楚,任何試錯都要付出代價,而不斷嘗試,不停“折騰”,找到人生所求,就是青春的意義。
劇中,即將步入社會的青年在離開象牙塔前的最后一課上高聲吶喊:“我們必須去工作,去談戀愛,去奮斗!這件事十萬火急,我們一天也不能等!”
間歇性的雞血,夾雜在持續的迷茫困頓間。忙于生計、疲于應對婚姻中各種雞毛蒜皮的向南說:“我總覺得大學一畢業,好日子就都過去了。”因考試作弊無法順利拿到畢業證,在父母的失望和自身的無能中,選擇結束生命的高強說:“現在畢業就是失業,連一個月八百的活都一堆人搶著去干。”作為陸濤的莽撞青春的旁觀者,徐志森感嘆:“很好的理想,很壞的現實。”
那時的理想還有自己的空間,歌詞寫著“想飛上天,和太陽肩并肩,世界等著我去改變”。
石康始終認為,藝術創作的真正價值是能啟發人對現實生活的把握、對未來的展望。《奮斗》做到了,那其實也是時代賦予創作者的烏托邦。
“貧”出一個時代
一部影視劇的爆紅法則無可復制,但在今天重新審視,它依然具備創作方法上的鑒賞價值。

臺詞文本的打磨、現實題材的拍攝手法、服裝道具取景地的選用……諸多細節上呈現出的創意與誠意,都為同類型作品提供了范本。
在臺詞的共鳴點上,《奮斗》瞄準了“80后”年輕一代的肆意張揚、干脆直接,一些臺詞的設置尖銳辛辣。
在與上一輩人的溝通問題上,陸濤忿忿不平:“我就不明白了,為什么他們見到歲數小的就要教訓幾句,難道大人生孩子就是為了有個下命令的機會嗎?”在兩性關系上,楊曉蕓說:“我覺得男人好色,完全就是因為他們比我們少了個子宮,根本就不用承擔任何后果。”夏琳認為:“男人永遠分不清占有和愛。”對于婚姻,楊曉蕓總結:“結婚就是麻煩,敢結婚就是不怕麻煩。”

北京話的貧嘴風趣也給了《奮斗》詼諧的基因,許多被奉為經典的名場面都來自角色之間的斗嘴。向南和楊曉蕓這對歡喜冤家,總是以爭吵表達感情,以互相傷害傳達愛意。有時是話趕話挑釁式的對答:“我這都熄火了你怎么還不下車?”“你熄火了我還沒熄火呢。”有時即使煽情也充滿滑稽與荒誕,如吵架中責備式的表白:“你就是個小偷,你就是全世界最能偷的小偷,你是一個欲壑難填的小偷,你偷了我的心。”又如離婚時氣急敗壞的挽留:“我告訴你,我就是你的初戀,我就是你的最愛,我就是你離不了的婚!”
為求生活化、真實感而在劇情上削弱的戲劇痕跡,在語言上得到了補充,人物個性直接反映在了密集的臺詞演繹之上。遇到需要表現強烈情感的橋段,還會出現大篇幅充滿文學性的臺詞,這時演員需要用極快語速說出,在隨處可見的日常布景里,以近似舞臺劇的表演方式與環境對沖,戲劇沖突從而展現得淋漓盡致。
這只是一個普通的雨后清晨,但對身處窘境的人物來說,有些看似堅固的東西已經發生了動搖。
除了在臺詞方面下功夫,趙寶剛也極擅長在小事里埋藏復雜而微妙的象征意義。
有一場戲,向南、華子因各自一連串糟心事,被迫一同在向南的小奧拓上對付了一宿。第二天醒來,向南發現自己竟然上班遲到了。他曾自信自己遇到任何情況都從不遲到,心中的秩序感就在這一刻突然崩塌了。
石康本以為這一段會被趙寶剛拍成過場戲,或者干脆直接略過,但成片效果卻讓他驚喜,他看到了文學被精準地進行了影視化表達。
“社會擠壓人,使人生面臨挫敗,不是轟轟烈烈的,而是一點一滴的。”趙寶剛讓車停在一個廣場上,車外是高樓大廈,夜里下過雨,雨滴掛在車窗上。這只是一個普通的雨后清晨,但對身處窘境的人物來說,有些看似堅固的東西已經發生了動搖。
這樣的風格也延續到了之后的《我的青春誰做主》《北京青年》,它們和《奮斗》被統稱為趙寶剛的“青春三部曲”。后續作品雖不及《奮斗》的輝煌,但仍擁有較高的關注度和話題度。
2019年的《青春斗》,是趙寶剛在這一題材上做的最后一次嘗試。他啟用流量,迎合市場,已過花甲之年的他明顯力不從心,不斷向前的時代沒有再給他迎頭趕上的機會。這部最終以低評分、低收視率慘淡收場的劇集,也成了伴隨“趙寶剛式青春”長大的幾代人青春的謝幕。
沒有人能永遠年輕,但永遠有人正值青春年華。
今天的創作者有他們的觀察視角,今天的年輕人也有自己愿意關心的生活。在17年后,或許我們還會像華子一樣發問:“到底什么才是成功?”而17年前的答案依舊有效,那便是:找到目標,為之奮斗。
“那目標就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它可以讓我們不空虛不放棄。其實那目標是什么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