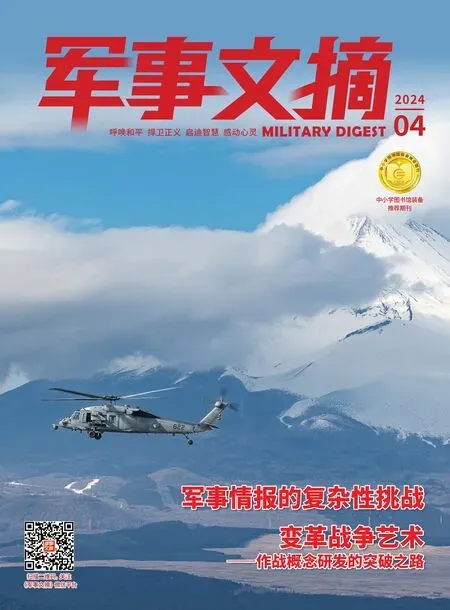基于新興作戰概念視角下的現代戰爭制勝機理探析
陳志華

戰爭制勝機理,是指戰爭的制勝規律、路徑以及方式方法。受到科技進步的推動、武器裝備的變革、戰爭目的的變化等因素的制約,現代戰爭制勝機理也隨之發生變化。習主席深刻指出:“現代戰爭確實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些變化看上去眼花繚亂,但背后是有規律可循的,根本的是戰爭的制勝機理變了。”今天,以美國為首的世界軍事強國都在加緊作戰概念設計研究。深入分析新興作戰概念內涵特點,挖掘其內在邏輯,找準現代戰爭制勝機理,對于把握世界新軍事變革機遇,打贏未來戰爭,意義重大。
以認知戰塑造認知先導優勢
認知戰聚焦意識思維層面的對抗,通過傳遞選擇性加工后的信息,影響決策判斷、改變價值觀念、爭奪人心向背,進而引導戰爭態勢向利于己而不利于敵的方向發展。認知戰是敵我雙方在認知領域展開的攻防作戰,對抗的核心是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的爭奪,重點是加強認知攻擊,同時兼顧認知防御。
主導意識形態領域是認知戰的核心。一是引導政治認知。意識形態決定了認知的理性根基。圍繞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的爭奪成為敵我認知對抗的核心,重點是塑造有利于已的政治信念、戰爭態度和價值觀念。政治認知引導旨在對政黨合法性、執政理念合理性、政治生態健康性等內容的刻畫,凝聚或破壞政治共識、堅定或動搖政治信念、拓展或瓦解政治陣營,培植對政治立場、信仰、理念等的認同或否定情感,鋪設利己、不利于敵的政治認知布局。
二是引導價值認知。戰爭認知引導旨在塑造戰爭本質、性質、法理依據等內容,引導各方對戰爭正義性、合法性的價值評判,影響助戰或反戰輿論走向,調控民眾承擔戰爭義務意愿的強弱。價值認知引導旨在圍繞價值觀念評判與取向展開激烈爭奪,通過傳播倫理道德、是非善惡、人性美丑等內容,謀求社會普遍情感認同。
迫誘認知攻心奪志是認知戰的重點。認知攻擊是認知戰的重點,圍繞攻擊內容和方法,采取有重點的進攻,對于塑造敵方錯誤認知,形成有利于我之態勢,意義重大。從內容上看,迫誘認知應重點圍繞社會群類心理開展造勢活動。通過塑造認知差異謀求不同民族、不同種族、不同地域、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之間的對立心理,積累社會各界對政權當局的不滿情緒,破壞國家內部的團結穩定,誘發社會動蕩分裂。從方法上看,應在“平時”認知迫誘的基礎上,聚焦“戰時”攻心奪志。
戰時認知攻擊的對象不僅包括參戰力量,還包括戰爭支持力量。針對參戰力量,應靶向瞄準敵各級指揮員,通過認知操控、信息欺騙、利誘勸降等方式,削弱其抵抗意志,干擾其指揮決策,達成瓦解敵軍目的;針對戰爭支持力量,應廣泛運用電臺、廣播、新媒體等媒介,宣傳重大戰果、敵方潰敗逃散、慘烈戰場畫面等內容,誘發民眾恐慌厭戰情緒,削弱敵戰爭潛力。

戰爭認知引導旨在塑造戰爭本質、性質、法理依據等
筑牢防線凝心控局是認知戰的根基。認知戰的重點是攻,而基礎是守。在加強對敵方認知攻擊的同時,還應重點做好認知防御。認知防御的重點是筑牢防線、穩控大局。針對參戰力量,應注重發揮政治工作優勢,廣泛開展政治動員,激發官兵英勇無畏、奮勇殺敵的精神傳承和保家衛國、舍身忘死的意志品質,積極開展立功受獎樹立典型榜樣,鼓舞軍心士氣;針對社會支撐力量,應廣泛宣傳戰爭正義性、合法性,不斷強化愛國主義教育,激發全民責任意識和憂患意識,凝心聚魂。
此外,還應采取積極有效的行動,最大限度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國際社會的支持,雖然主要依靠政治、外交活動爭取,但積極開展人道主義救援,廣泛傳播己方立場態度與價值理念,往往能夠推動國際社會態度的轉變,為爭取最廣泛的國際社會支持創造有利條件。
以混合戰確立戰略主動優勢
混合戰爭是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外交、科技、文化、軍事等多樣化手段,將網絡戰、輿論戰、經濟戰、科技戰以及隱蔽的常規軍事行動結合起來,攪局亂局,破壞對手戰爭潛力,以最終達成戰略目的的戰爭。在強弱對抗競爭中,有效運用混合戰爭,不僅可以塑造有利戰略態勢,對沖大國戰略競爭,而且能夠達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絕佳效果,確立戰略主動優勢。
以強勝弱,不戰屈人之兵。戰爭,是國家或者政治集團之間為了達成一定的政治目的,使用武裝力量進行的大規模激烈交戰的軍事斗爭。這種傳統戰爭樣式以軍事硬實力比拼作為主要斗爭手段,雖然能夠快捷直觀地達成戰略目的,但極有可能出現“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被動局面,且容易招致國際輿論譴責和全面制裁。特別是在強弱對抗競爭中,強者一方本就占據絕對優勢,這不僅體現在軍事領域,而且體現在政治、經濟、外交、科技、文化等諸多領域。因此,以軍事實力為支撐的非常規混合戰爭展現出愈發靈活多樣的運用可能性。善用混合戰爭,就是在掌握我之優勢、敵之劣勢的基礎上,優先選用政治、外交、經濟、輿論等能夠揚長避短的非軍事手段,以已之長攻敵之短,追求“少戰”或“不戰”而屈人之兵。

混合戰爭是多樣化手段的綜合運用
以強對強,對沖大國競爭。當今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時期,大國關系進入全方位角力新階段,有的軍事強國為維護其單級霸權地位,加緊拉攏分化,蓄意挑起爭端,并不斷運用混合戰爭手段遏制打壓競爭對手,加劇大國競爭緊張局勢。在強與強的力量對抗中,要想不落下風,就必須拿起混合戰爭這個利器,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要積極確立混合戰爭思維理念,摸清搞透敵混合戰爭特點規律,在對比掌握敵我底數優長的基礎上,靈活運用混合戰爭策略,以我之優勢對敵之劣勢,在確保對等反制的基礎上,妥善加強戰略防范與應對,以此改變被動不利局面,謀求戰略均勢,爭取戰略勝勢。
以弱勝強,塑造有利態勢。強勝弱敗是基本法則。弱勢一方要想占據主動或是扭轉頹勢,斷然不能以弱碰硬、以卵擊石,積極采取混合戰爭策略不失為一種絕佳選擇。尤其是在全球一體化進程加速演進背景下,各國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等諸多領域間的往來愈發密切,這也為混合戰爭運用提供了重要現實支撐。弱勢一方雖然總體實力處于劣勢地位,但可憑借某些領域的優長,堅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以靈活主動的斗爭策略謀篇布局,困敵、擾敵,使敵無法發揮全部優勢,以此改變強弱力量對比態勢,努力爭取戰略均勢,或是為國家安全發展爭取戰略機遇窗口期,創造有利條件。
以聯合全域戰贏得體系優勢
自2016 年美陸軍提出多域戰(MDB)以來,美軍先后提出多個聯合作戰概念,從多域作戰(MDO),到全域作戰(ADO),再到聯合全域作戰(JADO),美軍作戰概念如雨后春筍般相繼涌現。聯合全域作戰概念的本質是多軍種深度聯合作戰,目的是實現陸、海、空、天、網、電等全領域的多域協同與跨域融合,以體系優勢制勝現代戰爭。
跨域協同是聯合全域戰的制勝基石。與傳統聯合作戰追求各軍種之間的聯合不同,聯合全域作戰追求的是各作戰域之間的聯合,通過多域聯合、跨域協同,謀求整體對敵優勢,實現體系制勝。主要表現為以下兩點:一方面是非對稱制衡。強調非對稱作戰,避免與實力相當的對手在傳統作戰領域展開“針尖對麥芒”的以硬碰硬,強調揚長避短,發揮網絡、電磁和太空等關鍵領域優勢,善用人工智能、生物安全等新型領域優勢,以關鍵要害領域優勢,支撐聯合作戰獲得勝利。另一方面是體系制衡。實現跨域協同作戰的關鍵是通過聯合全域指揮控制將太空、網絡、電磁領域與傳統陸海空戰場進行深度融合,確保聯合任務部隊在陸、海、空、天、網、電六大作戰域內高效運用各種作戰能力,以“能力集成”取代“能力疊加”,瞄準敵方短板弱項,體系融合發力,產生優于各部分總和的整體效果。
優先決策是聯合全域戰的克敵法寶。聯合全域作戰克敵的關鍵是確保己方決策優勢,優先決策。首先是贏得信息優勢。聯合全域指揮控制能夠融合來自各域的情報信息,通過關聯分析、融合集成形成全面詳實的戰場態勢圖,支撐指揮員全面態勢感知,實現信息優勢。

聯合全域指揮控制(JADC2)是聯合全域作戰概念的重要支撐
其次是確立決策優勢。指揮員基于全面詳實的戰場態勢信息,在智能化輔助決策支持下,科學快速定下決心,形成方案計劃,并優先落實高效行動。不同于“通過加快OODA循環以達成作戰優勢”的傳統OODA理論,聯合全域指揮控制致力于建立更為高效的“DA循環”,即通過在決策(D環節)和行動(A環節)之間建立自適應的反饋過程,依據決策確定行動,反過來根據行動結果反饋及時調整決策,并不斷加速這一循環,確保在提高自身決策效率的同時,使敵陷入“決策困境”,達到擾敵、制敵目的,以此確立決策優勢。
最后,先進智能算法的運用強化了這一優勢。數據處理算法讓態勢感知和情報分析更有洞察力,智能博弈算法讓作戰籌劃和輔助決策更有創造力,自主控制算法讓兵力編組和任務實施更有執行力。可以說,先進智能算法深度融入觀察、判斷、決策、打擊和評估殺傷鏈的各個環節,使得聯合全域作戰決策優勢進一步凸顯。
敏捷指控是聯合全域戰的重要支撐。聯合全域指揮控制是聯合全域作戰實現敏捷高效指揮控制的重要支撐。傳統的指控手段難以實現戰場感知數據的跨域集成,難以滿足跨軍種一體化指揮控制要求,也難以應對未來作戰的復雜性和時效性。而聯合全域指揮控制旨在將所有傳感器與射手實時地連接起來,確保在陸、海、空、天、電、網各作戰域內,各軍種內部、各軍種間以及盟友之間,實現無縫通信,協調一致開展軍事行動,努力構建支撐無人化智能化作戰的“網絡之網絡”。
一方面,實現跨域一體化指揮控制。聯合全域指揮控制聚焦實現跨軍種的端到端信息轉換與通信,從線性、靜態、煙囪式的殺傷鏈向全域互聯的殺傷網演進,各軍種能夠靈活調用非自身建制的傳感器和打擊平臺,極大豐富了單一軍種的偵察手段和打擊選項,在降低目標選取失誤的同時,顯著加快OODA環。
另一方面,比對手更快完成決策和行動。聯合全域指揮控制通過全域多維情報收集、高效自主態勢融合,極大提升OODA鏈路中的感知和判斷能力。同時,采用多路徑同步傳輸的網狀通信結構取代傳統高度集中的通信節點,優化信息分發共享,加快有效信息流轉速率,先敵決策,先敵行動,實現以快制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