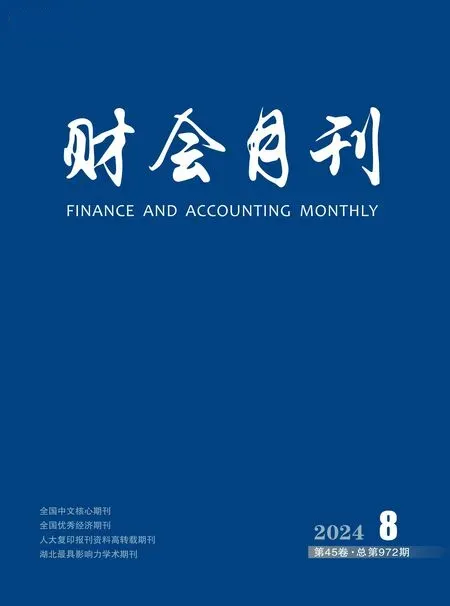信息披露會加劇ESG評級分歧嗎
朱富顯,徐曉莉(博士生導師),李雙圓
一、引言
2006 年聯合國支持的負責任投資原則一經推出,迅速吸引了全球各大機構投資者做出將ESG(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信息納入投資決策的承諾。同時,在政策的指引下,投資者認知逐漸發生變化,ESG信息作為可以進行比較的非財務信息,在政府的支持下迅速擴散。2006 ~2018 年交易所、證券業協會等自律組織以及中國證監會相關部門先后發布《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引》《環境信息披露指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逐步提升對企業ESG 相關信息的披露要求。此后,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披露ESG相關信息(Eccles等,2019)。
隨著企業ESG 信息披露的增多,各個ESG 評級機構在詮釋和使用ESG 信息方面存在較大分歧。首先,由于缺乏ESG 指標的標準定義,各評級機構制定了自己的ESG 計量方法和指標體系,以最佳地捕捉其偏好的重要性指標。由于各個評級機構所采用的衡量標準和權重不同,對同一公司ESG 表現的評估可能會有所不同,久而久之衍生成一個由ESG 指標、數據來源和評級組成的復雜生態系統,這就需要正確的語境來解釋才能成功地將其用于分析和投資決策(Chatterji 等,2016)。投資者尤其是個人投資者由于缺乏高度的信息集合和專業的信息解讀經驗,面對評級的差異,很難用正確的語境做出科學的決策,進而導致資本錯配,阻礙企業高質量發展。因此,探尋ESG評級產生分歧的原因顯得尤為重要。
本文的主要貢獻有:第一,驗證了ESG 評級存在分歧的特征事實。第二,已有文獻更多的是研究企業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經濟后果以及ESG 評級與企業信息披露之間的關系,很少有文獻從ESG 評級分歧角度出發探究信息披露與企業ESG評級分歧之間的關系。本文將企業信息披露和ESG 評級機構納入同一框架進行分析,從信息披露視角探究了ESG 評級分歧產生的深層次原因。第三,分別從高管特定經歷、ESG 得分、ESG 環境敏感性、是否被問詢視角出發,深入分析了信息披露程度對ESG 評級分歧的作用程度,為理解ESG 評級分歧如何產生和縮小ESG評級分歧提供了實證經驗。
二、文獻綜述
(一)ESG評級分歧的相關研究
隨著可持續投資的快速增長和ESG數據市場的迅猛發展,ESG評級分歧問題也日益凸顯。
一部分學者聚焦于ESG 評級分歧出現原因的研究。首先,國際上缺乏管理ESG 信息披露的標準,且ESG 評級程序不受監管,評級方法具有專有性和不透明性,比較不同公司的ESG 數據并非易事,從而導致數據提供者之間存在重大分歧(Mackintosh,2018)。其次,ESG 評級機構是為金融機構提供針對上市公司ESG 評級、數據及研究咨詢服務的營利性團體,在既定的ESG 評級市場中,后加入的評級機構往往會建立一套與市場已有評級標準相異的準則,并發布區別于已有的評級結果,從而吸引更多的金融機構依據自己的評級結果指導投資決策,由此在既定的市場份額中獲取更多利潤,這也就導致了ESG評級結果的多元化。最后,除了評級標準不統一和評級機構自身逐利因素,ESG 評級分歧還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比如Berg 等(2022)將ESG 評級分歧分解為范圍、測量和重量三個維度,并分別計算這三個維度對ESG 評級分歧的貢獻度,他們認為評級者對公司的整體看法影響了特定類別的測量,即評級機構存在評級者效應,并建議投資者更加關注ESG評級背后數據的客觀真實性而不是ESG 評級結果。Christensen 等(2021)研究發現,被評級單位ESG 信息披露與ESG 評級分歧正相關,即披露的ESG信息越多,ESG評級分歧就會越大,并且相較于輸入型ESG指標,結果型ESG指標存在更大的分歧。
另一部分學者聚焦于ESG 評級分歧經濟后果的研究,主要從兩個視角展開討論。其一,基于投資者的視角。Dimson等(2020)認為ESG評級可以幫助投資者選擇具有卓越財務前景的企業,投資者可以按照ESG 投資指數篩選企業并進行投資組合,但較大的ESG 評級分歧降低了ESG 評級的可信度,使得單獨使用ESG 評級作為決策標準不太可能對投資組合的高回報做出重大貢獻。其二,基于企業的視角。Avramov等(2022)利用六家評級機構的數據證實了ESG 評級分歧現象的存在,發現因ESG評級分歧的存在,投資者面臨的可持續投資風險更高,從而降低了投資參與度,損害了企業的經濟福利;Christensen等(2021)發現,ESG評級分歧越大的公司面臨的外部融資約束也越大,只能更多地依賴于內部融資。
(二)信息披露的相關研究
信息披露是連接股票市場資金供給方和需求方的重要紐帶,而第三方評級機構作為資本市場重要的信息中介,其評價結果大部分以企業披露的數據為依據。企業增加信息披露不僅可以緩解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還可以向市場傳遞出積極的信號,使潛在投資者更愿意投資于公司,從而提高股票流動性,降低融資成本。在資本市場發展初期,只有少量企業自愿或被強制披露會計信息;隨著我國資本市場法律法規的逐步完善以及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日益興起,投資者和市場監管部門逐漸要求企業披露更多非財務數據,輔助投資者做出決策,提升資本市場配置效率。因此,學者們的研究視角也逐漸從會計信息披露轉移到內部控制信息披露(楊玉鳳等,2010)、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宋獻中等,2017)、環境信息披露(畢茜等,2012)、碳信息披露(孫曉華等,2023)和ESG信息披露(武龍等,2023)中來。
關于信息披露,大致可以分為信息披露意愿的來源性研究和經濟后果性研究兩類。關于信息披露意愿的來源性研究,羅煒和朱春艷(2010)發現,當企業代理成本較高時,管理者更有可能出于自利性考慮,做出有損公司利益的決策,此時會向外界披露較少的信息或者刻意隱藏壞信息。關于信息披露經濟后果的研究,張純和呂偉(2009)指出,對于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公司來說,其融資較為便利,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較低,并且由于信息中介的存在,企業在進行披露后,非效率投資和過度投資行為得到抑制。
此外,還有學者從企業創新機理與治理效應角度研究了企業信息披露的傳導效應。在政府部門和資本市場的雙重監管之下,企業高質量的信息披露能夠提升管理者薪酬的敏感性,緩解信息不對稱和委托代理問題,對創新產出發揮治理作用,迫使企業從被動治理轉向主動防治的綠色轉型戰略(王曉祺和寧金輝,2020)。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首先,基于信息不對稱理論,評級機構很難掌握上市公司的所有信息,即使能夠完全掌握公司所有信息,由于利益勾稽,評級機構也善于對所披露的信息進行主動或是被動的修飾。通常情況下,較高程度的信息披露能夠緩解信息不對稱,縮小對某一現象的評級分歧。但是在現實情況下,由于環境、社會和治理評級指標的選取及賦權存在主觀性,企業信息披露得越多,ESG評級分歧就越大。其次,從社會學角度來看,ESG 作為一個新興領域,評級規則和規范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企業信息披露增加了評級機構對信息做出不同解釋的機會(Lamont,2012),這進一步加劇了ESG 評級分歧現象。具體來說,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程度越高,ESG 評級機構所獲得的信息就越多,對于同一維度,選取的子維度差異就越大,如公司治理(G)的二級指標商業道德的量化,對于信息披露較多的公司,某一評級機構可能會選取該企業的舉報制度作為商業道德的子指標,而另一家機構可能會選取法律訴訟數來衡量商業道德,但是對于僅披露了法律訴訟而未披露舉報制度的公司來說,ESG 評級機構就只能選取該指標作為衡量商業道德的標準,由此造成該維度評級結果相近。這就意味著,企業對外披露的信息越多,評級機構對于各個指標的評價就會有更多的選擇余地,ESG評級分歧就會越大。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信息披露程度與ESG評級分歧正相關。
四、變量選擇與模型設計
(一)變量選擇
1.ESG 評級分歧(Dis_esg)。為測算ESG 評級分歧,本文選擇Wind、富時羅素、華證三個評級機構作為數據來源。考慮到富時羅素評分區間為0 ~3,華證采用的是百分制,Wind評分區間為0 ~10,三個機構評分維度不一致,首先對各個評級機構評級企業得分按年份做標準化處理,使其評級機構之間的評分標準具有可比性。其次,參考Avramov等(2022)、方先明和胡丁(2023)的做法,對于每個企業,分別計算兩兩機構評級分歧(三個評級機構形成兩個評級差異)。最后,計算這兩個差異的標準差,即為該企業該年度的ESG 評級分歧(Dis_esg)。具體而言,令Zj,t,A和Zj,t,B分別表示評級機構A和B在第t年對企業j 的ESG 評分。兩兩機構評級分歧的計算公式為。鑒于數據的可得性,在對環境、社會、治理三個子維度分歧進行計算時,本文選取Wind、華證和富時羅素的評級數據,分別按照上述方法進行測算,得出三個子維度的分歧(dis_e/dis_s/dis_g)。
2.信息披露程度(czpl)。公司信息披露程度是指外界人士對公司信息的獲取程度,可以從公司的會計報告體系、私人信息獲取活動和信息擴散過程三個方面對信息披露程度進行測量(吳聯生等,2010)。自2001年起,深圳證券交易所會對上一年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進行考核,并將其劃分為A、B、C、D 四個等級作為考核結果,同時進行對外披露。深圳證券交易所對其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評級兼具獨立性和權威性,因此其對信息披露做出的評價結果也具有外部獨立性和公正性。通過手工收集得到2018 ~2022 年各個上市公司的披露指數,并將其劃分為1 ~4分,以此衡量信息披露程度(czpl)。分值越高表示其有效信息越多,即信息披露程度越高。
3.控制變量。除此之外,本文選取股權集中度(cztoptenholder)、企業年齡(age)、資產負債率(zcfzl)、企業價值(tobinq)、企業規模(gdzcje)作為控制變量。
變量定義見表1,描述性統計見表2。

表1 變量定義

表2 描述性統計
(二)樣本選擇與模型設定
本文以2018 ~2022 年滬深A 股上市公司為樣本數據,數據來源分為兩類:其一,關于企業基本信息、財務指標的數據均來自國泰安數據庫;其二,關于涉及的評級機構ESG 評級數據來自各個機構官網。在此基礎上,對數據進行以下預處理:①剔除金融行業樣本;②剔除ST/*ST 類樣本;③在5%的水平上進行縮尾處理。數據處理主要用SPSS 和STATA 軟件來實現。采用控制穩健標準誤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模型設計如下:
其中,Disit代表ESG 評級分歧和各個維度的分歧,czplit、cztoptenholderit、ageit、zcfzlit、tobinqit、gdzcjeit表 示控制變量,γi、λt分別表示年份和個體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五、實證分析
(一)ESG評級分歧是否存在
本文在對ESG 評分做相關研究時發現,大部分企業的評分存在較大差異。就深圳能源來說,富時羅素在2022年給出的評分是滿分3分,在評級企業中排名第一,而同年華證給出的評分是69.69分(百分制),在4974家參與評級的企業中排名第4246位,Wind給出的評分是6.01分(十分制),在4811 家參與評級的企業中排名第2437位。這種評級存在差異的企業不乏少數,為進一步驗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這種現象,選取Wind、富時羅素和華證三家權威的評級機構,在進行殘缺值剔除后留下2018~2022年17458家參與評選的企業進行標準化處理,使得樣本具有橫向可比性。然后,分別選取10%、25%、50%、75%、90%分位數進行描述性統計,如表3 所示。結果顯示三家評級機構存在較大差異,如在50%分位數段,富時羅素評分在0.522,華證為0.627,而Wind 為0.461,三家評級機構存在較大的評分差異。

表3 分位數統計
為進一步從統計學角度驗證企業ESG評級是否存在分歧,本文又進行了Friedman檢驗,結果顯示,三家評級機構的平均秩分別為2.01、2.36、1.63,存在差異,且2-sided 檢驗p 值為0.000,拒絕Friedman 檢驗的原假設,進一步驗證了ESG評級差異現象確實存在。
(二)基準回歸
表4 報告了基準回歸的結果(限于篇幅,僅報告主要變量的回歸結果,下同)。其中,第(1)列中信息披露程度與ESG 評級分歧呈現出正相關關系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企業在提高信息披露程度之后會加劇ESG 評級分歧。在第(2)~(4)的分項回歸結果中,信息披露程度和環境(E)、社會(S)和治理(G)評級分歧均在1%的水平上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說明企業信息披露的增加不僅會加劇ESG 評級分歧,還會增加各個分指標評級的分歧。因此,企業信息披露會通過增加評級機構自主選擇的可能性而引起更大的ESG評級分歧,假設1得以初步驗證。

表4 基準回歸
(三)穩健性檢驗
1.高階固定效應。考慮到ESG 評級存在行業差別,比如重化工類企業可能由于自身行業特性,即使非常重視綠色可持續理念,也依舊是重污染企業,反觀新能源企業,即使不把環保理念引入日常生產經營,ESG評級機構也仍給出較高的評分。兩者的行業特性造成了ESG評級結果的差異,進而會造成ESG 評級分歧,為了控制因為行業固有特征帶來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在行業聚類層面進行高階固定效應回歸,系數的符號和顯著性依然不變。
2.剔除樣本。為遏制財務舞弊,中國證監會每年都會對一些信息披露存在重大舞弊行為的企業進行行政處罰,以此肅清證券市場。為了更好地檢驗企業ESG 評級分歧的來源是否真的是由于企業披露信息造成的,本文剔除2018 ~2022 年受到中國證監會行政處罰的企業,以保證樣本企業所披露信息的真實性,降低由于樣本企業披露信息失真導致的評級機構ESG評級偏差。檢驗結果保持穩健。
3.更換變量。將評級機構擴增為四家(Wind、富時羅素、華證、彭博),并且借鑒Avramov等(2022)的做法,對四家ESG評級機構當年共同評價的企業按照年份進行排名,然后算出兩兩機構的排名差,最后求得排名的標準差,以此作為新的ESG 評級分歧指標,再與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結果依舊穩健。
4.內生性處理。傳統的擬合回歸會由于選擇性偏差和混合性偏差而出現估計結果存在偏誤的情況,為了解決信息披露程度和ESG評級分歧之間的實際因果關系判斷問題,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進行“反事實”估計,得到了一致的結果。具體的實證思路為:在前文計算出ESG 評級分歧的基礎上,對整個樣本得分進行由低到高的排序,將前20%的低分歧樣本視作不存在ESG 評級分歧,取值為0,其余樣本視作存在ESG 評級分歧,取值為1,在構造虛擬變量的基礎上,比較存在分歧和無分歧的相對差異性,得到信息披露程度對ESG評級分歧的凈效應。
六、異質性分析
(一)ESG得分異質性
基于合法性理論,企業ESG 行為受到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外部壓力影響。為了獲得、維持和恢復環境合法性地位,滿足外部利益相關者的訴求,低ESG 評分的企業更傾向于通過加強信息披露來提升ESG水平。但是相較于高ESG 評分的企業,低ESG 評分的企業缺乏相應的能力去提升輸出信息的有用性并更好地向外推送信息(謝紅軍和呂雪,2022)。因此,低ESG 評分企業的信息披露會加劇信息不對稱現象,加大ESG評級分歧。
ESG 評級分歧是基于ESG 評分算出來的,但ESG 評級分歧抹去了原有ESG 評分高低的絕對差異,僅保留相對差異。那么,對于ESG 評分普遍較高的企業和ESG 評分普遍較低的企業,信息披露數量的多少對ESG 評級分歧的正向關系是否存在差異?為了探究這一問題,在每年各個機構對樣本公司標準化后的評分的基礎上,計算出三個評級機構的平均值作為ESG 的平均得分,以得分50%為分位數分組進行異質性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ESG得分異質性分析
從分析結果來看,對于ESG 得分較低的企業,其信息披露程度對ESG 評級分歧的影響在1%的水平上顯著,而對于高ESG 得分企業,兩者的正相關關系有所減弱。從分項指標來看,得分較低的企業,其信息披露程度對ESG 評級分歧的影響反而弱于高ESG 得分企業。其原因可能在于,對于體量較大而又符合ESG 評級理念的科技型環保企業,ESG 評級機構往往傾向于給予其較高的評分,又或是對一些相對傳統的夕陽產業,ESG評級機構普遍會給出較低的評分,這兩種極端的樣本共有的特征是ESG 評級分歧較小,會使回歸結果失真。為了緩解這部分樣本帶來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剔除前后10%分位數的樣本,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剔除極端值后的ESG得分異質性分析
在剔除了評分較高和較低的企業之后,信息披露程度和ESG 評級分歧之間至少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分維度來看,環境維度系數的顯著性在低ESG 得分組中要高于ESG高得分組,符合預期,但是對于社會維度和治理維度,還是低ESG 得分組系數的顯著性低于高ESG 得分組。其原因可能是:在低ESG得分組中,企業披露的整體標準可能與ESG 評級理念不太契合,即使信息披露程度提升,ESG評級機構也都普遍傾向于給出較低的評分,此時ESG 評級分歧也就不會因為披露信息的多少而有所改變;對于高ESG 得分組,企業可能一開始就對ESG 評級理念較為重視,且善于運用各種手段去修飾披露的信息,而作為專業能力參差不齊的評級機構,對于信息的甄別能力具有一定的差異,對于專業能力強的機構來說,其很容易發現哪些指標存在修飾的嫌疑,出于客觀公正性和結果真實科學性,這些機構就會傾向于選取更真實的、未經修飾的指標進行替換,由此造成評級機構間更大的ESG評級分歧。
(二)ESG環境敏感性異質性分析
盡管企業可以自己決定是否披露環境、社會和治理方面的信息,但是不同特征的行業可能對ESG 評級分歧的敏感性存在較大差異。一方面,部分學者研究發現,相比于ESG 環境低敏感性(簡稱“低敏感性”)行業,ESG 環境高敏感性(簡稱“高敏感性”)行業的ESG評級分歧更大且披露動機更強。另一方面,高敏感性企業面臨著更大的公共監管與社會監督壓力,這會促使企業根據經營目標和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感知制定相應的ESG 策略,同時影響主要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態度與看法。因此,考慮到企業參與信息披露是出于合法性與制度動機的雙重動力,將企業分為高敏感性企業與低敏感性企業,引入異眾比率(Vm0)來衡量企業對ESG 環境的敏感程度(Waal 和Thijssems,2019),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N 表示參與ESG 評級的某個行業的所有企業數;fm0被稱為眾數組個數,表示該行業中落在某評級的企業最多的個數。當異眾比率較高時,說明該行業的所有公司ESG 評級分布較為分散,對于不同的ESG 子指標表現出較大的區別,這類行業即為高敏感性行業;反之,當異眾比率較低時,說明該行業的公司ESG 評級結果比較集中,該行業的各個公司對于相同的指標表現相似,評級得分較接近,因此認為該行業對ESG評級不敏感,這類行業即為低敏感性行業。據此得出的分類結果為:采礦業,制造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金融業,房地產業屬于高敏感性行業;其他行業屬于低敏感性行業。分組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

表7 環境敏感性異質性分析
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出,信息披露程度對ESG 評級分歧的影響會因企業所處行業的ESG環境敏感性而產生差異。對于高敏感性行業,信息披露程度對ESG 評級分歧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對于低敏感性行業,信息披露程度對ESG 評級分歧不存在顯著影響。其原因可能在于,對于低敏感性行業來說,如餐飲業、批發零售業、租賃業等,ESG理念對其滲透較淺,企業自身的經營發展與ESG倡導的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理念交集較少,缺乏相應的量化指標,企業所披露的信息中可供ESG 評級機構選擇的較少,因此低敏感性行業企業的信息披露對于ESG評級分歧的影響并不顯著。分維度來看,相比于環境維度,治理和社會維度系數的顯著性不存在差異,原因可能是人們對社會和治理的認識要多于環境維度,對社會和治理維度的認識也更全面和統一。因此,不論是高敏感性行業還是低敏感性行業,對于社會和治理指標的影響差異要更低,且都存在顯著性。
(三)問詢制度異質性分析
問詢制度是我國資本市場監管體制的重大變革,問詢監管壓力被視為一種會計信息風險信號,會影響外部審計機構和分析師的樂觀預測。當企業被問詢后,年報問詢議題也可能會對ESG評級機構的關鍵評級指標產生影響。問詢制度作為一種信息披露的監督機制,能夠通過對信息披露和異常交易進行問詢,促進外部審計機構、評級機構等第三方機構和管理層的溝通,加速信息的傳遞,進而使得外部第三方機構更多地了解企業,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因此,有必要就企業信息披露對ESG評級分歧的影響是否受到問詢制度的影響進行探究。選取是否被問詢作為分組依據,分組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

表8 問詢制度異質性分析
以上回歸結果也符合預期,即:對于沒有被問詢的企業,信息披露程度與ESG 評級分歧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對于被問詢的企業,信息披露程度與ESG 評級分歧之間的關系不顯著。其原因可能在于,被問詢的內容一般都是可能存在虛假舞弊或是容易被修飾的信息,當企業被問詢后,必須就問詢的內容做出答復,相關審計機構和第三方機構要出具審查意見并對外披露,這極大地降低了企業與外部利益相關者的信息不對稱程度,有效緩解了企業管理者的合謀與盈余管理行為,使得ESG評級機構得到的信息是具有共性且準確的,因此信息披露程度對ESG評級分歧的影響在被問詢企業中不顯著。
七、信息披露、高管特定經歷與ESG 評級分歧
信息披露對ESG評級分歧的影響可能會因為高管的不同經歷而產生差異。首先,根據委托代理理論,管理者在自愿信息披露方面具有很大的獨立性,其有能力通過干預自愿信息披露的內容來解決ESG評級分歧帶來的問題,以此作為一項任期政績以滿足個人的晉升考核需求。其次,行為學認為當下個體行為與之前的經歷有關,高階梯隊理論認為團隊領導行為具有較強的個性化色彩,高管的管理風格和治理模式都會對企業經營產生影響,因此不少文獻都從高管經歷角度去探究企業的某些特定行為。受此啟發,本文認為高管的特定經歷可能會影響公司信息披露與ESG 評級分歧之間的關系,原因在于:管理者過往特定經歷的存在,使管理者具備了對相關信息的甄別和篩選能力,管理者就會有選擇性地披露相關信息,來契合ESG評級標準,減少分歧。
基于此,借鑒已有的研究思路,手工查找CEO 以前是否受到過綠色相關教育的經歷或者從事綠色相關的工作來量化高管環境維度的經歷,若有過這種經歷,在當年及在任年度取1,否則取0,原因在于高管不僅對該維度的評級標準更加了解,而且對環境治理的信息披露更有選擇性和針對性,外部評級機構利用公開信息進行該維度評級的分歧就會減小(原因同下)。在社會維度,收集企業是否進行過社會捐贈,如果進行過社會捐贈,則捐贈當年取1,反之取0(李敬強和劉鳳軍,2010),理由是管理者作為企業的決策者,社會捐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管理者意志的體現,企業進行社會捐贈,能夠從側面彰顯出管理者的社會責任和社會擔當。在治理維度,手工收集CEO 是否從事過財務職位,若有高管有過這種經歷,在當年及在任年度取1,否則取0。然后,將三者交乘篩選出CEO既接受過綠色相關教育,又有社會責任意識,同時擔任過財務職位的企業,對其取1,否則取0,以此作為高管特定經歷(ceoexp)的代理變量。在此基礎上,檢驗公司信息披露對ESG評級分歧的作用是否會受高管特定經歷的影響。
從表9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高管特定經歷在信息披露程度對ESG評級分歧的影響中起到顯著的正向調節效應;在加入高管特定經歷這一調節變量后,企業的信息披露雖說也會顯著影響ESG 評級分歧,但顯著性降低;對于環境、社會、治理分項指標,回歸結果均顯示,由于高管團隊特定經歷的存在,信息披露程度對ESG 評級分歧的影響顯著性降低甚至不顯著。可能的解釋是,在高管存在特定經歷的企業中,高管更有可能重視企業的相關指標,在環境、社會、治理方面投入較多資源,同時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去合謀修改、粉飾相關指標,達到“漂綠”的目的。因此向外界披露的數據也是利益相關者想看到的結果,特別是ESG 評級機構,利用所披露的修飾過的指標對企業進行打分,得到的結果也大同小異。因此,對于有特定經歷的高管所在的企業,信息披露程度對企業ESG評級的影響顯著性降低或不存在顯著影響。

表9 高管特定經歷的調節效應
八、進一步分析
(一)ESG評級分歧在時間維度是否收斂
在人類社會化進程中,認識具有反復性和上升性,新生事物的出現總是會受到巨大的社會阻力,伴隨著漫長的演變,逐步被大眾接受,是一個波浪式前進和螺旋式上升的過程。作為符合當下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新生事物,ESG 評級體系也繞不開這個規律。ESG 評級在我國起步較晚,雖然大部分機構都是沿用的國外評級理念,但為了更符合中國本土化特征,各機構選擇的評級維度和量化方式大相徑庭。隨著時間的推移,專業評級機構對可持續發展和負責任投資的認識更加深刻,那么它們的ESG評級分歧差異是否會變小,即ESG 評級是否會在時間序列上存在分歧收斂特性?為此,本文參考鄭淑妮等(2021)的研究,計算各個維度分歧在時間序列上的差異系數(CVt),公式如下:
其中,sdt為年度企業三個評級機構ESG 評分的標準差,meant是年度企業三個評級機構ESG評分的均值。在得出各個企業當年差異系數的基礎上,對當年所有企業差異系數求平均值,就得到了每一年的差異系數。
從差異系數計算結果(見表10)來看,ESG 評級分歧的差異系數在時間維度上是逐漸變小的,也就是說,隨著對ESG 理念的反復辯證,人們的認識不斷加深,各評級機構對ESG評價標準存在趨同趨勢。從各個維度的分歧可以發現,環境作為ESG 評級三個維度里辯證時間最短的維度,變異系數也是三個維度里最高的,說明評級機構對環境維度的認識分歧最大,這也恰恰說明對于新生事物的認識,需要一個漫長的辯證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和治理兩個維度的差異系數也逐漸變小,并且同一時間維度,社會和治理維度的差異系數遠小于環境維度的差異系數,原因可能在于社會和治理的辯證歷史要長于環境,各個評級機構對社會和治理兩個維度的認識能達成更多的共識。

表10 差異系數分析結果
(二)ESG評級分歧的經濟后果檢驗
伴隨著ESG 評級分歧現象的出現,學者們對ESG 評級分歧的后果也褒貶不一,本文就ESG 評級分歧可能導致的經濟后果進行探討。一方面,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作為ESG 評級信息重要使用對象的外部投資者處于信息的劣勢方,其并不完全知曉企業的真實運營狀況,更多的是依靠第三方機構披露的信息進行投資決策。因此,ESG 評級分歧的出現能夠為市場提供更多增量信息。但評級信息通常具有專業性,且多元信息的出現使得評級結果的復雜性更高,需要專業分析師對這些信息進行解讀或再分解(何太明等,2023),并向市場出具報告,以此緩解投資者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因此,本文用分析師關注度(analyst)作為衡量外界信息獲取難易程度的代理變量(苑澤明等,2020)。另一方面,作為被評級的企業,會聚焦于各個評級機構的評級標準,進而去同頻披露相應的信息,以增加各個評級機構統一給出較高評分的可能。但由于評級機構作為第三方,其評級的公允性也是決定自身聲譽的關鍵,這就減少了與企業合謀修改粉飾ESG 評級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管理者出于晉升和考核的壓力,會將更多資源投資于短期能夠迅速提升企業ESG評級的項目,而忽視更具有長遠價值的項目(劉柏等,2023),從而造成管理者短視,影響企業長遠發展。因此,本文用年報語調出現短視相關的詞語的頻次作為衡量管理者短視(dturn)的代理變量(胡楠等,2021)。
從回歸結果(見表11)可以看出:ESG 評級結果的多樣性確實會吸引更多的分析師關注并解讀分歧信息,從而向投資者提供更多決策信息;而從企業角度來看,由于ESG評級分歧的存在,管理者迫于股東的壓力,會加劇不利于企業長期發展的短視行為以迎合評級標準,以期在下個評級周期獲得較好的評級結果。

表11 ESG評級分歧經濟后果分析
九、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
本文從ESG 評級視角出發,基于2018 ~2022 年間滬深A 股上市公司數據,分析了信息披露程度對企業ESG評級分歧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①信息披露程度對企業ESG 評級分歧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企業披露的信息越多,ESG 評級機構對同一個維度評價相似的可能性就越低,所得出的評級結果差異越大。②高管特定經歷能夠壓縮因為信息披露的增加給ESG評級機構信息選擇的差異性空間,即高管特定經歷能夠緩解信息披露程度對企業ESG 評級分歧的正向促進作用。③無論是高ESG得分的企業還是低ESG 得分的企業,信息披露程度對ESG 評級分歧的影響均顯著;相比于ESG 環境低敏感性企業,在ESG 環境高敏感性較高的企業中,信息披露程度對ESG 評級分歧的影響更為顯著;除此之外,未被問詢的企業信息披露對ESG評級分歧的表現也呈現顯著性特征,而在被發放問詢函的企業中不顯著。④ESG 評級分歧在時間維度上呈現出顯著的收斂特征,且分歧的存在會減輕外部投資者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并加劇管理者的短視心理。
(二)建議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逐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我國證券行業起步較晚,初期制度措施的不完善導致一些上市公司存在虛假披露或是隱匿披露的現象,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健全導致披露違規披露的成本偏低,違規披露情況屢禁不止,信息評級機構不能合理無偏地給出客觀的評價尺度,從而導致了市場上的投資者信息認知偏差。因此,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違規披露成本,規范評級標準,減少信息認知偏差。
2.強化對企業管理層的監管。ESG
評級市場作為符合當下生態環境理念的新生市場,現如今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各評級機構評級維度大相徑庭,評級結果參差不齊,再加上委托代理問題的存在,更會加劇投資者與管理層的信息不對稱。因此,市場參與者要加大對市場主體的監管,減少管理者的自利行為,提高企業信息的流通度和透明度,保證外部評級機構客觀準確地對企業做出評價和判斷。
3.構建中國特色的ESG評級體系。我國經濟已經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ESG 評級所代表的可持續發展和負責任投資理念與我國當前所強調的高質量發展不謀而合。因此,要改變企業傳統的發展模式,提高企業對ESG評級的認同感和重視度,促進可持續發展。
4.隨著對ESG 領域認識的不斷深化,認識會逐步統一。相關評級機構要結合我國國情,將ESG 評級標準與中國式現代化相契合,促進對ESG 認識標準的趨同,重視因ESG 評級分歧帶來的經濟后果,為我國證券市場的平穩健康發展提供保障,使得ESG 評級體系更好地與中國特色估值體系相協調,與建設中國統一大市場相銜接。
【 主要參考文獻】
畢茜,彭玨,左永彥.環境信息披露制度、公司治理和環境信息披露[J].會計研究,2012(7):39 ~47+96.
方先明,胡丁.企業ESG 表現與創新——來自A 股上市公司的證據[J].經濟研究,2023(2):91 ~106.
何太明,李亦普,王崢等.ESG 評級分歧提高了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嗎?[J].會計與經濟研究,2023(3):54 ~70.
胡楠,薛付婧,王昊楠.管理者短視主義影響企業長期投資嗎?——基于文本分析和機器學習[J].管理世界,2021(5):139 ~156+11+19 ~21.
李敬強,劉鳳軍.企業慈善捐贈對市場影響的實證研究——以“5·12”地震慈善捐贈為例[J].中國軟科學,2010(6):160 ~166.
劉柏,盧家銳,琚濤.形式主義還是實質主義:ESG 評級軟監管下的綠色創新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2023(5):16 ~28.
羅煒,朱春艷.代理成本與公司自愿性披露[J].經濟研究,2010(10):143 ~155.
宋獻中,胡珺,李四海.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與股價崩盤風險——基于信息效應與聲譽保險效應的路徑分析[J].金融研究,2017(4):161 ~175.
孫曉華,車天琪,馬雪嬌.企業碳信息披露的迎合行為:識別、溢價損失與作用機制[J].中國工業經濟,2023(1):132 ~150.
王曉祺,寧金輝.強制社會責任披露能否驅動企業綠色轉型?——基于我國上市公司綠色專利數據的證據[J].審計與經濟研究,2020(4):69 ~77.
吳聯生,林景藝,王亞平.薪酬外部公平性、股權性質與公司業績[J].管理世界,2010(3):117 ~126+188.
武龍,李穎穎,楊柳.ESG 信息披露影響企業信貸可得性嗎[J].金融與經濟,2023(4):19 ~30.
謝紅軍,呂雪.負責任的國際投資:ESG 與中國OFDI[J].經濟研究,2022(3):83 ~99.
楊玉鳳,王火欣,曹瓊.內部控制信息披露質量與代理成本相關性研究——基于滬市2007年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J].審計研究,2010(1):82 ~88+46.
苑澤明,高靜楠,王培林.分析師關注與研發操縱:抑制亦或促進[J].財會月刊,2020(20):23 ~29.
張純,呂偉.信息披露、信息中介與企業過度投資[J].會計研究,2009(1):60 ~65+97.
鄭淑妮,白鴻宇,周文華.基于差異系數的城鄉客運一體化評價模型修正[J].重慶交通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1(2):54 ~60.
Avramov D.,Cheng S.,Abraham L.,et al..Sustainable investing with ESG rating uncertainty[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22(2):642 ~664.
Berg F.,Koelbel J.F.,Rigobon R..Aggregate confusion:The divergence of ESG ratings[J].Review of Finance,2022(6):1315 ~1344.
Chatterji A.,Durand R.,Levine D.,et al..Do ratings of firms converge?Implications for managers,investors and strategy researcher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6(8):1597 ~1614.
Dimson E.,Marsh P.,Staunton M..Divergent ESG ratings[J].The 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2020(1):75 ~87.
Eccles R.G.,Lee L.E.,Stroehle J.C..The social origins of ESG:An analysis of Innovest and KLD[J].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2019(1):575 ~596.
Lamont M..Toward 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valuation and evaluation[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12(38):201 ~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