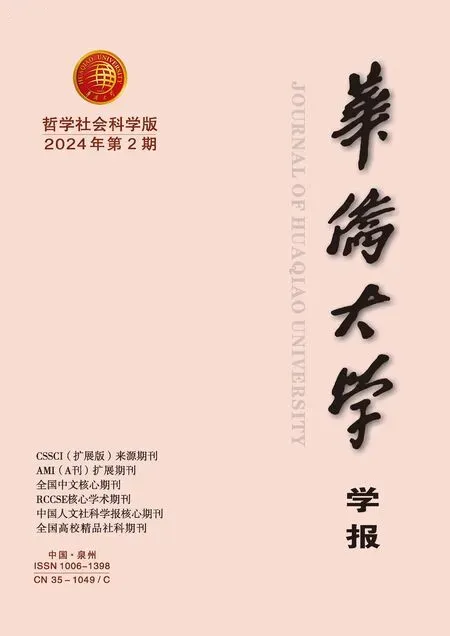福利國家視角下的中國公民生育意愿
——基于CFPS2018的定量分析
○趙 靜 鐘本章
一 文獻回顧與問題提出
生育關乎人類繁衍與發展。小至個人福祉與家庭興衰,大至社會繁榮與國家經濟增長,皆與生育息息相關。從微觀層面來看,不論是理性的還是非意愿的生育行為皆會對個人境遇、家庭生活產生重要影響。從宏觀層面來看,社會整體的生育趨勢意味著一個時代的人口結構、勞動力供給水平以及國家養老負擔(1)吳帆:《生育意愿研究:理論與實證》,《社會學研究》2020年第4期,第218—240+246頁。。在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要健全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2)《習近平主持召開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強調 加快建設以實體經濟為支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共產黨員網,(2023-05-05)[2023-12-21],https://www.12371.cn/2023/05/05/ARTI1683294362354245.shtml。,足見生育問題對國家和社會的重要意義。然而,近年來中國面臨著低生育率現狀,第六次、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指出中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18、1.3,均低于國際公認標準(3)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第2 104頁。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國人口普查年鑒2020》,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第1 612頁。《總和生育率低至1.3,我國是否跌入“低生育率陷阱”?》,新華網,(2021-05-17)[2023-12-2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5/17/c_1127456086.htm。。為應對此困境,國家于2013年、2015年分別出臺單獨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來放松生育限制,又于2021年啟動三孩政策以進一步鼓勵生育,但2022年中國仍出現了人口自然負增長和總量負增長(4)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見》,2013年12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2015修正)》第十八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2021修正)》第十八條第一款。《以人口均衡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③)——訪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人民日報》,2023年5月25日第14版。。這說明公民生育或許并不只是允許與否的問題,更是愿意與否的問題,因此,關注并解釋中國公民的生育意愿顯得至關重要。
生育意愿包含個人在生育數量、生育性別、生育時間等不同維度的偏好。其中,數量維度的生育意愿與實際的生育行為關系最為緊密,且關乎國家人口結構和勞動力供給。面對中國的低生育率現狀和老齡化壓力,將生育數量作為生育意愿的核心要素來展開研究尤為必要。基于此,本文的生育意愿特指個人在生育數量方面的偏好,其代表著個人的理想子女數、希望生育的子女數或結合自身情況打算生育的子女數(5)楊菊華:《意愿與行為的悖離:發達國家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研究述評及對中國的啟示》,《學海》2008年第1期,第27—37頁。吳帆:《生育意愿研究:理論與實證》,第218—240+246頁。。
既有研究指出,影響中國公民生育意愿的因素主要涉及兩個方面。其一為公民的個人特征,具體包括:基本人口特征,如性別、年齡、城鄉背景、獨生性質(6)石智雷、楊云彥:《符合“單獨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人口研究》2014年第5期,第27—40頁。賈志科、風笑天:《城市“單獨夫婦”的二胎生育意愿——基于南京、保定五類行業558名青年的調查分析》,《人口學刊》2015年第3期,第5—15頁。楊菊華:《單獨二孩政策下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試析》,《中國人口科學》2015年第1期,第89—96+128頁。Min Zhou,Wei Guo.Fertility intentions of having a second child amo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and home ownership.Population,Space and Place,2020,26(2),pp.1—14.;社會流動與社會分層情況(7)劉厚蓮:《配偶隨遷降低了流動人口生育意愿嗎?》,《人口學刊》2017年第4期,第40—49頁。葛佳:《全面二孩時代二孩生育的階層差異研究》,《人口與經濟》2017年第3期,第109—118頁。陳衛民、李曉晴:《階層認同和社會流動預期對生育意愿的影響——兼論低生育率陷阱的形成機制》,《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第18—30頁。;人力資本,如受教育水平、健康狀況(8)張樨樨、崔玉倩:《高人力資本女性更愿意生育二孩嗎——基于人力資本的生育意愿轉化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第182—193頁。;社會資本(9)徐萌娜、王明琳:《社會資本怎樣影響生育意愿——基于CGSS數據的實證研究》,《財經論叢》2021年第11期,第3—12頁。;工作性質(10)李紅陽:《非正規就業對已婚女性個體生育意愿的影響——基于CHNS數據的研究》,《財經論叢》2022年第1期,第3—14頁。;經濟能力,如收入水平和住房條件(11)何秀玲、林麗梅:《家庭人均收入、女性教育水平與中國育齡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7數據的經驗分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第98—108頁。李勇輝、沈波瀾、李小琴:《未能安居,焉能育兒?住房對育齡人群生育意愿的影響研究》,《中國經濟問題》2021年第2期,第68—81頁。;商業參保行為(12)王國軍、高立飛:《低生育意愿的一個解釋:養兒防老向商業保險養老轉變——基于CGSS2015數據的實證分析》,《蘭州學刊》2021年第2期,第179—195頁。;互聯網使用情況(13)王小潔、聶文潔、劉鵬程:《互聯網使用與個體生育意愿——基于信息成本和家庭代際視角的分析》,《財經研究》2021年第10期,第110—124頁。;觀念或感知,如性別觀念、風險感知(14)胡榮、林彬彬:《性別平等觀念與女性生育意愿》,《求索》2020年第4期,第142—148頁。周國紅、何雨璐、楊均中:《“生育主力”緣何有名無實?——基于743份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問卷調查分析》,《浙江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第77—86+157—158頁。。其二是家庭特征,已有子女數量和性別、子女照料支持、養老壓力等家庭因素都會對公民生育意愿產生重要影響(15)馬良、方行明、雷震、蔡曉陳:《獨生子女性別會影響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嗎?基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數據的研究》,《人口學刊》2016年第6期,第17—26頁。黃秀女、郭圣莉、張昊:《協同抑或擠出:贍養壓力對流動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影響分析》,《現代財經(天津財經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第30—41頁。田艷芳、盧詩語、張蘋:《兒童照料與二孩生育意愿——來自上海的證據》,《人口學刊》2020年第3期,第18—29頁。Min Zhou,Wei Guo.Comparison of second child fertility intentions between local and migrant women in urban China:A blinder—oaxaca decomposition.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2021,47(11),pp.2 417—2 438.Ying Qian,et al.Investigating fertility intentions for a second child in contemporary China based on user—generated cont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20,17,pp.1—15.。不難看出,既有研究集中從社會視角解釋中國公民的生育意愿,其為我們理解個體特征、家庭特征對中國公民生育意愿的影響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然而,遺憾的是,既有研究缺少來自國家視角的解釋,尤其缺少對福利國家的關注。福利國家指“國家在管理和組織經濟方面的重要角色”,其在就業、教育、家庭照料等福利制度安排上,深刻地影響著公民權利與社會結構(16)[丹麥]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鄭秉文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5頁、第248—257頁。。例如,在瑞典,社會民主主義福利體制可能造成女性占多數的公共部門勞動者與男性占多數的私人部門勞動者之間的沖突。在德國,保守主義福利體制可能造成工商界、工會等局內人和以外籍勞工為主的局外人之間的敵對。而在中國,雙軌的城鄉福利供給體制可能導致城鄉居民之間的公民權利鴻溝(17)[丹麥]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鄭秉文譯,第248—257頁。[美]蘇黛瑞:《在中國城市中爭取公民權》,王春光、單麗卿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4頁。。可見,盡管當前鮮有研究正式關注福利國家對中國公民生育意愿的作用,但福利國家對公民權利(尤其是社會權利)的重要意義引導我們合理地推測,其極有可能影響著中國公民的生育意愿。
實際上已有一些來自社保領域的研究證據初步支持了這種推測。有研究表明,國家在醫療、養老方面的福利供給很可能抑制了中國公民的生育意愿,因為這些福利供給使中國公民無需依靠“養兒”來“防老”(18)王天宇、彭曉博:《社會保障對生育意愿的影響:來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證據》,《經濟研究》2015年第2期,第103—117頁。康傳坤、孫根緊:《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對生育意愿的影響》,《財經科學》2018年第3期,第67—79頁。。然而,上述研究結論尚難以完全令人信服,因為另有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證據,指出國家的“新農合”醫療福利供給增強了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而養老福利供給對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沒有明顯影響(19)黃秀女、徐鵬:《社會保障與流動人口二孩生育意愿——來自基本醫療保險的經驗證據》,《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9年第4期,第104—117頁。。這說明,福利國家及其不同類型的福利供給與中國公民生育意愿之間的關系還需進一步厘清。
那么,福利國家究竟是釋放還是抑制了中國公民的生育意愿?國家不同類型的福利供給是否會對中國公民的生育意愿產生差異化影響?文章將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之上繼續推進對這些問題的理解。為此,將從相關文獻中尋找更多的理論資源,以探究福利國家與中國公民生育意愿之間的關系,并據此先提出研究假設,進行研究設計與實證分析,對研究假設進行驗證。最后進行總結與討論,闡明用福利國家來解釋中國公民生育意愿的理論價值與政策啟示,并探討今后有必要繼續關注的研究方向。
二 理論與假設
(一)“福利國家”概念在中國的適用性
在正式討論福利國家對中國公民生育意愿的影響前,有必要交代清楚“福利國家”這個概念及其與中國經驗的適配性。
傳統觀點將福利國家視為一種特殊的國家形態。與其他國家相比,福利國家為公民提供了更廣泛的和更無差別的教育、就業、醫療、養老等服務,國家因此負擔著高昂的社會福利財政支出。二戰后,隨著貝弗里奇(Beveridge)的社會服務國家理念和馬歇爾(T.H.Marshall)的公民權利理論出現,福利國家在英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迎來了一段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這些早期福利國家的特征使人們常常將福利國家與民主、資本主義、高額的社會福利財政支出聯系在一起(20)肖濱:《政治學導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27—329頁。,故而福利國家更像是一種西方話語。相應地,早期的福利國家研究也以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福利體制分析為主(21)[丹麥]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鄭秉文譯。岳經綸、劉洋:《新興福利國家:概念、研究進展及對中國的啟示》,《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0年第4期,第114—127+158頁。。若僅以此來看,中國似乎難以被歸為“福利國家”之列。
然而,時至今日,福利國家更多被用于描述國家在經濟分配中的角色(22)[丹麥]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鄭秉文譯,第2—5頁。或國家在福利供給方面的制度安排(23)Ian Gough.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welfare regimes:The East Asian case.Global Social Policy,2001,1(2),pp.163—189.。從實踐來看,在拉美、東亞,一批后工業化國家迅速興起,它們在追求經濟增長過程中催生了一系列社會保障職能,這使其國家角色從發展型國家逐漸向福利國家擴展(24)Ian Gough.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welfare regimes:The East Asian case.pp.163—189。岳經綸、劉洋:《新興福利國家:概念、研究進展及對中國的啟示》,第114—127+158頁。。從理論來看,學界對福利國家的認識極大地豐富了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關于福利體制的三種經典劃分,即除了自由主義福利國家、保守主義福利國家和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國家之外(25)[丹麥]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鄭秉文譯,第29—32頁。,當今世界的發展中經濟體還出現了各種類型的新興福利國家(26)岳經綸、劉洋:《新興福利國家:概念、研究進展及對中國的啟示》,第114—127+158頁。。其中,生產型福利國家通過福利供給來促進市場發展,保護型福利國家注重在市場競爭下對特定群體提供保護,而雙重型福利國家的福利供給混合了發展和保護兩種意圖(27)Nita Rudra.Welfare stat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Unique or universal?The Journal of Politics,2007,69(2),pp.378—396.。由此可見,“福利國家”已不再是專屬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概念,它可以用來描述將福利供給作為一項基本職能的任何國家(28)David Garland.The welfare state: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Chapter 9.,這當然包括中國。
更聚焦地看,目前已有部分文獻將“福利國家”概念運用于中國研究當中。例如,學者們指出,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屬于社會主義福利體制,公民福利由國家、集體和國企共同承擔(29)Gordon White.Social security reforms in China:Towards an East Asian model?In Roger Goodman,et al. (eds.).The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Welfare orientalism and the state.Taylor &Francis e—Library,2001,pp.175—197.Nara Dillon.Radical inequalities:China’s revolutionary welfare stat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p.1.。而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福利體制愈發接近東亞的發展型福利國家,其核心特征是國家主要通過調節、監管等非財政手段來提供公民福利,并倡導家庭、企業和社區發揮福利供給作用,從而使國家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還能夠以較低水平的福利支出來實現較高水平的公民福利(30)Gordon White.Social security reforms in China:Towards an East Asian model?In Roger Goodman,et al. (eds.).The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Welfare orientalism and the state.pp.175—197.Xinping Guan.China’s social policy: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market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In Huck—ju Kwon (ed.).Transforming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in East Asia.Palgrave Macmillan,2005,pp.231—256.。此外,進入21世紀,中國似乎成為了混合型福利國家,由國家、市場、家庭共同負責福利供給(31)Bingqin Li,Bent Greve.Introduction:Radical change in welfare systems in China—The interaction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other actors.Social Policy &Administration,2011,45(6),pp.629—632.。但總體而言,中國仍然處于福利國家發展的初步階段(32)岳經綸、劉璐:《中國正在走向福利國家嗎——國家意圖、政策能力、社會壓力三維分析》,《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6期,第30—36頁。。
綜上所述,“福利國家”概念的內涵已擴展至國家的福利供給角色,其外延則可涵蓋所有為公民提供福利的國家。因此,我們將“福利國家”概念運用到中國研究中有著較為充分的理論依據。
(二)福利國家與中國公民生育意愿
福利國家通過福利供給與公民產生聯系。國家向公民提供的福利通常包括就業、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類型。針對這些福利,國家在供給主體、供給對象和供給數量方面做出制度安排并予以實施,其對公民個體的基本生存狀況和人生境遇產生影響,并塑造著社會公平、利益和權力(33)Ian Gough.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welfare regimes:The East Asian case.Global Social Policy,2001,1(2),pp.163—189.。
為了考察福利國家對公民生育意愿的影響,我們需要觀察國家的福利供給差異是否會造成公民的生育意愿差異。換言之,在控制其它影響因素的前提下,如果公民享受(相對于不享受)國家福利會改變其生育意愿的話,我們就能夠據此判斷二者之間存在因果關系,而這首先需要確定可供分析的國家福利類型。在中國,國家供給的基礎福利也不外乎上述幾種。其中,公民能否獲得就業和住房福利,除了受國家調控之外,還受到個人能力、資源和市場競爭的強烈影響。可見,這兩種類型的福利供給較為復雜,不利于我們辨明國家的作用。另外在教育方面,國家福利供給從數量來看處于高度普及的水平(34)《中國統計年鑒2021》數據指出,2020年中國兒童的小學入學率為100%、小學升學率為99.5%,這說明國家在基礎教育方面的福利供給具有較高普遍性。,其難以呈現出差異,同樣無助于我們開展研究。因此,文章最終選擇以養老、醫療這兩種由國家高度參與且尚未完全普及的福利類型作為考察對象,其供給程度正好處于就業、住房福利與教育福利中間,最適合用于差異化比較分析(35)《中國統計年鑒2022》數據指出,2021年中國人口總數為141 260萬人,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為102 871.4萬人,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人數為136 296.7萬人,可見國家的養老、醫療福利供給仍然存在個體差異。。
就國家養老福利供給與中國公民生育意愿之間的關系而言,有研究表明,享受國家養老福利的公民比沒有享受相應福利的公民有著明顯更低的生育意愿(36)康傳坤、孫根緊:《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對生育意愿的影響》,第67—79頁。。盡管缺乏更多的證據支持,但這種現象背后的理論邏輯有著較為充分的說服力。具體而言,傳統中國公民的生育行為具有經濟功能,生育子女能夠使父母在年邁時獲得收入和照料,俗稱“養兒防老”。故而生育是一種理性選擇,養老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中國公民的生育意愿。特別在改革開放初,由于國家、社會、市場的養老功能尚未健全完善,因此以家庭為根基的子女贍養幾乎是中國公民養老的唯一途徑,這勢必會釋放出較為強烈的生育意愿。但當福利國家發展起來后,國家的養老福利供給為中國公民創造了額外的養老途徑,使其在年邁時即使缺少子女贍養,也能獲得基本的生活支持。進一步看,國家養老福利供給可能通過三種機制改變中國公民生育男孩的偏好,從而降低公民生育意愿:第一,國家養老福利供給將會弱化中國公民的傳統生育觀念;第二,國家養老福利供給有助于降低中國公民的老年生活憂慮;第三,國家養老福利供給提高了中國公民當前的生活質量(37)阮榮平、焦萬慧、鄭風田:《社會養老保障能削弱傳統生育偏好嗎?》,《社會》2021年第4期,第216—240頁。。可見,對于用經濟理性邏輯去考慮生育決策的中國公民而言,在育兒成本不斷攀升且育兒收益不夠穩定的情況下,制度化、權威的國家養老福利供給的出現意味著生育從“必選項”變為了“可選項”,此時中國公民的生育意愿降低不難想見。歸根結底,其實就是享受國家的養老福利對由經濟理性引起的個體生育行為產生了替代作用(38)康傳坤、孫根緊:《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對生育意愿的影響》,第67—79頁。,所以國家的養老福利供給抑制了中國公民的生育意愿。據此,提出假設1:
假設1:與未享受國家養老福利的公民相比,享受國家養老福利的公民有著明顯更低的生育意愿。
就國家醫療福利供給對中國公民生育意愿的影響而言,目前有兩項相關研究對此存在爭議。其中一項研究指出,享受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這類國家福利會降低女性的生育意愿。與養老福利相似,國家醫療福利供給很可能對中國公民的生育行為產生替代作用,因為其有助于緩解公民的醫療消費負擔,減少公民在患病期間對子女的經濟依賴,這或許會導致公民的生育積極性降低(39)王天宇、彭曉博:《社會保障對生育意愿的影響:來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證據》,第103—117頁。。但另一項研究卻表明,享受同樣的國家福利會增強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由于醫療福利對個體的支持不像養老福利一般主要針對未來,而是更著眼于現在,所以對適齡生育的中國公民來說,享受國家醫療福利不僅更有助于對抗當下的生育風險和身體疾病,還能通過減少醫療投入來放松家庭預算約束,從而間接增加育兒投入。正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由于其實施年度繳費和報銷機制,且財政補貼力度大,故其相較于福利享受更為滯后的養老保險而言對家庭經濟的即時補充效應更為強烈,這或許有助于增強公民的生育積極性(40)黃秀女、徐鵬:《社會保障與流動人口二孩生育意愿——來自基本醫療保險的經驗證據》,第104—117頁。。鑒于上述兩種觀點各有合理性,故文章認為關于國家醫療福利供給對中國公民生育意愿的影響的理論預設可更具開放性,并據此提出兩種假設:
假設2a:與未享受國家醫療福利的公民相比,享受國家醫療福利的公民有著明顯更低的生育意愿。
假設2b:與未享受國家醫療福利的公民相比,享受國家醫療福利的公民有著明顯更高的生育意愿。
總之,福利國家會深刻地影響中國公民的生育意愿。這種影響可能因國家福利供給類型的不同而存在差異,福利國家及其不同類型的福利供給對中國公民生育意愿的影響或許遵循著兩種邏輯——替代與補充,并產生兩種作用——抑制和釋放。為檢驗這些猜想,接下來將進入研究設計部分,以交代研究思路、數據、變量與方法等內容。
三 研究設計
(一)研究思路與數據來源
文章關注福利國家及其福利供給類型對中國公民生育意愿的影響,因變量是公民生育意愿,兩個核心自變量分別是國家養老福利供給和國家醫療福利供給。為控制其它因素的干擾,還將既有研究所涉及的社會視角因素納入分析,具體研究思路與變量設計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思路與變量設計(筆者自制)
為使研究結論能夠反映中國的基本情況,文章決定通過對全國性抽樣調查數據的分析來檢驗福利國家與公民生育意愿之間的關系。具體將使用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簡稱“CFPS2018”)數據來進行經驗論證。如此選擇是基于三點考慮:第一,CFPS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提供,是目前中國最權威、最具規模的調查數據之一,其能為本研究的效度與信度提供良好的保障;第二,CFPS調查了被訪者的個人基本信息、家庭、就業、社會保障、觀念等方面的情況,能夠為本研究提供豐富的變量信息;第三,CFPS2018能夠較好地平衡數據時效與政策時效,有助于了解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來中國公民的生育意愿及其影響因素。CFPS2018共發布了家庭關系、家庭經濟、個人、少兒家長代答和跨年核心變量共5個模塊的數據。本研究所需數據均來自于個人庫,其初始樣本量為37354個。由于個人庫中收錄了9~15歲青少年的數據和因身體等原因導致代答的數據,這部分樣本并不適用于生育意愿分析,且其信息在一些關鍵變量上存在較多缺失,因此去掉這部分不符合要求的數據。基于相似的原因,在CFPS2018中,生育意愿、國家的養老或醫療福利供給等核心變量因一些人群不適用而存在部分缺失,亦剔除了這部分數據。最終,經此處理后的樣本觀測值為23378個。
(二)變量設置
1.因變量。用CFPS2018中“您認為自己有幾個孩子比較理想”一題來測量被訪者的生育意愿,問題答案記錄“期望孩子個數”。
2.自變量。CFPS2018用“您參保了哪幾種養老保險項目”一題來調查被訪者參與養老保險的情況。問題選項涉及“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商業養老保險”“農村養老保險”“離退休金”“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城鎮居民養老保險”七類。其中,前三類養老保險要么并非國家主導,要么不受國家財政補貼,故從嚴格意義上來看,它們均不屬于國家福利。而后四類養老保險全由國家主導或由國家提供財政補貼,屬于真正意義上的國家福利,與本研究的目的相符。因此,用被訪者是否參與離退休金、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養老保險來測量被訪者是否享受由國家供給的養老福利,問題答案記錄為“是”或“否”。
CFPS2018還用“您享有哪些醫療保險”一題來調查被訪者參與醫療保險的情況。問題選項包括“補充醫療保險”“公費醫療”“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五類。其中,補充醫療保險是自愿參與的,不屬于國家主導的醫療福利范疇。而其余四類醫療保險均由國家主導或由國家財政支持,屬于本研究所關注的國家福利。因此,用被訪者是否參與公費醫療、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來測量被訪者是否享受由國家提供的醫療福利,問題答案同樣記錄為“是”或“否”(41)有關各類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的參保人群特征、國家參與情況等具體信息參見CFPS2018問卷。。
3.控制變量。CFPS2018還收錄了與被訪者的基本人口特征、人力資本、工作狀況、社會地位、婚姻狀況和撫養觀念相關的信息,它們能夠很好地從社會視角去揭示個人和家庭因素對生育意愿的影響。在既有研究基礎上,將它們納入分析并對其進行控制,以助于識別國家福利供給對公民生育意愿的影響。
這些控制變量及其測量包括:第一,性別,選項記錄“男”或“女”。第二,年齡,樣本中涵蓋了16歲以上人群。第三,目前戶籍性質,選項主要包括“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第四,目前所在地區,原選項記錄被訪者所在省份,參照《中國統計年鑒2022》,將其重新編碼為“東北”“西部”“中部”“東部”四大地區。第五,插補后的受教育年限,其為CFPS項目組清理后的綜合變量。第六,自評健康狀況,包括“非常健康”“很健康”“比較健康”“一般”“不健康”5級定序選項。第七,目前工作狀態,主要有“退出勞動力市場”“失業”“在業”三種選項,將前兩項合并,生成包含“不在業”“在業”的二分類變量。第八,自評社會地位,包括從“很低”到“高”共5級定序選項。第九,婚姻段數,主要包括“0段”“1段”“2段”“3段”四種回答。本文用婚姻段數去考察被訪者組建家庭的情況,并參照既有研究的做法將其重新編碼為“無”和“1段及以上婚姻”(42)馬良、方行明、雷震、蔡曉陳:《獨生子女性別會影響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嗎?基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數據的研究》,第17—26頁。何秀玲、林麗梅:《家庭人均收入、女性教育水平與中國育齡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7數據的經驗分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第98—108頁。,前者意味著被訪者尚未組建家庭,后者意味著被訪者已組建家庭。第十,撫養費影響,問題為“撫養費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您要孩子的決定”,回答包括從“幾乎沒有影響”到“影響非常大”共5級定序選項。撫養費影響代表著被訪者對子女養育成本的看法,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訪者的家庭經濟情況。由于CFPS2018中沒有直接調查被訪者已有子女數量的題項,因此我們基于既有理論選擇了撫養費影響這一替代性變量去進行分析(43)黃秀女、郭圣莉、張昊:《協同抑或擠出:贍養壓力對流動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影響分析》,第30—41頁。。
(三)分析方法
在描述統計部分,將在展示樣本中各變量的基本信息之后對各類參保者與未參保者之間的期望孩子個數進行初步比較。推斷兩個組別在因變量上的取值是否相同可以采用t檢驗,該檢驗假設兩組之間的均值相等,拒絕此假設則說明兩個組別的因變量均值有明顯不同(44)UCLAStatistical Methods and Data Analytics,[2023-12-06],https://stats.oarc.ucla.edu/stata/output/t—test/。。
在回歸分析部分,由于測量生育意愿的“期望孩子個數”是取值為非負整數的計數型變量,因此可以考慮采用泊松回歸、負二項回歸、零膨脹泊松回歸或零膨脹負二項回歸等計數模型,這亦符合生育意愿相關研究的主流做法(45)陳衛民、李曉晴:《階層認同和社會流動預期對生育意愿的影響——兼論低生育率陷阱的形成機制》,第18—30頁。胡榮、林彬彬:《性別平等觀念與女性生育意愿》,第142—148頁。王天宇、彭曉博:《社會保障對生育意愿的影響:來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證據》,第103—117頁。。“期望孩子個數”觀測值的分布特征和模型擬合優度檢驗結果表明,更適宜采用泊松回歸進行分析,其公式如下:
四 實證檢驗
(一)描述統計
本研究各變量的基本情況(見表1)。其中,期望孩子個數的取值在0到10之間,平均值為1.99。這表明,被訪者期望生育的孩子個數平均值不超過2個,低于近年來國家號召的生育數量。在養老保險方面,參與離退休金者占比3%,參與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者占比13.73%,參與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者占比33.71%,而參與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者占比3.91%。在醫療保險方面,參與公費醫療、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被訪者依次占比1.92%、13.73%、7.82%和68.35%。這些數據說明,不同類型的國家福利在適用人群和實際覆蓋范圍方面差異明顯。就其它信息而言,女性被訪者和男性被訪者各占比49.92%、50.08%,其平均年齡約為41歲,擁有農業或非農戶籍者分別占比77.64%和22.36%,來自東北、西部、中部和東部地區者分別占比12.61%、31.63%、23.61%和32.16%。同時,被訪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63年,自評健康狀況略低于比較健康這一水平,目前在業的比例為83.19%。此外,在所有被訪者中,目前有至少一段婚姻的占比79.23%,對撫養費影響要孩子決定這一問題的平均看法處于中等偏上的認可水平。

表1 變量描述統計
另外,采取t檢驗來考察各類養老、醫療保險參保者與未參保者之間的期望孩子個數是否不同(見表2)。所有類型的參保者與未參保者之間的期望孩子個數均存在顯著差異,這說明是否享受國家養老、醫療福利很可能會對中國公民的生育意愿產生影響。由于t檢驗僅關注單一因素的不同組別在因變量上的均值差異,未考慮期望子女個數是否受到各類保險參保情況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響,因此仍需通過多變量的回歸分析來進一步識別因果關系。

表2 參保者與未參保者期望孩子個數差異t檢驗
(二)回歸分析
在控制其它變量的情況下,分別檢驗了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與期望孩子個數之間的關系(見表3、表4)。

表3 養老保險與期望孩子個數模型結果

表4 醫療保險與期望孩子個數模型結果
模型1至模型4逐一考察了四類由國家提供的養老保險與期望孩子個數之間的關系(見表3)。模型1顯示,是否參與離退休金與期望孩子個數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性。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離退休金主要向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提供,參保群體的特殊性或許會導致某些更重要的因素影響其期望生育的孩子數量。模型2、模型3和模型4顯示,是否參與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與期望孩子個數之間顯著負相關。這說明,與未參與這三類養老保險的人相比,參與這三類養老保險的人期望生更少的孩子。這三個模型的結果還表明,參與這些養老保險都會使個人期望少生孩子,而不論養老保險的具體類型如何。可見,養老保險類型的差異并沒有對期望孩子個數產生異質性影響。
為了更嚴謹地檢驗四類養老保險與期望孩子個數之間的關系,將它們同時放入模型5中進行分析,通過相互控制來排除彼此之間的干擾。顯然,模型5的結果再一次表明,在控制了其它變量的情況下,個人是否參與離退休金與期望孩子個數之間無顯著相關性,而個人是否參與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與期望孩子個數間呈現出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三類參保者的期望孩子個數分別是未參保者的0.934、0.945、0.920倍(46)此處匯報根據系數計算出的發生率比,下同。,該結果分別在0.001和0.01的顯著性水平上成立。
整體看來,除了離退休金外,參與其它三類養老保險均會對個人期望孩子個數產生消極影響。這意味著,享受由國家提供的養老福利確實會抑制中國公民的生育意愿,研究假設1基本得到了證實。
同樣,模型6到模型9分別考察了四類由國家提供的醫療保險與個人期望孩子個數之間的關系(見表4)。模型6表明,是否參與公費醫療不會顯著地影響個人期望生育的孩子數量。與離退休金相似,享受公費醫療者以體制內工作人員為主,其期望孩子個數可能主要與其它特殊因素有關。模型7和模型8顯示,是否參與城鎮職工或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對個人期望孩子個數產生顯著負向影響。與之不同,模型9顯示,參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對個人期望孩子個數有顯著正向的影響。可見,不同類型的醫療保險對期望孩子個數的影響似乎是不同的。
為了進一步評估這四類醫療保險與期望孩子個數之間的關系,模型10仍然通過對四者的相互控制來識別其效用。結果表明,在控制了其它變量的情況下,個人是否參與公費醫療不會明顯地改變其期望孩子個數。而個人是否參與城鎮職工或居民醫療保險依舊與其期望孩子個數顯著負相關,兩類參保者期望生育的孩子個數分別是未參保者的0.933、0.911倍,此結果在0.01和0.001的顯著性水平上有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參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對個人期望孩子個數的正向影響不再顯著。這揭示出城鄉醫療保險的差異化作用。
總之,就醫療保險對期望孩子個數的影響而言,研究結果表明,是否參與公費醫療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皆對個人期望孩子個數沒有顯著的影響。而參與城鎮職工或居民醫療保險會對個人期望孩子個數產生消極影響。與未參與這兩種保險的個人相比,參保者傾向于少生孩子。僅此可知,與養老福利相似,享受國家醫療福利會對公民生育意愿產生抑制作用。該結果支持了研究假設2a,而研究假設2b未被證實。這意味著從長期來看,國家醫療福利供給對公民生育意愿的影響很可能仍然遵循替代邏輯。對步入老齡階段的公民而言,國家醫療福利能夠減輕其在喪失勞動能力和缺少經濟支持條件下的醫療負擔,這或許亦能實現對養兒防老的功能性替代,從而使公民生育意愿降低。
在控制變量方面,表3、表4中的模型均呈現出較為一致的結果。首先,期望孩子個數并不存在顯著的兩性差異。年齡大者可能期望生育更多的孩子。與擁有農業戶口者相比,擁有非農戶口者期望少生孩子。東北地區的人期望孩子個數明顯少于西部、中部和東部地區。其次,受教育年限越長的人,期望孩子個數越少。健康狀況可能與期望孩子個數正相關,但這種關系并不顯著。目前有工作者期望生育的孩子個數比無工作者更少。社會地位越高者可能期望生育更多孩子,但其間關系也不顯著。最后,有婚姻經歷者期望孩子個數比未婚者更多,而越擔憂撫養費者則越期望少生孩子。
(三)穩健性檢驗
在上一小節中,模型5和模型10已對研究結果的穩健性進行了初步的檢驗。在此基礎上,通過替換因變量的編碼方式和替換模型,將“期望孩子個數”重新編碼為“是/否想要三個或以上孩子”(否=0),再采用Logit模型來繼續檢驗。
在表5中,如模型11所示,在控制了其它變量的情況下,參與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或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者生育三個或以上孩子的意愿明顯比未參保者低,此結果與前文相同。然而,不同之處在于,模型11顯示參與離退休金跟是否想生三個或以上孩子顯著負相關,此發現或許有助于強化國家養老福利供給抑制中國公民生育意愿的結論,而不論養老福利的具體類型為何。當然,由于是否想要三個或以上孩子與期望孩子個數的實際含義可能略有不同,故我們對這一推論應持審慎態度。模型12顯示,與未參與城鎮職工或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者相比,參保者更不想生育三個或以上孩子。同時,是否參與公費醫療、是否參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不會對是否想生三個或以上孩子產生明顯的影響。可見,模型11的結果與表4的結果保持一致。整體看來,經反復檢驗可知,本研究的模型結果具有較強的穩健性。

表5 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與是否想生三個或以上孩子模型結果
五 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結論
在國家視角下,福利國家無疑是影響中國公民生育意愿的核心因素,因為國家對社會經濟資源的再分配會深刻地影響公民的生存狀況和個人利益,進而影響其生育決策。通過對調查數據進行分析,探討福利國家及其不同類型的福利供給對中國公民生育意愿的影響,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福利國家的確會影響中國公民的生育意愿。與未享受特定類型國家福利的公民生育意愿相比,享受這些福利的公民生育意愿明顯不同。這些國家福利包括養老方面的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以及醫療方面的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第二,上述國家福利均會對公民的生育意愿產生抑制作用。不論是養老福利還是醫療福利,享受它們都會使公民期望少生孩子。第三,并非所有類型的國家福利都會影響公民生育意愿。享受離退休金這一國家養老福利和享受公費醫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這兩種國家醫療福利的公民與未享受者之間的生育意愿很可能沒有明顯差異。
(二)討論與展望
基于上述結論不難看出,福利國家抑制了中國公民的生育意愿。從理論來看,一方面,該發現有助于我們從有別于既有研究的新視角來繼續探討生育意愿。在開展相關研究時,需留意國家這一看似無形實則有形的力量,因為國家對社會資源的再分配決定了公民享受某種福利的資格、數量和質量,繼而決定了公民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塑造其生存條件、行為和觀念特征,從而影響其生育決策。歸根結底,文章試圖說明福利國家對解釋公民生育意愿的重要性。這本質上涉及對“國家與公民關系”的探討,其有別于“國家與社會關系”,是國家這一結構性力量與個體之間的緊密互動。另一方面,此發現也為福利國家的中國研究提供一種新思路,即關注福利國家的作用,檢驗福利國家在扶貧濟困、促進社會公平、影響公民行為和觀念等方面的效果,而非集中于對福利國家規范理論的引介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福利體制的剖析。總之,關注福利國家與生育意愿之間的關系不僅有助于更全面地探究中國公民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還有助于通過實證研究進一步認識福利國家理論。從實踐來看,福利國家對中國公民生育意愿的消極影響提示政策制定者應謹慎考慮福利制度設計,并在供給福利與維持勞動力之間取得平衡。僅從研究的結論來看,福利供給使公民期望少生孩子,這可能導致國家勞動力不斷減少,并進一步影響人口結構、社會運行負擔和國家經濟發展。然而,福利供給是現代國家的一項基本職能,其關涉公民權利、政治參與和社會穩定,影響深遠。可見,上述發現揭示出當下國家治理的困局——國家既需提供福利,同時又要發展經濟。福利供給很可能通過減少勞動力來阻礙經濟發展,這或許意味著國家應該減少福利供給。但同時,缺少必要的福利供給可能會危及國家的長治久安,故其對國家而言又是必不可缺的。針對此種困局,政策制定者需要通盤考慮,謹慎取舍。
最后,必須指出的是,本研究仍有疏漏,這或許可以成為今后繼續探索的方向。第一,受數據可及性影響,僅考察了是否維度的國家福利供給差異,但未能探討多少維度的國家福利供給差異,今后有必要豐富數據和測量以進一步分析國家福利供給的多少影響中國公民生育意愿的程度。第二,僅關注國家的養老和醫療福利對中國公民生育意愿的影響,接下來可擴展更多的國家福利類型,并分析整體的國家福利體系對公民生育意愿的作用。第三,從方法嚴謹性來看,主要揭示部分由國家供給的養老、醫療福利與公民生育意愿之間的相關性,至于其間因果推斷是否可靠、因果機制如何實現等問題,仍待使用更高階的定量技術和更扎實的定性研究來分別呈現。第四,對離退休金、公費醫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這三類國家福利而言,是否存在其他機制或因素的作用使得它們與中國公民生育意愿之間的關系更為復雜?亦值得進一步思考。第五,僅關注中國公民的生育意愿,而福利國家對生育意愿的影響究竟只是“中國特色”還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國?開展福利國家與生育意愿的國別比較研究亦可成為未來的研究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