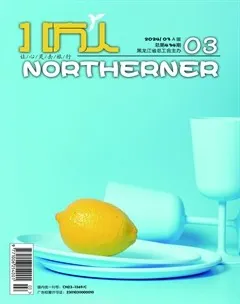賽馬會上的“帽子秀”
傅瑩

我第一次應邀出席賽馬會時,對服飾不太有把握。請柬標注的座位在皇家觀眾席,按照要求應該穿女士日間禮服,或者穿民族服裝。我選擇了民族服裝,一件中式短袖旗袍,長度過膝,外搭一件風衣,以防雨后降溫。佩戴一枚與旗袍顏色相近的頭飾,這算是我的討巧之舉,因為那種羽毛裝飾的夸張女士帽子不但價格高昂,而且不適合搭配旗袍,但是頭上完全沒有裝飾在這種場合似乎也不大合時宜。根據約定俗成的通例,觀看賽馬時女士戴的帽子越奇葩越好。進入包間后,門口有一個架子,專供男士放禮帽用,而女士帽子可以始終不摘,包括進餐時。
不過午餐時,我對面的男士被夾在兩位戴著大檐帽的女士中間,整個過程都在試圖躲避被兩邊的大帽檐戳到,防不勝防,我們之間的談話經常被打斷。他無奈地沖著我笑笑,聳聳肩。
賽馬會如果趕上大風天氣,女士們就有點狼狽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在自傳里寫到,她小時候去觀看古德伍德馬術節時一個有趣的細節:“賽馬的行話和術語我一竅不通。對我來說,賽馬就意味著站在那里,戴著插滿鮮花、極不聽話的帽子,一有風吹來就要拉緊六個帽針……”
自從中世紀以來,帽子就是英國女性日間正式著裝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到“二戰”以后“帽子文化”才變得沒有那么嚴格,只在特殊場合得以保留,賽馬會便是其中之一。
在邀請函里對女士戴帽子有明確要求,尤其是比賽第三天,定為“金杯日”,是賽程最關鍵、最繁忙的一天。這一天又被稱作“女士日”,是展示帽子的節日,女士們會選擇最夸張、最驚艷的帽飾為自己增色,或復古或摩登,或華麗或怪誕,團團簇簇,大放異彩。這一天的一個重要節目就是評選出最佳帽子。
女性王室成員們佩戴的帽子仍以典雅端莊為特征。伊麗莎白二世自登基以來,出席公眾場合時戴過的帽子有5000頂之多,幾乎從不重復。在60多年時間里,她以“小處多變化,大處不變化”的形象引領著英國帽子文化潮流。而猜測女王每年出席皇家賽馬會時會戴什么顏色的帽子也是人們熱衷討論的話題,甚至有人為此下注。英國王室傳記作家羅伯特·蘭斯說,帽子對女王的意義不僅僅是佩飾:“當女王戴著帽子時,她戴的是某種王冠的替代,帽子此時不僅僅是一個裝飾,還代表著一種威嚴。”
至于時尚人士和普通民眾,在帽子上可以發揮的空間就更大了:可以看到五彩斑斕的花草蜂蝶,各色絲帶珍珠羽毛構成的奇異造型,甚至蔬菜水果、車船模型、仿真動物、埃菲爾鐵塔和大本鐘都可能出現在女士們頭頂,讓人嘆為觀止。在頭上做巨大裝飾的浮夸審美曾風靡于18—19世紀的歐洲,之后漸漸消失在歷史中。賽馬會給了人們一個復古和懷舊的機會。
帽子設計師史蒂芬·瓊斯對禮帽之于賽馬的意義有獨到解讀:“帽子就像蛋糕頂端的櫻桃,充分滿足人們的幻想,也把衣服變成真正的時裝。”
(摘自中信出版集團《大使衣櫥:外交禮儀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