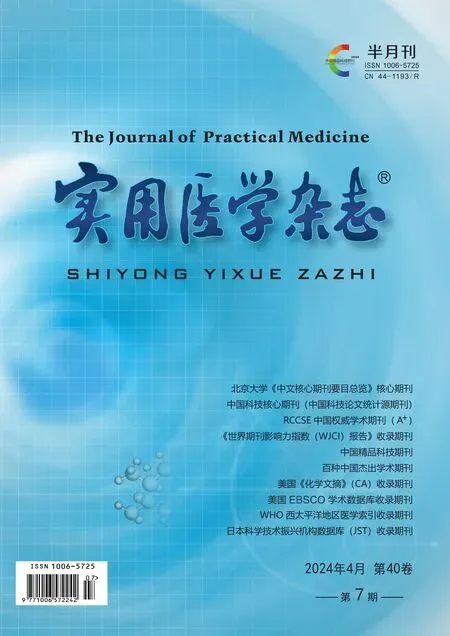內質網-線粒體互作在卒中后認知障礙中的研究進展
陳露露 羅萌 蘇凱奇 高靜 馮曉東
1河南中醫藥大學(鄭州 450046 );2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康復中心(鄭州 450000 )
卒中后認知障礙(post-stroke cognitive impairment, PSCI)是指由卒中引起的注意力、記憶力、執行力、理解力等多方面認知功能的下降,包括了從卒中后非癡呆型認知障礙到卒中后癡呆的一系列臨床表現[1-2]。由于人口老齡化和中風幸存者數量的增加,每年將有超過100 萬的PSCI 患者出現[3]。持續性和進展性的PSCI 嚴重影響患者日常生活能力,阻礙患者康復進程,現已成為當下臨床干預的重點和難點。PSCI 發病機制復雜,與多種病理過程密切相關,而內質網和線粒體作為細胞內的核心細胞器,其異常的功能狀態是許多病理過程發生的關鍵環節[4]。研究[5-6]發現內質網和線粒體通過線粒體相關內質網膜(mitochondria-associated endoplasmic reticulum mem-branes, MAMs)進行廣泛而頻繁的互作,不僅在維持內質網和線粒體功能中扮演重要角色,更成為整合細胞內Ca2+信號和調節脂質代謝的核心樞紐。盡管目前對于內質網-線粒體互作的報道主要集中在神經退行性疾病[7-8],但不少研究已證實內質網-線粒體間的交互串擾可通過上述途徑介入PSCI 發生發展的多個環節。因此,調控內質網-線粒體互作或許可成為防治PSCI 的新策略。本文將重點闡明內質網-線粒體互作與PSCI 的關系,以期為今后PSCI 靶向藥物的開發提供新的理論依據和參考。
1 內質網-線粒體互作相關概述
1.1 內質網-線粒體互作的結構基礎內質網-線粒體的交互作用是通過它們間的膜接觸位點(membrane contact sites, MCSs)來實現的。長期以來細胞器被認為是細胞中獨立的單元,但實際上彼此間可通過MCSs 形成結構和功能上的聯系,特別是具有廣闊膜面積的內質網與線粒體兩大細胞器,早已在進化過程形成了MAMs 這一動態膜偶聯區域[9]。MAMs 是內質網和線粒體外膜(outer mitochondrial membrane, OMM)之間形成的物理連接平臺,最早由COPELAND 等[10]于1952 年使用電子顯微鏡觀察大鼠肝細胞時發現;隨著技術的發展,VANCE 等[11]于1990 年從大鼠肝臟中首次分離出MAMs。現代研究已證實MAMs 是由內質網膜與OMM 間高度共定位的蛋白質連接形成的5%~20%膜偶聯區域。構成MAMs 的蛋白眾多且復雜,迄今為止,在哺乳動物中已經鑒定出包括電壓依賴性陰離子通道(voltage-dependent anion channel, VDAC)、鈣聯接蛋白(calnexin, CNX)、肌醇1,4,5-三磷酸受體(inositol 1,4,5-trisphosphate receptor, IP3R)、葡萄糖調控蛋 75(glucose-regulated protein 75, Grp75)、動力相關蛋白 1(dynaminrelated protein-1, Drp1)、線粒體分裂蛋白(mitochondrial fission protein 1, Fis1)線粒體融合蛋白( mitofusin-2, Mfn2)、突觸融合蛋白17(syntaxin-17, Stx17)等1 300 種以上的相關蛋白[12]。更重要的是,細胞內的MAMs 并不是靜態恒定的,細胞的功能狀態決定著MAMs 招募的蛋白質種類與數量;而MAMs招募的蛋白質種類與數量又可以影響MAMs 接觸面積與間距。因此,在不同的組織細胞中,同一細胞的不同功能狀態下MAMs 可有明顯的差異。
1.2 內質網-線粒體互作的生物學功能內質網-線粒體互作的生物學功能主要由MAMs 實現,而MAMs 上蛋白質的廣泛富集,提示內質網-線粒體互作可能存在多樣的生物學功能。事實也的確如此,如MAMs 上招募的Mfn2、Drp1、Fis1、Stx17 等線粒體動力學相關蛋白,可以調節線粒體分裂/融合的過程來維持線粒體的形態的穩定與mtDNA的完整性;而富集的其他蛋白如PINK1(PTEN induced putative kinase 1)和Parkin 蛋白則與線粒體自噬密切相關[13]。更值得一提的是,為了完成更復雜的生物學功能,MAMs 上富集的蛋白質往往以蛋白質復合體的形式存在,如VDAC1 通過Grp75 與IP3R 形成的VDAC1-GRP75-IP3R 復合體、Mmm1/Mdm10/Mdm12/Mdm34 形成的內質網線粒體聯接復合物以及蛋白酪氨酸磷酸酶相互作用蛋白51(protein tyrosine phos-phatase-interacting protein 51, PTPIP51)和囊泡相關膜蛋白相關蛋白 B
(vesicle-associated membrane proteinassociated protein B, VAPB)形成的VAPB-PTPIP51 復合體[12]。其中VDAC1-GRP75-IP3R 和VAPB-PTPIP51 復合體在局部內質網-線粒體Ca2+轉移遞中發揮重要作用,內質網線粒體聯接復合物則被認為與脂質代謝相關。內質網-線粒體的互作除了在上述生物學過程中發揮作用外,也有研究報道其在炎癥反應和其他方面的功能,見表1。

表1 內質網-線粒體互作的生物學功能及其相關蛋白Tab.1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endoplasmic reticulum-mitochondrial interactionsand their associated proteins
2 內質網-線粒體互作與PSCI
PSCI 發病機制尚未完全闡明,但不少研究證實促進或抑制MAMs 的連接,介導內質網-線粒體互作的加強和減弱,可通過調控Ca2+穩態、脂質代謝平衡、線粒體動力學、自噬、神經炎癥進而對PSCI 的發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2.1 Ca2+穩態與PSCICa2+作為細胞內重要的信息傳遞者,其穩態的維持對于神經元功能的正常發揮至關重要。先前的研究早已證實腦缺血缺氧后,由于ATP 合成減少,興奮性氨基酸毒性等多種原因相互作用可導致大量的Ca2+內流,而胞內過多Ca2+觸發一系列的有害代謝反應被認為是腦缺血再灌注損傷的重要途徑[14]。同時,一項動物實驗發現[15]電針通過下調Ca2+濃度可以減少MCAO模型大鼠的腦梗死體積并改善其學習和記憶能力,這也從側面印證了鈣超載引起神經元的廣泛損傷可能是PSCI 發生的主要原因。
內質網-線粒體互作通過MAMs 形成的“高鈣通道”在維持Ca2+穩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其中VDAC1-GRP75-IP3R 復合體、VAPB-PTPIP51 復合體以及sigma-1 受體是MAMs 上調控鈣釋放與轉運,實現Ca2+平衡的關鍵蛋白。正常情況下,其可將適當的Ca2+轉運至線粒體基質,從而激活三羧酸(TCA)循環,刺激線粒體ATP 合成,這對于能量需求較大的神經元來說尤為重要。此外,HUTCHINS 等[16]發現抑制VDAC1-GRP75-IP3R 復合體介導的局部內質網-線粒體鈣轉移可降低突觸的可塑性與軸突的生長速度,這也進一步揭示了內質網-線粒體間的鈣離子調控對神經元的功能有重要影響。然而,在缺氧或者內質網應激的條件下,內質網和線粒體對Ca2+調控的緊密配合將會被打破,線粒體內不斷積累的Ca2+會觸發線粒體膜通透性的改變,致使大量細胞色素C(Cytoc)釋放介導細胞凋亡程序的啟動,而大量神經元的凋亡又會加重神經功能缺損[17]。CHANG等[18]研究發現糖尿病小鼠的認知缺陷與異常的MAMs 形成有關,而SIRT3 通過限制異常MAMs 的形成,減少VDAC1-GRP75-IP3R 復合物引起的線粒體Ca2+超載,可改善糖尿病小鼠的認知功能障礙。此外,有研究[19]發現金絲桃昔通過調控內質網-線粒體鈣信號轉導可減輕癡呆小鼠海馬區β淀粉樣蛋白的毒性和神經元凋亡進而改善其學習記憶缺陷。綜上所述,Ca2+穩態與內質網-線粒體交互密切相關,內質網-線粒體交互的異常可能通過影響Ca2+穩態而阻礙軸突的生長和神經元過度凋亡而參與PSCI 的發生與發展。
2.2 脂質代謝與PSCI大腦是僅次于脂肪組織的第二大脂質聚集地,脂質含量豐富已成為大腦的結構特征之一。大腦內豐富的脂質不僅參與構成細胞膜和髓鞘膜在維持大腦結構穩定方面發揮作用,更介導了神經的發生和突觸的連接在維持大腦功能方面有突出貢獻[20]。SABOGAL-GUáQUETA 等[21]的研究發現腦缺血大鼠海馬體中與神經傳遞有關的磷脂(主要是磷脂酰膽堿)大大減少,而外源性補充這類物質將對癡呆患者的記憶、情緒和認知有積極影響。與此同時,LIU 等[22]的脂質組學分析揭示了銀杏葉提取物很可能是通過恢復脂質代謝平衡來發揮其對癡呆小鼠神經保護作用。此外,一項薈萃分析顯示[23],脂質代謝紊亂引起的動脈粥樣硬化與卒中后癡呆風險增加有關;且卒中后使用他汀類降脂藥物可以降低認知障礙風險,這也進一步證明了PSCI 的發生可能與脂質代謝紊亂密切相關。
正常的脂質代謝依賴于各種脂質代謝酶的廣泛參與,而MAMs 上豐富的脂質代謝酶以及介導脂質在內質網和線粒體之間轉運的特性,使其在維持脂質正常代謝中發揮重要。研究[24]發現內質網-線粒體結構偶聯解離,可以引起磷脂合成過程受阻,并且一些脂質合成的關鍵限速酶如磷脂酰絲氨酸(phosphatidylserine,PS)合酶、N-甲基轉移酶2(phosphatidylethanolamine N-methyltransferase 2,PEMT2)僅在MAMs 存在更加證實了上述觀點。此外,多項研究[25-26]已證明阻斷是一種在MAMs 軸上富集的膽固醇儲存酶-膽固醇酰基轉移酶1/甾醇O-酰基轉移酶1(ACAT1/SOAT1)是可以減少淀粉樣蛋白病理并挽救AD 小鼠模型中的認知缺陷。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脂質的代謝異常是PSCI 發病的機制之一,而內質網-線粒體交互作用調控脂質代謝可能為PSCI 的治療提供了新的靶點。
2.3 線粒體動力學與PSCI線粒體動力學是線粒體內獨特的質量控制體系,包括了融合與分裂兩大基本事件。異常的融合與分裂往往會引起線粒體的損傷,而線粒體損傷介導的氧化應激、能量缺陷以及細胞凋亡等病理過程與卒中后神經元損傷密切相關[27]。LAI 等[28]的研究發現無論在體內還是在體外,腦缺血均會引起視神經萎縮蛋白1(optic atrophy protein-1, OPA1)(介導線粒體內膜融合的關鍵蛋白)的過度切割,并伴隨著大量的神經元凋亡和線粒體的形態異常,相反上調OPA1 的表達可有效緩解上述現象并減少腦缺血帶來的認知的損傷。除了線粒體融合障礙外,線粒體分裂異常也是引起PSCI 的重要因素。Drp1 催化的線粒體裂變是線粒體生物發生和維持健康線粒體所必需的。然而,在腦缺血期間,Drp1 的過度激活一方面可導致線粒體破碎而加重線粒體功能障礙;另一方面又可誘導Tau 的磷酸化而加重神經元毒性,特異性Drp1 抑制劑mdivi-1 已被證明可有效減少MCAO 小鼠體內海馬神經元的損傷而提高其學習記憶能力[29-30]。并且有研究[31]發現瘦素的神經保護作用是通過抑制Fis1 的上調和Mfn2 的下調,進而平衡線粒體動力學和改善線粒體功能來實現的,這又進一步證實了線粒體動力學的失衡是可能是PSCI 發生的關鍵環節。
內質網-線粒體互作在調控線粒體融合/分裂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FRIEDMAN 等[32]通過熒光顯微鏡觀察發現線粒體往往在與內質網接觸點處收縮,并隨后在此位點招募分裂蛋白,進而介導線粒體分裂的啟動。OUYANG 等人[33]發現雙側頸總動脈閉塞會引起大鼠海馬CA1 區MAMs 結構疏松和Mfn2 蛋白減少,而辣椒素可通過上調Mfn2、改善MAMs 結構疏松來提高大鼠學習記憶能力。此外,JIANG 等人[34]通過敲除小鼠海馬神經元中的Mfn2 從反面驗證了MAMs 調控的線粒體動力學在保護海馬神經元以及維持大腦認知功能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內質網-線粒體互作形成的偶聯域不僅是線粒體分裂/融合啟動的關鍵位點,更重要的是通過調控內質網-線粒體互作改善卒中神經元的線粒體動力學異常可成為治療PSCI 有效新途徑。
2.4 自噬與PSCI自噬是指細胞在自噬相關基因的調控下利用溶酶體降解自身受損細胞器和大分子物質的過程。目前學界普遍認為自噬在缺血性中風的病理過程中扮演了雙刃劍的角色。LIU 等[35]的一項基礎實驗發現雙側頸動脈閉塞大鼠的學習記憶障礙與海馬CA1、CA3 區錐體神經元內大量的自噬體的形成有關,但是也有報道發現敲低自噬蛋白(如Beclin 1)也可加重腦缺血引起的損傷。此外,自噬抑制劑消除了缺血預處理的神經保護作用[36]。由此可見,自噬的激活在腦缺血損傷中是有益還是有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細胞的自噬能力與自噬需求是否平衡,適度的自噬流量可清除細胞內受損細胞器來促進神經元存活,而自噬的過度激活會導致神經元的大量凋亡而加重認知缺陷。那如何利用好自噬這把雙刃劍呢?內質網-線粒體互作的出現或許給出了我們答案。
先前的研究[37]發現前自噬體標記ATG14 和自噬體形成標記ATG5 定位于MAMs。并且有研究[38]發現敲低STX17 或Mfn2 干擾MAMs 的形成可形阻斷自噬小體的發生,這也再次印證了MAMs 可能是細胞內促進自噬體形成與成熟的關鍵平臺。調控線粒體自噬以保護細胞免受線粒體代謝紊亂引起的損傷是目前治療缺血再灌注損傷的主流干預靶點。一項基礎研究[39]表明,調控線粒體自噬可明顯減少缺氧/復氧引起的心肌細胞凋亡。ZHAO 等[40]研究也證實了紫參活血湯改善癡呆患者的臨床表現與激活海馬CA1 區PINK1/Parkin 介導的線粒體自噬,挽救海馬神經元的線粒體結構損傷密切相關。有研究指出在線粒體自噬過程中,PINK1 通常是在MAMs 上富集,進而促進內質網-線粒體接觸和自噬體形成。更有趣的發現是,MAMs 除了能直接參與線粒體的自噬外,還可通過VAPB/PTPIP51 蛋白復合體影響Ca2+的信號傳遞間接介導線粒體自噬的發生。所以說,盡管如何調控自噬平衡,最大程度地發揮其優勢效應尚不明確;但毋庸置疑的是,MAMs 在自噬/線粒體自噬的發生發展過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通過MAMs 調節自噬平衡或許是未來治療PSCI 的研究熱點。
2.5 神經炎癥與PSCI卒中后的神經炎癥是PSCI 發生的關鍵病理生理途徑。一方面,其可引起大腦內常駐免疫細胞(如小膠質細胞、星形膠質細胞)的活化和外周免疫細胞的浸潤,導致白細胞介素-1β、腫瘤壞死因子、NO、超氧化物、活性氧等大量炎性介質的釋放而加重血腦屏障破壞、神經元損傷和腦水腫,最終加劇神經元凋亡并損害神經可塑性。另一方面,其又可通過擾亂全身免疫平衡,破壞自身免疫微環境而阻礙認知修復[41]。陳虹茹等[42]研究發現電針聯合重復經顱磁刺激改善癡呆大鼠的學習記憶能力與抑制神經炎癥反應有關。并且最近的一項Meta 分析發現全身性免疫炎癥指數與卒中后不良結局呈正相關,這也進一步證實了神經炎癥帶來的級聯損傷已成為PSCI發生的重要因素。
核苷酸結合寡聚化結構域樣受體蛋3(nucleotide-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like receptor protein 3, NLRP3)是介導上述炎癥反應的關鍵途徑之一。生理狀態下,其以游離的形式存于細胞質中,但在缺血缺氧的刺激下,NLRP3 以及其銜接子,即含有CARD(ASC)的凋亡相關斑點樣蛋白可被重新定位到MAMs 上,并在此位點進行組裝和激活。激活的NLRP3 炎癥小體不僅能加劇小膠質細胞的活化還能介導神經元的焦亡進而損害海馬神經元的發生,相反腹腔注射NLRP3 的抑制劑可逆轉上述過程改善認知損傷[43]。此外,一項miRNA 的量化分析[44]顯示炎癥反應性microRNA主要富集在MAMs,并且SHA 等[45]的研究證實電針可通過上調炎癥相關的miRNA-223 的水平來抑制NLRP3 炎癥小體的活化,從而改善MCAO 大鼠神經功能障礙。以上證據均表明,MAMs 功能異常引起的NLRP3 炎癥小體的激活可介導神經炎癥加重海馬損傷,而適當的調控則有可能促進缺血后神經元的恢復并減輕認知障礙,見圖1。

注:MAMs=線粒體相關內質網膜圖1 內質網-線粒體互作治療PSCI 的潛在靶點(本圖由Figdraw 繪制)Fig.1 Potential targets of endoplasmic reticulummitochondrial interactions for PSCI treatment(By Figdraw)
3 總結與展望
內質網和線粒體通過MAMs 實現的交互作用在維持細胞的正常生命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盡管目前通過調控內質網-線粒體互作改善PSCI的直接證據還比較少,但從當今對PSCI 發病機制的研究上來看,內質網-線粒體互作調控的多種生物學過程與PSCI 復雜的病理機制密切交織。本文從Ca2+穩態、脂質代謝、線粒體動力學、自噬、神經炎癥等方面總結了內質網-線粒體互作異常可能PSCI 發生發展的潛在途徑,并提出了調控內質網-線粒體互作可能是治療PSCI 的有效手段這一觀點。然而,考慮到MAMs 蛋白的復雜性與多樣性,內質網-線粒體交互的生物學功能還尚未闡明,內質網-線粒體互作與PSCI 的治療策略之間可能還存在新的交叉靶點,內質網-線粒體互作在PSCI 發揮作用的具體調節機制仍需進一步探討。未來,隨著對內質網-線粒體互作更深入的研究,我們將進一步揭示其在PSCI 病理過程的變化機制,以期為精準調控內質網-線粒體互作,靶向開發治療PSCI 的臨床藥物提供新的參考資料。
【Author contributions】CHEN Lulu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conception and writing of the paper; LUO Meng was contributed to the literature search and organisation; SU Kaiqi organised and produced the figures and tables of the paper; GAO Jing revised the first draft ;FENG Xiaodong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revisions of the final draft of the pape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the paper and its proofreading, and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paper as a whole; all the authors confirmed the final draft of the paper.
【Conflict of interest】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