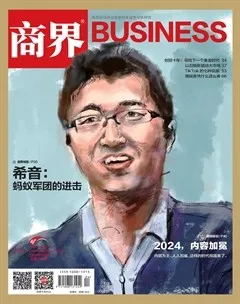什么是“新質生產力”?
王勇

今年兩會期間,“新質生產力”一詞無疑是最大的焦點之一,不僅被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更成為“C位”熱詞,引起廣泛關注。
與此同時,圍繞新質生產力,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了十多個產業領域,如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前沿新興氫能、新材料、低空經濟、量子技術、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
毋庸置疑,這些產業也將成為國家接下來重點扶持的對象和就業新導向。那么新質生產力意味著什么?又為何在當下這個時間點引發高度關注?
新質生產力是新時代的先進生產力
我們并不否認外部壓力傳導使我們不得不加快轉型發展,但從學術視角來看,地緣政治的變化只是外因,發揮主導作用的還是內因,也就是中國自身經濟轉型升級的內在要求。
中央在幾年前就已經提出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本質上是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著力點。
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加深理解。
一是供給側。
舊模式、舊生產力所生產的產品大多是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技術門檻比較低的,在國際競爭中已經逐漸失去比較優勢。我們的人口已經轉向負增長,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帶來的低成本優勢已經不在,中國自己的礦產資源、水資源,包括國際貿易環境,都已經無法持續支撐粗放低效的經濟增長模式。
二是需求側。
中國已經從物質短缺走向了產能過剩,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換句話說,過去要著力解決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問題,如今要解決從多到好、從粗到精的問題。
人們已經無法接受嚴重的環境污染。海外需求也一樣,歐盟已經啟動碳邊境調節機制(碳關稅),全世界都已經開始遭遇極端天氣,對于過度的碳排放,容忍度越來越低,我們已經不可能再走歐美那種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因此,逆全球化、地緣政治趨緊、國際友好氛圍的褪色只是我們向高質量發展和新質生產力轉型的一個加速器,關鍵還是我們自己發展的內在要求、底層邏輯。
“三高”是新質生產力的本質
概括地說,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它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
首先,新質生產力必須由“三高”(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的創新打底。
這一點與我們近幾年一直講的高質量發展、新發展理念、以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等都一脈相承,同時又突出了新的“三高”關鍵點。
它不僅是先進的生產力,不僅要有較高的科技含量,還要具備高效能、高質量,也就是生產資料的投入要更集約,生產方式要高效能,而且產出也必須是高質量的、環境友好的。
其次,新質生產力有明確的產業支撐。
新質生產力相比原來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并不是簡單的重復,更不是簡單等同于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調整的產業升級,不是農業升級為工業、工業升級為服務業的結構轉型。新質生產力更加強調的是質態,而不是業態。
比如采用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的選種育種,數字技術支撐的自動化種植、收割、深加工等,同樣可以構成新質生產力的質態。
戰略性新興產業不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它必須同時滿足兩點:
一是產業先進且意義重大,未來甚至可能會成為影響整體經濟的潛在增長率的重要產業;
二是相關的業態已經在一些國家形成較大規模,其實踐路徑已經相對明確,理論上的認知相對已經形成廣泛共識。
最后,新質生產力還能滿足戰略上的攻防兩用。
對中國而言,“三明治困境”(在整個產業鏈條上處于一種“夾層狀態”,像三明治當中的肉一樣,夾在上下游之間)就是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底部壓力大增,各種要素成本已經高企,相對于后起的越南、泰國等已經沒有成本上的優勢。
除了底部的壓力,頂部也有壓力,相對于美國等發達國家,我們產品與服務的技術含量尚不足,還處于微笑曲線的底部,在國際競爭中缺乏獨特優勢。
因此,中國經濟需要雙線作戰,謀求突圍。
怎么突圍?答案是只能往上走。
中國如果錯失這次機會,未必還能像前三次工業革命一樣有再學習、再追趕的機會。人工智能的威力可能遠遠超過蒸汽機、電力、互聯網。這也是中國加大力度、加快速度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戰略意義所在。
新質生產力的創新原則
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是創新,但創新的關鍵又是什么?
一個是市場化的創新,就是企業家群體、科學家群體的組合創新;另一個是政府主導的、舉國體制推進的創新。
比如,對于芯片,中國本來沒有必要由政府大力推動創新,靠市場換技術一步步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也可以,但美國“卡脖子”,中國馬上就面臨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加以應對的問題。
不僅如此,美國已經在關于中國人才引進、學生留學等領域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也就是說我國從產品市場到要素流動都面臨市場失靈問題,很多東西不再是我們愿意花錢就能買到的。
關于創新,經濟學上的基本原則還是政府著力于營造和維護創新的制度與文化環境,比如產權保護,尤其是知識產權保護,給企業家一個基于法治的、穩定的預期。創新的主力棒還是要交給市場、交給企業家,政府非必要不親自下場創新。
即便有些產業有必要通過舉國體制創新,也一定是通過新型舉國體制,比如以母基金投資的方式,或者支持基礎科研的方式,調動市場化的力量,絕不是政府親自入場、從頭做起。
新結構經濟學把產業分成五大類,分別是追趕型、領先型、轉進型、換道超車型和戰略型。
這五大類中,其他四類產業都需要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去發展,以市場為主,政府扮演的主要是因勢利導的次要角色。只有戰略型產業,即涉及國防安全或者經濟安全的產業,即使不符合當前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政府也要重點扶持發展,親力親為。其他四類產業的主力棒都應該交給市場。
比如高端芯片就是戰略型產業,它不同于服裝鞋帽,一旦斷供,不僅僅是我們的高科技產業鏈容易癱瘓,還可能造成我們錯失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窗口期。

因此在面臨“卡脖子”風險的情況下,政府就必須下場干預,比如持續投資中芯國際,再比如加強理工科人才的培養。但要謹防把新型舉國體制等同于計劃經濟的回潮。
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是創新,創新就意味著巨大的不確定性。新質生產力中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持續的投資,技術方向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未來產業更是連技術方向都不清楚,比不確定性還多了一層不可知性。
面對高度的不確定性、不可知性,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市場和企業家去試錯和創新,政府只能做相對確定且容易考核的工作,否則政府的創新資金很容易被套利。
市場和企業家又怎么去創新?最關鍵的就是金融市場和法治環境。
金融市場的關鍵是資本市場,只有通過健康發達的資本市場,企業家才有可能調動全社會的資本進行創新,投資者既分擔創新的風險,也共享創新的收益。
過去,中國主要是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市場,在銀行借債有利息,到期要還本付息,不利于支持高風險的創新創業項目。
因此,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就必須配套建設金融強國,尤其是健康友好的資本市場,這是中國目前一個巨大的短板,必須補齊。當然,資本市場不僅僅是指股市,還有天使投資、創業投資和私募股權投資,是一個完整的生態。
法治環境的關鍵是穩定預期和可信承諾。
以生物制藥為例,一個新產品的研發投入高達10億美元,如果知識產權保護不力,仿冒產品頻出,創新的企業就無法收回成本,更談不上創新的超額收益帶來的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