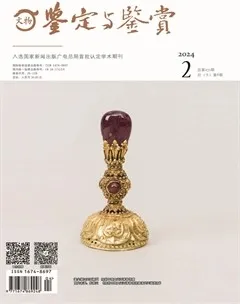重慶市江津區大路山東漢至蜀漢畫像石棺的圖像探究
朱心玥



摘 要:2018年4月,重慶市江津區的文物保護工作者在大路山發掘出了兩個磚室墓穴,其中一個是重慶地區罕見的合葬畫像石棺墓。根據墓葬形制、壁畫內容和出土器物,這座墓葬可以追溯到公元220—223年,該墓葬的出土畫像石棺畫面豐富多樣。墓葬藝術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歷史最悠久、根植最深的一種藝術形式。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區生存環境各異,這種長期的影響,使各地區的墓室藝術都有其對應的圖像特征。對于不同石棺畫像的分析與闡釋,可為漢化圖像志提供全面的資料,增進對漢代喪葬美術藝術的理解。
關鍵詞:畫像石棺;圖像程序;漢代墓葬美術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4.04.028
0 前言
2018年4月,重慶市文物保護工作者在重慶市江津區大路山上發掘了2個磚室墓穴。其中,M1出土畫像石棺2具,是重慶地區為數不多合葬畫像石棺墓。M1左棺長224厘米,上寬64厘米,高71厘米,內深51厘米。M1右棺長208厘米,上寬64厘米,高74厘米,內深53厘米。墓葬形制為豎穴土壙磚室墓,根據墓葬形制、壁畫內容和出土器物判斷,墓葬時間為公元220—223年①。
早在20世紀80年代,巫鴻先生便總結了四川石棺畫像的象征結構,即石棺上圖案的“配置意義”,上面刻畫的每一種題材,每一個畫面都是由目的與其他畫面組合而成的,多種題材與圖案裝飾石棺,從而一個個單獨的畫面形成了一個整體的“象征結構”②。
巫鴻認為,美術史的核心是圖像和形式,而基礎的圖像志辨識,為更加深入的圖像研究奠定了基礎。這一點,在前幾年的討論中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可以通過考察不同類型的圖像在歷史上經歷過的長期演變,以及這些長期演變中產生的諸多圖像在建筑和禮儀環境中聯系方式,來認識這些“圖像程序”③。通過對重慶市江津區大路山漢墓石棺上的畫像進行研究,探討其畫像的圖像程序,以期豐富現有的漢化圖像志。
1 大路山東漢至蜀漢畫像M1左右二石棺的圖像探究
1.1 棺蓋
兩具石棺的棺蓋中部皆為柿蒂紋。柿蒂紋中部為圓形的圖案,四周各散發一片花瓣,看似柿子的柿蒂(圖1)。這種花瓣的圖案是漢代時期民間常見的裝飾樣式,多見于墓葬之中。柿蒂紋在漢代墓葬裝飾中大量出現,這種紋樣也會出現在漢代生活物品之中。此類植物紋樣,表達了古人對于植物的原始信仰。柿蒂紋象征宇宙世界,在墓室頂部正中方位,也可以說明柿蒂紋宇宙中心地位的敘事空間。在漢代,人們認為天上神仙居于人間,有長生不死之術,所以漢代人在墓室頂部裝飾這種植物紋樣,表達了希望墓主能夠升天的訴求。
柿蒂紋在漢代墓葬中的出現,一方面是對西漢時期先民生活的一種美好憧憬,另一方面也體現出漢代人對于墓室頂部的一種特殊情結④。M1左棺除柿蒂紋外,另有龍銜壁、蟾蜍與鱘魚與二小人(圖2)。在漢代,蟾蜍被認為是祥瑞之性,東晉葛洪撰《抱樸子》曰“蟾蜍壽三千歲”⑤,因此蟾蜍具有長壽、不死之寓意。與此同時,因為魚的繁殖能力強,有著多子多孫、人丁興旺、家族昌盛的寓意。
1.2 前檔
二棺的前檔皆刻“雙闕圖”,為單闕廡殿頂。M1右棺的雙闕頂上均有兩只神鳥(圖3),M1左棺闕上只有一只神鳥(圖4),神鳥站在雙闕上,強調這不是凡間的城池,更像是一扇通往天堂的大門,用來指引人通過天門。這對闕標志著墓地的入口。它的意義與漢代墓地神道兩側的雙闕相同,即“死者世界”的入口。兩座宮闕的形象,象征著墓主在死亡之后會從天門進入天堂,這樣的設計意圖,引導靈魂進入墓室的“闕門”,也被不少學者稱為“天門”。四川、重慶等地東漢時期較為通行的天門觀念,表達了對墓主羽化而登仙,從西王母所主宰的昆侖仙境進入天國的期盼⑥。這也與古代的“天人感應”觀念相吻合。“天人合一”是漢代以來儒家哲學和道家思想共同遵循的核心觀念。古人認為,人死之后靈魂將升入天庭,因此人們在墓葬設計中通常以各種方式來表現其生前所向往的天國境界。
1.3 后檔
M1右棺后檔刻鳳鳥圖(圖5)。在古巴蜀地區的石棺圖像程序中,鳳鳥圖大量單獨出現,常在棺身一端,而另一端多為天門。漢時期石棺圖像程序的鳳鳥圖是一種宗教信仰或精神寄托。在巴蜀地區石棺圖像程序中,鳳鳥圖形經常出現在棺左右兩側。巴蜀地區石棺圖像程序的鳳鳥圖一般不直接表現人或動物的形象,而是將它人格化或者神物化。鳳是百鳥之王,是百鳥之王的象征。《說文解字》中有言:“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麟后,蛇頸魚尾,鸛鵽鴛思,龍文虎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于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⑦鳳與龍被認為是天地交合而生,故它們常與天、地等神合一,成為“天人感應”和“天人合一”的象征。在畫像中出現則是作為天國仙境的象征。
M1左棺后檔則刻伏羲女媧圖(圖6)。漢代墓葬中伏羲、女媧形象出現,反映出漢代社會民眾普遍存在對死后升天和長生不死渴望,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仙人崇拜”、神仙信仰現象。關于伏羲、女媧人首蛇身形象的記載,最早出現在先秦文獻中。在《山海經》中,有若干處關于伏羲女媧的記載,《列子》描述:“庖牲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圣之德。”⑧在這段文字中,伏羲女媧的形象被描述為人首蛇身,是神話傳說中的神祇。巧奪天工的匠人們便把伏羲女媧形象繪制在石棺上,伏羲舉日,女媧舉月,作為一種精神信仰的圖騰象征,形成一種來世宇宙的認知,在民間廣泛流傳。伏羲女媧為兩位仙人,在漢代,民間多有以伏羲、女媧作為死者升天升仙、不死的象征。
1.4 左側幫
M1右棺左側幫飾有水波紋、卷云紋、錢紋。錢紋是漢代普遍存在的錢幣崇拜觀念,也是大墓的主人所祈求的,希望來生能得到寶貴的財富。下欄為車馬出行圖,前方為女媧,人首蛇身,其次為一導騎,中間是墓主乘坐著軺車,后有伏羲(圖7)。信立祥認為漢代車馬出行圖具有兩種圖像學意義,一是表現墓主乘坐車馬去往墓地接收子孫的祭祀,二是表現墓主生前最榮耀的一段歷程⑨。巫鴻從蒼山石刻引發思考,認為車馬行列與車馬行駛方向象征了死后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起自祖廟而至于墓葬,第二個階段則是起自墓葬,然后被期望著離開墓葬而抵達天堂。車馬出行圖這一題材頻繁地出現在漢畫像石中⑩,突出了墓主在天國出行與到達仙境的理想,也表現了漢代人“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k中的“事死如事生”的觀念。這種觀念深刻地影響了漢以后的墓葬文化,在漢代以后的唐代大墓中,墓道旁也多有車馬出行圖的身影。
M1左棺左側幫上欄內左格飾纏帶紋,中格飾菱形聯璧紋,右格為勝紋。下欄根據人物組合可分為四組畫面,從左至右依次為:樹下跪拜圖、對拜圖、相擁圖、胡人執劍圖(圖8)。漢畫像畫面繁密,不同主題的畫面安排在同一側卻十分有序,為了使畫面不留空白,工匠在上欄填上裝飾紋,漢畫像繁密的特征與儒家美學的審美觀念“仁”息息相關,表現出“大而全”的特點l。
1.5 右側幫
M1右棺的右側幫下欄為樂舞百戲圖(圖9),在漢畫像石中,樂舞百戲圖是較為常見的題材,它富于變化的圖像組合同樣展現了漢代人的生死觀念m。圖中有飛劍、吹笛、跳丸者或作舞蹈狀,人物形象刻畫得栩栩如生,表現了漢代人豐富多彩的娛樂生活。漢代人將日常生活場景帶入墓室,從而更為生動地展現亡靈的美好生活。
M1左棺的右側幫下欄為鳳鳥銜簋圖(圖10)。簋是古代貴族用來盛放食物的重要器皿,在商周禮制中,簋與鼎于祭祀時搭配使用。鳳鳥銜簋與瀘州市麻柳灣崖墓鳳鳥銜鼎類似,其意圖是祈求墓主能夠順利升天。
2 漢代畫像石棺藝術的美學淵源
兩漢時期,神仙巫術信仰的濃厚氛圍對當時的社會有很大的影響。人們對生死和超自然現象的探索和思考也在不斷增加。漢朝初期,黃老之學盛行,升仙思想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迅速發展起來的,漢代人對死后能升仙的渴望日益迫切。《抱樸子》有云:仙有三等,上等肉身飛升,稱“天仙”;中等長生不死,優游于名山海島,稱“地仙”;下等肉身不得不死,死后身心蛻化,永生于天上、仙山或“地下主”,稱“尸解”n。
“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為太平道,修為五斗米道。”o巴蜀地區自古盛行巫術,五斗米道或繼承了該地的仙道傳說,進而發展成為長生不死的觀念。墓葬是現實生活的另一面鏡子,古人將生活中的事物融入墓葬的設計與建造中,在墓葬圖像里可體現出當時的社會環境,而五斗米道的思想也反映在喪葬儀禮之中。東漢巴蜀地區為五斗米道的盛行區域,亦是漢畫像繁盛的區域。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追求永恒的生命和超凡的境界,漢代人開始對自己的葬具進行更精致華美的設計,力圖通過外在的形式來達到內在的目的。在這一過程中,漢代人拋棄了脆弱而易損的木材,轉而選擇最為堅硬和優美的材料,如石頭、玉石等,來鑄就自己死后的居所。石頭的堅硬特性被漢代人民賦予“永恒”的觀念,人們相信通過使用石材能達到升仙的目的,在這一時期,石棺成了諸多仰慕升仙思想的人選擇的葬具p。石棺寄托著人們對于身后生命的延續和永恒的希望。相信使用石棺能夠保護身軀,不受外力侵害,期望石棺上的畫像可以將人的靈魂引向升仙的道路。
兩漢時期,石棺上的畫像,是一種獨具風格的藝術形式。在葬具的設計上,人們在棺中添加了許多神秘的圖案,以便幫助他們在死后實現升仙的愿望。他們認為,在石棺中刻下代表神仙世界的西王母、伏羲女媧、“四方位神”等,可以將石棺轉化為一個微型宇宙,使自己獲得神仙的眷顧,在神仙的帶領下以確保升仙之路的順利。與此同時,這些石棺畫像內容豐富,主題多樣,除了表現神仙世界外,還有社會生活、歷史事件、神話傳說、祥瑞題材等,有著精湛的技藝。石棺畫像被用于裝飾石棺,以寄托死者對來世的希望和對美好生活的渴望。
重慶市江津區大路山M1左棺的棺蓋為柿蒂紋,象征宇宙天國,而龍銜壁與蟾蜍、魚圖案則相輔相成地表明希望墓主能順利進入天國并長生不死。前檔鳳鳥代表著南方之神,象征太陽崇拜,與代表著天國之路的雙闕共同置于一圖,代表著期望墓主能通過神道順利升天。后檔的伏羲女媧圖具有生殖崇拜、陰陽調和的含義。漢代時期,夫妻合葬較為普遍,以此推斷M1左棺和M1右棺或為夫妻合葬于同一磚室墓。M1左棺右側的鳥銜簋圖意味著墓主順利升天。考慮到漢代有神樹崇拜的觀念,神樹形象具有長生升仙、子嗣繁茂等意義,故左側幫圖像應與漢代的夫妻觀共同解讀,墓主夫婦在兒孫們的寄望下于黃泉之路相見,并共赴天國,表達了生命的延續。
M1右棺的棺蓋同為柿蒂紋,象征天國仙境。前檔的朱雀站在雙闕上,表明墓主在朱雀的引導下進入升仙之路。后檔為朱雀,引導死者的靈魂升天,也有祥瑞避邪之意。左側為車馬出行圖,意味著墓主在伏羲和女媧的引導下乘坐車馬進入天國。右側則是樂舞百戲圖,具有娛神的功能,展示了墓主升仙后的美好生活,體現了漢代“事死如事生”的觀念。
山東的漢代畫像石表現出豐富的儒家思想,以歷史典故、西王母像等神仙故事為主要題材,人物形象莊重嚴肅,富有權威感。河南的漢代畫像石題材比較廣泛,天文圖像是其最獨特的內容。四川地區的漢代畫像石題材獨樹一幟,因其在秦漢時具有良好的經濟基礎,因此四川畫像石除了表現部分神話故事以外,大部分刻畫了現實生活,以精細的雕刻和活潑的姿態為特點q。
簡而言之,漢朝升仙觀念的出現,讓人們產生了一種光明的信仰,他們渴望在死亡之后得到永生,達到一種更高層次的境界,并以此作為對長生不死的追求,而作為達到這個目的的一種方式,喪葬藝術也就成了他們表達升仙志向的一個重要標志。無論是葬具的華麗與神秘,還是葬儀中所蘊含的道教思想與佛教理念,都無法讓人們真正轉變為升仙的存在。漢代升仙思想興起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人們對永恒生命的追求,卻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人們對死后未知境界的恐懼。無論是墓室、棺槨、棺槨上的圖案或雕刻,抑或是建筑構件、裝飾紋樣,都是漢代人在生前對于永生所做過的努力。因此,通過葬具來實現升仙的企圖,無疑是人們對于死亡的一種恐懼和抗爭。
3 結語
從時間和空間的角度來看,墓室美術的意象關系是一種藝術形式和區域特征之間的聯系。內容涵蓋了不同時代、地區、題材等。石棺作為古代人類的墓葬器具,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和文化記憶,通過探討石棺畫像所反映出來的社會和歷史背景,有助于今人對漢時的歷史和文化進行深入的研究與還原。
漢代的石棺畫像具有一定的程序結構,大路山東漢至蜀漢畫像石棺也不例外。漢人想象力豐富,將對于仙界的向往與死后原有生活的延續思想表現在石棺上。雖已有不少學者總結漢代畫像石棺的類型與含義,但隨著新的石棺不斷被發掘,仍需要人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它們進行分析與闡釋,不斷地從新的角度加以深化和理解,為現有的漢畫圖像志增添新的內容和視角,通過研究不同石棺畫像的共性和特點,為漢化圖像志提供更加全面和系統的資料,從而可以對漢代墓葬美術有一個更深的認識。
(文章圖片均引自: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江津區文物管理所.重慶市江津區大路山東漢至蜀漢磚室墓發掘簡報[J].四川文物,2019(6):5-20,2,97.)
注釋
①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江津區文物管理所.重慶市江津區大路山東漢至蜀漢磚室墓發掘簡報[J].四川文物,2019(6):5-20,2,97.
②⑩p巫鴻.禮儀中的美術[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③巫鴻.空間的敦煌[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
④劉焱.漢畫像柿蒂紋空間性研究[J].雞西大學學報,2015(6):53-55.
⑤n葛洪.抱樸子內篇[M].張松輝,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⑥秦臻.圖畫天地:沈府君闕的視覺程序與象征結構[J].古代墓葬美術研究,2017(00):91-110.
⑦許慎.說文解字[M].湯可敬,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
⑧葉蓓卿.列子[M].北京:中華書局,2018.
⑨王巍.中國考古學百年史(1921—2021):第三卷:上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
k胡平生.禮記[M].張萌,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7.
l朱存明.民俗之雅:漢畫像中的民俗研究[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m劉茜.漢畫像石圖像藝術與漢代生死觀[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o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2012.
q潘馳宇,劉曉峰.中國繪畫概論[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