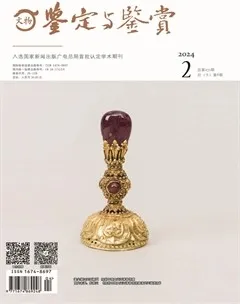淺析回譯在文物公示語翻譯中的應(yīng)用
桑雨心 雷簡
摘 要:在“講好中國故事”的背景下,博物館展品的英文公示語至關(guān)重要。婦好墓出土文物作為中國國家博物館的一張?zhí)厣涔菊Z的英文翻譯卻有所缺失,未能有效發(fā)揮其文化傳播的作用。基于此,文章著眼于婦好墓出土文物的英文公示語,依循回譯性原則,淺析回譯在英文公示語中的應(yīng)用及可能性,進(jìn)而為英文公示語在傳播展品內(nèi)涵與文化方面提供參考,同時也為同類文物公示語的英文翻譯提供可能性。
關(guān)鍵詞:回譯;文物翻譯;公示語;中國國家博物館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4.04.020
博物館是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隨著全球化發(fā)展,中外文化交流愈加頻繁,博物館中越來越多的文物增添了英文說明。為文物增添英文說明能夠增強(qiáng)加強(qiáng)國際游客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理解,是對外宣傳的一種重要方式。文物翻譯不僅要考慮歷史學(xué)、考古學(xué)知識,更要考慮翻譯文本的信息準(zhǔn)確性和文化互動性。師新民在《考古文物名詞英譯探討》一文中提出文物翻譯需遵循回譯性;陳志杰和潘華凌認(rèn)為,回譯法是翻譯研究、翻譯質(zhì)量評價和研究兩種語言間中相互關(guān)系的方法,它不但可以檢驗譯文的準(zhǔn)確性,還可以為觀測不同語言文化差異提供一個遠(yuǎn)景視角。探討回譯在文物翻譯中的應(yīng)用有助于借譯文進(jìn)行文化傳播與交互。
本文搜集分析了中國國家博物館(以下簡稱“國博”)古代中國展區(qū)婦好墓展品介紹,發(fā)現(xiàn)部分文物缺少英文譯文或存在譯文不準(zhǔn)確的問題,因此通過回譯對其英文譯文進(jìn)行補(bǔ)充、改進(jìn),并探討回譯在文物翻譯中的應(yīng)用及作用。
1 回譯的概念
回譯(back translation)是一種翻譯活動,沙特爾沃思(M. Shuttleworth)和考伊(M. Cowie)的《翻譯研究詞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對“回譯”的界定是:Back-transla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a text which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a given language is retranslated into SL(回譯是一個將被翻譯為某種語言的文本重新譯回源語的過程)。馮慶華先生認(rèn)為回譯是以譯文為原文的翻譯。它的特殊之處在于其過程是從譯文回歸到源文本。李全安等則從語言學(xué)角度出發(fā),指出回譯就是“將甲語種譯入乙語種后又再作為素材引用從乙語種譯回甲語種或從第三第四語種譯回原始語種”。
回譯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為有本回譯,一類為無本回譯。顧名思義,有本回譯即有原文可供參考,故而可以通過回譯檢驗譯文是否較好地傳達(dá)了原文的含義,而無本回譯則無完整原文可考。由于同一時代或同一類型的文物存在相似性,其文字介紹亦存在相似性,故仍有相似原文可視作局部原文作為參照。此外,無論是作為“缺乏原譯的回譯”,還是作為異語寫作的回譯,都不是絕對的“無根回譯”。無本回譯雖沒有原文,但其傳達(dá)的文化是有根的。故筆者認(rèn)為,若無本譯文回譯后能夠較為明確地傳達(dá)源語本意和文化,且與同類型文本的表達(dá)無較大出入,則可視為優(yōu)質(zhì)。聶佳偉基于王正良的“未至譯”理論提出的“無本無至譯”,也支持了這一觀點(diǎn)。
本文搜集整理了中國國家博物館婦好墓出土文物公示語,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部分公示語的翻譯存在缺失、翻譯不當(dāng)?shù)膯栴}。本文將運(yùn)用回譯對其中的文物公示語進(jìn)行改進(jìn),并通過對回譯過程的研究分析翻譯對文化交流的作用。
2 對回譯在婦好墓文物公示語翻譯中的分析
回譯一直被看作是翻譯研究、翻譯質(zhì)量評價和研究兩種語言間相互關(guān)系的方法。在文物翻譯中運(yùn)用回譯法不但能檢驗翻譯的準(zhǔn)確性,還能根據(jù)語言關(guān)系研究中英文化的差異,也能為文物翻譯的“歸化”和“異化”提供思考途徑。因此,本文將應(yīng)用回譯法檢驗婦好墓出土的三件藏品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官方網(wǎng)站所公示的英文介紹。其分別是“婦好”青銅偶方彝、“婦好”青銅鸮尊、“婦好”青銅三聯(lián)甗。
例1:“婦好”青銅偶方彝部分簡介
源文本:器由器身與器蓋兩部分組成,形似兩尊方彝聯(lián)成一體。器身呈長方形,口部微斂,方唇長邊一側(cè)有7個方槽,另一側(cè)有7個尖槽;肩部內(nèi)凹為弧形;腹部呈長方形,體腔中空,兩端置附耳,腹下部略內(nèi)收;整器以云雷紋為地,飾鳥紋、夔龍紋、饕餮紋及三角紋,異常華美。
譯文:“Fu Hao” Bronze Paired Fangyi (wine vessel)
The vessel is composed of two parts,the body and the cover, which together resemble the combination of two fangyi. The body is rectangular, with a slightly converging mouth. There are seven square grooves on one side of the long edge of the square lip and seven pointed grooves on the other side. The shoulders are concave and arc-shaped. The abdomen is rectangular with a hollow body cavity, the two ends are attached to the ears, and the lower part of the abdomen is slightly retracted. The entire vessel is covered with cloud and thunder patterns and decorated with birdpatterns, kui dragon patterns, taotie patterns and triangle patterns, making it exceptionally gorgeous.
分析:可以看出,源文本較為簡潔客觀,所以回譯后大部分能與源文本對應(yīng)。但由于源文本包含一定具有強(qiáng)烈的古語特色或中文專有的詞匯,如“四轉(zhuǎn)角均置扉棱”“腹下部略內(nèi)收”,故在漢譯英時需先將中文意譯再進(jìn)行漢譯英,如此會使源文本有一定的變形。所以回譯后專有詞的英文并不能完全對應(yīng)其源文本,而更多對應(yīng)的是源文本的二次加工文本,如對“The vessel is composed of two parts,the body and the cover, which together resemble the combination of two fangyi”進(jìn)行直接回譯則為“容器由兩部分組成,這兩部分是身體和蓋子,它們一起像兩個方彝的組合”。王克非基于對漢英/英漢對應(yīng)語料庫的考察,發(fā)現(xiàn)譯本擴(kuò)增現(xiàn)象。也就是說在漢譯英時,英文譯文出現(xiàn)了一定的顯化(explicitness),即譯者增添了解釋性語言、連接詞以增強(qiáng)譯文邏輯性,這導(dǎo)致回譯后相比于源文本,回譯文略顯冗長。
柯飛提出,譯文是否忠實于原文,可以說是檢驗翻譯優(yōu)劣的永恒標(biāo)準(zhǔn)。但是忠實并不代表刻板,故不能將以回譯檢驗準(zhǔn)確性的標(biāo)準(zhǔn)定為字字對應(yīng)。正如穆善培先生所認(rèn)為的:“要忠于(或基本忠于)原著精神而又英文通達(dá)為目的。”
例2:“婦好”青銅鸮尊部分簡介
源文本:“Fu Hao” Owl-shaped Bronze Zun (wine vessel)
This marvelous artifac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pinnacle of bronze art in the late Shang period. The shape of this zun is a standing owl balanced with a tail and two feet arranged both functionally and aesthetically. After the technical exploration of the pre-shang period the bronze casting of the late Shang witnessed a huge leap forward in both smelting and pattern-making techniques. (By Huang Yi).
譯文①:這件神奇的工藝品堪稱商代晚期青銅藝術(shù)的巔峰之作。該尊的造型是一只雙腳平穩(wěn)站立、帶有尾巴的鸮,這種造型設(shè)計同時兼具功能性和美感。經(jīng)過商代前期的技術(shù)探索,商代晚期的青銅鑄造在冶煉和紋樣技術(shù)上都有了巨大的飛躍(筆者譯)。
譯文②:婦好鵠尊可謂商后期青銅器造型藝術(shù)的鴻篇巨制。整器外形呈站立的猛鵠,下垂的鵠尾在構(gòu)思上匠心獨(dú)具,形成與雙足平衡的三點(diǎn),功能與審美二者兼?zhèn)洹=?jīng)過商前期的技術(shù)探索,商后期的青銅器鑄造無論在冶鑄工藝還是在紋樣制作工藝方面,均有巨大飛躍(中國國家博物館官網(wǎng)譯)。
分析:該段英文介紹回譯后與原文絕大部分內(nèi)容重合,無較大出入,故而可認(rèn)為英文譯文較好地、基本完整地傳達(dá)了原文內(nèi)容。值得注意的是,“鸮”一字雖指貓頭鷹,卻為古稱,蘊(yùn)含了古代文化內(nèi)涵,與今名不完全相等,故在展品名稱和介紹中應(yīng)將其拼音添注在旁。此外,原文中不存在需要進(jìn)一步解釋的專有名詞或文言表達(dá),故翻譯難度較小,能較好地與原文對應(yīng)。
例3:“婦好”青銅三聯(lián)甗部分簡介
源文本:“Fu Hao” Triple Bronze Yan (steamer)
The “Fu Hao”triple bronze yan (steamer)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upper part (three cauldrons) and the lower part (the joint rectangular body). It is similar infunction to the modern stove, lending it its name “the triple yan.” Fires can be lit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yan, which can also function as a steaming apparatus. The triple yan is able to cook several kinds of food at the same time, and represents one of the earliest ancient bronze cookers with multiple vessels existing today.
譯文①:“婦好”三聯(lián)甗(蒸鍋)由兩部分組成:上部—三鼎,下部—相連的長方體。它在功能上與現(xiàn)代火爐相似,因此得名“三聯(lián)甗”。甗的下部可以生火,也可以用作蒸設(shè)備。三灶能夠同時烹飪多種食物,是最早的同時具有多個容器的古代青銅炊具之一。
譯文②:此甗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為甑,用以盛物,下部為鬲。該甗由并列的三個大圓甑和一長方形承甑器組成。
此段介紹在官網(wǎng)并無完整的相應(yīng)的原文,屬于較為特殊的無本回譯類型。由上文筆者翻譯可知,該英文公示語回譯基本能完整傳達(dá)其所想表達(dá)的含義。
但與其部分原文對比后,可見“甑”“鬲”二字在英文公示語中的缺失,雖無礙表意,卻在傳播文化的層面上有所缺失,無法回溯到“文化的根”。回譯視角下認(rèn)為這屬于文化未返回,應(yīng)該將二字的拼音以括號的形式分別注解在“上部”“下部”一旁。
分析:以上三件展品名稱的英文翻譯均在原有中文上增加了對展品原功用的注釋,如“wine vessel”“steamer”,以便于英文讀者更好理解展品的基本信息和內(nèi)涵。
除展品介紹以外,可對展品介紹中的部分生僻字、文言文、相關(guān)背景、同類展品基本信息和隱性文化內(nèi)涵進(jìn)行補(bǔ)充講解。就婦好墓出土文物而言,以下內(nèi)容可作為回譯后與源語相比多出的補(bǔ)充講解:“鸮”“甗”等字的解釋;青銅器的產(chǎn)生、沒落、基本技法、常見器物等信息的介紹;禮器的定義、用途、重要意義、相關(guān)歷史文化背景等。以上信息對于大多源語為母語的參觀者而言是常識,而對于外國參觀者而言是充分理解展品應(yīng)當(dāng)具備卻實際不具備的背景知識,故是相當(dāng)重要的。這正如江慧敏、王宏印采用無本回譯法研究高羅佩翻譯《狄公案》時所發(fā)現(xiàn)的一般,高羅佩為外國讀者增補(bǔ)部分中國文化背景(狄仁杰作為偵探卻能一變成為擁有較多醫(yī)藥知識的行醫(yī)進(jìn)行查案的原因)以助理解。額外提供背景相關(guān)信息有助于更好地傳達(dá)原文所蘊(yùn)含的內(nèi)涵。此亦是回譯帶給我們的新的啟發(fā)。
3 回譯在文化翻譯與交流中的作用
回譯一般被認(rèn)為是檢驗翻譯準(zhǔn)確性、有效性的方法,用回譯法對譯文進(jìn)行檢驗有利于提升譯文的準(zhǔn)確性,提升文化傳播的有效性。此外,師新民提出回譯性原則是文物翻譯應(yīng)遵循的原則之一。此處的回譯性原則是指英文譯名的形式與結(jié)構(gòu)應(yīng)盡量與中文相似。這樣中文母語者聽到其英文譯名時能想到其對應(yīng)中文,有利于文化與信息傳播的雙向性。
但是,在回譯過程中會發(fā)現(xiàn),譯文并不完全與源文本對應(yīng),有時甚至?xí)霈F(xiàn)偏離。一個文本被翻譯為目的語后,會滲透、吸收、利用目的語文化,又重新翻譯回源語可能會對源語言文化產(chǎn)生影響。故翻譯的偏離不符合回譯性原則,但這并不一定是負(fù)面的,反而反映出文化的交織和互相影響,從而提供一條觀照本文化的途徑。
翻譯活動是一種文化交流、關(guān)照并且融合的過程。通過翻譯的“異化”,源語言的文化被轉(zhuǎn)化為具有譯入語特色的一種文化交織體。“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張力作用下,任何譯本都是不同文化/文學(xué)體系間沖突和妥協(xié)的結(jié)果”,故將文化交流與傳播看作原封不動的輸出是一個偽命題。翻譯學(xué)就是要研究“文學(xué)現(xiàn)象穿越語言的界限通過翻譯而在目的語環(huán)境中得到接受的過程”。在翻譯中,譯者需要參考?xì)v史學(xué)、考古學(xué)、語言學(xué)知識,并對譯入語文化進(jìn)行研究,經(jīng)過這一系列加工,譯文會發(fā)生變化,重新譯回源文本時就會出現(xiàn)文本的變異。回譯者往往要通過一系列過程復(fù)現(xiàn)文本變異的發(fā)生軌跡。因此,回譯成了一種逆向思考、探尋并且能再現(xiàn)文化交往發(fā)生軌跡的過程。
總而言之,回譯不僅是一種翻譯方法,也是一條文化觀照的路徑。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qiáng)與國際地位的提升,我國的文化自信越來越強(qiáng),譯出的任務(wù)也會越來越重。王寧先生指出:“翻譯的重點(diǎn)就應(yīng)該從外翻中轉(zhuǎn)變成中翻外。也就是說要把中國文化的精品、中國文學(xué)的精品翻譯成世界上的主要語言—英文,使它在世界上擁有更廣泛的讀者。我想這也是全球化時代文化翻譯的另一個方向。”
如今,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希望了解中國文化,博物館作為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應(yīng)將更多的中國歷史文化珍寶介紹給世界。英文公示語將文物作為一張名片展示給世界,更好地彰顯中國文化軟實力。未來,隨著譯出文本的增多,回譯活動也會愈來愈頻繁。譯者不應(yīng)機(jī)械地使用回譯法,僅僅將其當(dāng)作文本檢驗的工具,而應(yīng)通過回譯法發(fā)掘文化之根所在,深入理解本國文化,同時覺察不同文化特質(zhì)。將譯文作為文化融合的產(chǎn)物來看待,在翻譯工作中融合理解,產(chǎn)出更好的譯本,在推進(jìn)文化全球化的同時,堅持本國文化的民族性與獨(dú)特性。
4 結(jié)論
婦好墓出土文物多為青銅器,中文公示語具有古語色彩濃厚、重復(fù)詞匯多、短句多等特點(diǎn),與英文用語習(xí)慣有著較大出入。因此,回譯后的文本與源文本存在一定偏差。通過筆者分析,這些偏差的存在不一定證明了譯文不忠于原文,故回譯法不應(yīng)被機(jī)械地視為檢驗英文譯文的工具。但同時,從回譯視角來看,在文物翻譯中是否達(dá)成以下兩點(diǎn)要求尤為重要:一是能簡明扼要地傳達(dá)文物原有內(nèi)涵和文化;二是能保留文化根源。倘若可以實現(xiàn)以上兩點(diǎn)目標(biāo),則可以較好地實現(xiàn)以英文公示語傳達(dá)中國文化的目的。
文物翻譯是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媒介,不僅要保留本民族的文化內(nèi)核,還需讓譯出語國家的讀者清晰明了地領(lǐng)會譯文。這需要譯者運(yùn)用回譯對兩種不同的語言文化進(jìn)行觀察、觀照、對比、分析,以挖掘二者之間的不同及聯(lián)系,在此基礎(chǔ)上譯出忠于原文且具有文化融合特質(zhì)的譯文,較好地傳達(dá)文物所蘊(yùn)含的內(nèi)涵和文化。■
參考文獻(xiàn)
[1]Mark Shuttleworth,MoiraCowie.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陳志杰,潘華凌.回譯:文化全球化與本土化的交匯處[J].上海翻譯,2008(3):55-59.
[3]馮慶華.文體翻譯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
[4]江慧敏,王宏印.狄公案系列小說的漢英翻譯、異語創(chuàng)作與無本回譯:漢學(xué)家高羅佩個案研究[J].中國翻譯,2017(2):35-42.
[5]柯飛.翻譯中的隱和顯[J].外語教學(xué)與研究,2005(4):303-307.
[6]李全安.文學(xué)翻譯275問[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7]穆善培.歷史文物漢譯英的忠實與通順問題[J].上海科技翻譯,1991(3):11-15
[8]聶家偉.回譯的類型與意義探究[J].西南石油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9(5):98-105.
[9]石春讓,肖佳麗,趙秋蘋.回譯理論指導(dǎo)下中國古代建筑術(shù)語的翻譯策略[J].翻譯與傳播,2022(2):144-164.
[10]師新民.考古文物名詞英譯探討[J].中國科技翻譯,2007(3):61-62,35.
[11]王建國.回譯與翻譯研究、英漢對比研究之間的關(guān)系[J].外語學(xué)刊,2005(4):78-83,112.
[12]王寧.翻譯的文化建構(gòu)和文化研究的翻譯學(xué)轉(zhuǎn)向[J].中國翻譯,2005(6):5-9.
[13]王宏印.從“異語寫作”到“無本回譯”:關(guān)于創(chuàng)作與翻譯的理論思考[J].上海翻譯,2015(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