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苦行”到“思惟”
—— “釋迦思惟出山像”諸問題考①
曲 藝(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 設(shè)計(jì)學(xué)院,江蘇 南京 210013)
一、研究對(duì)象與問題
美國(guó)底特律藝術(shù)中心(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藏一尊木雕干漆、貼金施彩人物坐像,高29.8厘米,寬20.6厘米,深16.5厘米(圖1)。人物頂有肉髻,肉髻下的螺發(fā)與面部短小的卷胡相呼應(yīng),髻珠凸顯于頭部正前方的發(fā)髻之中,卷曲的絡(luò)腮胡后一對(duì)大耳,肥大耳垂上的耳洞暗示了此像此前可能配有耳飾。人物垂頭并側(cè)向左下方,頷抵于相疊的雙手之上,雙手則伏于向前支起的左腿膝蓋上,右腿彎曲,水平放于身體前面。紅色袒右衣鋪于底座,露出的鎖骨、肋骨和枯瘦的手臂和小腿表現(xiàn)了人物肉體的羸弱;而低垂的雙眼如同凝望深淵一般,賦予人物深邃的精神力量。②因其肉體和精神狀態(tài)的動(dòng)人描繪,此尊木雕被視作東亞最感人的雕塑之一。參見Birgitta Augustin.Like stars seen on the bottom of deep wells’.Recalling a Shakyamuni in Detroit[J].Orientations, 2021,52(1): 74-76.木雕后背長(zhǎng)條形開口,內(nèi)原藏有佛經(jīng)。博物館將其命名為“釋迦苦行像”(Shakyamuni as an Ascetic),并將其制作時(shí)間定為13世紀(jì)末至14世紀(jì)初之間。[1]

圖1 元代,“釋迦苦行像”,高29.8厘米,寬20.6厘米,深16.5厘米,美國(guó)底特律藝術(shù)中心藏
筆者粗略搜索后發(fā)現(xiàn),海內(nèi)外各大博物館也藏有大量明清時(shí)期此類坐姿的青銅人物坐像,如美國(guó)賓夕法尼亞大學(xué)博物館(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圖2)、普林斯頓大學(xué)博物館(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圖3)、中國(guó)國(guó)家博物館(圖4)、遼寧省博物館(圖5)、洛陽(yáng)博物館(圖6)、故宮博物院(圖7)、美國(guó)克利夫蘭藝術(shù)博物館(圖8)、美國(guó)舊金山亞洲藝術(shù)博物館(圖9-10)、英國(guó)維克多與阿爾伯特美術(shù)館(圖11)等,以及其他材料的此類坐姿的坐像,如彩瓷(圖12)和玉(圖13)。

圖2 元代,“釋迦牟尼佛冥想坐像”,81厘米高,83.3厘米寬,61厘米深,美國(guó)賓夕法尼亞大學(xué)博物館藏

圖3 元代,“羅漢苦行像”,高28厘米,寬31厘米,深32厘米,普林斯頓大學(xué)博物館藏

圖4 明代,“釋迦伏膝冥思像”,鎏金青銅,中國(guó)國(guó)家博物館藏

圖6 元代,“雪山大士像”,銅像,高87.5厘米,洛陽(yáng)博物館藏

圖7 明代,“達(dá)摩坐像”,銅像,故宮博物院藏

圖8 元代,“釋迦思惟出山”,鎏金銅像,高44.2厘米,寬31.8厘米,美國(guó)克利夫蘭藝術(shù)博物館藏

圖9 14世紀(jì),“釋迦牟尼佛坐像”,鎏金銅像,美國(guó)舊金山亞洲藝術(shù)博物館藏

圖10 明末清初(17世紀(jì)),“釋迦牟尼苦行像”,鎏金銅像,高55.9厘米,寬47.9厘米,身55.9厘米,美國(guó)舊金山亞洲藝術(shù)博物館藏

圖11 17世紀(jì),“佛苦行坐像”,銅像,英國(guó)維克多與阿爾伯特美術(shù)館藏

圖12 明(1474年),“釋迦牟尼佛”,彩瓷,美國(guó)舊金山亞洲藝術(shù)博物館藏

圖13 “悉達(dá)多太子苦行像”,玉雕像,美國(guó)舊金山亞洲藝術(shù)博物館藏
這些坐像具體表現(xiàn)各有不同:首先,一些坐像頭部有肉髻、髻珠或白毫等釋迦出山悟道成佛后身體所具佛相特征,③關(guān)于髻珠的分辨,參見王靜嫻,常青.試論佛頂髻珠的來源與發(fā)展[J].故宮博物院院刊,2022(10):32-46、139.而另一些則沒有;另外,坐像人物在面容表情和身體狀況上也有較大差異,其中一些坐像人物枯瘦,陷入深邃的沉思中,另一些坐像人物身體圓潤(rùn),面露微笑,祥和而滿足,還有一些坐像并沒有強(qiáng)調(diào)身體狀況,人物面容平靜;此外,多數(shù)坐像為袈裟搭于雙肩之上,一些則為半袒式,還有坐像枯瘦的人物背負(fù)一條衣帶,另有一尊裸露上身;最后,大部分此類坐像呈現(xiàn)人物頷或頰抵于疊加雙手之上這種南宋后才出現(xiàn)的姿態(tài)。正是這些差異讓博物館對(duì)此類坐像的命名各異,如“雪山大士”“釋迦苦行像”“釋迦坐像”“悉達(dá)多太子苦行像”“達(dá)摩坐像”“羅漢坐像”等。
一些圖像具備區(qū)別于其他圖像所共有的特征,這是區(qū)別圖像類型的“圖像志”(Iconography)特征;而一種圖像類型中仍具有相互區(qū)別的其他特征,這是不影響其所屬圖像類型的“形式風(fēng)格”(Form and Style)或“圖像學(xué)”(Iconology)的特征。
早在1965年,德國(guó)的東亞藝術(shù)史學(xué)者謝愷(Dietrich Seckel,1910—2007)就在其一篇討論梁楷“釋迦出山圖”的宏文中注意到此類坐姿,提出它是“釋迦苦行像”在東亞的發(fā)展,并指出這種坐像的起源和實(shí)際意義仍有待澄清,即它是如何從犍陀羅藝術(shù)中的“釋迦苦行像”的結(jié)跏趺坐姿和極度消瘦的身體脫離出來,并賦予了人物沉思的,甚或是抒情的特征。[2]近年來,中國(guó)學(xué)者也注意到此類坐像,王中旭首先關(guān)注到天津博物館藏晚明畫家丁云鵬“釋迦牟尼像”掛軸中的這一坐姿,確定了此畫的圖像學(xué)意義,并將其重新定名為“釋迦思惟出山像”;[3]張萌梳理了幾尊海內(nèi)外博物館藏這類坐像,通過圖像與文獻(xiàn)對(duì)照,將此類坐像定名為“釋迦伏膝冥思像”。[4]本文將借助敘事性佛傳壁畫、版畫和繪畫中的敘事性場(chǎng)景和其他母題元素,以及佛教經(jīng)文和碑刻題記等確定此類坐像的圖像類型,澄清其意義,并嘗試追溯此類坐姿的源起。
此類坐像所具有的具體特征是不影響其作為同一圖像類型的特征,可以通過形式風(fēng)格以及圖像學(xué)方法解釋。一些坐像,如底特律藝術(shù)中心藏元代款和舊金山亞洲藝術(shù)博物館藏清玉雕在身形、姿態(tài)與人物氣質(zhì)方面極為相似,可推測(cè)為元代經(jīng)典款的影響和流傳;又如故宮博物院款和英國(guó)維克多與阿爾伯特美術(shù)館款在材質(zhì)、人物身體狀態(tài)方面類似;而遼寧省博物館藏款、洛陽(yáng)博物院藏款和美國(guó)克利夫蘭藝術(shù)博物館藏款的人物衣飾及穿著方式相仿,這些都可以從時(shí)代或地域的形式風(fēng)格特征去追尋原因。但由于雕塑的可移動(dòng)性,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它們脫離了歷史原境,形式風(fēng)格分析常常很難得出具體可靠的結(jié)論,因此本文將不會(huì)在此部分展開。而一些坐像,如人物是否具有佛相特征;面部表情是困惑、平靜還是微笑;身形狀態(tài)是枯瘦還是圓潤(rùn)等,更適合圖像學(xué)方法,即放在禪宗信仰和修學(xué)觀念中去理解此類坐像產(chǎn)生的宗教時(shí)代背景。文章最后嘗試在探析這類現(xiàn)象的潘諾夫斯基所謂原初意義和約定性意義之后,闡釋此類坐像作為本質(zhì)的“內(nèi)在意義或內(nèi)容”。[5]
二、坐像身份——雪山大士、釋迦牟尼、龍樹菩薩、鳥窠禪師、達(dá)摩或羅漢?
博物館和現(xiàn)代出版物定義這類坐像的人物身份有雪山大士、釋迦牟尼、達(dá)摩和羅漢等。與一些佛教宗派以哲學(xué)思辨將佛轉(zhuǎn)變?yōu)槌橄蟠嬖诓煌@些人物是追求直接宗教體驗(yàn)的禪宗所關(guān)注的具體歷史人物,[6]在他們的生平中,都曾經(jīng)歷過苦修,而苦修所帶來的諸如身體羸弱、發(fā)須濃密、手腳指甲尖長(zhǎng)等特征可能是這些人物身份常被混淆不清的原因。
關(guān)于雪山大士的故事是世尊在過去世“作婆羅門修菩薩行”時(shí),曾住于雪山苦行,帝釋天變身羅剎,以偈語(yǔ)考驗(yàn)他,雪山大士舍身聞偈。[7]經(jīng)張萌的梳理,雪山大士的圖像在西魏、隋和晚唐的莫高窟壁畫共出現(xiàn)三次,另還出現(xiàn)在北齊安陽(yáng)小南海石窟和宋大足寶頂石龕內(nèi)。最多表現(xiàn)的是雪山大士為聞偈縱身躍下的戲劇性場(chǎng)景,即使如敦煌西魏壁畫和安陽(yáng)小南海石窟通過多個(gè)敘事性場(chǎng)景描繪雪山大士故事,其中出現(xiàn)了雪山大士苦行像,人物也是結(jié)跏趺坐坐像。[4]可見“苦行”并不是雪山大士人物身份的典型象征,更沒有其他圖像和文獻(xiàn)支持支單腿、雙手相疊置于支單腿膝蓋,呈低目凝思狀的坐像為雪山大士。這一誤解的另一個(gè)原因可能與釋迦牟尼得道成佛前曾在雪山六年苦行,被稱為“雪山童子”有關(guān)。
目前,大部分博物館和出版物將此類坐像命名為“釋迦牟尼佛坐像”“釋迦苦行像”或“悉達(dá)多太子苦行像”,即根據(jù)大部分此類坐像頭頂有肉髻、髻珠或白毫等佛相特征,定義此坐像人物身份為釋迦牟尼;又根據(jù)一些坐像人物羸瘦和尖長(zhǎng)的手足指甲等特征,判斷其表現(xiàn)的是釋迦牟尼的六年苦行。
“六年苦行”是釋迦牟尼佛傳故事中的一個(gè)重要轉(zhuǎn)折點(diǎn),多部佛教經(jīng)典均有記載。如《過去現(xiàn)在因果經(jīng)》在佛傳故事部分記載:釋迦在詢問關(guān)于生老病死的問題并沒得到滿足后,便來到正覺山附近的苦行林中進(jìn)行嚴(yán)格的苦行。從一日一食到七日一食,持續(xù)六年,身如槁木,此后釋迦思惟苦行無益于悟道,從而舍棄苦行,在尼連禪河清凈身體,領(lǐng)受牧牛女獻(xiàn)上的乳糜后,步行大地震,青雀環(huán)繞,瑞云鮮映,成為菩薩。之后用吉祥草鋪成蓮花座,置于菩提樹下結(jié)跏趺坐禪定,最后降魔成道。[8]
多數(shù)佛教經(jīng)典都記載了釋迦是“結(jié)跏趺坐”苦行,如《普曜經(jīng)》《佛本行集經(jīng)》和《方廣大莊嚴(yán)經(jīng)》等。[9-11]加之多處經(jīng)文對(duì)釋迦苦行身體羸弱的狀態(tài)做了詳細(xì)描述,從3—4世紀(jì)犍陀羅到唐時(shí)期的炳靈寺、克孜爾、莫高窟等造像和壁畫都將苦行釋迦描繪為結(jié)跏趺坐,雙手結(jié)禪定印,身體枯瘦的形象。[12-13]本文所研究坐姿坐像并不見于犍陀羅、印度和中國(guó)元以前描繪釋迦六年苦行的主題中。此類坐姿可能是宋以后才出現(xiàn)的。[4]除了上文第一部分所述造像外,甘肅永登妙因寺萬歲殿和河北正定隆興寺摩尼殿兩處明代佛傳故事壁畫(圖14-16)、明代《顧氏畫譜》中“龍樹菩薩”頁(yè)(1603年)(圖17)、天津博物館藏丁云鵬1604年“釋迦牟尼佛”軸(圖18),以及大英博物館藏傳南宋劉國(guó)用“鵲窠禪師圖”軸(圖19)都出現(xiàn)這種坐姿。相較于造像脫離其歷史原境的情況,敘事性佛傳壁畫以及版畫和繪畫中的敘事性場(chǎng)景和其他母題元素為正確理解此類坐像提供了更多信息。

圖14 明代(1427年),“山林苦修”,甘肅永登妙因寺萬歲殿暗廊西段內(nèi)側(cè)壁北端壁畫

圖15 明(1427年),“知苦行非菩提因”,甘肅永登妙因寺萬歲殿暗廊東段內(nèi)側(cè)壁北端壁畫

圖16 明代(1486年或稍晚),“釋迦六年苦行”,河北正定隆興寺摩尼殿大殿東檐墻南段壁畫

圖17 明代,顧炳,《顧氏畫譜》(1603年),“龍樹菩薩”

圖18 丁云鵬,明代,“釋迦牟尼佛”軸,絹本設(shè)色,1604年,天津博物館藏

圖19 (傳)劉國(guó)用,南宋,“鵲窠禪師圖”軸,絹本設(shè)色,99厘米高,43厘米寬,大英博物館藏
甘肅永登妙因寺萬歲殿暗廊的東西壁有繪制于明宣德二年(1427)的佛傳故事壁畫,八十四個(gè)場(chǎng)景中有兩處與釋迦六年苦行相關(guān)。其中暗廊西段內(nèi)側(cè)壁北端上部描繪了釋迦結(jié)跏趺坐,坐于蓮臺(tái)之上,身后有巨大圓光,頭頂肉髻、中間飾有髻珠,身著紅色袒右袈裟,左手禪定印,右手抬至胸前;暗廊東段內(nèi)側(cè)壁北端上部描繪了同樣身著紅色袒右袈裟的釋迦形象,人物有頭光,支左腿,雙手疊加于左腿膝蓋上,頭部前傾,雙目低垂。圖錄將這兩幅圖像分別命名為“山林苦修”和“知苦行非菩提因”,[14]即釋迦六年苦行的兩個(gè)階段——釋迦六年苦行階段和經(jīng)過六年苦行后,思惟苦行并非菩提之因的時(shí)候。
另一處明代壁畫位于河北正定隆興寺摩尼殿大殿檐墻內(nèi),繪制于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或稍晚。[15]東墻南端標(biāo)題為“六年苦行”。此處,釋迦支左腿,雙手疊加伏于左膝之上,坐于鋪有草墊的巖石上,背景是一片白雪皚皚的冬景。人物頭后有綠色頭光,頭頂肉髻、中有髻珠,低目凝神靜思,表現(xiàn)的也應(yīng)為經(jīng)過六年苦行后,呈佛相的釋迦思惟苦行并非菩提之因的階段。值得注意的是,釋迦坐墊邊放置一個(gè)綠布紅節(jié)的包裹,根據(jù)包裹形狀,可推測(cè)里面包著的是一個(gè)佛缽。
類似包裹還出現(xiàn)在《顧氏畫譜》(初印于明萬歷三十一年,1603)此類坐姿人物旁,打結(jié)的包裹內(nèi)裝有一個(gè)缽形器皿,與隆興寺摩尼殿壁畫的十分相似。圖后跋語(yǔ)題部分引自《圖畫見聞志》卷三,題為:“仁宗皇帝天資穎悟,圣藝神奇,遇興援筆,超逾庶品。伏聞齊國(guó)獻(xiàn)穆大長(zhǎng)公主喪明之始,上親畫《龍樹菩薩》,命待詔傳模鏤版印施。”可見,宋仁宗曾繪“龍樹菩薩”,并令人鏤版印刷,《大唐西域記》載缽水投針的故事與龍樹菩薩相關(guān),[16]《顧氏畫譜》可能因此將缽作為龍樹菩薩的象征物,進(jìn)而將此幅人物與缽的圖像作為摹宋仁宗所繪“龍樹菩薩”收入書中。然現(xiàn)未有宋仁宗皇帝作品傳世,“龍樹菩薩”的形象也極少出現(xiàn)在繪畫作品中。而此插圖中的人物形象與《顧氏畫譜》中另一幅表現(xiàn)“東方三圣”(圖20),即老子、孔子和釋迦牟尼的插圖中具有“釋迦出山”典型特征(說法手印)的釋迦牟尼形象極為一致,兩幅插圖中的人物都是螺發(fā)、胡須卷曲茂密,兩耳垂肩并飾有耳環(huán),手足指甲尖長(zhǎng)。可以推測(cè),這兩幅插圖是顧炳摹仿釋迦經(jīng)過六年苦行后,思惟苦行并非菩提之因的時(shí)候和“釋迦出山”兩個(gè)主題的畫作繪制的,此處“龍樹菩薩”的真正身份應(yīng)為思惟出山的釋迦。尤其是此幅插圖與河北正定隆興寺摩尼殿大殿“六年苦行”壁畫中出現(xiàn)的佛缽,據(jù)佛本生故事的記載,應(yīng)是在釋迦苦行成道后,四天王奉缽時(shí)才第一次出現(xiàn),①對(duì)佛缽的表現(xiàn)除了出現(xiàn)在佛本生故事中,如“四王獻(xiàn)缽”,還出現(xiàn)在戴進(jìn)《達(dá)摩六代祖師圖》第一幅中,初祖達(dá)摩坐于草墊上面壁苦修,其身旁就放有一個(gè)用布包裹、打著結(jié)的佛缽,它是禪宗祖師傳承和傳法思想的體現(xiàn)。關(guān)于佛缽參見:孫英剛,李建欣.月光將出、靈缽應(yīng)降——中古佛教救世主信仰的文獻(xiàn)與圖像[J].全球史評(píng)論,2016(2):109-140、307.李建欣.中古時(shí)期中國(guó)的佛缽崇拜[J].中古中國(guó)研究,2017,1(0):191-210.關(guān)于禪宗祖師與佛缽參見:林有能.禪宗六祖惠能衣缽去向考釋[J].船山學(xué)刊,2015 (3):97-108.這兩處的佛缽與佛相特征共同塑造了釋迦的佛陀形象。

圖20 顧炳,明代,《顧氏畫譜》(1603年),“東方三圣:老子、孔子、釋迦牟尼”
丁云鵬晚于《顧氏畫譜》一年繪制的掛軸,天津博物館將其命名為“釋迦牟尼佛”,人物姿態(tài)和體型與《顧氏畫譜》極為相似,但人物發(fā)須更為茂密,手腳戴有手環(huán)、腳環(huán),衣服也更繁復(fù),人物坐在草墊上,身處環(huán)境也不同,王中旭在文章中令人信服地將此軸定名為“釋迦思惟出山圖”。[3]
大英博物館藏傳南宋劉國(guó)用“鵲窠禪師圖”掛軸,畫面中央一位人物坐于鋪上草葉的磐石之上,畫面背景亦為巨大石塊,人物成正面像,支左腿,右腿平放于身前,雙手疊加于左腿膝蓋之上,身披長(zhǎng)衣及地,人物頭頂有肉髻和髻珠,雙眼凝視前方,面露笑容。頭頂上方,一喜鵲正銜枝停落,似將要以頭筑巢,博物館將此軸命名為“鵲窠禪師圖”。鵲巢禪師為唐代著名高僧道林禪師,據(jù)宋代《景德傳燈錄》記載,道林禪師曾在秦望山看見一棵松樹枝葉繁茂、盤曲如蓋,于是棲止其上,時(shí)人稱為鳥窠禪師;后來,其側(cè)有鵲構(gòu)巢,故而又稱鵲巢和尚。[17]南宋梁楷所繪“八高僧圖卷”第三幅“白居易拱謁·鳥窠指說”描繪了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shí),慕道林之名入山拜晤、受其訓(xùn)誡的故事。畫面上鳥窠弓著背,盤坐在樹干彎折處,由干樹枝搭成了坐墊,他右手食指指甲尖長(zhǎng),指著前方合手拱謁的白居易,訓(xùn)誡其處境甚至比他更危險(xiǎn)。[18]觀察大英博物館藏“鵲窠禪師圖”雖未表現(xiàn)白居易拱謁的主題,但人物也并非坐于樹上,而是坐于鋪著草枝的磐石之上;此外,據(jù)《景德傳燈錄》“復(fù)有鵲巢于其側(cè)自然馴狎人”,而非在其頭上銜枝筑巢。相反,這些特征符合《僧伽羅剎所集經(jīng)》中對(duì)阿惟三佛由兔身變?yōu)槠兴_身后在山林禪定苦行之事的描述,即菩薩端坐思惟時(shí)發(fā)現(xiàn)頭頂有鳥在巢中孵蛋,因擔(dān)心蛋墜落而身不移動(dòng)。[19]敦煌藏經(jīng)洞唐代絹畫已將釋迦苦行加入了頭頂鵲巢的形象,加之大英博物館藏此軸上人物頭頂有肉髻、髻珠和白毫,由此可以斷定,此軸所繪并非“鵲窠禪師”,而應(yīng)為六年苦行時(shí)期的釋迦,只是人物由苦行結(jié)跏趺坐變?yōu)橹ё笸取㈦p手相疊伏于左膝的坐姿——即釋迦思惟出山時(shí)的坐姿。畫家將釋迦六年苦行和思惟出山兩個(gè)階段融合為一,人物呈正面的坐像,位于畫面中心,四周磐石圍繞,其間又空有留白,讓人物更具莊嚴(yán)感和崇拜感,而人物微笑的表情和不對(duì)稱的坐姿又消解了神圣感。畫面衣紋處理和山石皴法等風(fēng)格特征讓此幅掛軸的繪制年代指向明代以后。
此類坐像還會(huì)被稱作“達(dá)摩坐像”,如故宮博物院的坐像,此坐像與英國(guó)維克多與阿爾伯特美術(shù)館銅坐像不僅都未鎏金,而且人物頭部未抵相疊雙手之上,這與明清流行的某些達(dá)摩坐姿相似,然兩者區(qū)別在于,達(dá)摩支腿位于身體一側(cè),而非身體前方;且身體健碩挺拔,面部表情嚴(yán)肅,多戴風(fēng)帽。故宮博物院坐像人物頭頂?shù)娜怊佟⒌湍磕嫉臓顟B(tài)等特征符合釋迦思惟出山的人物特征。
普林斯頓大學(xué)博物館藏元代人物坐像頭部沒有肉髻和白毫,雙眉細(xì)長(zhǎng)下垂,人物上身幾乎袒露,身體極度前傾,人物側(cè)面幾乎呈由向前支起的右腿和前傾的上身所構(gòu)成的直角三角形。極端的姿態(tài)和瘦骨嶙峋的身體賦予坐像強(qiáng)烈的緊繃感,被稱為“羅漢苦行像”。相關(guān)十六羅漢的典據(jù)主要是唐玄奘所譯《大阿羅漢難提密多羅所說法住記》,其中只涉及名號(hào)和眷屬,并未對(duì)羅漢的姿態(tài)、身形和服飾有具體定義,這讓畫家或工匠對(duì)羅漢的面容和姿態(tài)描繪有很大發(fā)揮空間,這也衍生了后世對(duì)十八羅漢和五百羅漢的描繪。北宋文豪秦少游的《五百羅漢圖記》詳細(xì)記錄了吳僧法能所繪《五百羅漢圖》的內(nèi)容,近千字的敘述涉及羅漢的活動(dòng)及從事每種活動(dòng)羅漢的數(shù)量,也未見描述此坐姿坐像。縱觀清代以前羅漢圖像,均未發(fā)現(xiàn)此類坐像,清以后羅漢圖中出現(xiàn)所謂“靜思羅漢像”,應(yīng)是受到“思惟出山釋迦”形象的影響。[20]普林斯頓大學(xué)博物館款刻畫的也應(yīng)是釋迦出山前思惟的狀態(tài)。
三、坐像的定名、起源與特征
《方廣大莊嚴(yán)經(jīng)》卷七“往尼連河品”:“爾時(shí)菩薩六年苦行……作是思惟:過現(xiàn)未來所有沙門、若婆羅門,修苦行時(shí),逼迫身心受痛惱者,應(yīng)知是等但自苦己都無利益。”復(fù)作是念:“我今行此最極之苦,而不能證出世勝智,即知苦行非菩提因,亦非知苦斷集證滅修道,必有余法當(dāng)?shù)脭喑喜∷馈!睆?fù)作是念:“我昔于父王園中閻浮樹下修得初禪,我于爾時(shí)身心悅樂,如是乃至證得四禪,思惟往昔曾證得者,是菩提因,必能除滅生老病死。”[21]
此段經(jīng)文描述了釋迦出山前思惟的階段。王中旭根據(jù)清代儲(chǔ)大文在《陽(yáng)曲白云寺碑記》中所提及的山西陽(yáng)曲凈業(yè)庵供奉的“釋迦思惟出山像”,推測(cè)這一塑像是區(qū)別于結(jié)跏趺坐的釋迦六年苦行像,應(yīng)就是支單腿,雙手相疊伏支腿膝的坐像,并以“釋迦思惟出山像”命名此類坐像。[3]張萌將此類像定名為“釋迦伏膝冥思像”,這與美國(guó)賓夕法尼亞大學(xué)博物館對(duì)其藏品的命名“釋迦牟尼佛冥想坐像”(Seated figure of Shakyamuni Buddha in meditation)意思貼近。“釋迦思惟出山像”區(qū)別了釋迦苦行和出山前思惟兩個(gè)階段,更貼切佛經(jīng)“思惟”這一描述,筆者贊同這一命名,并在本文使用這一名稱。
“思惟”(梵文cintana^)即思考、推度的意思。佛教藝術(shù)中,“思惟”以手臂姿勢(shì)呈現(xiàn),其典型特征為單肘支膝,前臂上舉,以指支額或以手托頰,呈思惟狀。[22]思惟姿態(tài)的人物形象見諸多種人物身份和場(chǎng)景,在佛傳圖像中,主要表現(xiàn)題材有“納親圖”“樹下靜觀圖”“決意出家圖”等悉達(dá)多太子身處世俗愛欲與修行覺悟之間的艱難抉擇,并隱喻太子“思惟成佛”的覺悟途徑,[23]縱觀印度和宋以前的藝術(shù)表現(xiàn)中并未出現(xiàn)“釋迦思惟出山”題材。當(dāng)中國(guó)人開始表現(xiàn)這一題材的時(shí)候,他們放棄了傳統(tǒng)思惟像的形式,“釋迦思惟出山像”至少呈現(xiàn)三個(gè)特征:1.支單腿于身前,另一腿彎曲置于身前;2.雙手疊加伏于支腿之上;3.呈低目凝思狀;另外,大部分坐像人物頭部抵于雙手上。接下來將從這幾個(gè)方面分析坐姿的起源和特征。
人物支單腿的坐姿最早出現(xiàn)在4到5世紀(jì)的山西、陜西、甘肅和新疆等北方、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區(qū),5至6世紀(jì),南朝“竹林七賢畫像磚”上,向秀、嵇康、劉靈、山濤、阮籍等人物也呈支單腿坐姿。[24]此類坐姿繼而出現(xiàn)在唐及唐以降的士大夫、高士、隱士或一些佛教人物形象上,如傳五代顧宏中“韓熙載夜宴圖”的韓熙載,五代畫家孫位“高逸圖”、南宋“柳蔭高士圖”、南宋李唐“采薇圖”的高士,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征聘圖”中草廬內(nèi)的諸葛亮,[25]以及唐敦煌莫高窟壁畫《維摩詰經(jīng)變·問疾》的維摩詰和五代以降出現(xiàn)的支腿水月觀音等。這些人物都是一膝著地、一膝立起的坐姿;或是一手撐地、一手伏膝;或是兩手抱著立起的腿,呈現(xiàn)放松自在又閑適的狀態(tài)。然而,除了“竹林七賢畫像磚”上的劉靈和山濤,以及抱支腿的人物坐像外,其他坐像與“釋迦思惟出山像”的最大區(qū)別是人物支腿均在身體一側(cè),而非立于身前,而且所有坐像均不是雙手相疊伏于支腿膝蓋之上。
“文苑圖”和“琉璃堂人物圖”上出現(xiàn)雙手插入寬大袖管、伏在中間老松樹上的人物,與旁邊托腮持筆的人物一樣,都在構(gòu)思作文。可以觀察到南宋以后,繪畫中出現(xiàn)了人物雙手相疊的姿態(tài),如南宋劉松年的“羅漢圖”中雙手相疊伏于古松枝上的羅漢。南宋周季常和林庭珪“五百羅漢圖”上還出現(xiàn)兩處羅漢雙手伏于石塊上的畫面,他們或是雙手相疊,或是雙手插入寬大袖管內(nèi),低目凝思。傳五代石恪的“二祖調(diào)心圖軸”上,“伏虎圖軸”人物右臂支于身前老虎背上(圖21),有學(xué)者認(rèn)為這是倚虎豐干,有觀點(diǎn)認(rèn)為這是伏虎羅漢,亦有觀點(diǎn)認(rèn)為這是遭剪裁的“四睡圖”中的倚虎豐干。[26]13世紀(jì),倚虎豐干與寒山、拾得組合為“四睡圖”的新圖像形式,[6]日本15世紀(jì)畫家真藝(藝阿彌)的“四睡圖”上(圖22),可見寒山、拾得其中一人雙手插入袖管伏于虎背,另一人支單腿,雙手疊加置于支腿膝蓋上,已經(jīng)非常接近本文研究的“釋迦思惟出山像”的坐姿。

圖21 (傳)石恪,五代,“伏虎圖軸”,縱33.3厘米,橫64.4厘米,紙本墨筆,日本東京國(guó)立博物館藏

圖22 真藝(藝阿彌),“四睡圖”,不晚于1485年,載于《長(zhǎng)春閣鑒賞》第2集(川崎芳太郎 編,國(guó)華社 出版,大正3年[1914])
以上梳理雖然并未找到本文研究坐姿的具體范本,但可以推測(cè)的是,這一坐像是區(qū)別于傳統(tǒng)佛教“思惟像”的中國(guó)化形式,它結(jié)合了高士圖中“支單腿”坐姿,呈現(xiàn)了放松自在的狀態(tài);又借由南宋時(shí)羅漢圖像的豐富人物類型以及其他禪宗人物形象發(fā)展而來。此外,一些坐像人物頭部未抵相疊雙手之上,但人物頭頂?shù)娜怊倩蝼僦榉戏鹣嗟奶卣鳎矐?yīng)被視作“釋迦思惟出山”的主題。可見,在這類中國(guó)本土發(fā)展出來的“釋迦思惟出山像”中,“思惟”并非以手臂和頭部姿勢(shì)呈現(xiàn),而更多是體現(xiàn)在低目凝思的人物狀態(tài)上。
日本禪宗學(xué)者久松真一(Shin’ichi Hisamatsu,1889—1980)總結(jié)了禪宗藝術(shù)的七個(gè)特征:1.形式上的不規(guī)則(fukinsei);2.簡(jiǎn)素(kanso);3.孤高(kokou);4.自然,不受約束的自發(fā)性(shizen);5.幽玄(Yugen);6.超凡脫俗(datsuzoku);7.寂靜與孤獨(dú)(seijaku)。[27]可以說,“釋迦思惟出山像”的不對(duì)稱、樸素和單純、自然又莊嚴(yán)、深邃又自在的特征是受到禪宗觀念的影響,它也豐富了禪宗藝術(shù)的圖像類型。
四、坐像的意義和功能
厘清此類坐像的人物身份、命名、坐姿緣起和特征后,需要闡釋為何一些“釋迦思惟出山像”呈現(xiàn)佛相特征,而一些則沒有。布林克爾(Brinker)在對(duì)出山釋迦主題的研究中總結(jié)道,“出山釋迦像”根據(jù)具體情況可以分為已經(jīng)得道的佛陀和剛經(jīng)歷苦修的苦行僧形象,[28]這同樣適合理解“釋迦思惟出山像”。
“釋迦思惟出山”屬于釋迦六年苦行的最后一個(gè)階段,在印度經(jīng)典和佛傳中,釋迦上山苦行是對(duì)世界狀況的批判,他無法生活在現(xiàn)實(shí)世界中。而經(jīng)過六年苦行后,釋迦思惟領(lǐng)悟到折磨肉體對(duì)修行無益而出山,出山體現(xiàn)了對(duì)苦行的否定。在大乘佛教中,“釋迦六年苦行”“釋迦思惟出山”和“釋迦出山”都不屬于“釋迦八相”,釋迦是在出山后,在菩提樹下悟道成佛的。相關(guān)佛本生經(jīng)典中,從未說明釋迦思惟出山時(shí)已徹悟,但在大部分“釋迦思惟出山像”中,釋迦身上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徹悟的標(biāo)志,如白毫、肉髻和髻珠。“釋迦思惟出山像”呈現(xiàn)佛相特征證明此時(shí)釋迦已經(jīng)得道成佛,這必然要以肯定“苦行”并強(qiáng)調(diào)“思惟”為前提去理解。
板倉(cāng)圣哲注意到,相對(duì)于印度的經(jīng)典和佛傳對(duì)苦行無益的記載和強(qiáng)調(diào),一些漢譯佛經(jīng)不否定六年苦行,例如3世紀(jì)由支謙漢譯的《瑞應(yīng)本起經(jīng)》將苦行明確聯(lián)系至成道的結(jié)果,經(jīng)由六年苦行,從第一禪到第四禪,趕走魔鬼后成道:[29]
菩薩即拾槀草,以用布地,正基坐,叉手閉目,一心誓言:“使吾于此肌骨枯腐,不得佛,終不起。”天神進(jìn)食,一不肯受。天令左右,自生麻米,日食一麻一米,以續(xù)精氣。端坐六年,形體羸瘦,皮骨相連,玄清靖漠,寂默一心。內(nèi)思安般,一數(shù)、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凈,游志三四,出十二門,無分散意。神通微妙,棄欲惡法,無復(fù)五蓋,不受五欲。眾惡自滅,念計(jì)分明,思想無為,譬如健人得勝怨家,意以清凈,成一禪行。心自開解,卻情欲意,無惡可改,不復(fù)計(jì)視,念思已滅。譬如山頂之泉,水自中出,盈流于外,谿谷雨潦,無緣得入。恬惔守一,欣然不移,成二禪行。又棄喜意,唯見無婬,外諸好惡,一不得入,內(nèi)亦不起,心正身安,譬如蓮華根在水中,華合未開,根莖枝葉,潤(rùn)漬水中,以凈見真,成三禪行。棄苦樂意,無憂喜想,心不依善,亦不附惡,正在其中;如人沐浴潔凈,覆以鮮好白?,中外俱凈,表里無垢,喘息自滅,寂然無變,成四禪行。譬如陶家和埴調(diào)柔,中無沙礫,任作何器,精進(jìn)開發(fā),無所不能,以得定意;不舍大悲,智慧方便,究暢要妙,通三十七道品之行。[30]
而連接“苦行”和“成道”的關(guān)鍵便是“思惟”,通過苦行后的“思惟”(內(nèi)思安般),得以明心,最終得道成佛。“釋迦思惟出山像”突出宣揚(yáng)了禪宗的修習(xí)禪定和頓悟思想,它是禪宗在南宋時(shí)期發(fā)展到鼎盛階段的結(jié)果。這可以解釋一些“釋迦思惟出山像”出現(xiàn)佛相,并無苦修之狀,坐像身體圓潤(rùn)、面孔飽滿、一副平靜深思甚至微笑滿足的表情。
可以說,呈現(xiàn)頓悟后證得圓滿佛相特征的思惟出山釋迦形象是一種禪宗信仰的體現(xiàn),它一方面強(qiáng)調(diào)修習(xí)禪定的宗教實(shí)踐活動(dòng),另一方面又象征了覺悟成佛的一條重要途徑;而苦行僧式的“出山思惟釋迦”刻畫了歷史中的釋迦,反映了禪宗藝術(shù)的傾向,即偏離正統(tǒng)的佛教圖像學(xué)道路,從大乘佛教程式化的、靜態(tài)的、抽象的圖像轉(zhuǎn)向傳記性的、歷史敘事性的人物和軼事的刻畫。可以說,無論是否呈現(xiàn)佛相,“釋迦思惟出山像”的不對(duì)稱、樸素和單純、自然又莊嚴(yán)、深邃又自在的特征都體現(xiàn)了禪宗信仰反傳統(tǒng)、反偶像崇拜、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修行與頓悟、主張明心見性的修學(xué)觀念。
相關(guān)“釋迦思惟出山像”的功能由于缺乏文獻(xiàn)記載,只能通過此類雕塑的材質(zhì)、大小和相關(guān)主題圖像如“出山釋迦像”的功能來推測(cè)。“釋迦思惟出山像”雖然也出現(xiàn)在明及以后的佛傳故事壁畫、版畫和繪畫作品中,但更多是以雕塑形式出現(xiàn),并且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雕塑材質(zhì)種類豐富,包括木雕貼金、夾貯造貼金、青銅、彩瓷和玉等,雕塑的大小也相去甚遠(yuǎn),可見“釋迦思惟出山像”雕塑曾被不同階層的人供奉。此外,一些禪僧語(yǔ)錄和文集以及禪寺宗教活動(dòng)的文獻(xiàn)證實(shí),“出山釋迦像”主題的畫作會(huì)在十二月的第八天,即紀(jì)念釋迦牟尼徹悟的“佛成道節(jié)”張掛出來。[29]由此可以推測(cè),“釋迦思惟出山像”也可能是在這類節(jié)日被人尊奉和供養(yǎng)的。
總結(jié)
海內(nèi)外博物館藏有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以明清時(shí)期和青銅材質(zhì)為主的人物坐像。通過比較“釋迦思惟出山”塑像的異同,并借助敘事性佛傳壁畫、版畫和繪畫中的敘事性場(chǎng)景和其他母題元素,以及佛教經(jīng)文和碑刻題記等可以知道這些坐像刻畫的是釋迦六年苦行后思惟出山的時(shí)刻,并定名為“釋迦思惟出山像”,其圖像志特征主要體現(xiàn)在人物坐姿和氣質(zhì)狀態(tài)上,即支單腿、雙手相疊伏于支腿膝蓋上,另一腿彎曲置于身前,人物呈低目凝思狀。這類坐像是區(qū)別于傳統(tǒng)佛教“思惟像”的中國(guó)化形式,它結(jié)合了高士圖中“支單腿”坐姿,呈現(xiàn)了放松自在的狀態(tài);又借由南宋時(shí)羅漢圖像的豐富人物類型以及其他禪宗人物形象發(fā)展而來;在這類中國(guó)本土發(fā)展出來的“釋迦思惟出山像”中,“思惟”并非以手臂和頭部姿勢(shì)呈現(xiàn),而更多是體現(xiàn)在低目凝思的人物狀態(tài)中。一類“釋迦思惟出山像”呈現(xiàn)頓悟后證得圓滿佛相特征的思惟出山釋迦形象是禪宗信仰的體現(xiàn),它一方面強(qiáng)調(diào)修習(xí)禪定的宗教實(shí)踐活動(dòng),另一方面又象征了覺悟成佛的一條重要途徑;而苦行僧式的“釋迦思惟出山像”刻畫了歷史中的釋迦,反映了禪宗藝術(shù)的傾向,即偏離正統(tǒng)的佛教圖像學(xué)道路,從大乘佛教程式化的、靜態(tài)的、抽象的圖像轉(zhuǎn)向傳記性的、歷史敘事性的人物和軼事的刻畫。“釋迦思惟出山像”的不對(duì)稱、樸素和單純、自然又莊嚴(yán)、深邃又自在的特征受到禪宗觀念的影響,也豐富了禪宗藝術(shù)的圖像類型。
圖片來源:
圖1 美國(guó)底特律藝術(shù)中心官網(wǎng):https://dia.org/collection/shakyamuni-ascetic-37013.查閱時(shí)間2023年11月10日。
圖2 賓夕法尼亞大學(xué)博物館官網(wǎng):https://www.penn.museum/collections/object/66078.查閱時(shí)間2023年11月10日。
圖3 普林斯頓大學(xué)博物館官網(wǎng):https://artmuseum.princeton.edu/collections/objects/31671.查閱時(shí)間2023年11月10日。
圖4、6-7 張萌.釋迦伏膝冥思像考析[J].文物, 2022 (9):86-96.
圖5 遼寧省博物館.妙相莊嚴(yán):遼寧省博物館藏佛教造像精品集[G].沈陽(yáng):遼寧人民出版社,2011:68.
圖8 克利夫蘭藝術(shù)博物館官網(wǎng):https://www.clevelandart.org/art/1966.116.查閱時(shí)間2023年11月10日。
圖9-10 美國(guó)舊金山亞洲藝術(shù)博物館官網(wǎng):https://searchcollection.asianart.org/objects/3743/the-buddhashakyamuni-as-an-ascetic?ctx=feb3ac5d77dfe8cf86a55aceb 2756a78ee8c81eb&idx=24.查閱時(shí)間2023年11月10日。
圖11 英國(guó)維克多與阿爾伯特美術(shù)館官網(wǎng):https://collections.vam.ac.uk/item/O497792/emanciated-buddha-figure-ofbuddha/.查閱時(shí)間2023年11月10日。
圖12 https://searchcollection.asianart.org/objects/2387/thebuddha-shakyamuni?ctx=6b06b172あ4a584487b3e225f6638cf fa7019914&idx=0.查閱時(shí)間2023年11月10日。
圖13 https://searchcollection.asianart.org/objects/6205/shakyamuni-as-an-ascetic?ctx=6b06b172あ4a584487b3e225f 6638cあa7019914&idx=1.查閱時(shí)間2023年11月10日。
圖14-15 中國(guó)寺觀壁畫全集編輯委員會(huì),編.中國(guó)寺觀壁畫全集5:明清寺院佛傳圖[G].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186-圖216、217。
圖16 河北省正定縣文物保管所,編.正定隆興寺壁畫[G].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16-17.
圖17 明代,顧炳,《顧氏畫譜》(1603年),“龍樹菩薩”。
圖18 王中旭.丁云鵬《釋迦思惟出山像》考——兼談丁云鵬晚歲畫中的“枯木禪”[J].美術(shù)研究,2018(2):59-67.
圖19 英國(guó)大英博物館官網(wǎng):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36-1009-0-77.查閱時(shí)間2023年11月10日.
圖20 顧炳,明代,《顧氏畫譜》(1603年),“東方三圣:老子、孔子、釋迦牟尼”。
圖21馮翰林.打亂,重組與解讀——對(duì)石恪款《二祖調(diào)心圖》畫題的再考證[J].中國(guó)美術(shù),2018(3):142-149.
圖22 川崎芳太郎,編.長(zhǎng)春閣鑒賞:第2集[G].大阪:國(guó)華社,大正3年(19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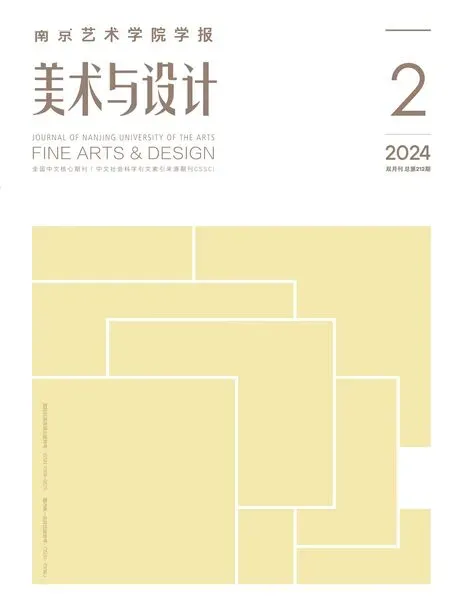 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美術(shù)與設(shè)計(jì))2024年2期
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美術(shù)與設(shè)計(jì))2024年2期
- 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美術(shù)與設(shè)計(jì))的其它文章
- 春 天
- 語(yǔ)言之思與現(xiàn)實(shí)關(guān)切的雙重變奏
- 張杰創(chuàng)作中的社會(huì)學(xué)敘事與觀看之道
- 宗旨、體制與革命:高等美術(shù)教育與中國(guó)傳統(tǒng)美術(shù)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三重維度①
- “以竹代塑”的審美倫理意蘊(yùn)
- 被身份重構(gòu)的晚明士人:主體覺醒與美學(xué)轉(zhuǎn)向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