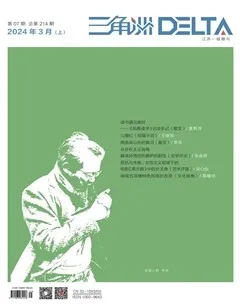民俗文化視野下山西壽陽(yáng)儺舞“愛社”的藝術(shù)特征及審美
張錦錦
山西民間舞蹈山西壽陽(yáng)縣儺舞“愛社”以身體語(yǔ)言豐富、形式多樣而家喻戶曉。儺舞既屬于舞蹈藝術(shù)的范疇,又屬于民俗文化的研究范疇。本文從三個(gè)部分,即壽陽(yáng)儺舞的源起、構(gòu)成和民俗審美解讀入手,分析山西民間舞在民俗文化視野下的審美特質(zhì)。
壽陽(yáng)儺舞“愛社”的緣起
山西民間舞蹈誕生于三晉大地,山西是中國(guó)古代文明的發(fā)源地之一,既是民間歌舞藝術(shù)的搖籃,又是黃河音樂的代表。悠久的歷史為山西帶來了文化的融合,形成了獨(dú)特的三晉文化,進(jìn)而推之形成了以地域文化生態(tài)為特征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的生態(tài)是對(duì)一個(gè)地區(qū)內(nèi)的歷史演變過程的動(dòng)態(tài)積聚,是對(duì)社會(huì)成員生存方式和人文歷史的充分展現(xiàn),與地域性密不可分。地域性當(dāng)前是民俗藝術(shù)影響因素中的“重頭戲”,以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huì)環(huán)境為主要因素。
一、壽陽(yáng)“愛社”的生成環(huán)境
據(jù)可靠文字記載,山西壽陽(yáng)縣的歷史距今已經(jīng)有2500多年。從近年來在壽陽(yáng)縣出土的石制斧頭、石制錐子等各種文物可以看出,早在新石器時(shí)代,壽陽(yáng)就已經(jīng)有原始人類生存過的足跡。那時(shí),人類活動(dòng)的行為就為壽陽(yáng)縣悠久的歷史文化奠定了基礎(chǔ)。壽陽(yáng)縣其古文化遺址也相較其他地區(qū)數(shù)量繁多,上至新石器時(shí)期下至魏晉期間。從唐代的上下寺、清虛寺到明代的朝陽(yáng)閣,為壽陽(yáng)縣深厚的文化底蘊(yùn)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壽陽(yáng)之名因水而得,壽陽(yáng)顧名思義與長(zhǎng)壽有著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自古以來,壽陽(yáng)人就有在桃子山、魯泉山等相關(guān)壽星的遺存前進(jìn)行祝禱、祭祀的傳統(tǒng)。除此之外,壽陽(yáng)人的民間信仰還有著區(qū)別于其他地區(qū)的特點(diǎn)。除了原始的長(zhǎng)壽觀念外,還有原始的宗教崇拜信仰,還受到了儒家、道家和佛家文化多方融合的影響。
二、“愛社”名稱的歷史淵源
關(guān)于“愛社”名稱的形成,在隨著研究的進(jìn)展逐漸形成了三派觀點(diǎn)。一派認(rèn)為“愛社”中的“愛”是熱情、狂熱的愛的意思,那“社”就會(huì)讓人聯(lián)想到江山社稷、國(guó)家社稷。“愛社”意為熱愛國(guó)家、熱愛江山。因此,“愛社”有歌頌黃帝為國(guó)為民之意。第二派解釋,將“愛”和“社”分別理解為地名和社火。這里將“愛”理解為一個(gè)地區(qū)的名稱,“愛社”即為社火的發(fā)源地。若仔細(xì)深入研究會(huì)發(fā)現(xiàn),壽陽(yáng)在明代有一地名為“宗艾”,合理地將“艾”諧音成了“愛”。后因人們口口相傳則把“艾”通譯成了“愛”,因此“愛社”之名由此誕生。第三派解釋則仍是相關(guān)黃帝戰(zhàn)蚩尤的故事,認(rèn)為“愛社”就是純粹的喜愛社火表演,在遠(yuǎn)古時(shí)期,黃帝戰(zhàn)勝蚩尤后,群體手舞足蹈、面戴面具來慶祝戰(zhàn)爭(zhēng)的勝利。
壽陽(yáng)儺舞“愛社”的藝術(shù)構(gòu)成
一、角色構(gòu)成程式化
“愛社”作為廟會(huì)祭祀中的重要部分,角色分配有著森嚴(yán)的程序和制度。每位演員必須按照角色的演繹來進(jìn)行分工,這些角色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種:第一種,領(lǐng)導(dǎo)者。其作用是活動(dòng)的組織者兼決策者,通常會(huì)是村長(zhǎng)或社火的傳承人。等級(jí)最高的人被稱為總領(lǐng)社首,除了日常事務(wù)管理外還承擔(dān)著組織演員們的排練、安排表演等事宜。第二種,“愛社”的表演人員。這些演出人員大多是本村的村民,有24人組成一個(gè)團(tuán)隊(duì),俗稱“二十四家怨頭鬼”。這個(gè)稱呼來源民間流傳著的24種鬼神形象,其中有6個(gè)主演人員稱之為“鬼頭”或“大鬼”。這些主要演員主要是村子表演“愛社”時(shí)間久、資歷深的人來扮演,全部為男性演員。在演出的時(shí)候剩余18個(gè)“小鬼”由村中選拔出來的男孩來扮演。18個(gè)“小鬼”分三個(gè)方向?qū)ⅰ按蠊怼眻F(tuán)團(tuán)圍住,并根據(jù)大鬼演出形式的變化,做出不同的助威動(dòng)作或者是吶喊動(dòng)作。最后一種則是演出時(shí)必不可少的伴奏人員,“愛社”的演出通常需要至少兩名鑼手和鼓手在旁伴奏。
二、演出形式程式化
“愛社”實(shí)際上是一種將舞蹈和武術(shù)動(dòng)作結(jié)合在一起的民俗民間表演活動(dòng),通過不同的情節(jié)遞進(jìn)來展現(xiàn)黃帝戰(zhàn)蚩尤的傳說。但是“愛社”由于表現(xiàn)的是大戰(zhàn)的場(chǎng)景,和普通的儺舞內(nèi)容題材有所不同,又因舞武不分家,故而加進(jìn)了許多武術(shù)動(dòng)作。“愛社”中“武”和“舞”,在代代傳承人的傳承中逐漸以一種相融相生的方式逐漸煥發(fā)出舞蹈和武術(shù)的魅力。剛?cè)岵?jì),硬中帶柔,在娛樂性之上又增添了許多觀賞性。
“愛社”的表演內(nèi)容是以“武勢(shì)”“倒上墻”“直墻”“小場(chǎng)”“過關(guān)”“耍桌”六套動(dòng)作來表現(xiàn)“軒轅黃帝大戰(zhàn)蚩尤”的傳說故事,再現(xiàn)了黃帝大戰(zhàn)蚩尤的激烈場(chǎng)面。“武勢(shì)”的主要內(nèi)容是將士們裝扮成“鬼”的模樣,假扮成它的樣子,為戰(zhàn)爭(zhēng)做好充分的準(zhǔn)備工作;“倒上墻”講述的是對(duì)手兵臨城下,緊迫感油然而生,戰(zhàn)士們商討作戰(zhàn)計(jì)劃并積極加緊練習(xí)。演員們伴隨著內(nèi)容的轉(zhuǎn)變由單人變?yōu)殡p人再到多人,隊(duì)形隨內(nèi)容變換;“直墻”是“愛社”表演內(nèi)容中的重點(diǎn),主要表演的內(nèi)容為面對(duì)艱難的戰(zhàn)爭(zhēng)形勢(shì),“大鬼”們雖如臨大敵,但仍英勇無(wú)畏,多次進(jìn)攻敵人的防守陣型。不同于其他部分的是,該部分對(duì)動(dòng)作的重復(fù)性較高,側(cè)面體現(xiàn)出堅(jiān)韌的對(duì)戰(zhàn)決心;“小場(chǎng)”講述的是使用陣法迷惑蚩尤,從而獲得集體調(diào)整的機(jī)會(huì);再到“過關(guān)”,是結(jié)尾處的高潮,“大鬼”包圍了蚩尤的敵軍,出其不意群起而攻之,后大獲全勝。這些表演內(nèi)容從“愛社”誕生后到今日,未曾有過較大變動(dòng),無(wú)論是北神山的廟會(huì)或其他廟會(huì),表演形式是一成不變,是程式化、固定化的。
“愛社”的隊(duì)列陣容其實(shí)是在模仿黃帝戰(zhàn)蚩尤時(shí)的軍隊(duì)列隊(duì)方式。如果說內(nèi)容是“愛社”的身體,那隊(duì)列則是“愛社”的左膀右臂,兩者共同合力構(gòu)成了完整的“愛社”演出。正是因?yàn)橹饕莩龅膬?nèi)容是戰(zhàn)爭(zhēng)的情節(jié),普通舞蹈動(dòng)作的詮釋并沒有多么的充分,所以就要在舞蹈動(dòng)作中通過隊(duì)列的變化來帶動(dòng)內(nèi)容的突進(jìn)和情緒的轉(zhuǎn)變。“愛社”的隊(duì)列變化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gè)方面:第一,列隊(duì)。在“愛社”中,列隊(duì)訓(xùn)練的要求如今日的軍隊(duì)般整齊劃一。與之相匹配的演員服裝更要統(tǒng)一整齊,這些要求有助于演員融入自己所飾演的角色中,更好地為觀眾呈現(xiàn)出視覺的饕餮盛宴。第二,位置變換。在戰(zhàn)爭(zhēng)的對(duì)戰(zhàn)中,主力軍是靠“大鬼”之間的單打獨(dú)斗來呈現(xiàn)的。從舞蹈藝術(shù)的角度看,“大鬼”對(duì)打的形式主要采用了變換位置的方法,“換位”從始至終伴隨著整場(chǎng)演出。換位并沒有像普通的舞蹈隊(duì)形變換單一,它的形式是多樣的,有十字步換位、倒卷簾換位等。位置的變化真實(shí)模擬了戰(zhàn)場(chǎng)的場(chǎng)景,同時(shí)又渲染了戰(zhàn)場(chǎng)緊張、凝重的氣氛,增強(qiáng)了表演的觀賞性。
三、“愛社”的藝術(shù)風(fēng)格成因
在山西地區(qū)的儺文化是“儺”支系中不容忽視的一支,它不僅結(jié)合了山西的地域特質(zhì),還在發(fā)展、演變、完善的過程中受到山西文化的影響,遵循傳統(tǒng)“儺”舞的規(guī)律。通過對(duì)壽陽(yáng)“愛社”的源起和藝術(shù)解析可以看出,“愛社”在發(fā)展過程中受諸多因素影響,使它形成了固有的藝術(shù)風(fēng)格。經(jīng)過形態(tài)的剖析可以直接總結(jié)出“愛社”舞武藝術(shù)風(fēng)格的具體成因:
首先,民間宗教信仰的影響。在原始社會(huì)的宗教崇拜中,多數(shù)有著性愛觀的崇拜,展示出了關(guān)于生殖、繁衍和孕育的渴望。在“愛社”的舞蹈動(dòng)作中,不難發(fā)現(xiàn)有多處擺胯、扭胯的動(dòng)作出現(xiàn),很好地反映了儺舞的形態(tài)是崇拜、信仰演變而來。另一種信仰文化展現(xiàn)在“愛社”的舞蹈隊(duì)形中,在觀看“愛社”表演時(shí)可以發(fā)現(xiàn),演出者們的隊(duì)形通常會(huì)由“圓”逐漸散開呈現(xiàn)出“方”的形狀。這種由圓到方的變化,就是中國(guó)道教文化中的“天圓地方”。在表演的過程中融入道教文化思想,可以側(cè)面反映出當(dāng)時(shí)演出“愛社”的人們是十分崇敬“天”和“地”的,認(rèn)為天地萬(wàn)物是自然法則,并且尊重上天和土地會(huì)帶來連年的豐收和保障生活的基本要求。
其次,自然環(huán)境的影響。壽陽(yáng)縣的地理位置不同于山西其他地區(qū),它位于山脈的中心,四周環(huán)繞著大大小小的山峰,形成了低洼的地勢(shì),有碎片似的小路和陡峭的山坡。行走在山地間,人們會(huì)下意識(shí)地讓自己的腳步變得輕緩,步子時(shí)大時(shí)小。因此也可以在“愛社”的表演中看到,演員們的步伐是在復(fù)刻人們?cè)谄閸绲牡貏?shì)行走的模樣。
最后,生產(chǎn)方式的影響。山西自古以來都是農(nóng)耕為主要生產(chǎn)勞作方式,農(nóng)耕歷史悠久。農(nóng)耕文化不僅影響著社會(huì)的形成,也影響著藝術(shù)文化的發(fā)展方向。壽陽(yáng)也是如此,農(nóng)耕是與黃土、日曬、作物打交道,會(huì)形成擦汗、耕地等經(jīng)典動(dòng)作。那么在“愛社”中,出現(xiàn)了遮陽(yáng)的動(dòng)作、拔東西的動(dòng)作以及屈膝彎腰狀的動(dòng)作,側(cè)面反映著“愛社”是接地氣的農(nóng)耕文化的產(chǎn)物。
壽陽(yáng)“愛社”的民俗審美文化解讀
一、祖先崇拜意識(shí)
中國(guó)從古至今都是一個(gè)血緣為上的國(guó)家,祖先對(duì)于每一位中國(guó)人而言都是尊崇的存在,而祭祀祖先的傳統(tǒng)也流傳至今。人們對(duì)于祖先的祭拜,不僅是對(duì)古祖德追憶,更是希望祖先在上蒼保佑子孫后代福澤綿延,生生不息,因而固定節(jié)日祭祀祖先就成了人們?nèi)粘I钪胁豢珊鲆暤囊画h(huán)節(jié)。黃帝治國(guó)有方、雄才大略,為社會(huì)和國(guó)家的發(fā)展推波助瀾,又教授萬(wàn)民播種糧食、制衣制工具,為人類的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xiàn)。“愛社”作為北神山軒轅廟廟會(huì)的主要活動(dòng),以祭祀祖先為主題,核心就是為了祭祀祖先黃帝。人們通過歌舞、焚香、叩拜等形式表達(dá)對(duì)祖先的尊敬、敬仰,以求得到黃帝先祖的庇佑。“愛社”的出現(xiàn)和表演的內(nèi)容,除了祭祀祖先外,更為中華兒女同宗同源留下了最好的鮮活例證。
二、哲學(xué)觀念匯集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尊崇儒家思想的思想家們不斷發(fā)展壯大的,終成一種獨(dú)特的哲學(xué)思想體系。大致內(nèi)容認(rèn)為天、地、人之間雖各行其道但也有著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三者相互對(duì)應(yīng)、相輔相成。人只有遵循了自然規(guī)律而為之,才能和自然和諧相處,形成人與宇宙、萬(wàn)物、世界之間的互聯(lián)互通,最后形成和諧、中庸的精神追求。“愛社”的演出中體現(xiàn)的也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舞蹈的表演可以說是時(shí)止則止,時(shí)行則行,或者說氣止則止,氣行則行,總是要順乎天時(shí),順乎陰陽(yáng)二氣的互動(dòng)運(yùn)行,以諧天地,以成萬(wàn)物。按照氣體本論,天氣屬陽(yáng),地氣屬陰,春日二氣和合而生萬(wàn)物,冬日氣二分而天地閉氣,萬(wàn)物休息。”從“愛社”的表演形式來看,是集中了三位一體的表演形式,像是天人合一理念中的“天、人、自然”一般。內(nèi)在精神是人、鬼、神之間達(dá)到一個(gè)相互制衡的、平衡的關(guān)系,形成人、鬼、神之間的宇宙觀念、“和”的觀念,進(jìn)而形成或者映射著“天人合一”哲學(xué)思維探討。
三、舞武觀念
從古至今,中國(guó)的武術(shù)和舞蹈就并稱為中國(guó)民俗文化中的雙劍合璧。二者雖然在本質(zhì)特征上、功能特性上有所差異,卻在外形動(dòng)作尚有相似,在蘊(yùn)含的意義上也有異曲同工之處。從民俗文化的特性來看,舞蹈的本質(zhì)并非一項(xiàng)簡(jiǎn)單的運(yùn)動(dòng),而是娛人、娛神、觀賞、趣味在一起的集約藝術(shù)形式。在尚未有文字形成的原始社會(huì)時(shí)期,人類的肢體動(dòng)作伴隨著文化逐漸被賦予了意義,舞蹈也應(yīng)運(yùn)而生。到了周朝,周武王為了慶祝戰(zhàn)爭(zhēng)的勝利或模擬訓(xùn)練的場(chǎng)景,將這些內(nèi)容制作成了歌頌功德的“武舞”《大武》。其實(shí),壽陽(yáng)“愛社”所具有的性質(zhì)與《大武》基本一致,塑造出了神形兼?zhèn)涞乃囆g(shù)形象。
從壽陽(yáng)“愛社”的發(fā)展中逐漸看出,整個(gè)“愛社”儺舞反映了遠(yuǎn)古人類文化向文明文化演變的過程,也展現(xiàn)了山西民俗文化影響下的獨(dú)特古老藝術(shù)的表演形式,深度挖掘了“愛社”的文化特質(zhì)和民俗特質(zhì),有利于山西乃至整個(gè)中原地區(qū)民俗文化的宣揚(yáng)和傳承,也有利于舞蹈中民俗舞蹈文化的擴(kuò)充。
作者簡(jiǎn)介:
張錦錦,女,漢族,山東濟(jì)寧人,太原師范學(xué)院藝術(shù)學(xué)理論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yàn)樗囆g(shù)批評(píng)。本文系2022年太原師范學(xué)院研究生教育創(chuàng)新項(xiàng)目“晉北民俗文化視域下的民俗舞蹈審美研究”成果(基金編號(hào):SYYJSYC-2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