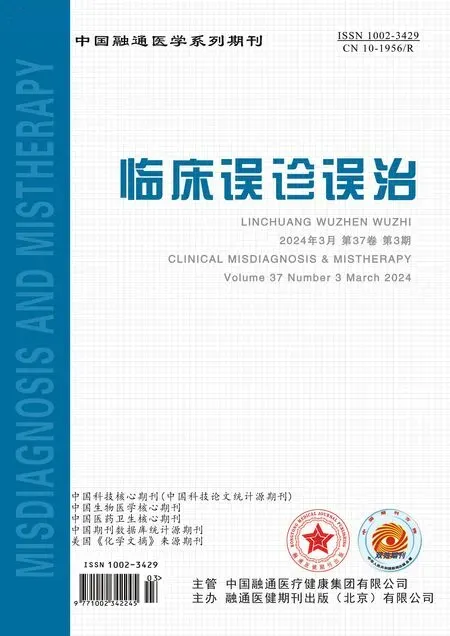感染性休克液體復蘇完成時限對病情轉歸的影響
張 麗,鄭祥德,田 琳
感染性休克病死率在醫療條件發達的今天仍高達40%,是重癥醫學科患者死亡的一個重要病因,故研究其優化的診療方法具有重要意義[1-2]。液體復蘇系感染性休克最基本療法,大量臨床實踐證實,其能及時糾正血容量不足與組織低灌注狀態,改善血流動力學,保護臟器功能,但需在嚴格評估下進行,否則不僅無效,還會加重患者病情[3-5]。早期國際指南建議感染性休克確診后在3 h內給予30 mL/kg初始液體復蘇,后期指南更新建議,在1 h內啟動30 mL/kg初始液體復蘇[6-7]。我國相關指南亦推薦早期、及時液體復蘇[8]。但對于初始液體復蘇完成時限指南未給出明確推薦,仍存有爭議。本研究探討感染性休克液體復蘇完成時限對病情轉歸的影響,為提高該病治療水平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納入標準:符合感染性休克診斷標準[9];成人;無活動性出血。排除標準:患者家屬拒絕有創性操作;妊娠期婦女;腎心肺肝功能衰竭;其他原因引起休克;血流動力學等資料缺失。選取2020年7月—2023年7月達州市中心醫院收治的156例感染性休克患者,根據液體復蘇完成時限分為<1 h組(n=68)、1~2 h組(n=57)、≥2 h組(n=31)。3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本文經達州市中心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2020年審(060)號],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表1 3組感染性休克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1.2 研究方法
全部對象均參考指南[9],確診后立即予30 mL/kg液體復蘇,同時嚴密監測血流動力學、尿量、血乳酸等,隨時調整液體速度,具體液體復蘇時間與方式由主治醫生在評估患者具體情況后決定,液體復蘇完成時限<1 h納入<1 h組,1~2 h納入1~2 h組,≥2 h納入≥2 h組,若經液體復蘇,平均動脈壓仍低于65 mmHg,酌情加用升壓藥。患者均監測有創血壓等血流動力學與呼吸指標、每小時尿量等,并在1 h內啟動抗感染治療,參考患者氧合情況,由主治醫生決定是否給予呼吸支持及其方案。液體復蘇成功標準:中心靜脈壓(CVP)8~12 mmHg,中心動脈壓不低于65 mmHg。
1.3 觀察指標
1)比較3組復蘇前后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狀況評分(APACHEⅡ)[10]、序貫器官衰竭評分(SOFA)[11]。2)比較3組血流動力學指標[外周血管阻力指數(SVRI)、CVP、心指數、每搏量指數(SVI)],復蘇前后監測連續心排血量,由PiCCO儀(德國PULSION,PC4000)獲取。3)比較3組復蘇前后血氣分析指標[血乳酸、pH值、動脈血氧分壓(PaO2)、動脈血二氧化碳分壓(PaCO2)]。4)比較3組復蘇前后血管外肺水指數(ELWI)、肺血管通透性指數(PVPI)、血肌酐,以及復蘇1 h、3 h液體復蘇量。其中ELWI、PVPI通過PiCCO監測儀獲取;血肌酐采用堿性苦味酸速率法測定。5)比較3組去甲腎上腺素應用劑量、重癥監護病房(ICU)住院時間、機械通氣時間。6)比較3組28 d生存率。
1.4 統計學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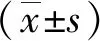
2 結果
2.1 APACHEⅡ、SOFA評分比較
3組復蘇后APACHEⅡ、SOFA評分均低于復蘇前(P<0.01);<1 h組、1~2 h組復蘇后APACHEⅡ、SOFA評分低于≥2 h組(P<0.05);<1 h組、1~2 h組復蘇后APACHEⅡ、SOFA評分比較無明顯差異(P>0.05)。見表2。

表2 3組感染性休克患者APACHEⅡ、SOFA評分比較分)
2.2 血流動力學指標比較
3組復蘇后CVP、心指數、SVI均高于復蘇前,SVRI均低于復蘇前(P<0.01);<1 h組、1~2 h組復蘇后CVP、心指數、SVI高于≥2 h組,SVRI低于≥2 h組(P<0.05);<1 h組、1~2 h組復蘇后CVP、心指數、SVRI、SVI比較無明顯差異(P>0.05)。見表3。

表3 3組感染性休克患者血流動力學指標比較
2.3 血乳酸、pH值、PaO2、PaCO2比較
pH值、3組復蘇后血乳酸、PaCO2均低于復蘇前,PaO2均高于復蘇前(P<0.01);<1 h組、1~2 h組復蘇后血乳酸低于≥2 h組(P<0.05);<1 h組、1~2 h組復蘇后血乳酸比較無明顯差異(P>0.05);3組復蘇后pH值、PaO2、PaCO2比較無明顯差異(P>0.05)。見表4。

表4 3組感染性休克患者血乳酸、pH值、PaO2、PaCO2比較
2.4 ELWI、PVPI、血肌酐、液體復蘇量比較
1~2 h組、≥2 h組復蘇后ELWI、PVPI、血肌酐與復蘇前比較無明顯差異(P>0.05);<1 h組復蘇后ELWI、PVPI、血肌酐高于復蘇前,并高于1~2 h組、≥2 h組(P<0.05);3組1 h液體復蘇量比較無明顯差異(P>0.05),<1 h組、1~2 h組、≥2 h組3 h液體復蘇量呈依次降低趨勢(P<0.05)。見表5。

表5 3組感染性休克患者ELWI、PVPI、血肌酐、液體復蘇量比較
2.5 去甲腎上腺素劑量、ICU住院時間、機械通氣時間比較
≥2 h組去甲腎上腺素劑量高于<1 h組、1~2 h組(P<0.05),<1 h組、1~2 h組比較無明顯差異(P>0.05);<1 h組ICU住院時間、機械通氣時間長于1~2 h組、≥2 h組(P<0.05),1~2 h組、≥2 h組比較無明顯差異(P>0.05)。見表6。

表6 3組感染性休克患者去甲腎上腺素劑量、ICU住院時間、機械通氣時間比較
2.6 28 d生存率比較
<1 h組28 d生存率為73.53%(50/68),1~2 h組28 d生存率為92.98%(53/57),≥2 h組28 d生存率為87.10%(27/31)。1~2 h組、≥2 h組28 d生存率高于<1 h組(P<0.05,P<0.01);1~2 h組、≥2 h組28 d生存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圖1。

<1 h組、1~2 h組、≥2 h組分別為液體復蘇完成時限為<1 h、1~2 h、≥2 h患者組。
3 討論
嚴重感染可激活自身免疫機制,以清除病原體,但這常引起自身毛細血管滲漏、凝血功能異常、局部炎癥損傷等,導致血液容量與容積改變,進而出現器官灌注不足和功能障礙[12]。目前普遍認同,感染性休克是臨床急重癥,一旦確診應根據病情啟動液體復蘇,治療時機越早越好,但多長時間內完成缺乏相關指南推薦,循證醫學報道亦較少[13]。
WU等[14]報道,完成液體復蘇時間與復蘇前后SOFA評分變化率有關,說明液體復蘇完成時限與預后有關,過早或過晚均不利于患者預后改善。本研究結果顯示,<1 h組、1~2 h組復蘇后APACHEⅡ、SOFA評分低于≥2 h組,<1 h組、1~2 h組無明顯差異,提示在1 h內完成初始30 mL/kg液體復蘇與1~2 h內完成對病情的改善作用相近,均優于≥2 h完成。對血流動力學指標進一步統計分析發現,<1 h組、1~2 h組復蘇后CVP、心指數、SVI高于≥2 h組,SVRI低于≥2 h組,<1 h組、1~2 h組以上指標無明顯差異,呈現出類似規律,說明液體復蘇在<1 h、1~2 h內完成均能有效促進血流動力學改善,這可能得益于早期完成液體復蘇,患者微循環灌注和心輸出量更早得到改善。正是由于≥2 h組血流動力學改善不理想,所以其去甲腎上腺素應用劑量最高。
當前仍未明確最佳初始液體復蘇量,若液體復蘇量過少,可造成心排血量不足,難以維持正常組織灌注,進而誘發多器官功能衰竭,升高病死率;若短時間內給予大量液體復蘇,亦可能對機體組織器官產生不利影響[15]。有資料顯示,膿毒癥患者液體復蘇第1日,21%的患者出現組織水腫,3 d內48%的患者出現液體負荷過高[16]。分析原因為,一方面感染性休克時內皮糖萼降解,短時間內補充大量液體可使糖萼脫落,并在原有基礎上加重血管通透性,誘發組織水腫;另一方面短時間內大量液體復蘇可能會超過Frank-Srarling心功能曲線平臺期,引起心房壓力與周身靜脈系統提升,進而影響各組織器官微循環與功能[17-18]。內皮糖萼脫落、降解增加可引起肺泡-毛細血管屏障損傷、肺水腫,升高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等肺部并發癥發生風險[19]。一項meta分析顯示,過量補液將明顯延長機械通氣時間[20]。本研究結果顯示,<1 h組復蘇后ELWI、PVPI高于1~2 h組、≥2 h組,而1~2 h組、≥2 h組則無明顯差異,ICU住院時間、機械通氣時間<1 h組患者亦是最長,表明<1 h完成液體復蘇可增加組織與肺水腫發生風險,延遲恢復,所以應警惕感染性休克患者初始液體復蘇超負荷帶來的消極影響與后果。
有研究用PiCCO儀指導液體復蘇,發現合并急性腎損傷的人群液體復蘇量更多,需接受血液凈化治療比例更高[21]。循證醫學證據顯示,過量補液與重癥患者發生急性腎損傷獨立相關[22]。也有資料表明,重癥液體復蘇患者急性腎損傷的發生率隨CVP上升而升高[23]。本研究結果顯示,<1 h組復蘇后血肌酐高于復蘇前,并高于1~2 h組、≥2 h組,3組1 h液體復蘇量比較無明顯差異,提示液體復蘇在<1 h完成會影響腎功能。其原因可能是,短時內補充大量液體,可使腎靜脈回流受阻、腹腔內壓力不同程度增大,不僅不利于腎灌注改善,還會造成腎功能惡化。可見應對感染性休克患者初始液體復蘇進行嚴格的液體管理,以預防組織器官損傷發生或加重。同時本研究1~2 h組、≥2 h組28 d生存率高于<1 h組,表明液體復蘇完成時限過早會增加不良預后風險,考慮可能與短時間內補充大量液體引起的肺水腫、組織水腫、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腎功能損傷等有關。
本研究仍有一定不足:首先為回顧性研究,可能存在數據偏倚;其次液體復蘇策略由臨床醫生根據患者病情制訂,不可避免存在主觀性與個體差異;本研究液體復蘇系初始液體復蘇,未進行容量反應性評估。下一步仍需積累病例,采用規程化措施,進行前瞻性試驗以進一步觀察分析。
綜上,感染性休克患者初始液體復蘇應在1~2 h內完成,能有效改善器官功能障礙和病情,維持血流動力學穩定,加快恢復進程,促進病情良好轉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