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趕時(shí)間,留住歲月凝固的精彩
文|李晶 楊帆
如果說浩如煙海的典籍只是歷史長河中的奇石或砂礫,古籍編輯不過是一線微光偶然將其照亮,默默地將蜉蝣般的生命堅(jiān)定地投擲于時(shí)間之河,在長河漫卷大浪淘沙的匆匆間隙,去留住那些典籍、文物中的精彩。

岳麓書社副社長兼文博考古編輯部主任王文西
面朝湘江,背倚岳麓,于喧囂熱鬧的長沙市井中,尋一處靜謐的院落,對燈獨(dú)坐,埋首書海,思接千載,對話圣賢,靜止的姿態(tài)背后,埋藏著中華文化根脈深處的堅(jiān)韌。
我們要尋找的,正是這樣一位古籍編輯。王文西,岳麓書社副社長兼文博考古編輯部主任,從業(yè)十七年,對于古籍編輯而言還是個(gè)“新兵”,參與國家級(jí)重點(diǎn)項(xiàng)目近20項(xiàng)。盡管拿過不少獎(jiǎng)、在省內(nèi)也小有名氣,但在王文西看來,他不過是岳麓書社眾多平凡編輯中的一員。板凳一坐十年冷,才是這份工作的常態(tài),并沒有什么值得說道的地方。
十二年前,未滿三十歲的王文西接手百年一遇的中華古籍大型系列類書《中華大典》的子項(xiàng)目《藝術(shù)典》編輯出版工作,為表明決心,他立下“項(xiàng)目不完成我就不剪頭發(fā)”的誓言。六年書成,他已是長發(fā)及腰。
如今距離《中華大典·藝術(shù)典》的完成,又過去了六年。留著平頭的王文西早已褪去了青澀,中年白頭是古籍編輯的常態(tài),但在骨子里,他依然是個(gè)與時(shí)間較勁的人。
古籍不等人,時(shí)間是每個(gè)編輯最大的敵人——面對深埋地下數(shù)千年才得以重見天日的簡牘、散布于山林田野日曬雨淋逐漸風(fēng)化的石刻,還有那些在無盡古籍出版事業(yè)中抱憾逝去的前輩,他只能以畢生精力去追趕。如果說浩如煙海的典籍只是歷史長河中的奇石或砂礫,古籍編輯不過是一線微光偶然將其照亮,默默地將蜉蝣般的生命堅(jiān)定地投擲于時(shí)間之河,在長河漫卷大浪淘沙的匆匆間隙,去留住那些典籍、文物中的精彩。
坐起冷板凳,一頭扎進(jìn)書海
雨后南園凝碧池,獨(dú)留清氣兩三枝。
寸心猶抱凌云志,一任春風(fēng)笑我癡。
——《文竹》 王文西
身為“冷門弟子”,坐冷板凳有什么不好?
2006年秋,即將研究生畢業(yè)的王文西面對著人生的十字路口。彼時(shí)的他拜在湖南師范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冷鵬飛教授門下攻讀秦漢史。導(dǎo)師姓冷,專業(yè)也“冷”,因此一眾師兄弟皆以“冷門弟子”自況。學(xué)生時(shí)代的王文西一心追隨導(dǎo)師步伐,下定決心沿著這條冷門道路走下去。不料臨近畢業(yè),導(dǎo)師生了一場病,隨導(dǎo)師繼續(xù)攻讀的想法只好暫時(shí)擱置,找工作變成了眼前最現(xiàn)實(shí)的問題。11月考上了岳麓書社,導(dǎo)師直接發(fā)話,讓家境困難的王文西不要再猶豫,早點(diǎn)找個(gè)班上,解決吃飯問題。思來想去,王文西遵從內(nèi)心的愿望,選擇了去岳麓書社做編輯。中學(xué)時(shí)編輯過校園文學(xué)社刊物《星語》,大一時(shí)當(dāng)過學(xué)院新生軍訓(xùn)刊物《九月》的采編,為了賺點(diǎn)生活費(fèi)參與過民營書商組織的《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匯編·草木典》的點(diǎn)校工作,或許就是他給編輯職業(yè)生涯最初埋下的三顆種子。
學(xué)生時(shí)代的王文西嗜書如命。一到周末他就去古舊書店淘書,從窯嶺轉(zhuǎn)到定王臺(tái),再到水風(fēng)井的長沙古舊書店,再到河西大學(xué)城的述古書店、商周書店,長沙所有古舊書店無一不被他和幾個(gè)書友淘遍。遇見心儀的書,他節(jié)衣縮食也要買。一次遇見一本零散的舊志,標(biāo)價(jià)竟只要兩塊五,他不動(dòng)聲色地買下來,出了店門撒腿就跑,生怕店家反悔,回宿舍后在扉頁小心翼翼題上兩行字:“珠玉蒙塵,棄之何忍。”在這段淘書的時(shí)光里,距離母校湖南師大散步只有十分鐘路程的古籍社岳麓書社,更是令這位“冷門弟子”倍感親切,入手了大量岳麓版的文史舊書。
自1982年創(chuàng)社以來,岳麓書社以整理出版湖湘文獻(xiàn)為己任,又擁抱全國市場,闖出了敢打敢拼的名聲。從這里走出了《船山全書》《曾國藩全集》《湖湘文庫》等一部部大書,留下了鍾叔河、楊堅(jiān)、夏劍欽、唐浩明等出版大家。在王文西看來,這些人、這些書,就是“一段歷史、一座照亮后來人前行之路的燈塔”。但當(dāng)時(shí)的王文西沒想到,與岳麓書社同齡的他也會(huì)在這個(gè)小院中留下自己的足跡,成為這段不斷續(xù)寫的出版歷史中雖微小但也重要的一個(gè)注腳。
王文西做出人生抉擇的2006年,也是岳麓書社歷史上極其重要的年份:大型文化工程《湖湘文庫》和《中華大典·藝術(shù)典》編輯出版項(xiàng)目在岳麓書社啟動(dòng),這家年輕的古籍出版社亟待掀開新的篇章。對于一個(gè)年輕的讀書人來說,在這方天地間應(yīng)當(dāng)可以有一番作為——王文西聽從了導(dǎo)師的建議,義無反顧來到岳麓書社坐起“冷板凳”。
在應(yīng)聘編輯崗位的考試中,王文西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績。試卷的最后一題,他一鼓作氣寫就了一篇以湖湘文化為主題的小論文。入職很久之后,王文西才從前輩那里得知,時(shí)任岳麓書社首席編輯唐浩明先生親自閱卷,對這篇小文章給予了高度評價(jià)。社里原計(jì)劃都招省外高校的畢業(yè)生以擴(kuò)充出版資源,如果不是唐浩明先生評分較高,王文西那一年就錯(cuò)過了岳麓書社,也許就轉(zhuǎn)而去當(dāng)老師走上了另一條職業(yè)道路,因此始終對唐先生心懷感激。
師徒相傳的專注,正是岳麓書社能在短短幾十年里成為南方古籍出版重鎮(zhèn)的原因。在這里,既有唐浩明這樣關(guān)心后進(jìn)的前輩大家,也有新人編輯職業(yè)生涯耐心專業(yè)的引導(dǎo)者,王文西覺得自己是幸運(yùn)的,因?yàn)樗龅搅艘晃弧昂脦煾怠薄獣r(shí)任歷史文化編輯部主任的管巧靈老師。管老師1985年進(jìn)社時(shí),時(shí)任總編輯鍾叔河先生立下規(guī)矩,每一個(gè)進(jìn)入書社的編輯,都要從校對古籍刻本做起。1985年,廈門大學(xué)畢業(yè)生管巧靈與北師大畢業(yè)生丁雙平、南開大學(xué)畢業(yè)生楊云輝、武漢大學(xué)畢業(yè)生曾德明、武漢師范學(xué)院畢業(yè)生丁方曉同年進(jìn)社做編輯,學(xué)到的第一課,就是校對刻本的基本功。2007年,王文西與北師大畢業(yè)生李業(yè)鵬、南開大學(xué)畢業(yè)生胡寶亮、武漢大學(xué)畢業(yè)生彭衛(wèi)才與劉文一起走進(jìn)岳麓書社的大門,這一傳統(tǒng)也被他們從前輩手中接續(xù)過來。
王文西眼中的管巧靈老師,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嚴(yán)師”,可能因?yàn)槎际寝r(nóng)村貧寒子弟出身,師徒二人無話不談,管老師重在言傳,勤勉嚴(yán)謹(jǐn)。王文西直接把房子租在了管老師小區(qū)對面,周末經(jīng)常跟著管老師一起去加班。入職第二年,管老師就開始“逼”他獨(dú)立做書。王文西硬著頭皮在慢慢摸索中做出一本小書,結(jié)果在付印清樣比紅環(huán)節(jié)就出現(xiàn)了一個(gè)校對錯(cuò)誤——目錄里“一將功成萬骨枯”,漏掉了一個(gè)“功”字。這個(gè)錯(cuò)誤就像一顆釘子,永遠(yuǎn)釘在王文西的職業(yè)生涯里,讓他時(shí)時(shí)刻刻提醒自己不能漏掉任何一個(gè)細(xì)節(jié)。時(shí)至今日,每當(dāng)有新人編輯加入編輯部,他都會(huì)把這件事講給他們聽。
懷抱著夢想與不安,王文西的編輯人生由此拉開了帷幕。
蓄長發(fā)明志,只為《大典》修成
彼岸花開慰寂寥,誅心何必奈何橋。
蕓編問世仙人杳,衣帶蒙塵謝女嬌。
磨劍歸來須醉酒,浮槎隱去任吹簫。
剪斷青絲君莫笑,余生未老不及腰。
——《藝術(shù)典修成剃發(fā)詠懷》 王文西
工作四年半,對于一個(gè)岳麓社的古籍編輯而言還是個(gè)尚未出師的學(xué)徒,王文西不會(huì)想到自己有一天能參與到百年一遇的古籍整理出版項(xiàng)目。
《中華大典》,中國出版史上的一顆明珠——全國共出版408冊、7.45億字,是繼唐代《藝文類聚》、宋代《太平御覽》、明代《永樂大典》和清代《古今圖書集成》之后的最大類書。
2012年元月,岳麓書社任命王文西為中華大典項(xiàng)目部副主任主持工作,接手《中華大典·藝術(shù)典》的編輯出版任務(wù)。王文西不知道接下來迎接他的將會(huì)是怎樣的挑戰(zhàn),但《中華大典》的分量,仍讓他感到誠惶誠恐。時(shí)任社長易言者三次找他談話,他最后回應(yīng)一句“事在人為”接下了任務(wù)。
早在1987年,岳麓書社就開始參與籌備《中華大典》的出版工作,2006年《中華大典·藝術(shù)典》的編纂工作便已啟動(dòng),但因?qū)I(yè)門檻高、編纂難度大,許多分典的進(jìn)度一直處于停滯狀態(tài),其中《書法藝術(shù)分典》的作者團(tuán)隊(duì)更是換來換去無人接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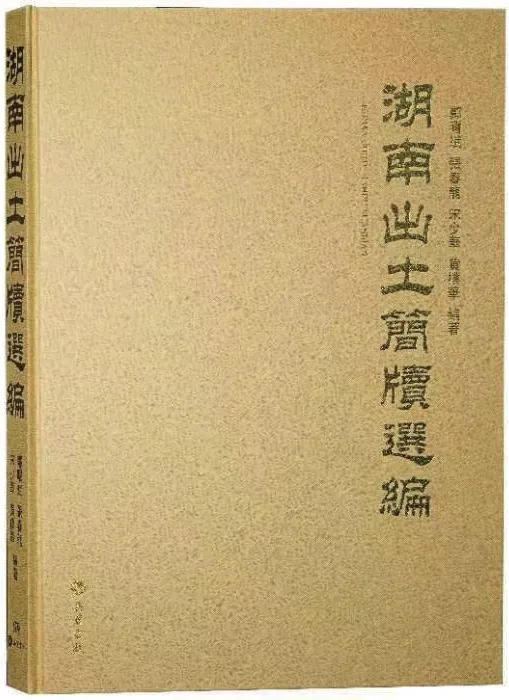
一個(gè)啟動(dòng)六年未完成的項(xiàng)目,如今由一位新人接手,難度可想而知。或許是察覺自己內(nèi)心的猶疑,在那年冬天的年度選題論證會(huì)上,面對前輩的質(zhì)疑,如坐針氈的他信口說出一句“請老師們放心,項(xiàng)目不完成我就不剪頭發(fā)”。
從文獻(xiàn)普查、引文摘錄,到書稿錄入、底本核對,再到歸經(jīng)入緯、斷句標(biāo)點(diǎn)……王文西與同事孫世杰既當(dāng)責(zé)任編輯,又當(dāng)不署名的作者,兩個(gè)人并肩作戰(zhàn)互相鼓勵(lì),歷時(shí)六年焚膏繼晷,書成之時(shí),王文西已是長發(fā)及腰,而孫世杰得了高血壓。孫世杰2010年從南京大學(xué)古典文獻(xiàn)學(xué)專業(yè)畢業(yè)后,一進(jìn)岳麓社就從事《藝術(shù)典》的編輯工作,八年的大好青春,都奉獻(xiàn)給了這套叢書。王文西說得很坦誠:“老實(shí)說,中間我們也曾有過遲疑、短暫的消沉,但是只要想起北方還有一位白發(fā)蒼蒼的九旬老人,與病痛抗?fàn)帲c時(shí)間賽跑,年復(fù)一年地等候著一部書的出版,我的心底就有一種無可言說的羞恥感涌上來,刺痛自己的神經(jīng),然后老老實(shí)實(shí)地回到辦公室,埋進(jìn)書稿當(dāng)中。”
從2013年到2018年,大女兒王依扉自出生起就沒見過王文西短頭發(fā)的樣子,經(jīng)常管他叫“西媽媽”。他有時(shí)把大女兒帶到辦公室加班,他在辦公室內(nèi)校稿子,女兒一個(gè)人在天臺(tái)上的小花園里看花花草草或是捉蟲子玩。偶爾周末陪著在小區(qū)里轉(zhuǎn)兩圈,這時(shí)他就會(huì)聽到女兒跟其他小朋友開玩笑說:“我是個(gè)沒有爸爸的小孩。”直到女兒快滿六歲的時(shí)候,《中華大典·藝術(shù)典》終于順利結(jié)項(xiàng)。2019年1月3日,王文西在女兒生日當(dāng)天,自費(fèi)在麓山賓館請客小聚,在社里前輩、同事、師友和家人的見證下,總編輯馬美著先生用一把編輯裁紙的剪刀,幫他剪掉長發(fā)。他將辮子裝進(jìn)書匣,藏在書柜的角落里。
如果時(shí)間可以倒流,或許王文西再也不敢“口出豪言”。唯有經(jīng)歷過此中辛酸,他終于理解了對于一個(gè)古籍編輯而言,時(shí)間究竟意味著什么。
他還記得第一次拜訪《戲曲文藝分典》主編、北師大教授李修生老師時(shí),一進(jìn)門就看到墻上掛著教授夫人的遺照。老先生對他說:“當(dāng)年項(xiàng)目啟動(dòng)的時(shí)候她還在,現(xiàn)在她已經(jīng)在墻上了。”
2018年2月12日,臘月二十七,當(dāng)王文西拿到《中華大典·藝術(shù)典》全套樣書時(shí),在日記中寫了一段話:“今天等到印刷廠送過來的新書,關(guān)起門坐在辦公室咬緊牙關(guān)抱著新書心緒難平。向臥病在床的九十四歲高齡的總主編金維諾先生致敬,向李修生、李真瑜、張大新、謝大勇、陳雨前、劉天琪等多位為書稿編纂工作付出多年心血的專家學(xué)者致敬,向等不到出書就已相繼鶴歸道山的特邀編輯廖承良先生、《服飾分典》主編李之檀先生再說一聲抱歉。……讀書人青春可耗,名利可失,寂寞可忍,志不可奪。莫問前程,埋首耕耘,但求無愧我心。今夜必須喝酒。”原本想年后再背上新書去給金老拜年,卻在幾天后驚聞老人家已于大年初二去世,王文西慟哭不已。
《中華大典·藝術(shù)典》給王文西的編輯生涯貼上了揮之不去的標(biāo)簽,也留下了關(guān)于遺憾的烙印。更重要的是,他自此意識(shí)到,在浩瀚的書海里,在無盡的時(shí)間長河里,一個(gè)編輯的職業(yè)生涯竟是如此地渺小與短暫:“一個(gè)古籍編輯,二十五歲進(jìn)社,爭取五年時(shí)間出師,到六十歲退休,也就只剩三十年的時(shí)間。陪著世杰兄做大典,我用了六年,石刻文獻(xiàn)至少要四年,真不知道我的職業(yè)生涯還能有幾個(gè)這樣的項(xiàng)目,能夠憑著心底不服輸?shù)囊豢跉獍境鰜怼!?/p>
他悔恨自己“少壯不努力”,周末守著湘江通宵釣魚寫詩填詞,卻不老老實(shí)實(shí)通宵看稿,“終究是欠的債太多,后半段要舍棄老命來趕時(shí)間”。正是從這一刻起,編輯王文西成了一個(gè)與時(shí)間賽跑的人。
人生如逆旅,亦可生生不息
獵戶征南又一年,星光落處正無眠。
家山只似楓橋店,火樹銀花映客船。
——《煙花》 王文西
2023年除夕,王文西回到瀏陽老家,從接手《中華大典·藝術(shù)典》已過去了十二年,期間他少有這般不用背著一書包的書稿回家過年。念及于此,已過不惑之年的他像前輩胡遐之老社長一樣,照例用一首小詩向師友拜年,并且發(fā)出感慨:“除夕夜賞煙花,念家山竟如旅店,匆匆聚散。”在這溫情時(shí)刻之外的大多數(shù)時(shí)間里,他總在埋首故紙堆,不曾停歇。
面對古籍文獻(xiàn)之海,王文西總是顯得身單力薄,最孤獨(dú)的時(shí)候,管巧靈老師內(nèi)退,師弟邱建明轉(zhuǎn)投湖南省博物館,新人還沒招上來,編輯部只剩下他一個(gè)人。而他與之“對抗”的方法也很簡單:那就是將時(shí)間投擲其間。頂著日常的編校壓力,面對著國家重點(diǎn)項(xiàng)目的結(jié)項(xiàng)時(shí)限要求,如履薄冰的他只能投入一個(gè)又一個(gè)夜晚。時(shí)間久了,他便成了書社出名的“加班狂”,門衛(wèi)何師傅拿他沒辦法,每到夜里十一二點(diǎn),都會(huì)打電話到王文西的辦公室,問他到底什么時(shí)候下班,叮囑他記得鎖門。
2019年,王文西接到急稿,他一個(gè)又一個(gè)通宵地加班,當(dāng)時(shí)兒子王 塵剛剛滿月,沒有老人幫忙帶,只能在晚上和妻子輪班。他一邊抱著容易驚醒的孩子,一邊趕稿子。突然想到管巧靈老師曾經(jīng)講過的故事:他剛做編輯的時(shí)候,住在單位租的宿舍樓,冬天特別冷,女兒還很小,只能一只手抱著女兒,另一只手校稿子,桌子底下放一個(gè)臉盆,備兩瓶開水,泡腳取暖。反觀自己如今還吹著空調(diào),不禁淚濕眼眶。
管巧靈老師反復(fù)給王文西灌輸一種觀念:做編輯絕對不能停留在做來料加工,或者純粹的案頭工作上,不能“別人給你一口飯,你就吃一口飯”,而是要自己主動(dòng)策劃選題,還要有前瞻性的眼光,“一年要把后面兩三年的事情都想好”。
正因如此,王文西把目光投向了湖南石刻、簡牘等出土文獻(xiàn)。他在一篇小文章《吾誰與歸:臨江望岳覓書香》中寫道:“湖南出土簡牘總量約占全國的2/3,大量檔案、公文、律令、簿記、醫(yī)書、美食方等深埋地下,勾勒出多少古人的人生履歷碎片和煙火氣息。俯身閱讀簡牘上的地名、官名、人名時(shí),總有一種歷史的厚重感撲面而來。他們有幸成為最初一批青史留名的湖南人,不幸的是一度隨著黃沙野草被歷史遺忘。千年之后,我輩從這些出土簡牘中得以窺見湖湘先民的社會(huì)生活風(fēng)貌,理應(yīng)心存感激。湖湘簡牘的陸續(xù)出版,必將給我們帶來更多驚喜,更多湖南人血脈的認(rèn)同。”
2010年前后,岳麓書社做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項(xiàng)目申報(bào)工作,管巧靈與王文西一起策劃出《湖南石刻文獻(xiàn)集成》的選題;2018年《中華大典·藝術(shù)典》結(jié)項(xiàng)時(shí),《湖南石刻文獻(xiàn)集成》的書稿便已擺上案頭;當(dāng)《湖南石刻文獻(xiàn)集成》于2022年結(jié)項(xiàng)時(shí),《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牘》無縫對接……接下來他還打算編輯出版《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校釋》,用王文西的話說,“至少十六冊,還要做八年”。
2023年,《長沙走馬樓西漢簡牘選粹》上架之時(shí),他的小女兒王洛汀出生,六個(gè)半月后,女兒喊了一聲“爸”。在無間歇的紙上勞作中,王文西的編輯生涯竟如人生一般,呈現(xiàn)出一種生生不息的面貌。“確實(shí)很慚愧,前面兩個(gè)小孩的童年沒管過,希望第三個(gè)能彌補(bǔ)一下。還有,《湖南出土簡牘集成》在我退休前估計(jì)是做不完了,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至于能否子承父業(yè),那也要隨緣了。”
寂寥人間世,有人重理夜燈

《中華大典·藝術(shù)典》
也曾彩筆和清淚,寫深情、繪佳麗。書城積稿塵封,一任蟲翻鼠戲。湮沒他年誰收拾,更誰人、夜燈重理。珠貝永沉埋,寂寥人間世。
——《晝夜樂》 茅于美
一個(gè)深夜,王文西在校稿時(shí)讀到現(xiàn)代著名女詞人茅于美教授(茅以升先生長女)詞集中的這一闋,那一刻,他感覺自己就是那個(gè)“夜燈重理”的“誰人”。他始終覺得編輯首先是一個(gè)讀書人,“夜燈重理”正是讀書人之間的一種托付,一種時(shí)空交錯(cuò)的傳承。
走進(jìn)王文西的辦公室,滿眼的圖書和書稿,只留尺許寬的過道。在浩如煙海的古籍文獻(xiàn)面前,編輯愈發(fā)顯得渺小。古籍文獻(xiàn)整理注定是寂寞而無止境之事。
“編輯石刻、簡牘這類出土文獻(xiàn),只能盡力去做,缺憾永遠(yuǎn)存在。”王文西坦言,《湖南石刻文獻(xiàn)集成》最后呈現(xiàn)出的只是精選本,因?yàn)楹芏嗍袒蚴菦]有拓片,或是照片不清晰,或是難以代替作者跑遍全省十四個(gè)地州市拍照片、補(bǔ)拓片,最終導(dǎo)致收錄進(jìn)書稿的碑刻條目不全面。
雖然明知結(jié)果總會(huì)不盡人意,真正閱讀這些出土文獻(xiàn)的人也不會(huì)很多,但王文西始終認(rèn)為事在人為,編輯應(yīng)該盡力去做,而且要即時(shí)即刻去做。“因?yàn)槲覀冏龅氖菗尵刃怨ぷ鳎豢桃膊荒艿取!北热缡蹋髦成鲜珍洸蝗牧R名,硬著頭皮也還是要去做這套書,再不去做,多少石刻將會(huì)風(fēng)化殆盡,多少湖湘先賢、今世凡人的祖先的行跡英名將徹底湮沒無聞……
王文西曾為詩詞自選集《幽篁集》題過一首小詩,其中有一句“蒙君慧眼識(shí)珠璣,愧我平生作嫁衣”。對此王文西感慨:幾套叢書數(shù)千萬字做完,我們這些編輯是需要一個(gè)字一個(gè)字看過來的,但是最后成書,編輯名字并不會(huì)署在封面上,我們都適應(yīng)了這個(gè)狀態(tài)。
但他并不認(rèn)為編輯是一門苦差事,在做古籍出版這件事上,十七年來興趣與職業(yè)交織,如今兩者根本無法分開,校稿成為逃避不了的“自己的事”,編輯已成為一種習(xí)慣之中的生活狀態(tài)。
一路走來,王文西見證了岳麓書社歷史文化編輯部轉(zhuǎn)變成為文博考古編輯部,所幸的是,他不再是一個(gè)人硬扛。“2021年從廈門大學(xué)引進(jìn)了包文放、從山西大學(xué)引進(jìn)了魯云云,疫情期間都是跟著我在深圳印刷廠蹲點(diǎn)改稿鍛煉過的”;師弟邱建明出走兩年后,也于2023年重新回到岳麓書社做編輯;“我們2024年上半年還將從武漢大學(xué)引進(jìn)學(xué)簡牘的聶永芳,從南京大學(xué)引進(jìn)學(xué)古典文獻(xiàn)學(xué)的夏富慶”,隊(duì)伍不斷擴(kuò)充,一切充滿希望。他時(shí)常會(huì)想起那些岳麓書社老一輩的編輯在時(shí)間的源流之處給予他啟示,他從這里獲得抵抗時(shí)間的勇氣,又將這一勇氣傳遞給更年輕的編輯……就這樣一棒接著一棒,幾代古籍出版從業(yè)者接力完成著時(shí)代賦予的責(zé)任與使命。岳麓人也不過是出版人、讀書人群體中的一個(gè)側(cè)影。中華文脈也正是在一代又一代出版人、讀書人傾注的時(shí)間中薪火相傳、綿延不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