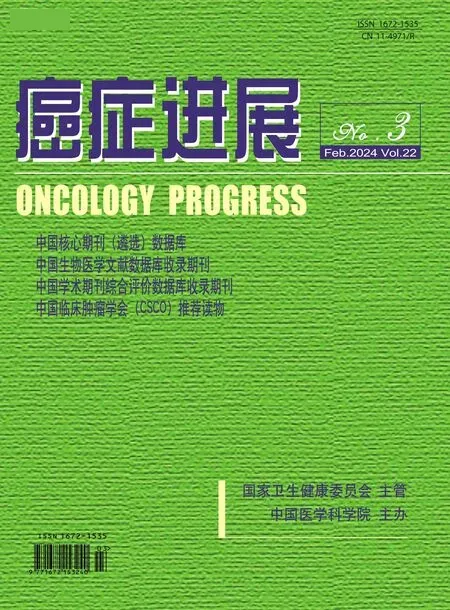轉化生長因子-β1、細胞角蛋白19、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對中晚期肝癌調強放療患者預后的預測價值△
艾冬冬,李麗芳,劉丹,付艷群
新余市人民醫院檢驗科,江西 新余 338000
肝癌是臨床常見的消化系統惡性腫瘤,早期癥狀缺乏特異性,容易被患者忽略,當其出現明顯癥狀就診時多已進展至中晚期,而中晚期患者的手術治療效果較差,多采用放療進行治療[1]。調強放療是目前中晚期肝癌患者較為常用的放療方式,其利用波束角和輻射束強度的波動減輕了放射線對周圍正常組織的損傷,安全性較高,且臨床療效優于傳統放療[2]。
為進一步改善患者的預后,放療后需要根據階段性療效評估結果調整維持治療方案,影像學檢查是直觀觀察腫瘤變化情況的檢查方式,但影像學檢查也具有一定的輻射,頻繁檢查也可能會對腫瘤造成不良影響,因此,臨床多采用血清學指標對臨床療效進行評價[3-4]。雖然目前臨床評估肝癌預后的血清學指標較多,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還需尋找靈敏度和特異度均較高的新指標,以進一步完善肝癌預后的評估方案。轉化生長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細胞角蛋白19(cytokeratin 19,CK19)和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是近年來新發現的腫瘤標志物,在多種腫瘤的診斷和預后評估中均具有較高的靈敏度[5-7]。基于此,本研究探討TGF-β1、CK19 和NLR 對肝癌調強放療患者預后的預測價值,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20 年1 月至2023 年8 月新余市人民醫院收治的中晚期肝癌患者。納入標準:①符合《原發性肝癌診療規范(2019 年版)》[8]中關于肝癌的診斷標準;②中國肝癌分期(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CNLC)為Ⅱa~Ⅳ期;③接受調強放療。排除標準:①合并血液疾病;②合并自身性免疫性疾病;③合并感染性疾病;④合并其他惡性腫瘤;⑤隨訪時間﹤8 周。依據納入和排除標準,本研究共納入72 例中晚期肝癌患者,其中男40 例,女32例;年齡42~75 歲,平均(58.61±10.26)歲;CNLC 分期:Ⅱa 期5 例,Ⅱb 期7 例,Ⅲa 期15 例,Ⅲb 期20例,Ⅳ期25 例。本研究經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通過,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
1.2 檢測方法
72 例患者均接受4 周的調強放療,治療前后抽取空腹肘靜脈血3 ml,3000 r/min 離心15 min,離心半徑10 cm,分離血清,采用AU480 全自動生化分析儀[貝克曼庫爾特實驗系統(蘇州)有限公司]檢測TGF-β1 水平、CK19 水平、中性粒細胞計數、淋巴細胞計數,計算NLR。
1.3 隨訪方法
72 例患者接受調強放療后,連續隨訪4 個月,復查腫瘤情況和生存情況,將患者生存且腫瘤靶病灶較治療前縮小或無明顯差異判定為預后良好,將患者生存但腫瘤靶病灶較治療前增大或出現新增病灶或死亡判定為預后不良。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6.0 軟件對所有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和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繪制受試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計算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AUC),評估TGF-β1、CK19、NLR 單獨和聯合檢測對中晚期肝癌調強放療患者預后的預測價值;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不同預后肝癌患者TGF-β1、CK19 水平和NLR 的比較
隨訪4 個月,72 例肝癌調強放療患者中,預后良好43 例,預后不良29 例。預后良好患者中,男23 例,女20 例;年齡42~75 歲;CNLC 分期:Ⅱ期8例,Ⅲ期20 例,Ⅳ期15 例。預后不良患者中,男17例,女12 例;年齡45~74 歲;CNLC 分期:Ⅱ期4 例,Ⅲ期15 例,Ⅳ期10 例。放療前,不同預后肝癌患者TGF-β1、CK19 水平和NLR 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放療后,預后不良肝癌患者TGF-β1、CK19 水平和NLR 均明顯高于預后良好患者,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表1)。
表1 放療前后不同預后肝癌調強放療患者TGF-β1、CK19 水平和NLR 的比較(±s)

表1 放療前后不同預后肝癌調強放療患者TGF-β1、CK19 水平和NLR 的比較(±s)
預后良好(n=43)不良(n=29)t值P值TGF-β1(ng/ml)放療前54.75±14.87 53.17±12.85 0.486 0.641 NLR放療后40.96±15.09 50.75±12.92 2.856 0.006 CK19(ng/ml)放療前154.48±22.62 153.34±24.18 0.204 0.839放療后111.16±32.48 150.01±31.81 5.019 0.000放療前4.38±0.84 4.40±0.80 0.067 0.947放療后3.38±0.78 4.63±1.36 4.935 0.000
2.2 TGF-β1、CK19、NLR 單獨和聯合檢測對中晚期肝癌調強放療患者預后的預測價值
ROC 曲線顯示,TGF-β1、CK19、NLR 聯合檢測預測中晚期肝癌調強放療患者預后的AUC 為0.894(95%CI:0.799~0.954),高于各指標單獨檢測,靈敏度為79.31%,特異度為93.02%。(表2、圖1)

圖1 TGF-β1、CK19、NLR單獨和聯合檢測預測中晚期肝癌調強放療患者預后的ROC曲線

表2 TGF-β1、CK19、NLR 單獨和聯合檢測對中晚期肝癌調強放療患者預后的預測價值
3 討論
調強放療是目前治療中晚期肝癌較為常用的放療方法,但是由于肝癌具有復發率高的特點,因此,放療結束后對其預后進行預測是進一步調整后續治療方案的重要前提[9]。血清學指標檢測是臨床評估中晚期肝癌放療患者預后的常用方法,雖然目前臨床使用的血清學指標較多,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還需挖掘更多的新指標來完善預后預測方案。
TGF-β1 是上皮-間充質轉化誘導因子的一種,在人體內可刺激間充質起源細胞的增殖并抑制神經外胚層和上皮起源細胞的生長,其與腫瘤的發生發展有一定相關性[10]。本研究結果顯示,預后不良患者TGF-β1 水平高于預后良好患者,這可能是因為肝癌患者會隨著病程進展出現免疫抑制,免疫抑制會誘導TGF-β1 水平升高,且由于肝臟中含有較多的間充質干細胞,TGF-β1 水平升高可刺激間充質干細胞異常增殖和癌變,加速腫瘤進展,而TGF-β1 水平降低會抑制生長因子活性,增強機體抗腫瘤免疫反應,進而抑制腫瘤進展,因此,放療后TGF-β1 水平較低患者的預后較好[11-12]。
CK19 屬于細胞體中間絲的一種,主要存在于上皮細胞中,機體發生腫瘤時,CK19 水平會升高[13]。本研究結果顯示,預后不良患者CK19 水平高于預后良好患者。分析原因是,CK19 可對細胞骨架結構進行重塑,因此,CK19 水平升高可激活肝癌細胞的上皮-間充質轉化過程,激活β-聯蛋白(β-catenin)信號通路相關蛋白的表達,增強肝癌細胞的轉移能力,促進肝癌細胞的生長和遷移,使患者的病情惡化,因此,CK19 水平越高,患者的預后越差[14-15]。
NLR 是炎癥反應標志物的一種,機體出現炎癥反應時其水平升高,而肝癌發生發展過程中也會導致免疫系統失衡,導致NLR 升高[16]。本研究結果顯示,預后不良患者NLR 高于預后良好患者,NLR 越高則患者的預后越差。分析原因是,NLR升高表示機體炎癥反應加重,而炎癥反應加劇會進一步使免疫失衡情況變得更嚴重,為腫瘤細胞生長和轉移提供良好的免疫逃逸微環境,對患者的預后造成負面影響[17-18]。
此外,本研究ROC 曲線結果顯示,TGF-β1、CK19、NLR 聯合檢測預測中晚期肝癌調強放療患者預后的AUC 為0.894(95%CI:0.799~0.954),高于各指標單獨檢測,表明聯合檢測對患者預后的預測價值最高,可為其預后預測提供有效依據。
綜上所述,TGF-β1、CK19、NLR 聯合檢測預測中晚期調強放療患者預后的價值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