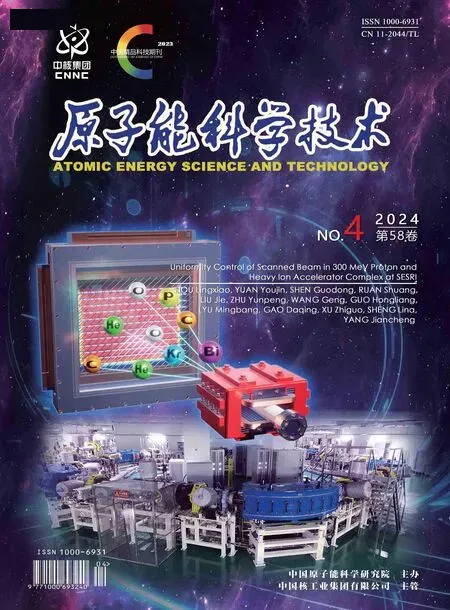壓水堆沉積物對包殼表面性能影響的模擬研究
沈 媛,來允塵,譚詩雨,矯彩山,侯洪國,晁 楠,高 楊,*
(1.哈爾濱工程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1;2.核電運行研究(上海)有限公司,上海 202150)
一回路結構材料產生的腐蝕產物會在燃料包殼表面沉積,20世紀40年代末,加拿大喬克河實驗室最先根據反應堆運行經驗命名了這種沉積物,即CRUD(Chalk River Unidentified Deposit)[1-2]。沉積物對反應堆操作和維護的安全性帶來的影響越來越重要,其中反應堆產生的最主要的風險來自沉積物中硼累積而造成的沉積物誘導的功率偏移(CIPS)和包殼腐蝕(CILC)。這兩種風險都與沉積物存在時壓水堆包殼表面傳熱與傳質性能發生的改變有關[3-5]。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針對輕水堆中的沉積物傳熱研究就拉開了帷幕,并形成了一系列以燈芯沸騰為核心的理論和模型研究。燈芯沸騰是基于沉積物結構所作的假設,很多模型均采用該假設來研究沉積物內的傳熱與流動情況。燈芯沸騰的機理認為沉積物的燈芯結構使得冷卻劑能夠通過內部顆粒空隙進入到沉積物中發生蒸發換熱的表面[6]。沉積物結構和傳熱機制細化、多物理場模擬拓展、維度拓展和網格劃分優化等方面已發展了一系列模型[7-12],并通過實驗確定包殼表面的沉積物為多孔且存在煙囪通道[13]。但是,一些研究者發現燈芯沸騰模型計算的結果與實際存在一些矛盾,如Short等[12]報道了燈芯沸騰計算所得的相對實際情況過高的液體過熱度,另外,模擬的有效CRUD熱導率也與實驗結果之間存在矛盾。這可能與燈芯沸騰的假設有關,因為在一般的燈芯沸騰模型中,冷卻劑與沉積物界面溫度為飽和溫度,煙囪通道壁面溫度等于飽和溫度,而沉積物內全部處于沸騰狀態。為了減小模擬結果與實驗結果的差異從而使模擬預測更接近實際,Jin等[14]及Yeo等[15-16]考慮了高熱通量下沉積物中同時存在燈芯沸騰和膜沸騰的這種過渡狀態的可能性,使得沉積物的傳熱模型計算結果更貼近真實值。然而,理論上CRUD中同時存在非沸騰和沸騰,所計算的過熱度將會低于完全沸騰的過熱度,但目前缺少同時考慮非沸騰與沸騰的過渡模型。為此,本文提出了基于燈芯沸騰機制優化的過渡傳熱模型用于預測沉積物中的傳熱情況。
壓水堆中的功率偏移,即AOA現象,被認為主要是因為過冷沸騰導致腐蝕產物在燃料元件上沉積引起的[17]。這是因為沉積物中會隱藏硼物質,無論是以骨架形式組成沉積物,還是由于過冷沸騰使得硼類物質在沉積物的孔隙或煙囪通道中累積,在出現功率偏移時,一個燃料循環周期結束后單根燃料棒的沉積物中所含硼的總質量約為57 mg[18]。而EPRI[19]給出的結果是在一個循環過程中整個堆芯的硼隱藏量約為0.27 kg,會導致軸向偏移率約為-3%,而發生嚴重功率偏移情況的堆芯中硼累積量約為1.1 kg。根據EPRI給出的評價指標,AOA的偏移率若小于3%,則認為CIPS是低風險的,若接近5%,則認為是中風險的,而若大于10%,則認為是高風險的[20]。對于預測CIPS,準確預估相應條件下包殼表面在沉積物中不同形式的硼累積量至關重要。而針對CILC的模擬預測,文獻[21]開發了新的包殼氧化模型,用于預測沉積物導致的包殼表面更大硼鋰濃度下的腐蝕行為,并對CILC的風險進行了分析。
因此,本文通過壓水堆包殼表面的多物理場過程分析,建立沉積物內部傳熱、傳質、流體流動和化學過程的多物理場耦合模型,預測不同操作條件、水化學條件和沉積物結構下沉積物對包殼表面性能的影響,分析相應情況下沉積物誘導包殼表面傳熱性能、硼累積風險變化,為堆芯設計、包殼材料開發和運行監測等提供建議。
1 包殼表面多物理過程分析和模擬
1.1 包殼表面沉積物的物理結構分析
燃料包殼表面的沉積物被視為帶煙囪的多孔結構,從物理結構上來說,較大的孔或縫隙相連,形成煙囪通道。研究人員通常將多孔沉積物內部的煙囪通道視為均勻分布,選擇一個沉積物結構單元來分析內部的物理和化學反應,并進行熱量和質量平衡計算。與其他模型一致,本文采用單煙囪及其周圍的多孔固體殼層作為沉積物的一個微小計算單元,如圖1a所示。為實現模型自動判斷沉積物中傳熱狀態,并能夠模擬沉積物中包括沸騰和非沸騰在內的過渡情況,設置了沸騰失效線(圖中紅線)以區分兩種機制。需要注意的是,沸騰失效線的位置根據程序在相應情況下對模型進行計算獲得。當溫度低于飽和溫度,即不發生沸騰的區域在紅線以上,則這條線以下的區域為沸騰區。當固體殼層中的液體發生沸騰時,氣體會匯聚在煙囪中而后向冷卻劑流動并重新冷卻。

a——沉積物單元;b——沿x正方向的節點與網格劃分
1.2 沉積物內部傳熱與流體流動分析和模擬
燈芯沸騰的傳熱過程發生在多孔沉積物覆蓋的包殼表面,傳熱介質包括固體殼層、孔隙內液體和煙囪內氣體,傳熱方式包括熱傳導、沸騰引起的傳熱和冷卻劑與固體界面的對流傳熱。其中,熱傳導發生在包圍單個煙囪的固體殼層中,而冷卻劑在相變導致的流體流動驅動力下通過較小的孔隙被吸入固體殼層中,當溫度超過飽和溫度時,液體會蒸發成蒸汽從煙囪中逸出。沉積物與冷卻劑界面發生對流傳熱,由于假設蒸汽溫度與液體飽和溫度相等,因此沉積物內忽略煙囪管道中氣體與固體殼層中的對流傳熱。在燈芯沸騰模型的基礎上,文獻[22]提出一種過渡模型來解決沉積物計算中被認為液體過熱度過高的問題。其中,當溫度超過飽和溫度時,冷卻劑在CRUD的煙囪壁或固體殼層的小孔內發生相變,然后沸騰導致的驅動力將主體冷卻劑推入多孔的CRUD中。達到穩態時,液體在沉積物的孔殼中質量守恒,即通過蒸發導致的質量傳遞和流體流動導致的質量傳遞進行衡算。
1.3 沉積物內部物質傳遞與化學過程分析和模擬
1.3.1包殼沉積物內物質傳遞 對于非揮發性物質傳遞,需先分析固體殼層中非揮發性物質在沉積物內部的輸運。為簡化方程,在選擇非揮發性物質時忽略了一些濃度特別低的物質,主要考慮沉積物孔殼內液體中含有的鋰、硼酸及其三聚體。固體沉積物中溶質的傳質形式考慮兩種,一種是流體流動的質量傳遞,另一種是由于濃度差導致的分子擴散過程。非揮發性物質的傳遞方程參見文獻[22]。
文獻[22]中,模型未考慮硼酸的揮發過程。由于硼酸具有一定的揮發性,其濃度對飽和溫度和腐蝕模擬會產生很大影響,因此本模型考慮硼酸的揮發過程。揮發性物質在固體殼層中的傳遞過程與非揮發性物質類似,不同的是,需要在溫度大于飽和溫度的情況下增加氣液分離產生的質量傳遞通量。因此,對于以液體形式存在于固體殼層中的揮發性物質,只需要在非揮發性物質的基礎上添加氣液分離導致的傳遞項djp。因此,煙囪中的物質傳遞項包括3部分,分別是由氣液分離引起的傳遞項djp、由水蒸氣流動引起的傳遞項djm,v以及因為濃度差引起的分子擴散項djc,v。同樣,將沉積物中煙囪的網格分成與固體殼層中相對應的邊界網格和主網格兩部分,每部分揮發性物質的傳遞過程和方程詳見文獻[21]。
1.3.2沉積物誘導硼累積過程 有研究者認為僅依靠沉積物Ni2FeBO5不足以導致實際運行中反應堆所達到的AOA值[4]。為探究除了以沉積物骨架的形式在包殼表面發生硼累積外,沉積物形成后誘導硼的再累積過程是否可補充解釋AOA現象,對沉積物內部孔隙和煙囪通道中的硼累積過程進行了分析和建模。
1) 沉積物孔隙中硼的吸附
硼對中子的吸收會導致CIPS現象發生,而硼在沉積物中存在的形式主要包括吸附硼、可溶硼、沉積硼。在發生燈芯沸騰的CRUD中,根據Park等[23]的研究,可溶硼在沉積物中的累積量相對于其他兩者更大,因此假設在發生硼的吸附和沉積時,溶液中硼的總量變化較小。因此,可溶硼(主要包括硼酸及其三聚體)可直接通過傳熱模型、流體流動模型和傳質模型3個模塊計算獲得。而吸附硼的量,采用文獻中通過對磁鐵礦吸附硼的實驗獲得的Temkin等溫吸附曲線進行溫度校正計算,當反應平衡時,吸附硼的量qa(B)(mol/m2)由式(1)[24]計算。
qa(B)=k1ln(k2c(B(OH)3))
(1)
k1=A1eE1/T
(2)
k2=A2eE2/T
(3)
其中:c(B(OH)3)為液體中硼酸的濃度,mol/m3;A1=1.938×10-5mol/m2,E1=222.7 K,A2=2.426×10-3m3/mol,E2=859.9 K。
2) 沉積物孔隙中硼的沉積
(1) LiBO2溶解
LiBO2的溶解反應為:

(4)
反應速率方程[25]表示為:
dc(B)/dt=fs(c(Bs))-c(B)/Ksl
(5)
其中:c(B)為LiBO2以離子形式存在的濃度,mol/m3;c(Bs)為LiBO2以未解離分子形式存在的濃度,mol/m3;Ksl為溶解平衡常數,mol/kg,Ksl與溫度T(K)的關系可由Byers等[26]在300~360 ℃的實驗關系式(式(6))表示;fs為收斂系數,由式(7)[27]計算。
lgKsl=-11.198 85+2 531.538/T+5.112 8lgT
(6)
(7)
計算時,假設溶液中硼酸和鋰通過傳質導致的濃度變化速率大于化學反應速率,即反應會很快達到平衡。根據EPRI模型計算的數據可知,若硼鋰能夠沉積,則約10 s即可產生數摩爾的LiBO2[27]。根據硼鋰反應方程式,當生成物和反應物的離子積大于該溫度下的硼沉積的溶度積,則會產生硼鋰沉積物的同時,沉積物空隙中的硼鋰濃度也因此更新。因此,在計算網格中的硼沉積之前,首先計算不考慮化學反應時由于物質運輸導致的節點物質濃度。其次,根據化學反應式計算離子積Q。
(8)
其中:m為濃度,mol/kg;γo為硼酸活度系數;aw為水的活度。
模型中計算硼累積量時應將溶質的物質傳遞過程與化學過程同步,由于考慮到硼酸沉積的時間非常快,首先計算不考慮化學反應的硼鋰濃度分布,而后通過硼沉積判斷硼鋰濃縮后是否可能會導致硼沉積。當離子積Q>溶解平衡常數Ksl,則溶液中離子濃度飽和,反應向逆向進行,產生偏硼酸鋰沉積物;反之,溶液未飽和,若有LiBO2(s)則會發生溶解,若沒有則溶液中不發生沉積。
(2) Li2B4O7的生成
在壓水堆中,當發生過冷沸騰,冷卻劑中含有大量的硼和鋰,硼鋰濃度的升高將會發生沉淀反應生成大量的Li2B4O7。當沉積物形成后,沉積物被視作分布著煙囪孔道的多孔結構,為氣泡的生成提供了條件。在沉積與釋放達到平衡時,Li2B4O7在燃料表面的穩定沉積量主要受到溫度、沉積物內流速和硼總濃度的影響。當達到穩態時,Li2B4O7中的硼沉積量WB(g/m2)可通過下式[4]計算。
(9)
其中:MB為硼的摩爾質量,g/mol;ρw為液體密度,kg/m3;ζB為B轉換釋放速率系數,是一經驗值,取0.016 s-1[4];K為沉積速率系數,與氣泡的產生和大小有關[28]。
(10)
其中:Rb為最大氣泡半徑,m;U為氣泡產生速率,m/s;μw為流體的黏度,Ns/m2;ρv為水蒸氣密度,kg/m3。根據Uchida等[4]的研究可知,RbU項在流體的流速(u)小于2 m/s時,與流速近似呈線性關系,通過對文獻數據[29]擬合,可得:
RbU=-0.018 75u+0.016
(11)
3) 總硼累積量計算
根據傳熱、傳質和流體流動模擬計算,可得固體殼層(sh)的包括非沸騰和沸騰的每個網格中的可溶硼量dc(H3BO3)sh(mol/m3)、吸附硼量dc(B)a(mol/m2)和沉積硼量dc(LiBO2)(mol/m3),煙囪通道(ch)的每個網格中的硼酸濃度dc(H3BO3)ch,發生沸騰的固體殼層的每個網格中還會沉積Li2B4O7,硼在該沉積物中的量為dWB(g/m2)。需要說明的是,所考慮的可溶硼、LiBO2和硼酸氣體累積區域在沉積物的孔隙和煙囪通道空間中,而吸附硼和Li2B4O7累積的區域是圍繞孔隙的固體殼層表面。通過單位換算,可獲取附著某一厚度沉積物的燃料棒單位面積所沉積的硼的量(lb,g/m2),如式(12)所示。
dc(LiBO2)+MB(1-f)hdc(H3BO3)ch)+
(12)
其中:1表示沉積物靠近冷卻劑的第一個網格;N為靠近包殼處的最后一個網格;j為開始發生沸騰的網格;h為網格寬度,μm;f為沉積物固體孔殼的占比;rp為孔隙半徑,取2×10-6μm;2/rp為孔隙的表面積比的簡化計算結果,即孔隙的表面積與孔隙的體積之比;ε為孔隙率。
2 包殼表面多物理場模型計算方法
通過迭代計算沉積物多物理過程的方程獲取多物理場量的分布。首先,根據沉積物厚度和網格長度計算出沉積物節點數n。假設所有沉積物節點的初始溫度為Ts+0.01,液體流速為0,固體殼層中的初始物質濃度等于冷卻劑中的對應濃度,煙囪中的氣體初始濃度為0。初始化后,通過表示流體流動離散方程的氣液體速度模塊,重新計算各節點的氣液體流速。其次,將新獲取的流速數據代入儲存流速的矩陣中更新流速參數,并利用包含物質傳遞方程的濃度模塊依次計算固體殼層中的非揮發性物質濃度、固體殼層中的揮發性物質液相濃度和煙囪通道中的揮發性物質氣相濃度。更新濃度參數后,利用傳熱方程的溫度模塊計算各節點的CRUD溫度。重復以上3個主要模塊的計算,并比較兩次連續計算沉積物所有節點溫度的差值。當所有節點的誤差小于設置的誤差,即0.01 K時,結束計算。需要注意的是,在每次計算后,3個模塊中使用的模型參數都會更新。
為實現模型的自適應計算方法,當第i個節點的溫度Ti低于飽和溫度,而第i+1個節點的溫度高于或等于飽和溫度時,第i個網格內充滿液體,不發生沸騰,則蒸發換熱系數接近于0。相應網格的流動驅動力被認為來自于發生相變的第i+1個網格。在這種情況下,認為第i個網格的流速等于i+1個網格的流速。而第i+1個節點中,利用飽和溫度計算蒸發換熱系數。當沉積物計算所得的平均溫度大于臨界溫度時,用于計算蒸發焓的液體溫度假設略低于臨界溫度,取373 ℃。
圖2為沉積物多物理過程耦合計算程序示意圖,顯示了計算的主要過程以及各模塊之間的關系,包括4個主要過程,分別是參數輸入、初始化、求解和輸出(圖2中第2列)。求解部分包括4個模塊,分別是流速迭代模塊、濃度迭代模塊、溫度迭代模塊和參數更新模塊(第3列),用于計算每個節點的溫度、氣液體速度、揮發性物質和非揮發性物質濃度;第4列表示第3列中各模塊使用的函數模塊,從上至下,依次計算水蒸氣密度、水密度、水蒸發焓、飽和溫度、蒸發換熱系數、水中溶質擴散系數、水蒸氣中溶質擴散系數、氣液平衡常數、氣相中質量傳遞系數、沉積物熱導率、水的對流換熱系數(各參數的計算方程參見文獻[21-22])。本文程序采用C語言編寫,計算的節點數根據所計算的沉積物厚度而不同,計算網格的寬度取1 μm。沉積物厚度在30~80 μm時,程序計算時長在1~3 min左右。

圖2 沉積物多物理過程耦合計算的程序模塊和函數
3 包殼表面多物理模型驗證和結果
3.1 模型驗證
為驗證模型,本文對WALT回路實驗中不同燃料棒實驗進行了選擇。WALT回路實驗報告[13]中,根據實驗所得的沉積物煙囪分布和直徑將實驗燃料棒分成不同組。因此,為更全面地檢驗沉積物傳熱傳質模型,選取不同組中的實驗燃料棒數據和沉積物的結構參數用于計算,熱通量的計算范圍是從低熱通量到略高熱通量。不同實驗燃料棒中所得的沉積物的煙囪密度、孔隙度、煙囪直徑、沉積物厚度和水力直徑列于表1。

表1 WALT回路實驗的燃料棒參數
在WALT回路實驗中,當計算的沸騰率小于0.814 kg/( m2·s)時,可認為沉積物中為氣液共存,即燈芯沸騰,當計算的沸騰率大于0.814 kg/(m2·s)時,認為沉積物內的孔隙中出現干化[23]。因此,將計算的包殼溫度與WALT回路實驗中沸騰率小于0.814 kg/(m2·s)時所獲取的包殼溫度進行對比。另外,目前很多涉及耦合沉積物物質傳遞的研究中未考慮包殼表面發生過冷沸騰時,沉積物固體殼層的孔隙中硼酸揮發的問題。為此,模型計算了考慮硼酸揮發和不考慮硼酸揮發兩種情況下的包殼表面溫度,并與WALT回路實驗數據進行了對比,如圖3所示。從圖3可看出,考慮硼酸揮發計算的包殼溫度比不考慮硼酸的結果更接近實驗值,最大相對誤差約為2.7%。

圖3 包殼溫度計算值與WALT回路實驗值的對比
3.2 沉積物對包殼傳熱性能影響分析
3.2.1包殼溫度與傳熱推動力 沉積物會對包殼表面溫度和燃料棒與冷卻劑的傳熱推動力帶來一定的影響,傳熱推動力由冷卻劑主體溫度和沉積物外界面溫度的差表示。沉積物存在時,不同熱通量、冷卻劑溫度、冷卻劑硼鋰濃度和沉積物結構下,包殼溫度相對變化值RT,clad和傳熱推動力相對變化值RT,force分別用式(13)和(14)計算。
(13)
(14)
當包殼溫度相對變化值RT,clad>0時,附著沉積物的燃料棒表面溫度高于干凈燃料棒,當條件改變時,該值減小,表示附著沉積物的包殼溫度變化值小于干凈燃料棒的包殼溫度的變化值。RT,force>0時,則有沉積物的燃料棒傳熱推動力比干凈燃料棒大,反之,比干凈燃料棒的傳熱推動力大。圖4展現了不同條件下所計算的包殼溫度與傳熱推動力的相對值,其中鋰濃度和煙囪直徑變化對附著沉積物的包殼表面傳熱影響較小,而熱通量、冷卻劑溫度、冷卻劑硼濃度、沉積物厚度、煙囪密度和孔隙率的影響較大。

圖4 不同條件下包殼溫度和傳熱推動力的變化
沉積物中的傳熱包括與冷卻劑的對流換熱、沉積物中的熱傳導和沸騰傳熱。如圖4所示,對于沉積物存在時所計算的RT,clad大于0,說明沉積物的存在會使包殼溫度增加,反映了沉積物對包殼表面熱量傳遞的阻礙作用。另外,相對干凈燃料棒,溫度劇增程度隨著沉積物厚度、硼濃度的增加而增大,隨著熱通量、冷卻劑溫度的增加而減小。這是沉積物的存在產生的熱阻使得包殼表面的沸騰程度加劇,與沉積物存在導致的硼濃度變化對沸騰換熱程度的反作用相制衡的結果。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當冷卻劑硼濃度增加時,包殼溫度略有增加,而RT,clad也增加,這提示提高冷卻劑硼濃度會促進沉積物導致的包殼溫度劇增效應。這是因為硼濃度會影響冷卻劑的飽和溫度,當硼濃度增加時,飽和溫度增加,而飽和溫度是過熱度計算中的關鍵變量,飽和溫度升高,過熱度(過熱度=T-Ts)會減小,從而抑制了沸騰換熱過程。根據飽和溫度Ts與水活度aw的關系(式(15)),繪制Ts和aw與硼濃縮因子(沉積物中物質濃度相對于冷卻劑劇增的倍數[6])的關系曲線,如圖5所示。由此可見,硼濃縮因子對飽和溫度的影響較大,飽和溫度與硼濃縮因子的關系曲線與EPRI報告[27]一致。

圖5 飽和溫度和水活度與硼濃縮因子的關系
Ts=344.94+199.01(1-aw)-
952.74(1-aw)2+26 013.91(1-aw)3-
262 916.0(1-aw)4+997 166.1(1-aw)5
(15)
根據圖4可知,RT,force反映了有沉積物和無沉積物包殼表面的傳熱推動力變化情況。RT,force>0時,相對于干凈燃料棒,沉積物會加強包殼與冷卻劑之間的傳熱推動力,反之,會減弱傳熱推動力。當RT,force變大,說明在某條件下,包殼表面在有沉積物時與主體冷卻劑的溫差變化小于無沉積物時主體冷卻劑的溫差變化,則傳熱推動力相對于無沉積物時提高的程度減小。根據計算結果,在沉積物厚度小于50 μm、熱通量0.4~1 MW/m2、冷卻劑溫度小于300 ℃、冷卻劑中硼濃度200~1 100 ppm、鋰濃度0.6~14 ppm時,相對于干凈燃料棒,沉積物的存在會提高包殼向冷卻劑的傳熱推動力;在沉積物厚度大于50 μm、q大于1 MW/m2、Tb大于300 ℃下,相對于干凈燃料棒,沉積物的存在會降低包殼向冷卻劑的傳熱推動力。其根本原因是沉積物導致的包殼表面熱阻和沸騰程度變化引起的傳熱變化。當條件變化時,相對于干凈燃料棒,傳熱推動力的提高程度隨著冷卻劑硼濃度的增加而增加,隨著沉積物厚度、熱通量和冷卻劑溫度的增加而減小。鋰濃度的變化對傳熱的影響幾乎可忽略。而沉積物的煙囪密度和孔隙率變大時,傳熱推動力減小。煙囪直徑對傳熱的影響較小。
3.2.2沸騰傳熱與物質傳遞 除了沉積物熱阻對包殼傳熱性能影響外,沉積物中發生的沸騰換熱作用也不可忽視。為分析沸騰換熱過程,除了分析沸騰換熱推動力,即過熱度、蒸發換熱系數變化外,還需要分析沸騰換熱的面積,沸騰換熱的面積可由本文所提出的沸騰失效率和沉積物厚度計算。物質傳遞直接受到沸騰程度的影響,沸騰程度越大,物質傳遞過程越劇烈,物質濃度提高越顯著。由于冷卻劑中的鋰類物質被認為是非揮發性物質,因此其在沉積物中的濃縮因子可反映包殼表面沸騰程度。圖6為計算的不同熱通量(0.4~1.5 MW/m2)、冷卻劑溫度(280~300 ℃)、硼濃度(240~1 100 ppm)、鋰濃度(0.6~14 ppm)下沉積物底部鋰和硼的濃縮因子。計算中,除去目標變量外,其他參數的控制值采用正常壓水堆操作條件,即熱通量1.0 MW/m2、冷卻劑溫度300 ℃、系統壓力15.5 MPa、鋰濃度2 ppm、硼濃度1 100 ppm、沉積物厚度40 μm、煙囪密度2×109m-2、煙囪半徑2.5 μm、孔隙率0.6。沸騰過程和物質傳遞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硼酸濃度的提高會對過熱度產生影響。不同的條件導致了蒸發換熱系數、過熱度和沸騰面積的變化,綜合結果表現為:當熱通量、冷卻劑溫度和沉積物厚度增大時,沸騰程度總體增大;對于冷卻劑溫度變化,存在一段平臺區;而冷卻劑硼濃度增大,沸騰程度減小。導致這些現象的原因如下:熱通量變化導致總熱量變化,從而引起沸騰程度的變化;冷卻劑溫度提高導致沸騰程度的變化存在平臺段是由于沉積物溫度提高和硼濃度提高導致的飽和溫度提高,共同制衡的過熱度變化引起的;沉積物厚度對沸騰程度影響起主導因素的是傳熱面積的提高;硼濃度對沸騰程度的制約來源于對過熱度的制約。

圖6 不同條件下的沉積物硼鋰濃縮因子
3.3 沉積物誘導包殼表面硼累積的分析
3.3.1沉積物空隙中的硼累積量 本文中,沉積物中硼的累積形式包括固體殼層溶液中的硼酸、煙囪氣體中的硼酸、固體殼層中的吸附硼和沉積硼。因此,本文中硼累積量指的是單位面積不同累積形式的硼質量。不同條件下沉積物空隙中硼累積量的分布如圖7所示。從圖7可看出,4種形式的硼累積量變化情況相似。不同形式硼累積量會隨著熱通量、冷卻劑溫度、冷卻劑硼濃度和沉積物厚度的增加而增加,這與Li等[30]模擬的結果趨勢一致。當冷卻劑中硼濃度從240 ppm增加到1 100 ppm時,可溶硼的累積量提高了2.5倍(圖7c),與EPRI中CCM的模擬結果一致。熱通量與硼累積量的增加關系近似為拋物線形,當熱通量逐漸增大時,硼累積量沒有特別大的增幅。而當冷卻劑中的鋰濃度增加且未達到使LiBO2發生沉積的條件時,鋰濃度的增加會一定程度減少硼累積量。

圖7 不同條件下沉積物空隙中硼累積量的分布
對于經典的壓水堆條件,固體殼層中可溶硼的累積量約為0.057 4 g/m2,煙囪通道中為1.40×10-5g/m2,吸附硼約為4.61×10-3g/m2。50 μm沉積物中,本模型計算的可溶硼量為0.073 g/m2,與同樣沉積物厚度下Li等[30]計算所得的可溶硼(0.103 1 g/m2)接近。60 μm沉積物中,模型計算的吸附硼為6.59×10-3g/m2,相同條件下,EPRI的CCM計算的一個煙囪的沉積物計算單元中的吸附硼約為2.3×10-15mol,即根據EPRI的CCM所用的煙囪密度3×109m-2進行單位換算后可得沉積物中吸附硼的量約為6.9×10-3g/m2。因此,模型計算的吸附硼量略小于CCM計算的,這是因為經過模型優化后,本文預測的溫度小于原模型,而吸附硼的量隨著溫度的升高而減小。另外,典型壓水堆條件下40 μm沉積物沉積硼的累積量約為8.34×10-5g/m2,主要是過冷沸騰導致的Li2B4O7沉積,由于該值不包括組成沉積物骨架的量,因此不做比較。計算所得沉積物多孔結構和煙囪通道中的硼累積以可溶硼為主,再是吸附硼,而后是沉積硼。
本文計算的硼沉積量主要是沉積物固體孔隙和煙囪通道空間或固液中的硼累積量,不包括組成沉積物骨架中的成分。本模型中,對這兩種硼沉積形式的考慮是不同的,對于Li2B4O7,結合了氣泡生長破裂原理來模擬硼沉積的過程。而對于LiBO2,主要考慮其發生化學反應沉積的過程,通過對比溶度積與離子積發現LiBO2的沉積反應不發生。在以往的燈芯沸騰模型中,由于假設沉積物中所有區域都會發生沸騰,所計算的溫度偏高,如CCM,假定冷卻劑與沉積物界面的溫度為飽和溫度,在60 μm沉積物中計算所得的沉積物與包殼界面溫度接近385 ℃,這種情況下LiBO2才會發生沉積[31]。對傳熱模型優化后,所計算的過熱度更合理,而沉積物溫度也比以往模型更低,因此更接近實驗值,溫度越小,LiBO2的溶解度越大,這就導致對于優化后的模型,即使沉積物中的Li+和B(OH)3濃縮后,依然不足以使這種化合物沉積。這種現象也與以往實驗中無法重現LiBO2的情況[32]一致。
3.3.2沉積物誘導硼累積的風險關系式 根據沉積物形成后誘導硼再次累積的過程分析和模型計算,獲取了不同條件下沉積物空隙中不同形式硼累積量,包括沉積物孔隙中的硼酸和煙囪通道中的硼酸、孔隙中發生沉積的硼和被吸附在固體殼層中的硼,但不包括組成沉積物骨架的沉積硼。根據EPRI給出的堆芯中累積270 g硼會引起功率偏移-3%,對不同條件下沉積物誘導硼累積的量所引起的風險進行估算。由于沉積物一般被認為在堆芯的上部分區域,此處取沉積區域為堆芯的1/8處,參照發生AOA現象的美國Callaway電廠第9循環周期的燃料棒表面積數據(7 706.8 m2)[25],則用沉積物誘導硼累積引起的功率偏移量衡量風險值,即沉積物誘導硼累積的風險估算如下:
Rlb=-Klb·lb
(16)
式中:Rlb為風險值;Klb=3%×7 706.8/(8×270)=0.107。
不同條件下沉積物中的硼累積量和所增加的瞬時風險值如圖8所示。

圖8 不同條件下沉積物空隙中的硼累積量和誘導的風險值變化
通過多元線性擬合分析不同因素下的數據,可獲取沉積物誘導包殼硼累積風險值與主要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如式(17)所示。
Ylb=∑RiFi+E
(17)
式中:Ylb為歸一化后的沉積物誘導包殼硼累積的風險值;Ri為回歸系數;Fi為歸一化后的影響因素,影響程度較大的因素包括熱通量、冷卻劑溫度、硼濃度、沉積物厚度、煙囪密度、孔隙率和孔隙直徑。
式(17)的各項式展開后如式(18)所示。
0.238 07
(18)
式中:q為熱通量,MW/m2;Tb冷卻劑溫度,℃;c(B)為冷卻劑中的硼濃度,ppm;δ為沉積物厚度,μm;Nc為煙囪密度,109m-2;rp為孔隙直徑,μm。
4 總結
本文通過對附著沉積物的包殼表面傳熱、傳質、流體流動、化學過程進行分析和建模,迭代計算了包殼表面多物理耦合模型。在對包殼表面的多物理過程模型優化和計算后,探討了各物理過程之間的耦合關系,定義了用于評估包殼表面沉積物誘導硼累積的風險值,分析了不同條件下沉積物對包殼表面傳熱性能的影響和沉積物誘導的硼累積風險變化,通過對比包殼表面多物理過程模型結果與美國西屋公司WALT回路實驗結果,驗證了優化后的模型能夠更真實預測附著沉積物的包殼表面性能。通過分析討論,沉積物對包殼表面性能影響表現如下。
1) 沉積物存在導致了包殼表面溫度劇增,沉積物存在時計算的RT,clad均大于0。溫度劇增程度隨著沉積物厚度、硼濃度的增加而增大,隨著熱通量、冷卻劑溫度的增加而減小。導致此現象的原因是,沉積物的熱阻使得熱量難以更快地從包殼表面傳輸到主體冷卻劑,從而使得包殼表面沉積物中的液體溫度升高更快,導致沸騰程度加劇。而溫度升高又加劇液體蒸發導致硼濃縮,造成飽和溫度升高從而影響過熱度。
2) 相對于干凈燃料棒,在沉積物厚度小于50 μm、熱通量0.4~1 MW/m2、冷卻劑溫度小于300 ℃時,沉積物的存在會提高包殼向冷卻劑的傳熱推動力;在厚度大于50 μm、熱通量大于1 MW/m2、冷卻劑溫度大于300 ℃時,沉積物的存在會降低包殼向冷卻劑的傳熱推動力。
3) 硼在沉積物孔隙和煙囪通道中累積導致的功率偏移的風險與不同條件對溫度、沸騰程度和硼酸揮發過程的影響有關,還與沉積物結構參數導致的硼累積區域變化有關。對于經典的壓水堆條件,40 μm沉積物微孔結構中,硼累積量主要來源于硼酸濃集(0.057 4 g/m2)和吸附硼(4.61×10-3g/m2),孔道中沉積硼來源于Li2B4O7預估值,為8.34×10-5g/m2,而LiBO2的熱力學計算結果表明本文計算的條件范圍內無法發生沉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