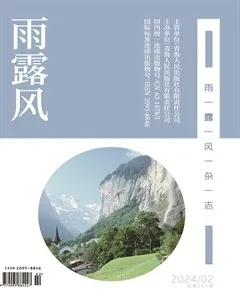《頑主》中的現實主義與史詩表達
易可


文學作品中的史詩感,通常需要用宏大的敘事與復雜的人物關系來襯托。縱觀當代許多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其史詩感的表達大多是在一個固定的時代背景或者社會環境下,一群特定人物的經歷再現。本文以王朔20世紀80年代所創作的《頑主》為例,探討這部作品在荒誕色彩中所呈現的現實主義文學品質與其獨有的“史詩”表達。
一、當代中國小說的史詩情結
每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都有與之相對應的史詩,雖然世界上的第一部史詩作品目前還無法考證,但是可以明確的一點是,史詩是一個文明集成文化的象征。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我國涌現出一大批反映歷史和時代變遷的優秀作品,形成所謂的“紅色經典”,《紅旗譜》《創業史》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盡管文學界出現了新的主題和熱點,但在一部分作家那里,史詩情結始終揮之不去。
在現代文學中,出于對世界認知追求的不同,人們對文學作品的認可多為追求“史詩感”而非追求“史詩”,具有史詩感的作品讓人感受到一種超越個體經驗的宏大氛圍,這樣的現象在白話文學成為中國文學主流之后更加明顯。在文學或藝術評論中,有時會用“史詩感”來形容那些具有史詩式氛圍和莊嚴氣息的作品,這是一種更加寬泛的表述,用以強調作品所傳達的宏偉和深遠的意境。
從文學以及劇作的角度出發,在描繪史詩時還原特定時代和文化是至關重要的,通過再現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化、風俗和社會結構,使觀眾能夠沉浸在那個時代的氛圍中。時代感、宏大敘事、典型角色的命運都是一部史詩作品的重要元素,通過這些元素多方面的融合,能夠在文學作品中有效地營造史詩感,使觀眾沉浸在一個宏偉、深刻且引人入勝的故事世界中。
二、《頑主》的現實主義價值
(一)小說《頑主》概述
《頑主》是作家王朔所著的一篇中篇諷刺主義小說,該作品發表于20世紀80年代,是一部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故事性十分飽滿。《頑主》主要講述于觀、馬青、楊重三位青年在時代交替的十字路口,用叛逆的態度對抗社會的規范和常規的故事。通過三位主人公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和對話,傳遞出對生活和社會的看法,展示生活中的荒誕和無常。
《頑主》的故事背景建立在改革開放之初的新中國,情節上運用了豐富的黑色幽默元素,通過夸張和荒謬的事件,將對社會現象的批判融入一種充滿戲謔和諷刺的敘事中。這種獨特的寫作風格讓小說既成為社會寓言,又帶有一定的文學實驗性質,不僅揭示了當時社會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同時也對人性進行了深刻而獨特的觀察。
林子懿對其評價道:“故事框架看似是非常荒誕的,但是如果是作為對一個社會樣本的觀察與嘲諷,這種方式顯然足夠了。”[1]《頑主》因其與眾不同的文風和對社會現象的敏銳觀察而引起了廣泛關注,以一種頗具張揚和叛逆的方式表達出作者對社會、人性和生活的獨到見解。
(二)《頑主》的現實主義表達
從小說的選題來看,“頑主”一詞是北京方言中對不務正業的年輕人的調侃,同時也是對當時主動破壞社會內在運行規則年輕人的一種蔑稱。用現在人的眼光看,《頑主》中的年輕人是在嘗試用新思路進行創業,但在當時,他們的行為自然無法被人理解。從小說情節的發展來看,“三T”公司的構想顯然是成功的,因為在故事的一開始,三位主人公就接到了公司開張后的第一筆訂單。作家寶康向他們闡述自己的理想以及對社會的遠大抱負,但自己的作品卻毫無名氣,所以希望“三T”公司能夠讓自己獲得一次站在聚光燈之下成為主角的機會。從人物的語言中可以感受到,寶康內心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個得到認可的作家,但又擺出一副看似淡泊名利的文人風骨的樣子,這一點被主人公于觀洞悉,于是就有了后面“3T”獎的故事。
在籌備頒獎禮的時候,于觀想辦法租借到會展中心作為場地,而對外招攬觀眾時用的理由卻是展會免費提供食品,還有節目看,對于所謂頒獎禮,于觀則沒有透露任何一個字,上臺的作家代表也是被雇傭來的托兒,目的就是為了襯托這一次的評委會大獎得主寶康。在這一部分,王朔十分直白地表明了寶康就是想要一個榮譽,而觀眾只想要免費的茶點,無論是會展中心的工作人員還是上臺的作家代表,都不過是收錢辦事的人,至于事情的結果是什么,王朔則收斂不提。這里的語言風格十分獨到,闡述了當事人的普遍想法與現實需求,由此我們可以從故事中看出,其實整篇小說都在諷刺這樣的虛假行為,但小說中的每一個人又默許了這樣事情的發生。楊重替一位醫生談戀愛,卻因為表現良好,引得醫生的女友對他好感倍增;馬青被委托當出氣筒,替丈夫承受妻子的怒火。即使明確對方不是自己可以肆意宣泄內心不快的人,但是因為委托關系的存在,雙方依舊默許了這樣的行為的現實性。[2]
從現實的角度來看,人們因為內在約束而羞于對外表達自己的直接需求,交錢讓人辦事成為這種情緒的出口,故事的另一層現實的價值就是在闡釋這個光怪陸離的時代。改革開放讓人們的生活發生了變化,但于觀的父母期望孩子的人生與自己一般無二。于觀在開放的社會環境中更傾向追求內心的自由,正因為社會的允許,他才能和自己的朋友一起成立公司。故事最后雖然三個年輕人闖下大禍,但又因為人們的欲望與內心深層次的需求的普遍存在,一邊認為公司不務正業,一邊卻又獲得了特殊時代下的市場的認可,被賦予了存在的價值。
三、《頑主》中的“史詩”價值
(一)作品對社會的客觀的“史詩”表達
從歷史的角度看,《頑主》的故事情節在史詩性上沒有明顯的表現,既沒有宏大的敘事結構,也沒有復雜的人物關系。“將故事延展開,從過去的時代看到《頑主》的年代,那么其史詩感便被充分的表現了出來。”[3]
從小說中可以推斷,“頑主”的父母是老一輩的革命英雄,為祖國的解放和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我們曾經是最好的年輕人,被送進了軍隊,現在,我們已經是一個遲暮的人了。”[4]他們因此變得憤世嫉俗,排斥傳統倫理和文化價值觀的壓制,所以王朔小說中的主角多有玩世不恭的性格特征。他們是底層的百姓,展現了最真實的生活,王朔將其統稱為“頑主”,在逐漸喪失自我后成為文化邊緣者。這種文化邊緣者與主流文化之間的矛盾與反抗,表現為對主流文化價值觀的抗拒。如果這個時候再結合王朔《動物兇猛》中的故事內容,那么我們可以說,故事里的馬小軍似乎在長大之后就會成為現實里的于觀,當前后的時間綿延了近二十年,故事本身的史詩感就被放大地表現了出來。
許多作品的評論將王朔的《頑主》與美國的嬉皮士文化相掛鉤,似乎在那個時代世界就進入了一個集體思維創新的年代。如果中國有“頑主”,那么西方就有“嬉皮士”,如果中國有《頑主》,那么西方就有《崩塌的一代》。
現如今世界依舊在有序地運轉著,其背后有獨特的邏輯,人在不能脫離社會存在的這個過程中,實際依舊是具有自主表達的權力的。但是普通人注重自己的現實生活,至于未來會發生什么,作者一直沒有評價,留給時間去鋪墊,人是如此,作品也會如此。因此我們可以說,無論是《頑主》還是西方《崩塌的一代》,都找到了現實與史詩內容對照的最好的平衡點,這樣的平衡點則可以讓作品歷久彌新,作品小而表達全。
(二)《頑主》的史詩表達在現代的延續
如果《頑主》的作品價值只用于闡述過去的生活,那仍然不足以被稱為史詩。在21世紀的第一個二十年過去之后,當人們在評價王朔的時候會發現,“王朔現象”并沒有消失,其作品的價值仍然在延續,成為客觀表達的存在。這一點可以從現代社會的另一種視聽語言作品——“電影”來解釋。
導演馮小剛所拍攝的兩部電影《甲方乙方》《私人訂制》,其中的荒誕主義就是脫胎于《頑主》故事的內容延展,其本質依舊是一種偏向于理想主義的內容表達,只是表達方式從小說變成了電影。某種意義上,馮小剛的電影正如王朔的小說一樣,不受主流價值的認可,但市場會肯定這些故事的價值。這實際上也是在說,即使老一輩的“頑主”已經老去,現代的年輕人依舊迷茫。
放在時下語境來看,人們可能不會再用“頑主”一詞來形容現在這類人。現代社會中年輕人普遍的迷茫,又使他們走上反對父輩的路,本質是對《頑主》內核的一種精神延續。所以可以說王朔是用自己的一部小說,前前后后影響了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到21世紀的人,雖然王朔本身沒有這個意圖,但是他的小說確實做到了這一點。
四、結語
縱觀王朔的此類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盡管缺乏嚴格意義上史詩作品所要求的廣闊時空背景、眾多角色和宏大沖突等要素,但是作品本身是需要人去解讀的,當作品被一個人深刻地解讀,那么故事內容就是屬于這個人獨特的符號記憶,當這樣的符號記憶從一個人發展到一群人,對于時代的挽歌就會成為一個必然的事實。因此,我們說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是有其特定的現實表達的,但是如果將把小說故事解構的觀眾們納入其中,兩者的化學反應催生出來的便是一種潛藏在時代記憶里的史詩的故事感,兩者不突兀,反而有了一種時代的平衡感。
注釋:
〔1〕林子懿.論王朔后期創作中的時態和覺悟——以《我的千歲寒》為例[D].石家莊:河北師范大學,2022.
〔2〕趙勇.在文學生產與視覺文化之間——1990年代以來作家“觸電”現象的回顧與反思[J].小說評論,2022(4):4-20.
〔3〕翁榮江.從“懷舊新頑主”到“時代寫實者”——論石一楓的都市青年書寫[D].武漢:武漢大學,2019.
〔4〕林芳毅,張檸.后頑主時代:從王朔到石一楓[J].文藝爭鳴,2021(7):189-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