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創作出發的文學研究
梁向陽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中有這樣一句話:“知識這種力量,可以改變一個人,甚至可以重新塑造一個人。”是的,我也是一個被知識所“重新塑造”的人。
我能走上文學創作與研究之路,與家庭氛圍與成長環境有關,與少年時代最初的閱讀分不開。我20 世紀60 年代中期出生于陜西省延安市延川縣一個普通的農村家庭,祖父是家鄉一位有名的書生,父親則是位鄉鎮語文老師。我是在窯洞里裱墻的報紙上完成所謂“學前識字”的。我小時候,祖父經常指著炕墻上的報紙教我認字,久而久之我就養成了愛識字的習慣。我愛看書,在全村孩子中出了名。我少年時代的所謂零花錢,幾乎全部來自挖藥材所得。這些零花錢,大都買成連環畫了。少年時代長期翻閱連環畫,就建立起了自己最初的“文學想象”。我老家的北京插隊知青很多,知青退潮后,留下很多“知識青年用書”,我一度迷戀上知青留下的這些書籍。我記得大約是小學三四年級時,我偶然得到北京知青留下來的《各國概況》,淡藍色封面,書前配有許多彩色插圖,專門介紹世界各國國旗;正文文字介紹世界各國基本情況。這本書對于一個正在向往外部世界的山村少年的誘惑可想而知。在那個精神食糧極度匱乏的年代,這本書自然就成了我的好朋友。后來,我讀路遙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發現田曉霞送給孫少平的禮物中就有本《各國概況》,看來它也給路遙留下了深刻記憶,把它設計成重塑孫少平人生的重要“道具”。
書籍給我提供了瞭望外部世界的窗口,同時也使我有機會產生興趣與愛好。這種潛移默化的作用,一直影響到我后來的職業選擇。2015 年,我在《中國政協》雜志上發表《最是書香能致遠》,系統回憶了少年時代讀書的種種趣事。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延川“山花”作家群路遙等人的直接引領。陜北有句俗語:“文出兩川,武看三邊。”其中的“一川”就是延川。延川百姓有著深厚的“尚文重教”傳統,延川的幾位文學青年于1972 年9 月辦起一張八開文藝小報《山花》。就是這張《山花》小報,點燃了延川人的文藝激情,推動了延川文藝的繁榮與發展。從此,延川的文學藝術以《山花》為“輻射源”,形成了一個以文學為引領,民間美術、戲曲、音樂等競相開放的獨特的“山花文藝”現象。我曾在《路遙傳》“前言”中這樣寫道:“路遙是我的文學前輩,我是路遙的追隨者,我們都是延川人。我少年夢的形成,人生的展開與飛翔,均與路遙、谷溪、聞頻、陶正、史鐵生等人的文學引導分不開。”
我在80 年代曾是延川縣的一名中學語文教師,因喜歡文學創作,并在《當代》《延河》等文學期刊上發表過幾篇小說,1990年秋從延川中學調入延大中文系擔任基礎寫作課教師。進入延安大學任教后,我要翻越由中學教師到高校寫作教師角色轉換的大山,也要翻越由文學創作到文學研究轉換的大山。在翻越這些大山時,我也曾有過苦悶,有過煩惱,但更多還是咬牙堅持。為了補齊自己的知識缺陷,我分別在復旦大學“文藝學暨現當代文學骨干教師進修班”、陜西師范大學“中國文學”碩士課程班學習,此后還跟隨北京大學中文系溫儒敏教授做了一年訪問學者。在“轉益多師是吾師”中,我有效地解決了知識短板。
長期以來,我國高校的學術評價制度重在對于教師知識積累的考察,而非對于教師創造性能力的激賞。大學中文系長期以來有一種觀點,認為寫作課僅僅是簡單的寫作技能的訓練課,是中文系的“三等課”。1942 年,在西南聯大國文系擔任寫作課教師的現代著名作家沈從文先生就在《學習寫作》一文中發過牢騷:“因照目前大學制度和傳統習慣,國文系學的大部分是考證研究,重在章句訓詁,基本知識的獲得,連欣賞古典都談不上,哪能說到寫作。這里雖照北方傳統,學校中有那么一課,照教育部規定,還得必修六個學分,名叫‘各體文習作’,其實是和‘寫作’不相干的,應個景兒罷了。寫作在大學校認為‘學術’,去事實還遠……我能夠做到的事,還不過是為全班學生中三兩個真有寫作興趣的朋友打打氣而已。”其實,寫作課不僅需要傳授知識,而且還需要訓練能力,它是一門“知識加能力”的課程,更需要既能在知識上融會貫通,同時富有豐富寫作經驗的優秀教師教授。古人說得好:“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要真正提升文章水平,就必須長期堅持寫作實踐,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道路,除此之外,別無其他捷徑。
既然到大學任教,就要適應大學的評價制度。與純粹的學院派研究不同,所謂的學術研究是由文學創作興趣轉型的研究,由愛讀散文、愛寫散文,走上愛琢磨散文與研究散文的路子上來的。要業余從事散文寫作,自然要了解當代散文的寫作情況,尤其是特定地域文化狀態中的散文,這也是一種邏輯的必然。這樣,我的視野逐漸關注到西北散文作家的寫作上來,希望通過對他們作品的閱讀,從他們文學創作的經驗中獲得有益的啟示,豐富自己的寫作實踐。當我把目光投向陜北籍文學前輩、首屆“魯迅文學獎·散文獎”獲得者劉成章先生后,我一方面發現他的“陜北風情散文”有著鮮明的藝術個性;另一方面本省的文學評論者似乎忽視了他的存在,僅僅寫過幾篇簡單的印象式文章。因為文化背景與精神氣質的相同,我對他的散文有一種更深刻的認識。這樣,我首先以劉成章的《安塞腰鼓》《扛椽樹》《走進紐約》等散文名篇為例,撰寫了一組鑒賞文章,分析這些散文的美學特征,教授學生如何進行文學閱讀、文學鑒賞。我的關于劉成章《安塞腰鼓》的賞析文章《高原生命的火烈頌歌,民族魂魄的詩性禮贊》發表后,很快被選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著的《語文教師教學用書》、上海辭書出版社編著的《學生現代詩文鑒賞詞典》《今文觀止》等書中。一些讀者也來信,充分肯定我對于作品的審美理解。直到現在,我關于劉成章《安塞腰鼓》的賞析文章仍繼續在部編版語文教師用書中堅守崗位。這些鼓勵,使得我更堅定了要“挖一口深井”的想法。在文學鑒賞的基礎上,我又對劉成章散文進行了系統研究,從整體審美特征與創作心理等多個角度切入,研究他散文寫作的成功之路,借以找到一些有益的啟示。
通過長期對劉成章散文創作的研究,我明白了“哪章得我哪章新”的道理,也就是文學創作一定要擁有一塊自己最熟悉的創作領地,一定要堅持自我。只有這樣,才有可能走向成功。于是,我在90 年代花了幾年時間認真寫出一組題材相對集中的“走過陜北”系列歷史文化散文。這組散文中的一些篇章被收入《中國西部散文》《中國西部散文百家》等散文選集,散文《漫步秦直道》被選入“1999 年度中國散文排行榜”,并入選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著的2000 年版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語文讀本》第一冊。可以說,我當初寫作這組散文的原動力就是在對于劉成章散文認真研究后的思考。倘若沒有對劉成章散文的長期跟蹤研究,我是悟不出這些道理的。就這樣從自我感覺出發,我的散文研究像“滾雪球”一樣滾起來了。
在此基礎上,我以散文寫作者的敏感心靈去關注“90 年代散文現象”。我的文學創作起步雖在80 年代,但最為用心的時候還是在90 年代。一個散文作者倘若不了解當下散文寫作風景,而純粹地自我復制,那也是十分可怕的。我把90 年代散文現象放置在百年散文體系中,用現代散文的特征指向作為參照系,來進行對比研究和加以評估。找到這種研究路徑后,我一口氣撰寫了《90 年代散文創作中人文精神因素的考察》《困惑與突變的風景——20 世紀90 年代散文現象淺論》《回歸自由與真實之岸——1990 年代“隨筆熱”現象考察》等學術論文,其中前兩篇論文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月刊全文轉載,《90 年代散文創作中人文精神因素的考察》還被多篇論文征引學術觀點。學術界的這種反應對于我來說是一種激勵,我感覺用“現代散文”的標準來評估90 年代散文成就與不足的方法是可行的。
既然這種方法可行,我就在鞏固研究陣地的同時,進一步擴大自己的研究領地,把目光投向整個“當代散文”領域。此時的我已經開始“串崗”,承擔“當代散文創作研究”選修課的教學任務。“當代散文創作研究”,就是對于當代散文創作歷史的系統把握,從中尋找出合適的研究與解讀路徑。我要進行“當代散文”研究,就不能人云亦云,而要換個角度看問題,即在用“現代散文”作為參照系的基礎上,還必須建立系統的思維觀念,充分尊重既成的歷史事實,把握當代散文出場的原因、方式、路徑、狀態與影響。于是,我撰寫了學術論文《從自由言說到自覺言說的整合——“延安時期”散文現象淺論》,旨在把握“延安時期”的散文狀態形成的原因,以及這種狀態對于當代散文的影響。論文發表后,很快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月刊在2002 年9月號“思潮與流派”欄目頭條全文轉載,也被一些學術論文征引觀點。這至少也說明我的觀點是得到了一些響應的。循著這個研究路徑,我又撰寫了《抒情機制的確立與抒情散文的興盛——“十七年時期”散文現象淺論》《“人道主義”視閾下的“新時期散文”——“新時期散文”(1976 —1989)現象淺論》等多篇論文,旨在尋求當代散文的出場方式、呈現狀態以及變化路徑。這組研究論文也不同程度地引起一些反響:《“大散文”:意象闊遠的散文天地》榮獲第二屆“冰心散文獎·散文理論獎”,《抒情機制的確立與抒情散文的興盛——“十七年時期”散文現象淺論》入選首都師范大學張志忠教授主編的《散文批評三十年》。這是從1980 年到2012 年三十余年間的上千篇散文研究成果中精挑細選的30 篇論文,是對新時期以來30 年當代散文研究成果的一個梳理與總結。我覺得我的這組散文研究論文能夠產生一些影響,其關鍵點是我的研究視野相對開闊,同時尊重既成的散文事實,分析它們存在的合理性與必然性,而不是隨意判斷和粘貼標簽。當然,建立在研究基礎上的教學就相對容易,學生覺得這位老師是在有理有據地說理,是有自己的話語體系的,而不是滿嘴荒唐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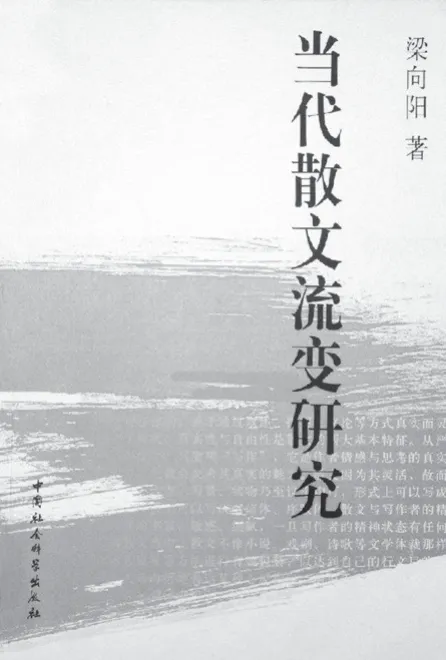
梁向陽:《當代散文流變研究》
在此基礎上,我撰寫了自己的第一部學術著作《當代散文流變研究》,并在2007 年8 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我國著名散文研究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樓肇明先生為該書作序,他熱情洋溢地肯定了這本書的特點:“梁向陽先生的這部散文專著,倘不能被認為其中最優異的一部,卻可以確認為其中學術態度極其嚴肅、學風優良,具有非平庸之輩所能及的卓越史實的一部。”我也因這部專著榮獲2007 年度北京大學訪問學者、進修教師“創新成果獎”。這部專著2008 年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第11 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成果表彰獎”,2009 年獲陜西省第9 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2010 年獲陜西省第二屆“柳青文學獎”。2009 年《中國社會科學》第2 期《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新時期當代散文研究三十年綜述》多處談到我的當代散文研究;2010 年1 月7 日,我應邀在《中國社會科學報》“學林”版刊發《眾里尋他千百度——我如何研究中國當代散文》,算是介紹自己的研究心得。
就這樣,我的學術研究從當代散文起步。此后,我又結合學校特色與個人特點,轉入延安文藝與路遙研究,進一步夯實自己的學術優勢。
路遙研究是我近二十年來的學術研究重點。路遙是我國當代著名現實主義作家,也是延安大學的杰出校友。以申沛昌老校長等為代表的老一代領導與學者,為延大作出了重要貢獻。因為長期在延大任教,我有研究路遙的諸多便利。一是我長期致力于路遙研究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工作。我曾主持的文學研究所與路遙研究會合作,先后推出《路遙研究資料匯編》《路遙紀念集》《路遙再解讀》《路遙與延安大學》《路遙的大學時代》等研究資料;二是我在學校支持下,于2007 年籌建并建成了路遙文學館。目前,該館已成為集紀念、研究與文學交流為一體的路遙研究的重要平臺,發揮了文學正能量作用;三是我在路遙著作的搜集整理上做了大量工作,先后應邀擔任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 年版《路遙全集》“特邀編輯”,以及2014 年版《路遙精品典藏紀念版》“選編者”。

厚夫 :《路遙傳》
我正式產生撰寫《路遙傳》的念頭,是在2002 年路遙逝世十周年紀念大會上。我發言時鄭重提出渴望具有學術品格的《路遙傳》設想,指出:“直到目前為止,社會上仍沒有出現一本擁有學術品格的《路遙傳》,這不能不說是種遺憾。呼喚《路遙傳》,應是呼喚路遙本體研究的一種重要成果的出現。”我的這個發言稿后來整理成《路遙研究述評》公開發表,被人大復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月刊,以及國內眾多路遙研究書籍多次轉載。我當時就暗下決心,自己撰寫一本介乎文學與學術的《路遙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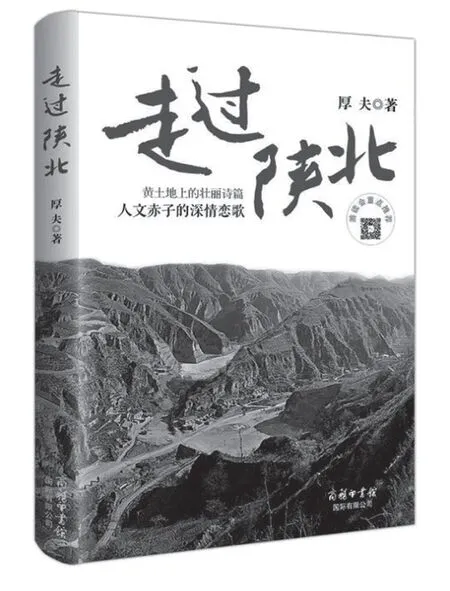
厚夫 :《走過陜北》
《路遙傳》是我“十年磨一劍”的成果,2015 年1 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該書自出版以來,先后18 次印刷,發行達十多萬冊,豆瓣讀書一直是8.1 的高分,創造了紀實文學成為“暢銷書”的奇跡。該書出版后,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國內上百家媒體先后報道、摘發、連載,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紀實春秋”節目連播全書;入選中國出版集團2015年第二期中版好書榜推薦圖書、鳳凰好書榜、2015 年全國教師暑期閱讀推薦書目等,入圍2015 年“中國好書”入選圖書;獲得“中國書業”2015 年度“最佳傳記類作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年“雙十佳”圖書等多種獎項。這本書在專業讀者與普通讀者中均產生了強烈反響。《光明日報》《文藝報》《文學報》《文藝爭鳴》《中國社會科學報》等刊發大量專業評論高度評價。湖南文藝出版社2016 年12 月出版的《路遙 路遙——〈路遙傳〉評論·訪談集》,收錄關于此書的代表性評論與訪談文章。此外,我還應邀在包括中共中央組織部、清華大學、武漢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寧波天一大講堂等在內的全國一百多個國家機關與高校傳播路遙文學精神,產生了廣泛的文化影響。
《路遙傳》能取得一些收獲,有這么幾點可以總結:第一,我任教的延安大學是路遙的母校,這使得我有研究他的諸多便利條件。第二,得益于我長期以來所堅持的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的表達。學術使人理性,文學使人感性,而我這種長期左右開弓的方式,使我較好地在理性與感性之間找到平衡點。傳記文學不同于虛構的人物故事為內容的其他文學作品,它具有“傳記”和“文學”雙重性質。作為傳記,它有信史的價值;作為文學,它有藝術的功能。正因為如此,我在《路遙傳》的撰寫中較好地處理了文學性與學術性之間的關系,使這部傳記既尊重歷史史實,又有流暢閱讀的快感,還有深刻思辨的深度,適合多層次讀者閱讀。第三,得益于人民文學出版社及優秀編輯團隊的重視和支持。
與此同時,我還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中國文學批評》《文藝理論與批評》《新文學史料》《文藝爭鳴》《南方文壇》《當代文壇》《小說評論》《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等報刊發表大量路遙研究論文與評論。其中,在《光明日報》刊發兩個整版文章:《陜北文化血脈與文學呈現》刊于《光明日報》2017 年3 月21日第10 版“光明講壇”整版;《路遙:“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刊于《光明日報》2018 年12 月14 日 第13 版 整版。2019 年10 月,我在《光明日報》刊發《為路遙立傳是我生命的自覺》,再次明確地表達我的路遙情結。
當然,我也從未放棄過自己的文學表達。我的散文《我的“延川老鄉”——關于北京知青的記憶》入選“2013 年度中國散文排行榜”,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我還出版過《心靈的邊際》《陜北味 故鄉情》《走過陜北》等散文集。此外,我也客串文學批評者的角色。因為有創作體會,我更能理解作家們的創作甘苦,總能在同情中超越,在印象中提升,在整體審美體驗中獲取批評靈感。
我這個人有一種愈挫愈進的性格,奮進之路越是艱難,越能激發我的斗志。我從未放棄過自己的夢想,也更懂得珍惜自己的每一次機會。這些年來,我在文學研究、創作、教育與傳播之間不斷發力。我以為不論是文學研究還是創作,均要有豐富的文化想象力、堅定的文化執行力,進而才能形成深刻的文化創造力。豐富的文化想象力是基本前提,堅定的文化執行力基本路徑,深刻的文化創造力是結果。
我記得路遙1988 年曾給母校延安大學贈言:“延大啊,這個溫暖的搖籃!”事實上,延安大學也是我“溫暖的搖籃”。回首幾十年來自己走過的路,我從內心里感激延安大學,是延安大學接納了我,并引導我走了一條由創作出發進入學術研究的人生之路。不管今后的路如何走,我不會放棄自己,因為有追求、有奮斗,自己的人生之路才充實、才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