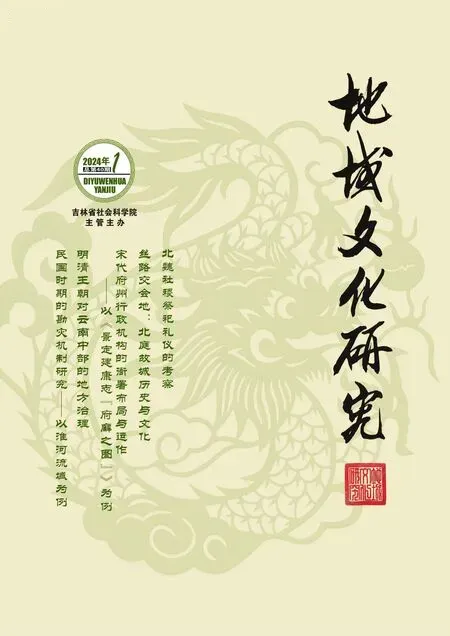清朝在改土歸流地區實行的保甲制度
方悅萌
改土歸流,即任命正式官吏替換土官或土司,是中原王朝整頓土司制度的一項重要舉措。明朝開始在局部地區改土歸流,仍限于針對少數違法土司的應急處置。作為普遍推行的一項改革措施,施行于清代的雍正時期,并取得顯著的成效。土官或土司被廢棄后,清朝在完成改土歸流的地區推行保甲制度,堪稱是一項重要的社會改革。關于清朝在改土歸流地區實行保甲制度的情形,迄今研究不多。因試為考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
清朝統治的一個特點是重視法治,而實現法治的重要手段是實行保甲制度。清代以前,一些朝代雖然有在基層設立組織機構的做法,但在基層正式實行保甲制度并不斷完善,同時使之貫穿于整個朝代,卻是清朝統治的一個重要特點。實行保甲制度的基本出發點,是依靠保甲制度來進行法治化管理,為此統治者在組織機構的建設、職掌和監察等諸多方面,都做出了嚴格的規定,并取得明顯的實效。在南方少數民族地區,早在全面進行改土歸流之前,受命統籌改土歸流的鄂爾泰,便對改土歸流中及其后實行保甲制度做出具體的設想,并闡述在改土歸流地區實行保甲制度具有的重要意義。
保甲制度不僅是國家對地方的控制,也是地方自治的一種方式。因為它不僅具有行政功能,還有司法功能。清代很多地方官員都重視這種制度的建設。清軍入關后,在全國推行此項制度。順治元年(1644),頒布了編制戶口的保甲之法。從《清史稿》可以了解到此法的內容。據《清史稿·志九十五·食貨一》:
世祖入關,有編制戶口牌甲之令。其法,州縣城鄉十戶立一牌長,十牌立一甲長,十甲立一保長。戶給印牌,書其姓名丁口。出則注所往,入則稽所來。其寺觀亦一律頒給,以稽僧道之出入。其客店令各立一簿,書寓客姓名行李,以便稽查。及乾隆二十二年,更定十五條:一,直省所屬每戶歲給門牌,牌長、甲長三年更代,保長一年更代。①趙尓巽等撰:《清史稿》卷120《志九十五·食貨一》,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7年,第3481頁。
清朝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申行保甲之法,雍正四年(1726)再次嚴申保甲之法。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式頒布15條《保甲組織法》,確定為保甲制度建設的基本法規。
在實行大規模改土歸流之前,雍正朝已明確將改土歸流及其后治理納入法制軌道的原則。雍正四年(1726)八月初,鄂爾泰在奏疏中對改土歸流中的分別流土考成、以專職守問題提出建議。他說流官固宜重其職守,“土司尤宜嚴其考成”。土司過去考成不嚴,是命盜之案卷日積的重要原因。苗疆發生殺人劫財,皆系苗倮所為,雖經報官隨即緝捕,但違法者潛匿寨中,莫可窺探,十無一解。不是知情故縱,便是受賄隱藏。反映出存在苗疆基層失控、官府束手無策的被動局面。“故劫殺愈多,盜賊愈甚”。
鄂爾泰認為解決的辦法是事各有專責,大致分為三種情形:盜由苗寨而生,專責土司;盜起于內地,責在文員;盜自外來,則責在武職。并強調盜由苗寨而起者,是平時基層不行管束,臨事又不行防閑,此為土司之罪。盜起南方諸省腹地者,是由于鄉保不行稽查,捕快又不能緝獲,此為文員之罪。盜自外面來者,緣由是塘汛不能盤詰,兵丁又不能救援,則為武職之罪。由此提出了在南方土司地區,根據具體情況區分責任、專職其守,以及基層、文員、武職各司其職、相互配合的基本原則。
鄂爾泰在奏疏中提出,清除盜賊之源,“莫善于保甲之法”。稱已與大臣楊名時、何世璂熟商酌議,擬立規條,行之云南、貴州兩省。一旦朝廷批準,當即頒行,一體遵奉。過去的保甲之法,是以十戶為建立單位。但云貴地區土、苗雜處,住戶畸零不等,以前保甲制度之不可行,皆因官員多持此議。但他們不知除生苗以外,無論民夷人等,凡自三戶起皆可編為一甲,若不及三戶,則令其遷附近地方,不許獨住,如此則逐村清理,逐戶稽查,責任在鄉保、甲長。一遇有事,罰先及鄉保、甲長,“一家被盜,一村干連”。若鄉保、甲長不能覺察,左鄰右舍不能救護,則各皆酌擬,連坐獲罪。若實行此法,盜賊來之時,合村百姓鳴鑼吶喊,互相守望,互相救護,即便是兇狠之盜亦不可敵當,而眾民看其來蹤,尾其去路,盡力跟尋訪緝,盜賊便無處可逃。
鄂爾泰還認為除建立保甲外,最重要者為嚴責捕快與汛兵。在腹地設置的捕快與汛兵,過去由于管理松懈,捕快多有知情,塘兵且為通氣。因此某方失盜,罪在相應的捕快。以后規定緝盜不獲者,“捕快與快頭一同治罪”。對汛兵亦須嚴加號令,定為成法。②《云貴總督鄂爾泰為分別流土考成、以專職守、以靖邊方奏事》(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故宮文物館編《朱批諭旨》鄂爾泰折二,1930年。雍正四年(1726)十二月二十一日,內閣等衙門議復,同意鄂爾泰上述奏疏的建議,乃在改土歸流地區普遍實行保甲制度,其基本原則亦遵循鄂爾泰建議所言。還規定在各地普遍設立捕快汛兵,若對盜賊逾限不獲,則將捕快、快頭一并治罪。在云南、貴州、四川、廣西、湖南五省,以上規定同時實行。①《清世宗實錄》卷51,雍正四年十二月,日本東京大藏株式會社影印本。
鄂爾泰關于在改土歸流地區實行保甲制度的設想,開初類似于內地的保甲制度,所不同者主要是強調在改土歸流地區,應注意居民分布分散,須組織必要的遷徙,使之集中居住以便管理。另外,鄂爾泰還提出充分發揮捕快與汛兵的作用,使其與保甲制度互為補充。對改土歸流地區實行保甲制度可能遇到的困難,鄂爾泰則估計不足,語調亦趨于樂觀。雍正四年(1726)十二月二十一日,鄂爾泰在論及東川地區遼闊,營長、伙目侵占田畝,私派錢糧甚至縱夷劫殺時說,若在緊要地區俱設職員分理,而將營長、伙目改立我鄉約、保長,實行保甲制度,“將稽查既嚴,漸染亦易,二三年后東川將為樂土”。②《云貴總督鄂爾泰為敬陳東川事宜奏事》(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故宮文物館編《朱批諭旨》鄂爾泰折二,1930年。
清代前期有相當一部分官員,并不贊同在已改土歸流地區全面推行法治,以及全面實行保甲制度。從廣西官員孔毓珣的奏折得知,雖然遵從雍正帝的旨意在廣西編查保甲,但他不主張在各州縣鄉村另編保甲,而是主張因其故俗,即利用原有的團練、堡目、款頭、鄉勇人等社會力量,并根據辦理的好壞予以獎罰。其理由有二。一是村落零星散處,相隔甚遠,難以聯系。二是廣西多為瑤僮雜處之地,向來未曾編查保甲,擔憂編查保甲會引起瑤僮百姓的驚擾。在城市及市鎮漢民聚集之處,孔毓珣則主張編查保甲。
經過幾年的試行,各地推行保甲制度的情形不能令雍正帝滿意,于是他決定加大推行的力度。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對大學士等官員說:
弭盜之法莫良于保甲,朕自御極以來,屢頒諭旨,必期實力奉行。乃地方官憚其繁難,視為故套,奉行不實,稽查不嚴。又有藉稱村落畸零,難編排甲。至各邊省,更藉稱土苗雜處,不便比照內地者。此甚不然。村落雖小,即數家亦可編為一甲,熟苗、熟僮即可編入齊民。茍有實心,自有實效。
雍正帝要求九卿對此詳議具奏。③(清)蔣良麒編:《雍正朝東華錄》第1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96輯,臺北:文海出版社,2006年,第148頁。在朝廷批準后,改土歸流地區皆遵令而行。在推行保甲制度的過程中,一些社會問題隨后暴露出來,有些情形還關系到改流的成果是否能鞏固,清朝對改土歸流地區的統治是否能持續的問題。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地方治安問題。清朝對南方土司地區的改土歸流動用了武力,明顯改變了土司地區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狀況。被改流的土司、被鎮壓的惡夷影響依然存在。土司地區人心浮動,具體表現在地方治安不穩定,若有風吹草動便影響社會治安,甚至釀成社會動亂,亟待朝廷進行安撫和有效的治理。
二
通過改土歸流,消除了朝廷深入管理和全面開發土司地區的障礙,外來人口大量進入改土歸流地區。這一現象既符合清朝統治者的預期,同時也出現嚴重的社會治安和管理方面的問題。雍正前期的南方土司地區,存在部分土司及夷霸橫行不法、危害社會等嚴重問題,為徹底解決上述問題,及早處理“目前雖無大害,日久將為隱憂”的邊疆土司,雍正朝進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可見雍正朝進行大規模改土歸流的一個緣由,是從土司及夷霸手中奪回土地等資源,以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改土歸流完成后,外來人口大量移居改土歸流地區,有效緩解了內地人口激增造成的壓力。清廷對此持默許態度,地方官府則貸給種仔與耕牛,招徠流民前來墾殖。
改土歸流完成后還出現一種情形,即不少田產,需要酌情安插漢民領種其地,在朝廷的安排之下,一些內地人口由此進入苗疆。乾隆元年(1736)十一月二十日,張廣泗為處理苗疆善后之事上奏,稱:貴州布政使馮光裕請將叛苗的田產安插漢人,借以變易苗俗的建議,已獲旨準。但漢人之善良者,終不肯輕入苗地,其愿就招攜者,大半皆無賴之徒,“恐轉滋事端,未為妥協”。以后朝廷將馮兆裕的奏疏抄寄張廣泗,令妥酌辦理。
張廣泗提出從前苗疆不可安插漢人,緣由是逆產無多,而苗人強悍。而此時的情形是可以安插漢人,“且有不容不安插之勢”。原因是“逆產頗多,而苗人不敢滋事”。安插之法是由近及遠,由淺及深。用兵之后,苗人戶口凋零,于附近城汛并彼此大路通達之區,可設立漢民村寨,以相聯絡。并在農工閑暇之時,組織漢民訓練,有事可望助守,則官軍勢強而苗人勢弱。但安插漢民領種反叛苗人的土地,必然造成苗、漢混雜,給維持社會秩序帶來困難。張廣泗建議凡安插之地,酌量田土多寡,務須一二百戶,或數十戶以上為一村寨,修砌土堡,使聚居一處,既不能讓內地之民零星散居,亦須隔絕漢民與苗人,“永遠不許與苗人摻雜居住”。在漢民村寨按戶編成牌甲,每堡擇立屯長,或鄉堡以統率之。“則無賴流棍之徒,亦不致潛行混入矣”。①《張廣泗奏苗疆善后事宜折》(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日),《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上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7年,第213頁。
還有一種情形也引起朝廷的重視。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二月二十一日,云貴總督李侍堯奏稱,江西、湖廣等省寄住云南的外省客民,經常出入邊隘,“與外夷暗通商販”。其中有男婦家口者已編入保甲,但游手好閑、蹤跡詭秘之人,若地方官查察稍疏,可能于山徑叢雜處所竄逸出關,“暗通消息,取悅外夷”。騰越州知州吳楷稱該州地面及各土境,有江楚游民41人,皆系單身游食,在各村寨中出入無定,“恐將來有偷越邊關、不法等事”。奏請批準查辦。李侍堯命令該州以清查保甲為名,“不動聲色,密查辦理”。可見此類情形也屬保甲制度管理的范圍。②《云貴總督李侍堯為查明邊隘江楚游民,仰祈睿鑒奏事》(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折》,1982年。
外來人口大量移居改土歸流地區,進而造成復雜而深遠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大批外來移民進入苗區墾種。既開發了這些地區,同時也與苗民爭奪土地、水源等資源,與當地苗民發生了矛盾,一些地方苗民起而驅趕外來客民。據記載:“永綏廳懸苗巢中,環城外寸地皆苗,不數十年盡占為民地。……奸苗倡言逐客民,復故地,而群寨爭殺,百戶響應矣”。乾隆六十年(1795),在貴州山區和相連的湖南地區,再次發生強驅趕外來人口的土民起義。貴州同仁府苗民石柳鄧率眾起事,湖南永綏廳黃瓜寨石三保發動苗眾響應。起事苗眾擊敗來犯清軍并包圍永綏,乾州、鎮筸苗民各圍其城,貴州總兵珠隆阿亦被圍困在正大營。“苗疆大震”。乾隆帝頒詔令云貴總督福康安、四川總督和琳、湖廣總督合兵剿之。嘉慶元年(1796),清軍與起事苗眾在乾州一帶相持,七省官兵持久年余。以后和琳攻下乾州,進攻平隴,并奏善后章程六事,大意是“民地歸民,苗地歸苗,盡罷舊設營汎,分授降苗官弁羈縻之”。因繳收槍械一事存在爭議,其議遂罷未行。不久和琳病死于軍中,額勒登保接任其職。清軍最后斬石柳鄧父子與吳廷義,起義被平定。①(清)魏源撰:《圣武記》卷7《嘉慶湖貴征苗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點校本,第314頁。
其次,外來人口大量進入新開發的礦山,既有利于礦業開發,同時也蘊藏相當大的隱患。雍正九年(1731)七月二十七日,雍正帝頒諭內閣,稱廣西道通交趾,聞該地方有無知愚民,拋棄家業,潛往交趾地方開礦,更有“奸匪之徒”,潛逃異域,以致追緝無蹤者。似此違禁妄行,漸不可長。令廣西巡撫、提鎮悉心商酌,于往來隘口及山僻可通之處,撥兵添汛,飭令該管官棄加緊巡查。倘有私行出口之人,務必押解原籍,“照例治罪”。②《清世宗實錄》卷108,雍正九年七月,日本東京大藏株式會社影印本。云南地區的情形亦較嚴重。乾隆三十一年(1766)六月四日,據云貴總督楊應琚奏稱,云南近年來礦廠日開,各處大小廠聚集砂丁人等不下數十萬人。現在各省來滇者猶絡繹不絕,其間江楚等省流寓倍于云南省,造成“各廠糧價倍貴于城市,而他處之糧亦因搬運空虛,市價日長”。③《云貴總督楊應琚為酌濟滇省銅廠事務,節其耗米之源,以欲民食奏事》(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四日),檔號36-0089-012;縮微號36-004-0745。
其三,一些品質欠佳的漢人,進入改土歸流地區后違法行事,甚至欺負或欺騙土民,導致刑事案件明顯增多。雍正五年(1727)正月二十五日,云貴總督鄂爾泰的奏疏稱,在兵、苗錯處之地,雖不能禁漢民不相往來,但因駐扎官兵,劫殺之風自可少息。其余無營汛之寨,專屬苗夷聚住處,原本不許漢民雜居,但一些漢人借貿易之名,“巧為勾通之計”。“川販漢奸,潛匿兇寨,非動官兵難以擒拿”。乃奏請規定凡擒獲川販、“漢奸”,審明實有通同苗夷劫殺案件,每擒獲一起,即記錄有功一次,有能出告川販、“漢奸”情實罪當者,其應加紀錄之官,每獲一人,賞出告人銀五兩。若如此,“不待三年,而川販漢奸或可絕跡矣”。雍正帝夾批:“甚合情理”④《云貴總督鄂爾泰為覆奏奏事》(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五日),故宮文物館編《朱批諭旨》鄂爾泰折三,1930年。。雍正五年(1727)二月三日,雍正帝詔諭云南、貴州、四川、廣西的督撫、提鎮等官員:稱仲苗素稱兇悍,加以“漢奸”、販棍潛藏其中,引誘為惡,以致燒殺劫掠,毒害善良,居民深受其擾。“此天下之共知、共聞者”。⑤《清世宗實錄》卷53,雍正五年二月,日本東京大藏株式會社影印本。
由于存在上述情形,在實現改土歸流的地區普遍實行保甲制度,充分發揮保甲制度在加強基層管控方面的作用,便顯得尤為重要。
三
在改土歸流地區普遍推行保甲制度,隨即遇到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即是否可任用土目。雍正五年(1727)三月十二日,云貴總督鄂爾泰就“改流之土民宜從國制”提出意見,認為將土目遷入腹地、“里長、甲首,令百姓輪流充當”的看法,可能致使“夷民恐兩不相習,轉難寧帖”。他認為撫夷之法,須以漢化夷,以夷制夷。土官雖類多殘刻,但其中為夷民所畏服并無異志者,仍可利用,流官若存委曲開導之意,日積月久,必然“知尊知親,生殺惟命”。雍正帝夾批:“甚是”①《云貴總督鄂爾泰為欽遵圣諭奏事》(雍正五年三月十二日),故宮文物館編《朱批諭旨》鄂爾泰折三,1930年。。雍正十年(1732)三月,苗疆地區的改土歸流接近尾聲,官員方顯奏請于苗疆編立保甲,建議每十人設一甲,擇一老成者為甲長,每十甲置一保,擇一強干者為保長。②《方顯奏請于苗疆編立保甲折》(雍正十年三月),故宮文物館編《朱批諭旨》,1930年。方顯所說可擇為“甲長”的“老成者”,以及充任“保長”的“強干者”,大都是苗人中負有名望之人,大部分是原來的土目,可見方顯贊同從土目選任甲長、保長的做法。
乾隆元年(1736)八月初八日,張廣泗在給乾隆帝的奏折中,就兵部侍郎王士俊關于苗疆可將征服各寨,大則以30寨為率,小則以50寨為率,“擇土司中之才能素堪服讋服群苗者,使管轄之”的建議,明確表示反對。張廣泗說苗疆回環2000余里,錯雜數十萬人,其各為雄長,向無統率,故人散而無所屬。無所屬則無定謀,不相連則無固志。若設以土目管轄之,欲強立一人以為土司,“苗人安肯聽其約司之設,于理、于勢皆有所不可也”。③《張廣泗奏遵旨復議王士俊條陳折》(乾隆元年八月初八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編《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上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189頁。
經過眾臣反復討論,朝廷基本上認同為夷民所畏服、并無異志的土目,仍可擔任甲長或保長。但在具體實行的過程中,也有少數“無賴濫充”的情形,使查點、首報“竟同虛設”。乾隆二十三年(1758)五月二十八日,清朝就云南等地推行保甲制度,存在“各鄉設立保長、甲長,類以市井無賴之徒充之,平時并不留心查察,雖督撫課最有力行保甲之條,不過故套相沿,毫無裨益”的情形,詔令進行整頓,說明這一類的情形并不少見。④《云貴總督愛必達等為欽奉上諭奏事》(乾隆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檔號0219-021;微縮號01-032-0608。
清朝在苗疆推行適當保留小土司的政策,以土官在政治上接受流官的管理、文化上接受王朝的教化作為基本前提。土官須受流官的嚴格管束。以廣西地區為例。桂西土司隸屬南寧、太平、慶遠、思恩、鎮安五府流官管控。上述五府官員缺額時,一般從廣西腹地五府調補。康熙二十六年(1687),廣西巡撫彭鵬奏稱,南寧、太平、慶遠、思恩四府地處邊遠,轄土屬50余處,水土惡劣,尤為難治,請求上述四府官員若有缺,以桂林、平樂等五府官員之廉能者“攀簽調補”,該建議為朝廷所采納,并提出“三年俸滿升用”的原則。
清朝既推行改土歸流,而基層土官的數量卻在增加,說明經過改土歸流取得的成績,主要是縣以上行政制度的重建。若僅從行政制度設置上看,改土歸流僅完成了行政制度的流官化。從司法角度來看,改土歸流不一定確土歸流地區適用國家法律。在鄉土社會中,基層社會存在的組織體制,對上層行政制度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若下層社會組織未發生改變,上層行政制度的功能可能減弱。
改土歸流以后,流官統治無法改變貴州“夷多漢少”的局面。改土歸流初期貴州城中皆兵,城外“流氓落落數十家,至群苗,則皆僻居溪洞籠箐中”。在茂密的山箐地區,有大量的少數民族人口。這些少數民族成分構成復雜,風俗各異,生產生活方式不一。類似地區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與內地社會存在明顯的差異。隨著國家權力在改土歸流區推進,地方政府對基層社會進行重構。在保甲制度向地方社會移植的過程中,因土目的權威具有根深蒂固的社會基礎,兼之土目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因此普遍被委派擔任里長、甲長,使其協助流官管理基層社會。這是在國家權力向基層社會推進受阻的形勢下,國家治理方式在地方社會的一種過渡性的措施。
實行改土歸流后,土目的政治身份轉換,從隸屬于土司轉向隸屬于流官。土目不再是土司時代具有軍、財、政集為一體的地方官,而是協助流官管理的非正式官員,他們在改土歸流地區的地位,并未獲得地方政府的書面認可。在官府的管轄下,由于苗民對土目的權威依然認同,基層社會的諸多事務只能委派土目才能處理,流官反而缺乏權威。土目的保留,使地方社會延續了土司時代的生產關系。土目為了有效控制基層社會,建立了管控民眾的相應組織。基層的權力主要由土目把持,土目成為改土歸流地區社會秩序的積極維護者。
在一些完成改土歸流的地區,通常是讓本地民族的首領出任各種土弁,通過他們對本地民族實行社會控制。在黔、湘、鄂、蜀諸省相鄰的地區,大都通過設置各種土目來對苗民進行控制,即由本地民族管理基層社會。雍正五年(1727)對此有過爭議,四川副將張瑛提出應將改流地區的土目全部內遷,對本地民族百姓強行剃發,收繳其器械。鄂爾泰認為這樣做將導致本地民族發動激烈的反抗,任命士目為里長、甲長的做法較為可取。
清朝在土司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改流的對象主要是構成明顯威脅的大土司。對一些小土司則采取懷柔、保留的政策,清末在南方仍然存在不少小土司。以廣西地區為例。據《清史稿》卷2《土司一》記載,廣西有土州26個,即忠州,歸德州、果化州、下雷州、下石西州、思陵州、憑祥州、江州、思州、萬承州、太平州、安平州、龍英州、都結州、結安州、上下凍州、佶倫州、全茗州、茗盈州、鎮遠州、那地州南丹州、田州、向武州、都康州、上映州:土縣四個,即羅陽土縣、上林土縣、羅白土縣、忻城土縣;長官司三個,即遷隆峒、永定司、水順司。廣西的土司政區合計有33個。
四
乾隆時期,統治者在改流地區更深入地推行保甲制度。乾隆時期的成功之處,在于不拘泥于內地的保甲編制,而是根據苗疆的地理環境和民族分布特點,因地制宜地靈活變通。清朝還將保甲制度移植到各民族社會,上述情況普遍存在于已實行改土歸流的一些地區。在廣東四會地區,乾隆二十一年(1756)的記載稱:“詳請裁革,瑤民編入各村寨保甲,與齊民一體稽查”。廣東思平縣也有“乾隆二十一年,以瑤民向化日久,瑤目可以不設,詳情裁革,編入保甲,與齊民一體稽查”的記載。這兩個地區都是由于瑤人與漢人社會發展相似而進行一體編甲,即在其基層社會組織中移植了保甲制度。在貴州黎平地區,咸豐四年(1854),侗族所立的碑約有“一家有盜,九家齊心,一甲為非,九家公罰”的內容,證明在當地實行了保甲制度。
清代前期朝廷的一系列措施,使國家行政權力在苗疆得以逐步深入,為中后期朝廷的管理奠定了堅實基礎。乾隆時期,清朝的措施較雍正時期更為詳細和具體。例如對增設郡縣和員弁,乾隆帝考慮得更為周密。乾隆元年(1736)十月,吏部等議覆云南總督尹繼善疏言:“廣南為粵西交趾分界之區,地方遼闊,事務殷繁,知府一員實難總理,請于廣南府添設附郭知縣一員,典吏一員,照例頒給印信……又舊設兵額不敷防守,請于廣南營添設兵三百名,廣羅協添設兵一百名,并添建衙署營房。”①《清高宗實錄》卷11,乾隆元年十月,日本東京大藏株式會社影印本。乾隆元年(1736)十一月,乾隆帝諭總理事務王大臣:
今朕思張廣泗所奏,第一條,請于新疆內地添設官兵,駐扎彈壓,自應照所請行。但所添兵丁,計一千三百余名,以之分布各處,朕意似稍覺不敷。現在安設營汛,是否定敷巡防之用?目前斷不可以節省錢糧,而為遷就之舉。其第二條,請設立郡縣,在目前似可不必。或因地方遼闊,所有同知、通判等官,難于統轄,酌設道員,彈壓巡查,似尚可行。②《清高宗實錄》卷51,乾隆元年十一月,日本東京大藏株式會社影印本。
在推行團練制度、保甲制度的過程中,在漢民地區、瑤僮地區采取的措施有所區別,即在漢民地區設團總、練總、保長、保甲,在偏遠分散的村落設立鄉老、村老、老人,地方緝捕事務和保甲稽查都歸練總、保長等負責;在瑤、僮地區則因其故俗,設瑤長、僮長,由瑤長、僮長約束各自村寨百姓,地方官據其執行的好壞予以賞罰。在漢民地區實行練總與保甲共同負責、地方官監督的制度,因此控制的程度較高。至于瑤、僮地區則以自我約束為主,保甲的作用并不明顯。
清朝在廣西地區推行的保甲制度、團練制度,實際上是一種以侗制侗、以款制款的政治方式。推行這種制度后,侗族地區的款組織進一步被官府利用,有些地區的款組織,實際上已被官府所指派的鄉正、團長把持,他們既是鄉正、團長,又是當地的大小款首。
乾隆二十三年(1758)五月二十八日,云貴總督愛必達等的奏疏,對云南省實行保甲制度的情形做了較全面的總結,并提出改進的意見,內容大致如下。
保甲制度方面的規定向有明文,“班班可考,只需逐一摘出,再行申飭,實力奉行”。云南地處邊徼,民風、土俗視他省稍殊,在一省之中,辦理情形亦有難于一致者,臣等當與司道參稽成例,“俯察輿情,因地制宜,悉心籌酌,定為編查考核各條”。說明在南方土司地區實行的保甲制度,與朝廷的規定大致相同,具體的內容可根據因地制宜的原則可有變通。
云南省“漢少夷多”,各地差別較大。保甲制度可根據具體情況變通。凡在城廂、市鎮與漢人參錯居處者,自應一體編入保甲,“毋庸分別”。而依山傍谷、自成村落的夷民,多者數十家,少者數家,服食起居俱與漢人迥別,更有于懸崖密箐之內搭寮而處者,隨時遷徙,更無定居,此種夷人若散給門牌,分編保甲,屬徒勞無益。夷人之中原設的火頭、寨長、目老、叭目等名目,職責、經管“與漢人之保長甲長無異”。可循其舊制,即令管事的頭目,將所轄戶口、姓名、年貌、生業造具清冊,一份送州縣,一份存該頭目收執,以備稽查。若有土司管轄之地,即令該土司查造清冊申送,按季循環輪換。
清朝還規定,夷民若有受文武土司以及土舍、土目、土千把、掌寨等管轄,其散在各郡縣者,“應照前條辦理”。至于沿邊一帶的土司,界連外域,未便與內地同例編排,尚令該土司各就所轄夷民,自行稽查約束,并將夷民的姓名等備造清冊,申送該管知府。季底出具未容留“漢奸”、外夷的文字,具結后呈報該府,轉送上司備查。
云南地產五金,隨處多有礦廠。湯丹、大碌的礦廠,聚眾至數萬人,其余數千以至數百人不等,“多系五方游守無籍之徒,礦旺則來,礦衰則散”。對這一部分人口,“稽查之法宜較城市倍加嚴密”。官府責成廠官、課長,各將本名下所管人役逐一清查,開造姓名、年貌、籍貫清冊,一送廠員,一存課長,再于一硐之內立一硐長,一爐之內立一爐頭,將所用夫役不時稽查,將去來、增減隨時報明課長。每于月朔呈送廠員,循環輪換。云南多產鹽井,鹽戶自一千數百家至數百家不等。領薪煎鹽,均設有灶頭、課長、鄉約、總保等頭目。現不必另立牌頭、甲長,即以灶頭為牌頭,以課長為甲長,以總保、鄉約為保長,在鹽井貿易、開鋪的商民與零星居住的漢夷人口,皆附于灶戶之內辦理。
清朝規定各省流寓云南等地的人口,凡置有產業、娶有家室,以及雖無產業、家室而在地開張貿易者,均編入保甲制度管理。往來商賈及走廠之人,則各設客長一至二人,不時查察逐一登記,交與客長,送官稽查。關于保甲的日常管理。朝廷規定將律例內人所易犯、法所必懲的各條逐一摘出,刊刻印刷,裝訂成冊,由地方官廣行頒發。保甲長平時互相提醒,有違法之事隨時稟官,以免致自己陷于刑罰。在實行保甲制度的地區,查點戶口、散給門牌,編造冊籍。保甲的門牌過去三年一換或五年一換,現規定門牌一年一換,牌頭、甲長,定為三年一換;保正統轄十甲,查察較難,定為一年一換。過去每年農隙之后,官府對各處保甲查點一次。現規定官員踏勘下鄉,可順帶冊籍,隨便查點。所排編保甲,“不實力奉行者,專兼統轄各官分別降調,處分甚重”。并強調指出,以上諸條,“最要者尤在慎選保長甲長,不使無賴應役”。①《云貴總督愛必達等為欽奉上諭奏事》(乾隆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檔號0219-021;微縮號01-032-0608。
小 結
從有關的記載來看,清朝在改土歸流各省實行保甲制度,做法與云南省大致相同。乾隆三年(1738)十月五日,據張廣泗奏,苗寨內所稱頭人,系各本寨中稍明白、能言語、強有力者,眾苗呼為“頭人”。清軍懲剿之時,“所有起事兇惡頭人,殲除殆盡”。現今存留各寨者,尚屬安分之人。今苗疆可就各寨擇其良善守法者,將姓名公舉報官,酌量寨子大小,每寨一二人或二三人,立為寨頭,注冊立案,本寨散苗聽其約束。“以仿內地保甲,設立鄉保、牌頭之意”。②《鄂爾泰等奏革除苗疆派累并厘定屯堡章程折》(乾隆三年十月初五日),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編《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上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255頁。
另據道光十二年(1832)九月庚寅的記載,湖南瑤人八大排之內,各舉老成知事者立為瑤老、千長。由綏瑤廳揀選承充,管理其排的事宜。其余的各小沖,為某大排的分支,統歸某大排瑤老、千長管領,并按戶給發門牌,將大小人口備載于上。并于八大排之內每排添設瑤練十名,統歸連山廳把總管帶差遣。如有官兵入山找借口敲詐之事,千長等可到官府告發,“照例治罪”。③《清宣宗實錄》卷222,道光十二年九月庚寅,日本東京大藏株式會社影印本。
至于在云南的瀾滄江以南、靠近中緬邊境的地區,在改土歸流之后,清朝基本上保留了土司。所謂:“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史籍稱:“江外歸車里土司,江內地全改流”。④(清)魏源撰:《圣武記·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點校本,第285頁。上述做法反映出在設立保甲制度的問題上,清朝亦奉行因地制宜的原則,并注意循時改進,使之逐漸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