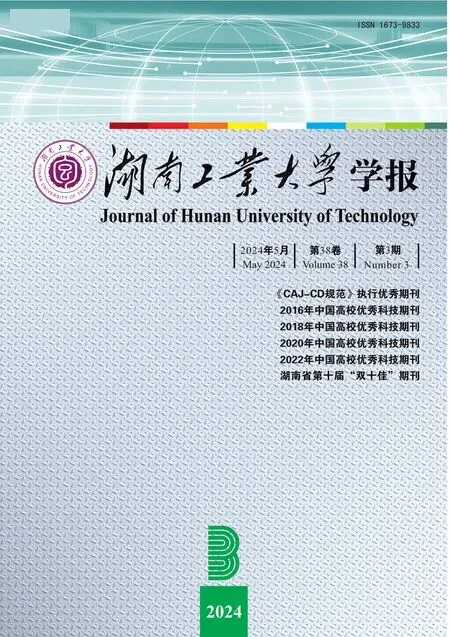環境規制對長三角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胡本田,胡 倩
(安徽大學 大數據與統計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1)
1 研究背景
長江三角洲作為我國經濟發展迅速、資源豐富的地區之一,目前正處于發展的關鍵階段。2020年8月20日,習總書記在扎實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座談會上強調,長三角地區不僅要在經濟發展上走在前列,還要在生態保護和建設上帶好頭。為了繪就高質量發展的生態底色,相關部門積極推動長三角區域生態環境共保聯治,但是能源消耗量持續增長、跨界水污染愈發嚴重、可再生資源相對匱乏等問題仍未解決,嚴重阻礙了長三角地區的可持續發展。立足于新發展階段,協同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能夠激發社會經濟發展的潛力,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因此,厘清環境規制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對于長三角地區早日實現“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穩定增長”雙贏的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作為保證環境與經濟和諧發展的有力抓手,環境規制是一種政府通過制定政策與措施,對企業的經濟活動進行調節,進而控制污染排放的宏觀政策工具[1]。關于環境規制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國內外學者的研究中存在3種不同的觀點:1)環境規制能夠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M.E.Porter等[2]提出“創新補償說”,認為環境規制能夠推動企業提高創新水平,從而抵消因遵循規制所產生的成本;何興邦[3]通過實證發現在經濟的效率、結構和穩定效應等因素的作用下,環境規制會顯著改善地區經濟增長質量;2)環境規制會抑制經濟高質量發展。新古典經濟學最早提出“遵循成本說”,認為環境規制加大了企業治污減排的成本,導致其生產效率下降,從而不利于經濟的發展[4];劉傳明等[5]分析得出,環境規制能在短期內通過擠占企業技術研發投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抑制作用;3)環境規制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呈非線性關系。熊艷[6]發現在環境規制實施前期,成本的“抑制效應”起主導作用,但是當其強度超過某一值后,創新的“補償效應”將起主導作用,二者之間呈現“U”型關系;薛蓮等[7]研究得出初期環境規制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激發企業進行技術創新,而過度的環境規制又會影響產業鏈節點的合理銜接,二者呈現倒“U”型關系。
綜上所述,學者們大多聚焦于省級層面數據,對長三角地區的研究較少,主要通過耦合分析、傳統線性回歸、門檻回歸等方法進行分析,未考慮二者可能存在空間溢出效應,且忽略了產業結構升級的中介作用。據此,本文擬構建空間杜賓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和中介效應模型,探討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影響以及產業結構升級的中介效應,以期為長三角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一定的參考依據。
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2.1 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
首先,環境規制的實施能夠在一定條件下激發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活力,促使其主動改進工藝和流程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時減少企業的生產成本,使得企業利潤增加,從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8];其次,政府部門通過頒發一系列與環境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引導高污染型企業改變以往的生產方式,將部分要素資源投入環境治理中,這樣既可以加速淘汰落后產能,又能抑制污染型產業規模的擴張,進一步助力城市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最后,環境規制的實施不僅可以推廣清潔能源的使用,推進節能環保產業的發展,還能為低碳技術成果的轉化提供合適的平臺,這既能促進企業實現低碳轉型,又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注入新動能。根據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H1。
H1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促進作用。
2.2 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
環境規制作為一種以保護環境為目標而制訂實施的各種政策措施的總和,其空間溢出效應是不容忽視的。一方面,根據I.Walter等[9]提出的“污染天堂假說”,高污染企業會迫于環境治理的高額成本壓力,將污染產業從環境規制較高的地區遷移至環境規制相對較低的鄰近地區,從而增加了周邊地區的污染排放,產生了環境污染的“空間溢出”,不利于周邊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環境規制的實施要求企業降低污染物排放,而污染排放具有跨區域的擴散特征,若一個地區降低了流動性強的大氣污染和水污染的排放,那么周邊地區也會從中獲益,產生“搭便車”效應[10]。根據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H2。
H2本地的環境規制可以通過空間溢出效應對周邊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影響。
2.3 產業結構升級的中介效應
環境規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限制傳統高能耗產業的發展,推進企業新生能源研發投入的增加,進而促使產業結構持續升級。此外,隨著環境規制強度深入,污染型產業的生產成本會逐步上升,在此情況下會倒逼企業進行技術創新,進一步深化產業分工,這樣有助于產業結構調整,進而實現產業轉型升級[11]。而且,面對“環境壁壘”效應,環境目標約束能嚴格控制企業的進入和退出,從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作為新經濟增長點,產業結構升級能通過優化要素間的資源配置,實現各部門之間均衡分配,進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根據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設H3。
H3環境規制可以通過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圖1為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制。

圖1 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制Fig .1 Specific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3 模型設定、變量說明與數據來源
3.1 變量說明
3.1.1 被解釋變量:經濟高質量發展(Vhqd)
基于數據的可獲取性,同時借鑒馬茹等[12]的研究思路,從綜合效益、科技創新、協調發展、生態文明、開放共享5個層面構建了涵蓋19項具體指標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運用熵值法[13]計算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模型各項指標的含義如表1所示。

表1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Table 1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x system
3.1.2 解釋變量:環境規制(Ver)
本文借鑒劉滿鳳等[14]的思路,基于單位工業產值的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衡量環境規制水平。
首先,對單位工業產值污染物排放量Rij取倒數:
其次,進行極差規格化變換并加0.000 1值平移處理,以消除量綱的影響:
最后,對處理后的值進行平均處理,計算出每個城市最終的環境規制水平:
3.1.3 中介變量:產業結構升級(Vis)
本文借鑒胡艷等[15]的方法,采用第二、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衡量產業結構升級。
3.1.4 控制變量
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以下控制變量。1)基礎設施水平(Vinf)。選取人均城市道路面積來衡量,并對該數值取自然對數。2)政府政策干預水平(Vgov)。以城鎮私營和個體從業人員數與就業人員總數的比值來表示。3)金融發展水平(Vfnc)。以金融機構貸款余額與儲蓄存款之比來表示。4)信息化水平(Vint)。選取郵電業務總量來衡量,并對該數值取自然對數。
3.2 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0—2019年長三角41個城市的面板數據作為樣本進行實證分析。數據來源于各省市統計年鑒和統計公報、《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1—2020)》和EPS全球數據庫。對于缺失的數據,采用線性差補法補全。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variables
3.3 模型設定
3.3.1 空間杜賓模型
為探究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本文擬構建空間杜賓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具體如下:
式中:Vhqd,it為城市i在t年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Ver,it為城市i在t年的環境規制水平;考慮到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可能會產生非線性影響,在模型中引入了環境規制的二次項Ver2,it;Vcontrols,it表示可能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一系列控制變量,包括基礎設施水平(Vinf)、政府政策干預水平(Vgov)、金融發展水平(Vfnc)和信息化水平(Vint);uit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ρ、αi、θi、為待估參數;W為空間權重矩陣,本文構建經濟距離權重矩陣和地理鄰接權重矩陣進行實證分析,具體設定如式(4)和式(5)所示:
3.3.2 中介效應模型
為進一步探究環境規制影響經濟高質量的作用機制,參考溫忠麟等[16]的研究思路,選取產業結構升級作為中介變量,構建中介效應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第一,以經濟高質量發展為被解釋變量,環境規制的一次項、二次項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估計:
第二,以產業結構升級為被解釋變量,環境規制的一次項、二次項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估計:
第三,以經濟高質量發展作為被解釋變量,將環境規制的一次項、二次項和產業結構升級同時納入模型中進行回歸估計:
式(6)~(8)中:βi、γi、σi為待估參數;Vis,it為城市i在t年的產業結構水平;ε1,it、ε2,it、ε3,it為隨機誤差項,其余變量與式(1)含義一致。
4 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證研究
4.1 空間相關性檢驗
本文首先選取全局Moran’s I進行空間自相關檢驗。在兩種空間權重矩陣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莫蘭指數在1%顯著性水平下均大于0,表明在樣本期內長三角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間相關性。因此,選取空間計量模型研究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效應是合理的。
表3展示了兩種空間權重下2010和2019年長三角地區不同城市的空間聚類具體情況。

表3 2010、2019年長三角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集聚情況Table 3 Spatial agglomeration table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2010 and 2019
總體來看,相較于2010年,2019年位于第一、三象限的城市個數略有減少,表明“高-高”和“低-低”空間集聚呈現出稍微下降的態勢,但是絕大多數城市仍然集中分布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具體來看,上海、蘇南、浙北地區主要集聚在第一象限,這些地區的城市能憑借地理位置的優勢,擁有眾多要素資源,經濟水平一直居于全國領先的位置,同時其周邊城市也呈現較高的水平;而皖北、蘇北地區的城市主要集聚在第三象限,這些城市經濟基礎相對較薄弱,資源稟賦缺乏,同時其周邊城市也呈現較低的水平。這也從側面說明了目前長三角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不平衡現象。
4.2 空間計量模型的選擇及分析
4.2.1 空間計量模型選擇
采用LM檢驗和穩健LM檢驗對空間相關性和空間滯后性進行分析。在經濟距離權重矩陣下,統計量的P值均小于5%;在地理鄰接權重矩陣下,統計量都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綜合來看,在這兩種權重矩陣下,選擇構建空間杜賓模型進行后續分析;LR檢驗的結果表明,兩種權重矩陣下,統計量的P值分別通過了1%和10%的顯著性檢驗,所以拒絕原假設;根據Hausman檢驗可知,統計量的P值均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所以最終選擇固定效應。
4.2.2 空間計量模型分析
分別構建包含時間固定、城市固定和雙向固定的SDM模型,具體見表5。依據模型中回歸的顯著性及擬合優度結果,在兩種不同空間權重矩陣下,本文均選擇包含時間固定效應的SDM模型進行后續分析。

表5 不同固定效應下SDM回歸估計結果Table 5 Spatial Durbin model (SDM) regression estimation results under different fixed effects
從表5可知,在兩種空間權重矩陣下,環境規制的一次項系數分別為0.079和0.046,分別通過了1%和10%的顯著性水平,說明環境規制的提高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促進作用,假設H1得到驗證;環境規制的二次項系數均為負值,表明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呈現倒“U”型的變化趨勢:當環境規制強度較低時,環境規制有利于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隨著環境規制強度不斷增加,超過拐點后,環境規制會抑制經濟增長質量[17]。
從控制變量來看,在經濟距離權重矩陣下,基礎設施(Vinf)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完善的基礎設施能夠降低地區之間生產要素的流動成本,提升經濟運行效率;而在地理鄰接權重矩陣下,基礎設施回歸系數為負且不顯著,可能是因為目前鄰近地區之間尚未建立起較為成熟的基礎設施網絡體系;政府政策干預(Vgov)的回歸系數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且系數最大,說明政府干預在推動經濟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它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金融發展(Vfnc)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下均顯著為正,說明金融發展能夠為實體經濟發展注入強勁動力;信息化水平(Vint)的估計系數大于0,且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資源自由流動實現優化配置,推進經濟實現提質增效。
4.2.3 空間效應分解
為了進一步分析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具體空間影響,本文計算了兩種空間權重矩陣下空間杜賓模型的直接效應、溢出效應和總效應,如表6所示。

表6 空間效應分解結果Table 6 Decomposition results of spatial effects
在經濟距離權重矩陣下,環境規制一次項的直接效應、溢出效應和總效應的系數大于0,且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環境規制不僅對本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有顯著促進作用,還會發揮正向空間溢出效應以促進經濟聯系密切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假設H2得到驗證。因為在政績考核和政治晉升的雙重刺激下,地方政府更傾向于“逐項競爭”策略,本地區政府在環境規制策略上會根據經濟關系密切地區所實施的環境規制強度制定一個更高的水平,迫使污染型企業的加速轉移,從而推動了經濟的高質量發展[18]。在地理鄰接權重矩陣下,其空間溢出效應為0.146且不顯著。這說明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在經濟空間下關聯性更強。
在經濟距離權重矩陣下,環境規制二次項系數的直接效應、空間溢出效應和總效應均為負值,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說明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先增加后減少的倒“U”型的變動趨勢。在環境規制實施前期,其有助于增強高質量發展的動力轉換;當越過某一臨界點之后,高強度的環境規制憑借其約束性,可能會加重企業的負擔[19],從而會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抑制作用。經過計算臨界值為1.308,而當前環境規制的均值是0.856,居于臨界值的左側,表明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促進作用,再次驗證了假設H1。
在控制變量中,政府政策干預(Vgov)和金融發展(Vfnc)的直接效應和總效應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本地政府政策干預的深入和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可以提升本地區經濟的質量。在經濟距離權重矩陣下,基礎設施對經濟高發展具有穩健的正向作用,其直接效應相對于總效應更加明顯;而地理鄰接矩陣權重下,基礎設施(Vinf)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所表現出的直接效應、空間溢出效應和總效應均為負值,但不顯著。可能是因為經濟發展越好的城市會憑借其優越的基礎設施條件,吸引周邊城市的資源流入,抑制了周邊城市的經濟發展。信息化水平(Vint)的溢出效應在經濟距離權重矩陣為負,在地理鄰接權重矩陣為正,均不顯著。說明本地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對周邊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的影響可能不盡相同,經濟鄰近地區會產生負面影響,而地理鄰近地區則會產生正面影響。
4.2.4 穩健性檢驗
為確保實證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運用替換解釋變量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借鑒相關學者[20-21]的方法,重新構建環境規制變量:第一,收集2010—2019年江浙滬皖省級政府工作報告,計算與生態環境保護相關詞語占全文總字數的比例(與生態環境保護相關詞語包括環境保護、環保、污染、能耗、減排、排污、生態、綠色、低碳、空氣、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二氧化碳、PM10和PM2.5);第二,計算各城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單位數占所屬省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單位總數的比例;第三,將二者相乘,得到最終的地級市環境規制指標。為便于分析,將該指標放大1 000倍進行觀測,對基礎模型進行再估計。從表7的穩健性檢驗結果可知,與原先回歸結果具有一致性,系數的符號相同,系數的大小有稍微的差別,由此可知本文的基本結論具有較高的可信度。

表7 穩健性檢驗結果Table 7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4.3 中介效應分析
為了檢驗產業結構升級在環境規制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中介效應,本文通過構建中介效應模型進一步分析,結果如表8所示。

表8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Table 8 Mediation effect results
模型(1)展示了全樣本回歸結果。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總效應為0.108,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有正向推動效應;模型(2)和模型(3)分別展示了以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為中介變量的回歸估計結果。環境規制和產業結構升級的系數均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具體來看,模型(2)中,環境規制實施強度每提高1個單位,產業結構升級將會提升0.027個單位,說明環境規制的實施對產業結構升級有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模型(3)中,環境規制的系數為0.064,相較于模型(1),系數有明顯變小的趨勢,意味著存在部分中介效應。產業結構系數為1.580,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說明環境規制通過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來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假設H3得到驗證。
5 結論及建議
5.1 結論
本文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運用空間計量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分析了環境規制對長三角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實證研究表明:1)環境規制有助于長三角地區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且二者之間呈現非線性的倒“U”型關系。目前,環境規制的均值處于臨界點的左側,說明加強環境規制的實施對長三角地區的高質量發展會產生促進效應。2)在經濟距離權重矩陣下,環境規制對長三角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顯著的正向溢出效應,本地環境規制的實施能夠促進經濟聯系密切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在地理鄰接權重矩陣下,環境規制的空間溢出效應不顯著。說明相較于地理因素,經濟因素對環境規制的溢出效應的作用更強。3)環境規制可以通過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對長三角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5.2 建議
為了進一步推動長三角地區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本文給出以下建議:
第一,完善環境規制相關政策,加大環境規制實施力度。要健全長三角地區之間的環境規制政策協調治理機制,積極推進節能減排的綠色考核機制及相關監管,進一步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第二,充分發揮空間溢出效應,實現長三角共同發展。上海、蘇南、浙北地區的城市之間要構建技術共享和交流平臺,實現要素之間的暢通流動;經濟稍微落后的皖北、蘇北地區的城市,要在保護環境的前提下加快推進產業集聚區建設,進一步縮小與長三角中心城市的經濟差距。第三,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培育壯大新興產業發展。構建符合現代化的產業體系,優化產業結構,同時加快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鼓勵企業使用循環發展的綠色生產模式,以此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