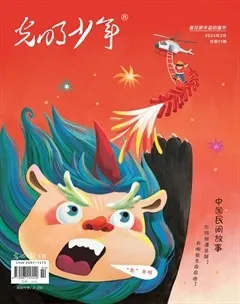童詩里的野孩子
關勝
我癡迷于那些充滿天真的句子,它們隱藏著對未來世界先知般的預言。泰戈爾、顧城、密斯特拉爾、謝爾·希爾弗斯坦等詩人的兒童詩,在少年時代走進我的生活里。至今,我仍然能記住他們童詩中有趣的詩句。
不想寫作業的泰戈爾,在媽媽督促寫作業時,期望“為什么黑夜不能在/十二點鐘的時候來到呢?”芬蘭瑞典語女作家伊迪絲·索德格朗站了一個夜晚,在臺階上看星星時寫下“你別赤腳在這草地上散步/我的花園到處是星星的碎片”。
每次讀這些偉大詩人的童詩時,總會被他們稀奇古怪的想象所折服。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用這樣的方式表達。顧城的《安慰》一直是我兒童時代念念不忘的一首詩:
青青的野葡萄/淡黃的小月亮/媽媽發愁了/怎么做果醬/我說:別加糖/在早晨的籬笆上/有一枚甜甜的/紅太陽
我曾把顧城的詩改編成一個故事:
在一個忙亂的正午,也許廚房里早已被各種食材所堆滿。客廳里,重要客人正等著吃飯。母親早已被三明治弄得什么也顧不過來,偏偏這時果醬還不見了。頑皮的孩子說,我知道果醬在哪里。母親滿懷期待地跟著,結果孩子指著窗外的紅太陽說,這不是嗎?我想,如果你這么做的話,現實中的母親一定會被你這個淘氣包氣得跺腳。詩意的語言創造一個美妙的世界,提醒我們,忙碌時別忘記生活中還有迷人的詩意。
我們來看看兒童詩中的野孩子。紅太陽怎么能說成果醬呢?這太不符合生活常識了,“星星”怎么會碎落在地上?這是我們內心深處的野孩子發出的聲音,更是想象力賦予了這些事物不同的“意義”。詩人為紅太陽建立了一個“果醬”的意義,為“星星”建立起一個“會碎”的設想。這個意義不一定是功利的、理性的,卻能引領孩子大開腦洞,發揮想象力。
再比如,火僅僅是火嗎?不是的,這些日常符號化的事物可以幻化。“火”在詩人眼中也許可以變成山羊的“一道美味午餐”。對于孩子們來說,講了多少遍的讀書重要性,遠遠不及引導孩子吃棒棒糖時,從吃的層面上領略這種吃食的美感,或者是把一次出游的機會,想象成放逐自由更具有特殊意義。
放下理性評判,進入詩人的內心世界。這些在現實生活里荒誕不經的想象,恰恰能開啟兒童詩的啟蒙。
讀懂一首詩,最重要的是要讀懂詩中所蘊含的意境。什么是意境?要了解這個概念,我們首先要明白物象和意象之間的區別。所謂物象,就是不帶任何情感和思想的客觀事物,比如一個村莊、太陽、晚霞、煙霧、樹、烏鴉等。這些都是客觀的存在。我們的內心世界就是一個沒長大的野孩子,也是一個大染缸。你可以想象一下將這些物象“撲通撲通”地丟進去,經過野孩子的揉捏之后會變成什么?大概就變成了“孤村落日殘霞,輕煙老樹寒鴉”之類的句子。詩中的每個詞語都是一個意象,而意象和意象之間搭伙組合在一起,就構成了秋日黃昏冷寂的獨特意境。
讀詩要從野孩子染色后的意象開始。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說:“在一粒沙子中看見一個世界,在一朵野花中看見天堂。”在一個微妙的意象里,也往往蘊藏著詩人波濤洶涌的情感世界。
詩人是野性的,頭腦中的野孩子帶著我們以不同的視角,看見平凡的世界里非凡的詩性,尋找“荒誕”的意義,重新審視我們的世界,打破庸常化單調的生活,豐盈我們的世界。兒童詩就是野孩子的化身,也是諍友,它坦蕩不羈的語言,有時恰恰能驚醒我們失去意義感的噩夢。
回歸童趣,有時候就這么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