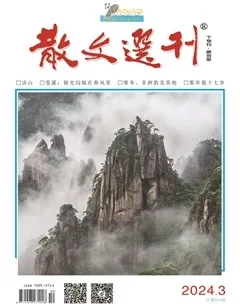寒冬、非洲豹及其他
金暉

和紀同學的相識,是在我剛剛二十歲冒頭的時候。二十歲以前,我活得沒心沒肺,二十歲以后,我開始表現得有點頹廢,對這個世界慢慢有了一些深刻的體驗。當然,很多體驗是不大讓人開心的。
和紀同學相識就是在這個時候,地點是在駕校學習的一輛比亞迪轎車上。
當時坐在車上的一共有四個人,除了教練和我,剩下的兩個里面就有紀同學。他長著一張微微發黃的臉龐,夾克衫,外翻著白襯衣領,有一種被社會打磨過的成熟氣質,這讓我對他莫名地生出些崇拜感。帶我們的教練很牛,滿嘴的陜西話,生氣的時候跟吃了炸藥一樣,逮著人張嘴就罵,這讓我苦不堪言,每次聽他講話的時候,我的腦袋都要比別人多轉上幾圈,才能努力搞清楚他的意思。當時同車的除了我是第一次上車練習的“零基礎”外,其他的都不能算是新手了,有的還是“二進宮”的“老江湖”了。但教練卻“一視同仁”,第一天的時候,他一看我一個人呆頭呆腦地站在那里,跟生瓜蛋子似的,就揚起手沖我喊道,喂,說你呢!瞅啥瞅,給我過來!我看了他一眼,不確定他是不是在叫我,還沒等我回頭看,就聽見車門發出“嘭”的一聲,他下來了,敞開著破呢子大衣,用手指了指駕駛座說,你,上來溜一圈兒!然后也不等我回話,就徑自向副駕駛座走去,“嘭”的一聲關上了門。我一看這架勢,躲是躲不過去了,心里直打鼓,一邊走一邊搔頭。等坐進去的時候,我問他,怎么啟動?他用力地看我一眼,蹙了下眉頭,頗為不屑道,踩離合!他的陜西腔實在太重了,我的腦子一下轉不過來,我為了討好他,低聲下氣地學著用陜西話說,你說啥?他瞪著眼睛,沒好氣地說,我叫你踩離合!你沒事找事是吧!我的臉一下就紅了,但紅了也不代表我懂了,我的腦袋嗡嗡作響。這個時候坐后面的紀同學就出來打圓場了,他說,教練讓你踩離合呢!我立刻向他投去了感激的目光,我問他哪個是離合?他也搖搖頭。
后來,我誤打誤撞,開始慢慢地在平地上開起來了。整個過程,教練坐在旁邊一言不發,嘴角不時地撇出一絲不易察覺的冷笑。車開出十幾米后,紀同學從包里掏出一包煙,抽出一根遞給教練,幫他點上火,兩人有說有笑。我見氣氛有所緩和,就偷眼看了看教練,痛心疾首地說,教練,我程度低,你不要放棄我。教練的臉色緩和了一點兒,說,我叫你認真學,在我面前可耍不了花槍。我趕緊接過話茬表決心說,一定的,一定的。說話的時候,前面突然出現了一個彎道,教練還在扭頭和紀同學說笑,我焦急地說,教練,接下來怎么辦?教練回過頭來說,大四大四(打死打死)!我一下愣在那里。眼看著就要沖上綠化帶了,我心急如焚,我扭頭問他什么大四?教練的眼睛一下就瞪圓了,但他來不及回答我,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他一把推開我的手,然后急打了一把方向盤,猛踹一腳剎車,車輪在馬路上摩擦了幾下,屁股離地幾厘米,緊接著發出一連串呲呲呲的沉悶聲,車窗前冒起了幾縷青煙。后面的人嚇得不輕,我更是面如土色。教練氣得手都發抖了說,我叫你打死你咋不聽哩?我哭喪著臉說,教練,我聽不懂。說完,我又沒頭沒腦地補充了一句,再說我今年也沒大四,我才大三啊。但我剛說完就后悔了,我就是再愚蠢也知道他說的不會是這個意思,但我說出口的好像不是這個意思,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有一肚子的委屈和不快,憑什么都是我的錯?果然,我一說完,教練就陡然變色,紀同學也感覺出了空氣中的異樣,他趕緊推了推我說,你沒聽清楚,教練是讓你打死,把方向盤打死!我做夢也想不到這句話居然是這么個意思,我的喉頭嚅動了幾次,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通常這種時候,我都會讓自己笑一下,但我知道自己此刻的笑肯定比哭還難看。教練終于發飆了,他的話像是瞄了很久的子彈一樣狠狠地射過來,你他×玩我是不是?我低聲囁嚅著說,教練,我再也不敢了,我下次一定注意。教練聽了,鼻子里哼了一聲,大聲地罵了一句,我×,你×還牛×了,沒下次了,滾!這次我聽懂了,我一秒鐘也沒有遲疑,我怕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趁他再次發飆前,趕緊打開車門溜了出來。
后來那天早上,我一直坐在路邊的板凳上,看著他們三個人在那輛車里倒騰來倒騰去,心里別提有多別扭了。我注意到,整個過程中,里面始終充滿了歡聲笑語,不時地隨風飄過來。有那么一個瞬間,我順著車窗看過去,和教練的臉打了個照面,我立刻讓自己換上一張笑吟吟的臉朝他頻頻點頭示意,但遺憾的是,他一個轉頭,看都不往這邊看一眼。我頓時受到了打擊,只覺得羞愧難當,血往腦門上涌。我陷入了艱難的思想斗爭,我在心里反復地問自己,到底要不要和他打?但打了又怎么樣,能挽回我的損失嗎?這樣想過之后,我在心里對自己說,行了吧暉哥,狗咬人一口,人也要咬狗一口嗎?
好不容易熬到了中午,我和其他學員們一起去食堂吃飯,一人一碗油潑辣子,加點蒜,伴著辣醬吃。吃完后,我一個人出來透氣,看到紀同學正仰著一張微黃的臉,對著天空抽煙,吐出來的煙霧在風中全碎了。看到我過來了,他像一個長者一樣微笑著拍拍我的肩說,沒事的,多買幾包香煙就行了。我說,能就這么簡單?他掏出一根煙在指甲上頓了頓,慢慢抽了兩口,說,你看我哪次不是來這里陪他說說笑笑?沒事的,到時候考試他坐旁邊的,大不了考出來再自己買輛車去馬路上練練。說完,又露出那種洞察世事般成熟的笑,湊近我耳朵悄悄地說,跟你講哦,我馬上要寫畢業論文了,到時候可能來不了幾次了,但煙還會照樣供上,到時候來走個過場就行……
我意外地獲得了學車的妙計是在冬季一個極為寒冷的天氣里,馬路上落葉紛飛,并且已經開始出現雨雪交加的天氣了。由于每個周末都要去學車,我每個周五晚上都要去一趟學校西門外的煙酒店,我一般只買那種35 元的芙蓉王(買貴的教練總懷疑是假的)。煙酒店的老板都認識我了,每次見到我,他都和藹地笑笑,并且親切地向我推薦其他幾種香煙,有時候還抽出幾根遞給我抽。看來這是一個有心人。朋友們,做一個有心人是多么令人感動啊。
慢慢地我發現,擁有了這種新的交流方式后,我逐漸有了一種不可名狀的心理安全感了。每次從我的手上接過香煙的時候,教練的臉都很燦爛,笑容如同悉尼歌劇院一樣層層綻放。當然,他開心了,我就會更開心,某種程度上,他對我的重要性和女朋友是一樣的,我們一榮俱榮。在這種情緒的鼓舞下,我開始喜歡上開車了。在練車場上,我聽著教練耐心的講解,進步飛速,一招一式都有出處,有幾次我還偷偷看到了一些女學員眼神里的向往。我看了都特別激動。這樣一段時間下來,我開始對自己有信心了。我不再是一個學車的門外漢了。
那是一個令人手腳凍僵的天氣,來自西伯利亞的風聲像刀子一樣切割著這個城市,高懸的太陽像是被藥水浸泡過一樣,流露出蒼白的光輝。我們站在駕校前面的空地上,等著交警陸續點名考試。寒風肆無忌憚地灌進我的脖子,我開始瑟瑟發抖,后脊背一陣陣發涼。就在這漫長的等待中,終于聽到了我的名字。這是這座西北著名的省會城市駕駛員考試新規出臺后的第一輪考試,明確規定考試期間一切教練不得隨同,學員必須在車載監控的監視下,獨立完成科目的測試。考試開始前,我朝路邊的教練點頭示意,然后一貓腰鉆進了車里,系好安全帶,踩下離合器,松開手剎,緩緩啟動,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幾個關卡之后,我按時返回,從教練頻頻的點頭里,我預知了自己即將成為一名真正的駕駛員的信息,我牛×地笑了。
后來的事情大概是發生在十分鐘之后。紀同學匆匆忙忙地趕來,只見他剛坐進車,就從兜里掏出幾包煙往教練的懷里塞,教練那張驚慌的臉上瞬間呈現出一種殷紅的血色,他一把抓過香煙,用力扔出了窗口,對著攝像頭大聲地說,你這是啥意思,你想腐蝕我?聲音大得讓我都為之臉紅。我們都看得呆了。由于他們的動靜太突兀,后來警察過去了,我不禁為紀同學倒吸了一口涼氣。紀同學的額頭上也瞬間冒出了一層冷汗,他看上去有點茫然,也不知道是真的茫然還是假的茫然,反正看上去很像是真的。后來,紀同學默默地從地上拿起了香煙,在交警的注視下啟動了汽車。
在他坐進駕駛座的那一瞬間,我和他的目光猝然相遇,但我們誰也沒吱聲。陽光透過車窗的縫隙,將條紋狀的陰影投在他身上,使坐在車廂里手忙腳亂的他看起來像一只受驚的非洲豹。
我默默地離開了。
那時候,我們都很年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