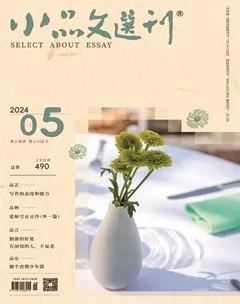李白的追求
王豬豬
最近李白突然火了,因為一部動畫片。
說李白之前,先講個笑話。我國東南某省改教材,把“祖國偉大詩人李白”一字之改,改成“中國偉大詩人李白”。其他的改“祖”為“中”的騷操作還有將祖國歷史、祖國地理、祖國古代文學統統變成為中國歷史、中國地理、中國古代文學。
可笑,不是你的國,你學他干嘛?
如果可以,這個省想跟祖國做全部的切割,只可惜辦不到。如果真的都切割了,他們的下一代就只能當文盲了。
再講個故事。伊朗有位古代詩人叫哈菲茲,生活年代相當于中國元朝。他的詩歌家喻戶曉老少會背,去伊朗旅游,哈菲茲陵園是必到之地。伊朗向導說,哈菲茲在我國,就像李白在你國。
聞聽此言,我頓時眼睛一亮:你們也知道我國偉大詩人哎!擊掌,敬伊朗的李白,敬中國的哈菲茲!
愛祖國有一千條一萬條理由,李白,一定是其中特別光彩奪目的那一條。
我國偉大詩人李白,這是歷史對他最高最深最貼切的評價。然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終其一生,發自肺腑,他都不愿做詩人。
詩詞曲賦,不過是點綴業余生活的小情趣小愛好,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終極夢想比起來,算得了什么?
就像,能夠寫大塊頭大文章,能夠作深度調查報道,能夠鐵肩擔道義,能夠補天之缺、解民之苦、推動社會公平公正進步,誰愿意去插科打諢、搞笑自嘲、編編吃喝玩樂、謅謅風花雪月、當所謂的“美食作家”?
李白自比管樂(管仲、樂毅)之才,目標是晏子、諸葛亮,這里頭,個個都是古代的大政治家,上報朝堂,下安黎民,千秋萬代,青史留名,將個人才華與時代需要結合到了極致。
有些人嘲笑李白是個官迷,有官癮。格局小了,小了!你們眼中的官,是吃香喝辣、作威作福、名利雙收、光耀門楣……如果真的是為了這些,那么李白,他其實早已經擁有了!
要知道他可是皇帝身邊的大紅人,他可是享受宰相脫靴、大內總管磨墨、皇帝親喂醒酒湯、貴妃表演歌舞的第一人!誰有這樣的待遇?誰有了這樣的待遇又不是感激涕零,從而沉湎享受其中?
可惜,他是李白,他是一千年就出一個的李白。
有些人嘲笑李白政治幼稚,說就算給他官做也做不好,不如安心當一個“詩人”。問題是,一個安心當“詩人”的李白,一個滿足于寫“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李白,還能是李白嗎?再說了,他這一輩子一次機會都不曾有過,你怎么就斷定他做得好做不好?連李林甫楊國忠之流都能成為宰相,李白做一地方父母官怎么就不行了?
古人文盲率99%,剩下的1%再除去性別為女,基本上能讀書識字的就能做官,無非官大官小。唐宋八大家,哪個不是官?哪個沒被貶過?又有哪個政治上很成熟了?
可惜,他是李白,他是一輩子都不能如愿的李白。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后人常將李杜并列。他們是同時代的人,也是好朋友,李白比杜甫年長十一歲。
李白的追求也是杜甫的追求,李白的遭遇也是杜甫的遭遇。只不過從生活條件來說,杜甫可能更慘一些。李白有五花馬千金裘,杜甫只有為秋風所破的茅屋。
成都有條河叫清水河,河邊有兩個著名的旅游景點,可以說凡是來成都的必去。一個是武侯祠,一個是少陵草堂,分別紀念的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和詩人。
我先去的是草堂,后去的是祠堂,草堂環境清雅,祠堂古意盎然,玩的時候很盡興,玩完了總覺得兩者之間似乎有著某種聯系,但又說不出來。是什么呢?
想啊想,回程路上突然一個念頭蹦了出來:三顧茅廬,知遇之恩,前者是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茅屋秋風,老病孤舟,后者是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現實寫照。
一個是李白的偶像,李白想成為的人,一個是李白的朋友,跟李白同病相憐的人。他們兩者,武侯祠和浣花溪,步行相距三公里。
最近魔都有兩個大展,都跟梵高有關,一個售票119元,一個售票120元,周邊產品也賣得很熱火。想想也真夠諷刺,梵高生前窮困潦倒只賣出了一幅畫,死后卻能養活一個產業。
多么像他們二人,死后什么都好,就是生前啥都沒有。
李白特別喜歡一種名叫大鵬的鳥。這種鳥名氣很大,自古很多人都聽過它的傳說,雖沒見過。
最早有記載的是《莊子·逍遙游》:“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
李白年輕的時候寫《大鵬賦》,“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后來寫《上李邕》,“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去了天臺山寫《天臺曉望》,“云垂大鵬翻,波動巨鰲沒”……
有個典故叫“孔子嘆鳳”,李白很喜歡用,他年輕時寫過“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但是現在,只有孔子是唯一能為大鵬鳥哭的人,卻也不在了。
故事中,李白一邊喝酒一邊吟著這輩子的最后一首詩,跌跌撞撞地走到了長江邊。但見明月皎皎,江水浩浩,天上一個月亮,水中一個月亮,上下交映,潔白生輝,一個純凈無比的世界。他看呆了,伸出手想去捉水里的那個月亮,跌了下去。
江水掀起激烈涌動,夜已深了,周圍沒有人察覺,浪花越來越小,越來越小,終于一切復歸平靜,就像什么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又過了不知許久,天快亮了,就在太陽升起的剎那間,忽見水面翻飛,云氣蒸騰,漫天彩霞間,一頭長鯨破水而出,再一眨眼,已然飛入九天。鯨背上站立一少年,身負長劍,手持玉笛,臨風而立,顧盼生輝,一如四十年前他第一次離開家鄉,乘船從群山萬壑的巴山蜀水直下廣袤江漢大地那般:長風破浪,直濟滄海。
選自“豬眼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