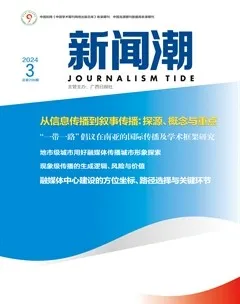“今日頭條”平臺少數民族賬號主體使用行為探究
金強 戴文君
【摘 要】本研究主要探討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視域下,“今日頭條”平臺少數民族賬號主體的使用特征與行為、存在的問題并給出可行性建議。分析認為不同少數民族在“今日頭條”上的賬號數量差異較大,回族、彝族、苗族、藏族、佤族賬號主體的數量相對較多。認證領域中以“三農”、音樂、vlog為最多。超九成賬號主體為個人賬號,獲機構認證標識的賬號較少。賬號主體發布主題以自然地理風光描繪、傳統風俗文化介紹、當地生活現狀紀實及個人特長經歷展示為主。客觀條件阻礙創作內容傳播,挖掘本民族文化深刻內涵不夠深入,需要進行有針對性的鼓勵與引導,以增強文化傳播效果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關鍵詞】少數民族;社交媒體;今日頭條;中華民族共同體
“頭條號”是“今日頭條”旗下開放的內容創作與分發平臺,實現政府部門、媒體、企業、個人等內容創作者與用戶之間的智能連接,實現信息內容的互動共享。據統計,“今日頭條”平臺平均每天發布150萬條內容。“今日頭條”也是一個通用信息平臺,可以在電腦網頁或者是手機客戶端使用,目前擁有推薦引擎、搜索引擎、關注訂閱和內容運營等多種分發方式,主要囊括圖文、視頻、問答、微頭條、專欄、新聞、小說、直播、音頻和小程序等多種內容體裁,并涵蓋科技、體育、健康、美食、教育、“三農”、國風等超過100個內容領域。本研究的少數民族賬號主體是指”今日頭條“平臺上以少數民族名稱運行的,且長期發布少數民族文化習俗內容的頭條號內容創作者。
一、“今日頭條”平臺少數民族賬號主體的使用現狀
(一)不同民族賬號主體的數量差異較大
各民族賬號主體在“今日頭條”的使用數量差異較為明顯,賬號主體數量可做如下層級劃分:第一層級為1000人及以上,第二層級為500~1000人,第三層級為100~500人,第四層級為100人及以下。55個少數民族中,第一層級的賬號主體有5個民族,分別是回族、彝族、苗族、藏族、佤族;第二層級的賬號主體共8個少數民族,分別是瑤族、傣族、滿族、壯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和白族;第三層級共有9個少數民族,分別是朝鮮族、羌族、畬族、蒙古族、哈尼族、黎族、傈僳族、水族和維吾爾族;第四層級共有33個少數民族,其中人數最少的少數民族賬號主體為門巴族。
“今日頭條”平臺少數民族賬號主體數量前十名為回族、彝族、苗族、藏族、佤族、瑤族、傣族、滿族、壯族和布依族,這10個民族的賬號主體占總數的80%。其中,回族賬號主體占據總量的38%,共8910人,彝族賬號主體人數為1875人,占比8%。少數民族賬號主體的數量整體基數較小,且分布不均,各民族之間的賬號主體數量差距較大。
除回族和彝族外,其余數量前十的少數民族賬號主體數量由多到少不斷遞減,且差值不大,呈現緩慢逐級遞減態勢。
(二)賬號主體及發布內容呈現出多樣性和豐富性
少數民族賬號主體未認證賬號比例大,內容領域相對集中。在社交媒體平臺發布內容和運營賬號時,大部分少數民族賬號主體還是處于未認證內容領域的狀態,其中,“三農”領域成了相對熱門的領域,其次是音樂和生活領域及時尚和體育領域。
“三農”領域賬號中,大部分賬號主要發布農業、種植業及農村生活相關內容,該類內容聚焦于當地農村發展及先進農業技術,包括一些助農產品的帶貨和推廣等。同時,由于民族聚居區多在遠郊地區或農村地區,少數民族賬號主體在“三農”領域的傳播內容相對較多。例如,賬號“瑤族小伍”是平臺認證的優質“三農”領域創作者,該賬號共有2.1萬粉絲,內容獲8.6萬個贊,IP屬地為湖南。該賬號以發布圖文或視頻內容來介紹湖南以及湖南當地的農產品,包括竹筍、冰草、杉樹菌菇等,內容包括食材的采集以及制作的全過程,同時開通了農貨店鋪的鏈接。
音樂領域賬號中,發布內容的方向主要集中于穿著少數民族標志性服飾的歌舞表演,該類內容注重個人風采結合民族特色的展示,休閑娛樂的互動性較強。例如,賬號“阿幼朵苗族”是平臺認證的歌手,IP屬地為貴州,其代表作主要有《苗嶺飛歌》《醉苗鄉》等。作為一名少數民族特色鮮明的歌唱表演者,其在“今日頭條”平臺上除發布個人歌唱視頻外,還會不定時發布一些新年祝福寄語視頻、旅游推薦視頻以及個人感悟和思考等,這些內容都與發布者自身的少數民族特色結合緊密,內容垂直度較高。
少數民族vlog創作者主要通過個人經歷分享來達到宣傳家鄉風光和文化的目的。例如,賬號“白瑪卓瑪”為優質vlog領域創作者,平臺粉絲為34萬,內容獲146萬個贊,IP屬地為四川。該賬號內容主要是川藏地區的獨特風景、城鄉生活的感知感受和思考,以及對于一些交通道路基礎設施(如鐵路)的宣傳和推廣、當地野生動植物的介紹、藏族特色的歌舞表演、特色服飾搭配短視頻軟件的特效變裝等,內容涉及范圍較廣,視頻時長一般為5~7分鐘,視頻開頭的問好均以漢藏雙語錄制,固定粉絲有相當一部分是當地藏族居民,視頻內容翔實豐富,融合部分四川和西藏地區的文化歷史背景和地理知識,且畫面多以當地實拍風景為主,優美雋秀,獲得大量網友的點贊。
“今日頭條”平臺少數民族賬號主體超過九成的頭條號類型都是個人賬號,不到一成賬號為機構賬號。個人賬號中也存在不同方向的平臺認證。例如,賬號“滿族旗袍傳承人陳玉秋”,作者是官方認證的吉林省非遺滿族旗袍傳統工藝項目代表傳承人;賬號“布依族作家戰贏”,作者是貴州省作家協會會員;賬號“湘西土家民族醫”,作者則是龍山縣石羔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內科主治醫師等。
(三)部分發布內容同時體現差異性和共同性
除了部分個人賬號的認證是歸屬于常規的內容偏好領域(如“三農”、音樂、vlog、文化、生活、體育、時尚等),還有部分認證是屬于賬號主體的職業,或是少數民族專業技能、習俗興趣領域的認證。
如賬號“苗族武功傳播”,其置頂視頻發布于2020年1月8日,內容為一段貴州省松桃苗族自治縣苗族棍術的教學和展示,該視頻總播放量超過1萬次,獲贊161次,評論60條,很吸引眼球。又如賬號“苗族剪紙姜文英”,其認證信息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苗族剪紙代表性傳承人。該賬號的發布內容均為苗族剪紙領域的相關信息,內容垂直度較高,具體包括苗族剪紙和苗族刺繡的關系和意義、苗族剪紙的教學,以及苗族剪紙圖案圖騰的來歷和神話傳說等,制作出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來使用。此外,還有賬號展示自己族群的優秀傳統特色文化及一些技能操作等。
少數民族賬號主體的內容主題主要集中在自然風光、傳統風俗、生活紀實以及個人特長等方面。其中自然風光和生活紀實方面更多體現的是共同性,而在傳統風俗和個人特長方面則更多體現差異性或獨特性。
二、“今日頭條”平臺少數民族賬號主體使用中存在的問題
(一)客觀使用條件阻礙高水平內容創作和傳播
“少數民族對自身位置與周邊關系形成良性關聯認知,對族群特性掌握表現出強烈族群依賴性。”[1]對于中西部農村地區尤其是民族地區而言,青年群體的流失常導致農村的網絡通信產業發展減緩。同時,這也導致老年人對于網絡等新興行業的輔助認知和環境培養機遇喪失,對網絡的學習能力和接受能力不斷下降。一方面,在老年人接觸網絡的初期,青年人一般會承擔“向導”角色,在農村這樣的輔助認知機會則相對不足。另一方面,青年人對網絡的依賴相比老年人更加強烈,這樣的需求也會促使社會環境的更新和迭代,例如,網約車、外賣、跑腿、金融服務等行業,更多是依靠青年人的需求催生出來的,但是在農村由于青年人數量較少,區域需求量不大,會導致這樣的“互聯網+生活”語境難以落地實現。
對于民族地區的農村地區來說,老年人更習慣使用民族語言或方言,與互聯網的語言環境匹配度不高,很難獲得高質量內容,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西部農村地區尤其是民族聚居區的網絡通信產業的普及和發展,從而阻礙了少數民族賬號主體中老年用戶的內容創作和網絡傳播。
(二)挖掘本民族文化深刻內涵不夠深入
少數民族群體雖然正在逐漸形成自己的文化輸出平臺和交流機制,但是更多的是集中于片面的、淺層化的、可視化的少數民族習俗、節日等領域。歌舞表演和自然環境的展示是熱度較高的兩個內容創作方向,此類內容相較于族群的整體文化底蘊和內涵來說還相對較淺。“少數民族形象呈現與傳播結構具有多樣性、復雜性、自發性等特點。而民族形象構建與民族關系管理是密切聯系的。在互聯網時代,各民族之間文化交流日益復雜,使得族群屬性模糊不清,同時區域認同則會消解‘一族一貌觀念。”[2]互聯網社交媒體平臺關于少數民族文化內容的輸出缺乏更加系統化的、深入的內容講解和介紹。
“少數民族群體以社交媒體為中介得到凝聚,這種緊密聯系不僅促進了民族成員之間的聯系,更提升了少數民族群體的民族身份認同感。”[3]社交媒體上的受眾更加追求簡單舒適放松的閱讀觀看體驗,并且更加喜歡一些新穎的內容推薦,如果只是把一些關于少數民族的歷史知識和人文變遷通過機械地堆疊和錄制來展現,很難在短時間內吸引受眾的關注。“大眾由此形成對少數民族的刻板印象,使其對少數民族及其文化表現出消極的接觸欲望,加深了少數民族對外傳播民族文化的難度,使大眾對少數民族的刻板印象呈現出愈發嚴重的態勢。”[4]少數民族賬號主體自發的民族文化宣傳和推廣行為,有益于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景觀呈現,然而社交媒體平臺對于相應的文化深度解析和傳播行為缺乏相應的鼓勵機制和獎勵措施,對于積極傳播少數民族特色文化的內容創作者缺乏積極的反饋,或者是反饋強度偏弱以及反饋缺乏針對性。
(三)缺乏對平臺的深層認識及相關組織機構的引導
首先,功能定位不夠準確,主要分為使用平臺功能定位不準確及賬號主體的自身功能定位不準確兩個方面。一些少數民族賬號主體在運營過程中并沒有充分了解平臺的特點,進行的基本上是無差別內容投放,這樣的傳播策略和模式會使得內容的傳播效果大打折扣。
其次,賬號主體對自身角色的功能定位不準確。如“今日頭條”的平臺定位是偏向新聞性的集合搜索平臺,頁面排版更喜歡單列的圖文形式以及圖文內部穿插視頻的形式,更偏向于利用算法推薦進行內容的精準匹配定位以及傳播內容的時效性和互動性。一些政府機構認證的頭條號與受眾的互動需要加強,特別是當出現輿情時,官方機構應積極地引導輿論,掌握事件的話語權和輿論風向。
最后,缺乏專業運營團隊。“今日頭條”平臺上,民族地區的政府機關社交媒體賬號運營主要是依靠圖片和文字來實現信息傳播,對于音頻視頻的傳播形式嘗試較少。這主要是由于音視頻的編輯加工和制作存在一定的技術門檻,而大部分政府機構內部的新媒體人才相對缺乏,且大部分都是非專業人員在負責政務社交媒體賬號的運營和管理,存在一定的專業技術缺失和專業人才流失問題。
三、提升“今日頭條”平臺少數民族賬號主體使用水平的建議
(一)引導賬號進行內容建設和選題策劃
要提升少數民族賬號主體對少數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的傳播主動性,地方政府應當積極運用文化互聯網領域的宏觀調控手段,積極做好互聯網社交平臺的方向引導和創作激勵,提供相應的政策扶持,激發少數民族賬號主體的創作熱情。
地方文化管理部門以及商務部門應針對當地的頭部少數民族賬號主體的特征,協調組織加強聯絡并促使其積極聯合起來。應加快組建少數民族本土化、特色化mcn(多頻道網絡)團隊,充分進行文化資源信息的整合和調配,充分發揮特色文化的輸出和創新優勢,改變當前創作者單打獨斗、內容重合度高等局面,加快建成當地特色民族文化產業集聚式發展的新興業態。民族地區特色文化內容傳播少不了大眾主流文化的環境支持,受眾面較廣的非民族地區互聯網社交媒體平臺,應該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接納和支持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播和融合,主動提供相應的內容傳播機會,給予相應的曝光流量傾斜。應積極進行相應的宣傳推廣,使少數民族文化和主流大眾文化充分交流融合。
(二)提升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媒介傳播力
民族地區大部分存在地域相對偏遠、經濟發展水平欠發達等問題,或者是與周邊城市地區的交流存在一定的交通障礙或文化壁壘,導致其本身信息交流可能存在一定閉塞滯后的情況,“少數民族對其族群網絡文化的自持能力和傳播建構,也對其媒介形象樹立和文化演進產生重要影響”[5]。應鼓勵頭部賬號主體在賦能學習的過程中,向下對其他有條件、有興趣、有能力的賬號主體或互聯網社交平臺的使用者進行適當的推廣,對有互聯網內容生產制作的少數民族受眾群體,提供一定程度的賦能教育和技術支持,進行技能教學的傳輸和引導,使有傳播需求、有創造愛好的少數民族群體在互聯網新媒體社交平臺上得以充分展現,從而推動少數民族優秀特色文化的傳播和發展。“科技發展帶來了交流對話的平臺,少數民族族群本身所重視的起源、血緣、地緣、記憶、文化和語言等,才能憑借這些重要元素來建構族群想象、界定我群的核心元素、劃定群體的邊界、鞏固族群認同。”[6]少數民族特色文化在優質頭條號內容創作者的帶領下逐步突破技術壁壘,成為民族文化傳播的新生力軍。
(三)重視并做好少數民族領域相關專門組織的引導作用
首先,政府相關部門應做好民族地區互聯網社交平臺的使用引導和創作激勵。民族地區可以充分發揮自身自然條件優勢,政府出臺相應政策鼓勵群眾使用互聯網社交平臺來進行宣傳和介紹,形成傳播矩陣,可以制定相關激勵政策,按照社交平臺作品的點贊數、轉發數、觀看數等來量化少數民族賬號主體的社交媒體宣傳行為,以此為依據進行獎勵。激勵政策需要盡量貼近實際、貼近群眾,盡量下沉到一線,到縣級單位,落實到人,才能發揮其最大效益和優勢。
其次,政府相關部門應加強當地少數民族優秀特色文化環境的營造和培育,提高當地少數民族群眾的文化傳承和文化創新能力。應建立健全優秀少數民族文化體系,開設特色文化課程,加強對優秀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播力和影響力的研討。鼓勵當地的少數民族賬號主體樂于傳播、善于傳播,并從傳播中受益。應適當開發當地民族特色節日呈現方式,巧妙利用當地民族博物館,展示相應的民族傳統文化和可考證的相關史實。可在當地學校開設相應的鄉土特色課程,加強優秀少數民族文化的宣傳教育力度,增強當地少數民族群眾的文化歸屬感,使少數民族賬號主體更加清晰明確地感受到自身對民族優秀文化的傳播責任和義務。
最后,政府相關部門應積極鼓勵本地具有民族特色的互聯網文化企業“走出去”,并不斷把外地的優秀文化企業“引進來”,實現內容和技術的強強聯合。可以利用互聯網的互通性,積極組織座談會、答疑會,進行互聯網傳播模式的精準輔導和選題引領。可先在企業間進行文化傳播策略的教學和研究,再細化到對頭部少數民族賬號主體進行有針對性的教學和訓練。可進行系統的社交媒體平臺使用規則的傳播賦能,包括拍攝設備的選擇和使用、腳本撰寫和串聯、視頻音頻的剪輯加工等,促進民族地區的互聯網文化發展。
四、結語
社交媒體平臺的崛起和發展,為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播帶來了新的機遇,提供了新的傳播渠道和可能,打破了民族地區間的文化傳播壁壘,大大增強了少數民族特色文化的可能性,并增強了民族文化傳播效果,加速推進了我國各民族之間的文化認同、心理認同和國家認同,促進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有益實踐,對于實現各民族繁榮發展和國家富強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2]安軍地.新媒體時代少數民族文化形象構建與傳播研究[J].國際公關,2023(8):151-153.
[3]張媛,程颯.從聯結走向聚合:社交媒體中介下的少數民族身份認同實踐[J].中國新聞傳播研究,2021(2):171-186.
[4]郭蓉.從“丁真事件”看社交媒體環境下的少數民族形象建構[J].西部廣播電視,2021,42(15):16-18.
[5]金強,熊艷.新媒體背景下少數民族文化的形象建構與傳播研究[J].廣西民族研究,2021(3):141-147.
[6]張媛.社交媒體時代的少數民族網絡社群建構[J].未來傳播,2019,26(6):87-93,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