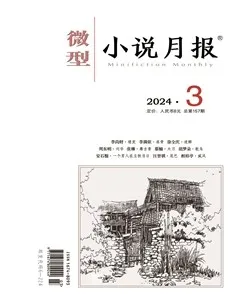淪波舟
2024-05-06 11:02:51周明全
微型小說月報 2024年3期
周明全

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其國人長十丈,編鳥獸之毛以蔽形。始皇與之語,及天地初開之時,了如親睹。曰:“臣少時躡虛卻行,日游萬里。及其老朽也,坐見天地之外事。臣國在威池日沒之所九萬里,以萬歲為一日。俗多陰霧,遇其晴日,則天豁然云裂,耿若江漢。則有玄龍黑鳳,翻翔而下。及夜,燃石以繼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皆自光澈,扣之則碎,狀如粟,一粒輝映一堂。昔炎帝始變生食,用此火也。國人今獻此石。或有投其石于溪洞中,則沸沫流于數(shù)十里,名其水為焦淵。臣國去軒轅之丘十萬里,少典之子采首山之銅,鑄為大鼎。臣先望其國有金火氣動,奔而往視之,三鼎已成。又見州有異氣,應有圣人生,果有慶都生堯。又見赤云入酆鎬,走而往視,果有丹雀瑞昌之符。”始皇曰:“此神人也。”彌信仙術焉。
晉人王嘉身為道士,作《拾遺記》意為弘揚道教,然《拾遺記》卻并未受其功利目的影響,“頗重藻思文心,文字縟麗,鋪彩錯金”(李劍國評)。這或許可以為今天的寫作者提供借鑒意義--寫作即便有功利的指向,但文學性應該高于目的性。文學必須是對生活的嚴肅審慎的思考,同時又能飄逸輕盈地抽身于現(xiàn)實之外,而不是對生活自然主義的再現(xiàn)。《淪波舟》寫的是宛渠國的風俗,但想象力豐沛,實乃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