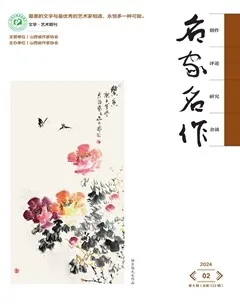論《局外人》的荒誕感與真實性
[摘要] 從俄國形式主義理論中的陌生化角度出發,分析加繆小說《局外人》中“現實社會的荒誕感”和“人物形象在荒誕外殼下的真實感”。其中“現實社會的荒誕感”分別從語言的陌生化、形式的陌生化和關系的陌生化三部分進行分析;“荒誕外殼中人物的真實性”部分論述主人公默爾索在現實困境下呈現的陌生化人物形象的真實意義。
[關? 鍵? 詞] 《局外人》;加繆;陌生化;荒誕感;真實性
一、淺論俄國形式主義陌生化理論
陌生化理論是什克洛夫斯基首創的,最初作為詩學的概念和雅克布遜提出的“文學性”共同成為俄國形式主義學派的兩個核心范疇,在俄國形式主義內部產生了廣泛影響。什克洛夫斯基強調文藝不是對外部生活的模仿和反映,而是有其自身的本質和內部規律。文學理論不應只研究文學的外部關系,而應重點研究文學作品本身及文學的內部規律。
陌生化手法打破常見的表現形式,呈現生活之為生活的本真狀態,喚起讀者最真實的審美感受。在藝術中,為了引人注意而“人為地”創作成這樣,使得讀者接受過程受到阻礙,達到盡可能緊張的程度和持續很長時間,拓寬讀者的審美視野;同時作品為了更好地恢復對生活的感受,不間斷地被接受、觀察、感受,通過揭露和重建矛盾,在本無區別的素材中重建區別。對陌生化的研究不僅限于詩歌語言和日常語言的差異,還旨在建立一種能夠概括文學一般規律的理論體系,將陌生化理論延伸到敘事領域中去,即敘事手法陌生化問題,這是用技巧或者手法取消語言及文本經驗的“先行性”,創造出“復雜化”和“難化”的過程,進而割裂傳統經驗給予閱讀主體的審美期待,促使閱讀主體以全新的視角去審視文本的內涵。
二、陌生化手法下現實社會的荒誕感
(一)語言的陌生化——短句的使用以及缺乏常規邏輯
文學是一門語言藝術,任何作家在創作的時候都在處理各種語言問題。作家在借助語言同讀者交流時又深刻地感受到語言帶來的束縛,正如詹姆遜所說的“語言的牢籠”。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篇中指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也。”是古代文論對作家語言困境的最好詮釋。作家處于這種“語言的牢籠”之中,必須有意識地突破語言的便捷,以表達自己的獨特感受,他們要做的是“用語言挑戰語言”,這意味著作家要不斷嘗試用陌生化語言來突破日常語言的邊界,進入一個嶄新的審美境界。
什克洛夫斯基指出,藝術語言是實現陌生化過程的重要保證與條件,藝術陌生化的前提是語言陌生化。更有學者認為,真正的文學語言就是陌生化的語言。陌生化理論在語言上的運用就是要通過語言使情節陌生化,并創造與眾不同的手法使作品的呈現更具吸引力,使讀者產生阻滯感。正如該范疇的理論內涵所呈現的特質——創造性。
《局外人》這部小說中語言的運用包括大量短句的使用、句法缺乏邏輯性以及語言的反復性等。小說基本上沒有出現過長難句和復雜的語法結構,而是經常有這樣一些短句“這與我無關”“我無所謂”“怎么都可以”。這樣短小精悍的句子,在文中占據重要地位,理解也沒有難度,可是當它們在文中反復出現且并不合時宜時,就會使讀者不得不注意它們在小說里獨特的意味,讓讀者在閱讀的同時不得不對語言本身加以懷疑,力圖層層揭開語言背后的真相。從陌生到理解,又從理解到困惑,收獲了不一樣的“新”的體驗,這無疑是加繆將陌生化應用在語言上的成功之處。
小說中語言缺乏邏輯性也是陌生化手法運用的表現。故事的敘述具有較大隨意性,故事情節似乎是隨手拈來,句子順序毫無邏輯性可言,進而導致情節缺乏邏輯性。因此“要想讓故事給讀者以荒誕的感覺,達到陌生化的審美效果,打破傳統的敘事邏輯性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敘事一旦失去了邏輯性,就會帶領讀者領會到荒誕性,進入不曾預料的世界,這是對傳統敘事結構的有力背叛。加繆刻意打破了小說語言的邏輯性和連貫性,讓敘事不以時間的先后順序展開,也沒有圍繞一個中心點有條理地來敘述,情節的發展僅僅是隨著主人公的思緒游走。
(二)形式的陌生化——荒誕與虛無
形式主義原本指的是一種只看事物的表象而對其本質的思想方法或者工作作風不加分析。在《局外人》這部小說中,形式的荒誕性與虛無感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個是母親下葬的形式才能證明母親死亡的事實,二是社會把追求形式作為判罪的關鍵。
社會性死亡才能宣告這個人真正的死亡。小說的第一部第一章在敘述母親葬禮的情節中向讀者傳達了一個明確的信息:要等到母親葬禮結束母親死亡這件事情才算確實發生。在母親葬禮準備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一絲不茍而煩瑣的程序、形式,形式的重要性甚至壓倒了事實的確切性,這種觀念的桎梏顯示了其形式的荒誕性。
真正的默爾索在小說中是其他人物難以理解的、無法言說的,是社會公理規訓所不能理解和容忍的。社會規訓和默爾索之間存在著深深的隔膜,前者作為社會公理的代表竭力以生命形式的存在以及表現為關鍵:默爾索在母親的葬禮上到底有沒有哭?默爾索在母親的停尸房有沒有喝咖啡、抽煙?葬禮之后默爾索有沒有和他的女朋友瑪麗游泳、看喜劇電影和做愛?后者把追求生命個體的真實性和存在性作為真諦,默爾索希望律師理解他對誠實原則的遵守,對個人邏輯和存在方式的理解,他希望得到的是自然而然、通情達理的辯護。但社會中的其他個體不能容忍作為感性的愛沒有以一種具象的形式出現在社會場面,小說中的其他人物慣性地認為沒有帶上社會規訓外殼的人是應該被驅逐出人類群體。默爾索被判處死刑不僅是因為默爾索開槍殺了人,而是對默爾索不遵守形式的懲罰。
這種形式的荒誕性已經入侵了現實生活的角落,而加繆的偉大之處,就是將這種習以為常的事物以巧妙的陌生化手法表達出來。什克洛夫斯基認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習以為常”會忽視很多美麗的“遇見”。作家的創作需要打破人們欣賞的習慣,打破日常思維表現被遮蔽的真實生活、觀察、感受,呈現生活的“本來面目”,在本無區別的素材中重建區別,進而達到陌生化的效果。
(三)關系的陌生化——個體關系的荒誕感以及關系的轉換
如果把主人公默爾索當作一個圓心,那么可以把他的人際關系輻射為養老院院長、門房、貝萊茲、女朋友瑪麗、默爾索的老板、同事埃馬努埃爾、小混混雷蒙、雷蒙的朋友馬松、鄰居養狗老人薩拉瑪諾、餐館老板塞萊斯特等。小說中主人公默爾索和其他人的交流顯示了現實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是日常生活人際關系的一種真實顯現,但在加繆的筆下卻顯示出一種荒誕感。
小說中的人物盡管相識,可是又好像沒有真正了解彼此,每個人都是彼此的“局外人”。在加繆的筆下,人們不得不相互關心,為了利益或者約定俗成和社會規訓成為朋友或者同盟,愚昧地遵循著這種集體無意識的狀態。小說中人與人之間的“局外感”導致讀者與小說人物之間也對自己的生活產生了“局外感”,而這種隔閡是超越文本獲得現實關照的真實狀態,讓讀者在文本的荒誕感中尋找到現實層面的熟悉感。這是陌生化手法喚醒讀者潛意識接受習慣的表現,由此產生了強烈的藝術魅力和震撼力。
默爾索是一個現代社會的“誤入者”,遵循自己的天然邏輯,從自我的生理經驗出發,表里如一地陳述自我的真實感受。在所謂的“社會規訓”推導中,它們全部被遮蔽掉了,甚至因此成為將默爾索送上斷頭臺的鐵證。他一系列再平常不過的生活感受被觀念、習俗的體系特別挑選出來,并被精心編織成為一個十惡不赦的犯罪神話。這所有的一切,都與被規訓、被社會異化的“其他人物”所區別開。默爾索與他們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他們是彼此的局外人。加繆不僅寫出了其他人物對默爾索的“局外感”,還表達出默爾索不被理解的“局外感”,這種人與人之間無法相互理解的深厚隔膜,是小說關系荒誕性的重要體現。
法庭上關系的顛倒是關系荒誕性的集中體現,審判和法律理性的消解在默爾索遵循的誠實的原則中產生了,默爾索從審判者的中心形象成為“局外人”。當默爾索再次重申母親下葬的場景,誠實地表示沒有對在母親葬禮上流淚時,檢察官想當然地認為默爾索是一個冷漠的人,以至于默爾索在守夜時抽煙、喝咖啡都成了他們眼中的道德淪喪,成為故意殺人的佐證。審判庭上的中心人物、殺人嫌疑犯默爾索在法理消解的情況下失去了為自己辯護的權利,成了“局外人”,憑別人發落自己的命運。
加繆在文本層面解構了日常生活的慣性,揭露了社會關系中個體與整體的矛盾,體現了社會慣例對個人自然感受的打壓。加繆以陌生化手法寫出了這種約定俗成中的不合理部分,是對慣常表現形式的諷刺和否定。在創造“復雜化”的過程中默爾索的種種行為以一種非晦澀的語言呈現,而小說中的其他人物卻極容易對此感到不解。當讀者跳出文本時,會發現自己容易成為現實生活中“其他人物”的翻版,這也是讀者在審視、觀照自己和默爾索的關系,因此讀者在閱讀接受的過程中,會獲得對社會認知新的理解和審美感受。
三、陌生化手法下人物形象在荒誕外殼下的真實感
陌生化手法在敘事層面上對人物形象的運用指的是通過將作品中的人物進行變形和扭曲,不直接向讀者展示清晰的人物角色和性格特征,讓讀者始終不能完整地把握人物的具體肖像、性格和體征等,只是靠感覺把握人物的特點。這種阻滯隔閡的陌生化書寫誘發了對主人公人物形象的玩味和揣摩,小說表面的荒誕性和通過人物形象展現出的真實性,讓文本充滿了張力,進而引發對《局外人》主題的思考。筆者認為默爾索的人物形象的獨特性背后有其積極意義,下面就默爾索所處的困境論述其人物形象的真實性。
(一)溫和得近乎透明的靜穆
加繆在為美國版《局外人》寫的序言中寫道:“他遠非麻木,他懷有一種執著而深沉的激情,對于絕對和真實的激情。”作者看來重要的是能在世界與自我的復雜的關系中找到靈魂與心靈的自由和生命的力量。默爾索個人式的生存理念顯示了對傳統社會主流觀念的叛逆,默爾索作為一個被誤讀的正常人,善良溫和,熱愛自然,真實坦率,不虛偽做作,能夠同情他人,是具體、生動和獨特的存在,他的性格是用來描述希臘雕塑的那種“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
也許在世俗的無意識的對立下,默爾索的表現就像一個與世俗脫離的局外人,但這是默爾索不虛偽做作的內心的真實呈現。面對朋友和朋友妻子的款待,默爾索并不作出客套的表現,而是大方地接受了朋友的熱情,當他面對朋友雷蒙和阿拉伯人的沖突,則是給出了中肯的意見;在馬松家,他面對家庭的溫暖怦然心動,產生了結婚的念頭,通過這些行為很難承認他是一個極致冷漠的人。習慣道謝這一行為或許讓人感覺默爾索已經被社會深深規訓了的錯覺,遇到人就想握手、道謝,顯然是被社會規訓之后的結果,已經成為一種文化上的慣性。但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這恰好證明默爾索本質上是一個溫和良善的人,這種妥協是默爾索善良本性的一種呈現。他從來不大張旗鼓地與世界抵抗,大多數時間是安靜地接受這個世界的某些不合理性,他站在自我與社會中間。
默爾索幾乎不使用任何感情色彩去渲染所發生的事情,而是誠實地還原眼中的世界,他對所有涉及自己的處境與將來需要斟酌的事務,都采取了超脫淡然的態度;在面臨抉擇的時候,經常講同一類口頭語:“對我都一樣”“我怎么都行”。他溫和得近乎透明,總是沉默著、順從著,在無可奈何的社會中尋找一個適合生活的點。默爾索看透了生活的本質,產生了一種握手言和的沖動,這是他內心善良底色的體現。他孤獨而獨特地溫和著、靜穆著,從不要求自己具有某種個性,相反,他總是認為自己和他人一樣。
(二)感受的細膩與性的坦誠
一方面,默爾索感觸敏銳、洞察靈敏,對事物有非凡的觀察能力。他的目光像個攝像頭,鏡頭所指每一幀都沒有浪費。在默爾索的第一人稱敘述下,出場了許多沒有面目重復的人物,小氣的老板、絮叨的門房、沒有鼻子的護士、看電影的一家三口、陽剛男人雷索、養狗的老頭……每個人都極富個性色彩。他對周遭世界的觀察細致入微,他甚至可以注意到公用的轉動毛巾被大家用一天已經全濕透了的現象,諸如此類。
默爾索的觀察細膩、敘述精確,在他的注視之下,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深刻的被觸動的溫和,無論是周末的街道,還是夏日的海邊,甚至是送殯的場景,都給我一種沉靜的溫柔。在默爾索眼里生活是生機勃勃的,人的狀態是豐富且不斷變化的,這種細膩的感受超過了絕大多數渾渾噩噩的世人。
另一方面,默爾索不怯于談人真實的欲望,小說用了大量的筆墨書寫兩性之間動物性的“腥味”。默爾索和《紅與黑》中于連為得到德瑞納夫人的“英雄主義”不同,與《包法利夫人》中愛瑪的“偽浪漫主義”不同,默爾索的情欲是真實而不加偽飾的,沒有英雄主義或者浪漫主義的外衣,赤裸裸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人的動物性是絕對不能因文學的“文藝”而不描寫的,顯然,加繆遵循了這個原則。
(三)反抗意識的爆發與面對死亡的釋然
默爾索作為一個生活邊緣人,在社會上尋找自我生存和社會規則的平衡點,但最終因為一場槍殺,和社會共同情感中不相符合的那部分被公之于眾。默爾索不理解自己的生存方式和邏輯思維為什么會成為他被判處死刑的關鍵,又或者他明白,只是不想再虛偽地為此妥協,轉向堅持自己內心的誠實。他作為“局外人”,在最終確認“存在”的必要時刻,所有被排斥的情感回光返照一般洶涌澎湃,在獄窗后的星辰下迸發。在臨死前,默爾索覺得他第一次真正對世界敞開了胸懷。
當默爾索被判處斬首后,神父來到監獄對他進行告誡,這是我們看到他唯一一次爆發,他終于把對世界壓抑已久的不滿傾瀉了出來。這時候的默爾索把從不理解宗教乃至社會的虛偽的憤懣傾瀉而出,一種徹悟和反抗意識占據了默爾索的大腦和心靈。他不是在罵神父,而是痛斥所有讓他眩暈厭煩卻如影隨形緊緊纏住他不放的虛偽。默爾索求生的愿望、刑前的絕望、對司法不公正的憤憤不平、對死亡的達觀與無奈、對宗教謊言的輕蔑、對眼前這位神父的厭煩以及長久監禁生活所郁積起來的焦躁聚合在一起,不再苦苦壓抑來應付虛偽的世界,讓讀者人得以看到他平時那冷漠的“地殼”下面即將噴發的狀態,而這也正是默爾索對母親去世的理解——不是痛苦,而是新生的希望。
默爾索期望世人都對他在母親葬禮上不哭的行為進行強烈譴責,向世人宣告這是大錯特錯的傻瓜行為,希望世人對世俗規訓的主觀性強于法律規則性、嚴密性,公理對個性壓制的愚蠢行為進行一種熱烈贊頌。實際上這是一切破碎后的不屑的無奈和嘲諷,就像是魯迅先生的那篇《復仇》,那裸著肌膚站在廣漠的曠野上的兩人,就好像是懷著幸福感走向死刑場的默爾索,而涌聚在兩人四周的路人,則是默爾索期待的看客。
在規則長期的制約下,人們的精神會形成一種增生,與規則成為同一塊血肉,變成不懂得思考的、盲目的“看客”,盡管他們本來是完全獨立的個體。默爾索被判處斬首之后,他才全然從這一場全人類參與的迷局當中獲得解脫,意識到生命存在的本身。他在這個過程中見證了一個新我的誕生,而這個新我就是一個全新的更高層面上的“局外人”。荒誕意味著不承認任何預設的價值,因為世界的冷漠,以死亡為代表的終極的冷漠,讓個體得到了為所欲為的自由,最終趨向自我的真實。默爾索感覺到的一種幸福,那是一種終于戳穿了虛假的幻覺之后認清了現實的幸福。盡管陌生化的手法模糊了默爾索的人物形象,但是在語言的阻滯中我們卻可以解讀出最終指向“人”本身的這一更加清晰的真諦。
四、結束語
陌生化理論是展現小說《局外人》荒誕性和真實感的重要表現手法,它將文學作品中的世界和既存的現實世界割裂開來,在兩者之間劃出了一條鴻溝,這條鴻溝就是陌生化打造出來的變形了的藝術空間,我們可以從這個具有表現性的藝術空間中汲取現實生活無法帶給我們的審美汁液,也正是加繆對陌生化的大膽運用,我們才可以解讀出小說的荒誕感以及從中透露出的人物真實性。
參考文獻:
[1]董鈺.論加繆的怪誕身體書寫:以小說《局外人》《鼠疫》為例[J].沈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2,24(2):219-226.
[2]柳鳴九.《局外人》的社會現實內涵與人性內涵[J].當代外國文學, 2002(1):90-97.
[3]陸曉芳.“毫無英雄的姿態,接受為真理而死”:解讀阿爾貝·加繆《局外人》中的默而索[J].山東社會科學, 2012(2):79-83.
[4]宣慶坤.竭盡此生就是幸福:加繆《局外人》的哲學解讀[J].安徽教育學院學報,2005,23(5):10-13.
作者簡介:
明瑜凡(2002—),女,漢族,山東濟南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外國文學、文學理論。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