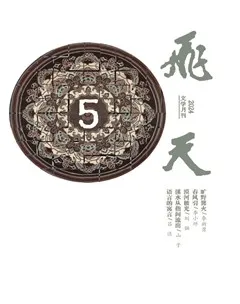路過哪里,哪里便會長滿青草(評論)
人鄰
之前沒看過山子的詩。朋友轉來她的詩讓我讀讀,說是一個很年輕詩人的作品,有潛力,刊物有意要推一把。
最初讀這些詩,沒太讀進去。放了一段,再讀讀,讀出一些意思。最初的不能讀進去,是習慣性的思維,亦是如今的人太忙,難得靜下心來,花時間細讀一個未經確認的新人。反省一下,也因此跟幾個詩人朋友說,讀詩要有警覺,尤其是讀新人的。一個人讀得久了,習慣了,會有審美上的固守,難得進入新的詩歌感受。人亦是無意義的忙,難得清凈,會無意識間排斥。
安靜下來,細細讀這些詩。山子自然是筆名,二十出頭的人,一個女子,用這樣一個筆名,取自然意味,也簡略,想必是有自己的想法。至少,這個筆名不矯情。也并不像另一些女詩人,在筆名上特別強調女性意識。
她的這些詩,一首一首讀過去,慢慢讀出她的清靈有味。一些詩句語言的處理有跳躍,有些跳躍也偶有突兀,似乎之間的牽連,無跡可尋。這可能是作者的問題,但也可能是我的問題。但是思維跟了過去的,豁然一下,知道原來詩意如此,驚喜一下。詩人畢竟是年輕,跟我的按部就班,語言循序的按住,逐步推進,詩意的加深,不一樣。
先看《清明帖》。詩人一上來寫:“清明過后,雨是如此的新”。這是詩人清明祭祀所感。“清明過后”,尋常語。“雨是如此的新”,卻別有意味。為何是“新”?祭奠亡者,是舊,一年一年,越來越舊。年年落下的雨水,如同“年年歲歲花相似”,卻是“歲歲年年人不同”,每每的“新”。其“新”,是相對于生命的逝去,不能復返的“新”。一個“新”字,用得好。而后,詩人繼續寫——
我們的親人
昨日親吻木窗的蝴蝶
塵埃
一如昨日塵埃
可菊
總會長出新的菊
舊日塵埃里,又是一個“新的菊”。 一舊一新,即歲月,亦即無限的一剎那。所有的惦念、不舍、無奈,就在這樣的詩句里了。
《雨夜》的語言表現,有其新妙處——
樓底下有很多小孩子
他們穿著雨鞋在跳舞
水泥地板盛開
一朵一朵煙花
對于人們習以為常的對某些物和形的無感忽略,這是富有想象力的句子。雨花,寫到的詩人很多,可是聯想到“煙花”,殊少。這個“煙花”,詩的結尾再次出現——
知道嗎
明天去往遠方的
也是一朵一朵的煙花
“煙花”是虛幻之物,甚至是虛無。詩人由小孩子腳下濺起的“煙花”聯想到“遠方”亦是“一朵一朵的煙花”,意在迷蒙,亦是對于未知的假設和想象。這是一個小女子在試圖體味虛無?也許,至少這個年齡還不該。可是,這其中也許并非全然是詩人提前對于虛幻的感悟,亦可能是詩人對于另一種虛無美的感悟。“煙花”,難道不是一種美么?即便其中有著虛幻的意味。
前面提到詩人語言的跳躍,語言的跳躍是省略了中間無謂的過渡,其間預設了橋梁,看似沒有橋面一樣,但有橋墩,有橋墩和橋墩之間影子似的牽連。初看似沒有,思維跟了過去,就有了橋。這里的問題,也是詩人的藝術功力,是如何在語言的“橋梁”過渡上,在跳躍上,盡可能保留適當的陌生感,這種陌生感會帶來讀者的閱讀喜悅和沖擊力。但其關鍵是,既要引著讀者讀過去,隨著詩人巧妙保留著的順“理”成“章”的線索隱秘,也要在這種跳躍中,需要適度的陌生感(閱讀的適度阻礙),以微妙的語言把控,忽然彰顯,渡己亦渡人。
拜訪去年的書信
杯子里的夕陽就高興起來
這兩句是詩人《故》里面的句子。“書信”“杯子”“夕陽”,瞬間的感覺鏈帶過去,聯想完成,詩意完成。這樣的寫法于笨拙的我來說,幾乎是不可思議,但是年輕的詩人就這樣寫了。猛然一下,似乎閱讀帶不過去,慢慢讀,真的如此。心境如許,萬象燦爛。
《戒指》的語言,有些句子似乎有些糾纏,比如這兩句——
抬頭
我們仍是多年的戀人
“我們仍是多年的戀人?”是很奇怪的說法。既是“戀人”?如何“仍是”?是,還是不是?也許就是“抬頭”的一瞬,再次相互的凝視,使得兩個人之間再次認定著這種感覺。“我們”“仍是”。一個“仍是”,從回憶到眼前,一切看似不指明,不確定,但就是這一個“仍是”,讓人知道,一切難以回避,一切還是。
詩人也有幾首詩,只是感覺,讀來有點無著的感覺。無著的感覺,也可以算是一種懂。詩,就是這樣。年輕一代的詩人,思維亦會與我等寫了幾十年的詩人不同。他們覺得在感覺上夠了,詩意的完成也就夠了。
年輕詩人看似無著的語言靈氣是隨處可見的——
黏土的耐心
足夠溫暖行人
我腳底的泥巴
你去往哪里
我的影子就落在哪里
——《秋》
明月樓啊
我手心的建筑仿佛活了過來
——《日記》
再讀讀《雨夜》——
我靈敏的愛意
混合著
雨水的青草
“靈敏”與“混合”,“愛意”與“雨水的青草”,詞語之間的碰撞,一碰就彈開,若即若離,造就了輕靈有味的詩意。《秋》《難過》這些詩,也同樣是只攫取一瞬間的感觸,更注重自己的心理私密感受,一味寫去,不大顧及所謂的閱讀。但這些詩有如蜻蜓點水,一點即飛去,留下了水紋的層層漫漶。
詩的讀解,歷來是麻煩的事情,糾纏不清的。有論者評論斯蒂文斯的詩,指出他的詩“是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這樣的指認,還不是中國詩歌所謂的“羚羊掛角”,而是在另一個詩的維度上談論斯蒂文斯的詩。斯蒂文斯的詩,有其不可解的玄學意味。國內詩人喜歡并且津津樂道多是《壇子》《觀察烏鶇的十三種方式》等。但其可能更為重要的一些詩,則很少為我們的詩人提及。弗羅斯特亦是。我們經常讀的是《牧場》《雪夜林邊駐足》《不能走的路》,而更多地放棄了他的詩歌異質的那一部分。山子年輕,如何研習這些,從中汲取,形成自己更為深入的詩意面貌,還有待來日。
詩人山子亦有《高歌》《鑰匙》這樣的閱讀起來相對指實的作品。這些詩作為同一個作者,她在寫作這些詩的時候,內心有著如何的考量?寫“形而上”和“形而下”,亦可以交互,都可以造就上佳的詩。詩人需要根據具體的詩意,讓其各自有深入拓展,而不是早早畫地為牢。山子這些詩,也許是她詩歌拓展的明證。
山子也有一些詩,是近乎匪夷所思的結尾。也許是她的把控失靈,也許是她有意識的試驗。我在她的《難過》里,讀到了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詩意。不管怎樣,詩人面對自己的作品,都需要警覺。她也有一些詩,有著兒童一樣的氣息。她筆下的《噴嚏》,亦有一點微妙的趣味。
每個詩人要緊的是,寫好自己的每個年齡段。山子的年齡,是寫好自己的青春懵懂,寫好初醒。欣喜的是,在她的詩里,我們有所讀到。她的《藍》里面有這樣的句子——
去海邊吧
我們都做新鮮的孩子
這看似尋常的句子,是詩人的懵懂也是初醒。世界是不斷地新舊循環,也是不斷地新鮮,而這個新鮮需要不斷的外力加持,詩是其一。人是喜新厭舊的動物。詩歌更是。比起新鮮,所謂的深刻是可笑的。陳丹青曾談論過一幅梵高的畫,好像是《海邊的孩子》。這幅畫應該是梵高的未完成稿,甚至孩子的面部,只是近乎胡亂涂抹的幾筆色塊。畫面上是一個混不吝的十四五歲甚或更小的孩子,無所謂地站著,浪蕩,玩世不恭,對萬物不屑一顧那樣,陳丹青卻覺得好得不得了。問題在哪里,其實就是一股完全的生命之氣,生命的原初氣息,無所謂美與不美。
對于山子來說,下一步的寫作,最為重要的是如何在語言把控能力不斷提升的過程中,保持住這股生氣、生命的力量、人性的自然美,這是關鍵。
自然,她也還需要在語言上有耐心的甄選組織。在詩意的場景里,要尋找到那唯一的一個詞,唯一的句子,唯一的詩句安排。
來日方長,祝福山子,好好寫吧。寫出獨獨屬于自己的詩。
題目“路過哪里,哪里便會長滿青草”,引自詩人的詩《路過》。
責任編輯 郭曉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