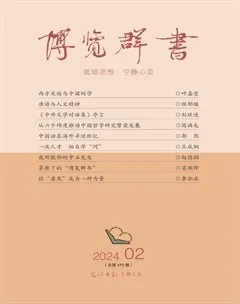訪河南方言島
王璐
在浙江、江蘇和江西的腹地,星羅棋布地分散著一個個與當?shù)厝苏Z音和習俗完全不同的村落,他們大多一口信陽方言,完全按照豫南的風俗生活,甚至改變了當?shù)氐姆窖院土曀祝纬闪艘粋€又一個“河南話方言島”,來自河南的方言甚至成為他們生活區(qū)域的“官方用語”,這是怎么回事?
江南地區(qū)為什么許多人說河南話
作為河南人,倘若到東南區(qū)旅游,問路的時候都要費盡心思地連猜帶比劃,因為當?shù)厝苏f話聽不懂。也確實如此,東南的吳方言、贛方言等跟北方方言完全是兩個系統(tǒng)。
但是,假如你到鎮(zhèn)江句容縣的茅山看道士,在山下則會遇到這樣的情況:路過的老大爺哼著豫劇,村頭大喇叭傳來信陽口音的開會通知,村小學教室里孩子用“信普”讀著課文。
句容縣,離鄭州700多公里,即使是豫南的信陽也有500多公里,中間還隔著安徽和長江,那么,為啥茅山周邊的村民都是一口信陽調?要知道,按照語言學的劃分,理論上這里是吳儂軟語的天下。
語言和風俗,是地方文化的左膀右臂,可是反觀茅山附近的袁相鄉(xiāng)、磨盤鄉(xiāng)、茅西鄉(xiāng)等鄉(xiāng)鎮(zhèn),為啥被信陽方言篡了權,成了為“官方唯一指定用語”?
根據(jù)2010年的全國人口普查,句容的常住人口為617680人,但是往上查幾代,祖籍是當?shù)氐牟⒉欢唷3W∪丝?萬多的磨盤鄉(xiāng),河南籍村民就有1.6萬。袁相鄉(xiāng)更甚,1.6萬人口里有1.5萬河南人。句容其他的鄉(xiāng)鎮(zhèn)里,或多或少也居住著一些河南人,多則四五千,少則四五百。除了句容,溧陽的上興,溧水的共和、白馬鄉(xiāng),宜興的善卷,吳江的菀坪,丹陽的埠城也有很多河南人。
早在三年前,江蘇媒體曾以《蘇州吳江有個“方言島”,小鎮(zhèn)居民都講河南話》為題,報道位于吳江太湖邊屬于吳方言區(qū)的菀坪鎮(zhèn),當?shù)匕傩諈s以河南話作為主要交流的語言,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方言島”,這在整個蘇州范圍內是獨一無二的。當?shù)胤窖詫<以谡{查中發(fā)現(xiàn),人口1萬多人的菀坪鎮(zhèn)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只說河南話,以中老年人居多。年輕人中,大多數(shù)既會說河南話,也會說吳語,至今全鎮(zhèn)人仍以河南話作為主要的語言使用。
河南話在菀坪如此盛行,有著特殊的原因。菀坪本是東太湖的一片蘆葦蕩,直到清末才開始有人在此定居,距今100多年,第一批拓荒者便是來自河南光山、羅山等地的難民。
除了江浙地區(qū),江西北部也發(fā)現(xiàn)有828個村落的方言已完全河南化,像群島一樣散布在鄱陽湖周圍,人口至少有11萬。贛北一戶郭姓家族,和鎮(zhèn)江句容磨盤鄉(xiāng)的一戶郭姓是四代的旁親,他們都自帶信陽口音。
有意思的是,這些河南人聚居的村落名稱也很有特點,大多叫“某棚”“某家棚子”“某邊”“某家邊”,僅磨盤鄉(xiāng),就有16個以“某棚”為名的村子,比如胡棚、王棚,數(shù)量驚人。
有這么多河南人的存在,也就能解釋得通,為啥鄉(xiāng)里沒人說吳方言。每每遇到略帶“河南腔兒”的蘇北人和皖北人,我都不得不折服于河南腔強大的影響力。
河南話如何同化了“吳儂軟語”
最早研究江南地區(qū)的河南話方言島現(xiàn)象的,應該是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郭熙。出身南陽社旗的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得知蘇南地區(qū)有不少河南人,他們操河南口音,行河南風俗,或與當?shù)厝穗s居,或自成村落,不少方面都與當?shù)厝隋漠悺?/p>
從1989年起,郭熙教授開始對這一現(xiàn)象進行調查,不下四次的走訪基礎上,又結合相關歷史文獻,初步摸清了來龍去脈。
自清咸豐三年(1853年)起,河南十年九災,非旱即澇,求生的本能迫使很多人以“一副蘿擔”離家出走,跟以往河南人一樣,出門向南,漫無目的地流浪漂泊。這一代河南人移民的基本規(guī)律是北部北移,南部南移,蘇南移民的主體就是河南難民,大多來自河南東南部的光山、羅山、商城等地。
歷史上,中原當了幾百年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但同樣,這也是一個飽經(jīng)戰(zhàn)火洗禮的地方,歷朝歷代,但凡遇到戰(zhàn)爭或者自然災害,中原人都會南下逃命。比如西晉的五胡亂華,唐朝的安史之亂。
明清時期的長江中下游平原,早已是物產豐富的膏腴之地。乾隆朝后期,久無戰(zhàn)事的中原人口激增,土地明顯不夠用,尤其是流行早婚的光山,人地矛盾更加尖銳。于是,一場浩浩蕩蕩的移民運動開始了。僅光山一縣,就向江蘇、浙江、安徽和江西近60個地方輸送了100萬移民。這件事,在江西多個縣的方志里都有記載。搭簡易窩棚而居的河南難民又被稱為“棚民”。
但在清嘉慶、道光年間,南方一些地區(qū)就開始控制流動人口了。例如浙江、安徽曾多次對已有“棚民”進行整頓,并且“不允許外省棚民再行遷入”。河南移民的高峰期在咸豐六年(1856年)到來了。豫南大部分地區(qū)多次發(fā)生旱澇相間的特大自然災害,莊稼絕收,人們只能吃草和樹葉樹皮。沒過多久,草木也吃完了,光山、羅山、商城等地的受災群眾只能挑著扁擔離開河南,繼續(xù)到江南討生活。恰巧就在此時,長江中下游平原遭受了太平天國民兵和清廷十余年的拉鋸戰(zhàn),生靈涂炭,人口銳減。
以句容縣為例,根據(jù)清光緒《句容縣志》記載:清軍和太平天國農民兵的一場戰(zhàn)爭之后,句容縣的人口少了70%,一半以上的耕地荒蕪了。這像是老天特意給了豫南移民一個安身立命的機會。同時,清廷為了安置流民,恢復糧食產量,下達了“修農利,安流徙”的命令,并設立“勸農局”“招墾局”等機構專門負責安置流民。有了這樣天時地利的條件,豫南移民大量涌入江南。到19世紀80年代,江南的多個鄉(xiāng)鎮(zhèn),移民人數(shù)遠超當?shù)赝林_@場轟轟烈烈的移民運動,一直持續(xù)到民國初年。
大量聚集起來的棚民村落,在人口密度上甚至超過了當?shù)厝耍灾劣诔霈F(xiàn)了當?shù)卣Z言文化被河南人同化的現(xiàn)象。
他們?yōu)樯稕]有喪失自己的鄉(xiāng)音
江蘇南部的鎮(zhèn)江市句容縣里,有兩個在蘇南人看來稍顯“異類”的鄉(xiāng):磨盤鄉(xiāng)和袁巷鄉(xiāng)。那里的村民,雖然戶口本和身份證歸屬鎮(zhèn)江,但他們的性格特征和風俗習慣卻一點也不“南方”。
家里來了客人,喝酒要豪爽地“雙一下”(喝兩杯),客人吃完了一碗飯,要突然地再扣一碗飯到客人的碗里。
過年不僅要過初一,還要隆重地過十五;不僅要在門框上貼對聯(lián),還要貼橫批和兩張大大的門神。要知道,句容人只是簡單地在門板上貼上一副對聯(lián)罷了。
作為移民,被當?shù)氐奈幕羰遣豢杀苊獾氖虑椋热玎囍莸母呱阶澹麄兊恼Z言幾乎被河南人同化,再如1949赴臺老兵的后代,也都會講著一口嗲嗲的臺灣腔。
然而,有趣的是,這些逃難的河南人,不僅沒有喪失自己的鄉(xiāng)音,反而同化了周邊的當?shù)厝恕_@是為什么呢?遙想北宋的靖康之變,南渡的開封人順利地融入臨安城,被當?shù)厝送僖舱也灰姰斈甑摹般炅哼z風”。
因為豫南移民,在墾荒的早期,其實是和當?shù)厝怂鸩蝗莸摹_@些一無所有的難民,一路流浪,哪個不是衣衫襤褸、形銷骨立?有一首民歌,充分再現(xiàn)了河南人逃荒的情景:
堂客挎著討飯籃,一擔稻籮下江南。
前頭挑著破棉絮,后頭挑著女和男。
當?shù)厝丝床黄鸾谢ㄗ右粯拥囊泼瘢锓Q他們?yōu)椤昂幽侠小焙汀昂幽腺ㄗ印保缓幽弦泼褡匀灰睬撇簧蠞M口鳥語的南方“蠻子”,加之當?shù)厝瞬豢献尦龇趾镣恋兀瑢е铝藰O其嚴重的矛盾。主客之間甚至發(fā)生械斗。在這種情況下,移民抱團住在一起,堅決不和當?shù)厝嘶ネㄓ袩o,更別提什么通婚融合了。在蘇浙皖交界的溧陽,移民成立了“河南會館”,專門為受到欺負的老鄉(xiāng)打抱不平。
在政府的干預下,河南移民最終獲得了一些土地,只是土壤比較貧瘠,位置比較偏僻。吳江菀坪的河南村,在太湖旁邊;江西北部的河南村,沿鄱陽湖分布;句容的河南村,都在茅山附近的小山丘上。這些被開發(fā)成旅游景區(qū)的“好山好水好地方”,當年都是人煙稀少的荒野。
我無法想象,這些移民是如何白手起家,篳路藍縷,把荒原變成了魚米之鄉(xiāng)。
也正是由于居住環(huán)境的相對獨立,河南移民才保留了自己的語言文化和風俗習慣。作為吳江菀坪東湖灘地的第一批開荒者,移民后代的河南話保留得非常完整,他們稱外祖父是“姥爺”,祖父是“爺爺”,父親是“大”,跟河南并無二輒;而當?shù)氐姆Q謂分別是“外公”“爹爹”和“阿爸”。在河南移民看來,不說河南話就是對祖宗的不忠。這種剛性的語言態(tài)度,影響了一部分當?shù)厝耍热缟衔奶岬降木淙菽ケP鄉(xiāng),從鄉(xiāng)政府官員到中小學老師,清一色的河南話。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主客關系的緩和,河南移民的后代開始和當?shù)厝寺?lián)姻。但是,如果夫妻雙方有一方是河南人,他們會較多選擇河南話作為家庭交流語言。他們的孩子,大多可以自如切換三種語言:普通話,當?shù)卦捄秃幽显挕?/p>
河南人吃苦耐勞的特性,在這些移民身上也有充分的體現(xiàn),即使生存條件再惡劣,只要有土地,有一口吃的,就能生生不息。作為農民,他們不可能把“尊重文化”這種虛的口號掛在嘴邊,但對于鄉(xiāng)音的執(zhí)著卻令人感動。
(作者系原《豫記》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