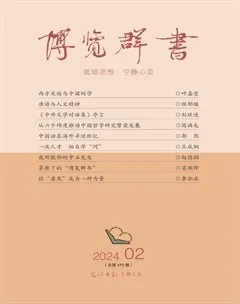為我一揮手 如聽萬壑松
馬達(d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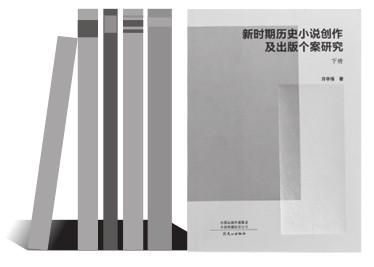
作為具有重視歷史傳統(tǒng)的國度,中國文學(xué)史上的頂級作品中,歷史類小說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進(jìn)入新時期以來,歷史小說及其衍生品,如電影、電視劇、廣播劇(評書連載)等載體的加入更使其在人們文化生活得到很大程度的豐富。
長篇歷史小說的創(chuàng)作出版自新時期以來呈現(xiàn)出繁榮昌盛的大好局面:以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為嚆矢,《少年天子》《張居正》《曾國藩》《大秦帝國》以及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落霞三部曲”等,共同形成中國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的新高潮,成為令人矚目的文化現(xiàn)象。文學(xué)界、評論界對這一現(xiàn)象有著較多的研究,但是卻鮮有學(xué)者對這些小說的出版過程,或曰作品問世的前世今生背后的故事,以及對后世的重要影響做較為系統(tǒng)的研究與思考。
近日,許華偉所著《新時期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及出版?zhèn)€案研究》(文心出版社2023年8月版)的問世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這一空白。因為許華偉本人即是其中幾部小說的策劃者、出版者,甚至是全程操作者,在《大秦帝國》的出版過程中與作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品嘗了與作者、出版社同行合作、競爭過程中的酸甜苦辣,親歷了從約稿、組稿、編輯、發(fā)行、宣傳、營銷的全過程,所以,展讀新書不僅倍感親切,讀后也能對編輯工作的體悟進(jìn)一步加深,從而受到啟發(fā)。
全書分上下冊,計36萬字。捧讀之后,對全書的特點無力進(jìn)行全面評價,謹(jǐn)略述數(shù)端,權(quán)作評介。
其一,脈絡(luò)清晰,爬梳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出版的線索,加以深入研究。該書以新時期的歷史小說代表作——姚雪垠所著《李自成》(第二卷)為開篇,充分肯定其在當(dāng)代中國文學(xué)史上的崇高歷史地位,稱為一部明末社會的“百科全書”,是新時期長篇歷史小說開山之作,有著無可替代的文學(xué)史地位,它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對當(dāng)代歷史小說的創(chuàng)作影響深遠(yuǎn)。
在該書的七輯內(nèi)容中除了首輯以《悲壯英雄——李自成》外,其余六輯分別以《少年天子》《白門柳》《雍正皇帝》《曾國藩》《張居正》《大秦帝國》為個案,對其文學(xué)創(chuàng)作出版過程予以梳理,基本勾勒出新時期小說問世的足跡。
其二,用較多筆墨對歷史小說出版過程中編輯的千辛萬苦詳加書寫,從而揭示出默默無聞的做嫁衣者的付出與奉獻(xiàn)。編輯是圖書出版的幕后推手。可以說沒有一部圖書出版的背后不凝聚著編輯的大量勞動。慧眼識珠者有之,起死回生者有之,精益求精者有之,參與修改甚至部分文字寫作者亦有之。早年出版社的年出書數(shù)量較少,比較重要的稿子會邀請作者到出版社改稿,有時可長達(dá)數(shù)月甚至更長的時間。在此交往的過程中,不僅修改稿子,修正寫作思路,編輯有時也在某種程度上參與到寫作過程中,從而結(jié)下深深的友誼,成為一生摯交。
許華偉謙虛地將自己職業(yè)生涯中打造的新時期歷史小說典范的故事放在全書的最后一輯(第七輯),即“改革、法治和統(tǒng)一——《大秦帝國》的故事”中。在該輯的第七章中,他詳細(xì)地回顧了自1999年開始接觸《大秦帝國》第一部《黑色裂變》至2009年5月該書典藏版出版的十余年間的“不離、不棄、不移、不易”的波折故事:
編輯都是幕后英雄。比起作家詩人來,人們不會把“才華”這樣的贊美送給他們……然而,當(dāng)你讀了《〈大秦帝國〉·編輯手記》,我相信你會改變自己的看法,甚至?xí)σ粋€編輯真正的價值與才華有較為客觀或者說更加完整的印象。
其三,秉筆直書,坦言自己的看法,月旦人物既有分寸又切中肯綮。與一般的讀者視角不同,許華偉以文藝編輯的眼光對論及的對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對姚雪垠《李自成》,他認(rèn)為作者不提李自成不屠城之事,而是虛構(gòu)了一個“王吉元的老娘”,刻畫他在敗軍之際仍然關(guān)心民眾的愛民形象,這讓人質(zhì)疑。對《李自成》小說中英雄人物形象塑造不夠真實,結(jié)構(gòu)上有重大缺失,第四、五卷文字比較粗疏、情節(jié)拖沓枝蔓以及歷史真實性不足等提出自己的質(zhì)疑,并在“同情的理解”基礎(chǔ)上對此種現(xiàn)象造成的原因予以理性的分析:既有人們對《李自成》創(chuàng)作動機的誤解,也有是否把歷史題材現(xiàn)代化的爭議,又有對英雄人物理想化的問題,但歸根結(jié)底還是作者姚雪垠先生個性上的問題:自信與自負(fù),春風(fēng)得意時不知收斂,加上卷入一場影響很大的文學(xué)爭論,終于使自己成為眾矢之的,最終結(jié)果不禁讓人唏噓不已。
作為責(zé)任編輯,親自“催生”《大秦帝國》的許華偉在與作者孫皓暉交往過程中的觀點沖突也毫不避諱地“公之于眾”:在該書第二部《國命縱橫》里,孫皓暉設(shè)置了張儀當(dāng)面罵孟子“娼婦處子”,孟子被罵得“簌簌發(fā)抖、欲語不能”等情節(jié),令他不能接受。他認(rèn)為作者對儒家和孟子貶損太過,“矯枉過正,對孟子貶斥過分”。孟子雖然好辯論,好罵人,但他提出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
爭論的過程痛苦而美好,既鞏固了友誼,也提升了雙方對問題的認(rèn)識水平。華偉兄由此得出結(jié)論:
總之,《大秦帝國》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對《大秦帝國》的創(chuàng)作理念,無論是褒揚,還是批評,其本身都必然會直接深入到中國文明史的價值評判討論之中。思想,總是在相互碰撞中一步步接近真理的。
讀史使人明智。作為官方書寫的《二十四史》固然比較完整地記錄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朝代更替、社會的興衰榮辱,但對普通人而言,了解民族歷史,廣益知識,還是通過正史以外的通俗易懂、讓大眾喜聞樂見的小說演義之類才更加容易理解與接受,而新時期歷史小說的繁榮在當(dāng)下社會里為普通民眾歷史知識的普及,乃至全體國民的歷史文化素養(yǎng)的提升,更是功不可沒。將這一現(xiàn)象上升到學(xué)術(shù)研究的高度加以探索,是許華偉的一次大膽嘗試,并首戰(zhàn)告捷。在此,我們期盼有更多的專家學(xué)者、編輯出版行業(yè)的同道中人,加入這個隊伍,以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績。
(作者系文心出版社總編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