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瓦礫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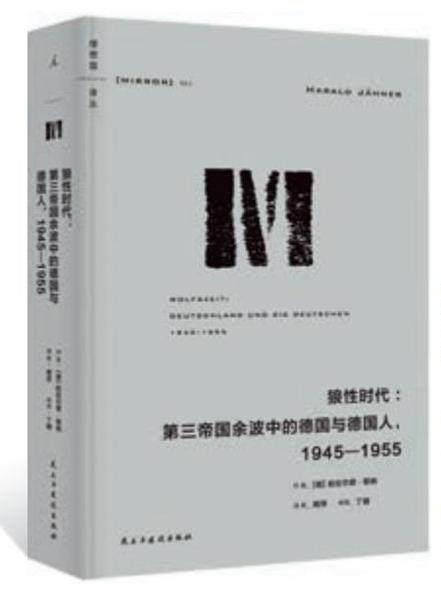
《狼性時代:第三帝國余波中的德國與德國人,1945-1955》
[德]哈拉爾德·耶納 著 周萍 譯
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2024年1月
戰爭在德國留下了大約5億立方米的瓦礫。為了讓這個量度更直觀,當時的人們做出了各種各樣的測算。《紐倫堡新聞報》以帝國黨代表大會會區內的齊柏林廣場作為參照,如把這些瓦礫堆積在這個長寬各300米的廣場上,它們將形成一座高達4000米的山,山峰上永遠白雪皚皚。有人則測算出柏林市的廢墟有5500萬立方米,在腦中搭建一道寬30米、高5米的向西延展的墻,這堵墻在想象中可從柏林延伸到科隆。借助于這樣的思維游戲,他們試圖使世人對必須清除瓦礫的龐大體量有一個具象感。當時曾見過不少城市的某些區域被徹底摧毀的人,如在德累斯頓、柏林、漢堡、基爾、杜伊斯堡或法蘭克福,都無法想象這些廢墟會如何被清除,更不用說重建了。在德累斯頓,每一個幸存的居民頭上都分攤著40立方米的瓦礫。
瓦礫堆當然不會以那種緊湊的立方體存在,而是脆弱地延綿在城市各處的廢墟中,在它們之間走動會是一件危及生命的事。那些還住在廢墟里的人們不得不爬過山丘般的瓦礫堆,穿梭過矗立的殘垣斷壁才能回到他們那個往往四面墻只剩三面,甚至連屋頂都沒有了的家。個別的內墻通常和房屋的外立墻一樣高,而且還沒有支撐它的側墻,所以隨時面臨倒塌的威脅。在頭頂上方,彎曲的鐵梁上懸掛著殘墻;有時整片的混凝土地板突兀地伸出于一面側墻之外,而孩子們就在這下面玩耍。
雖然到處都有令人絕望的理由,但大多數德國人不允許自己有片刻的沮喪。1945年4月23日,戰爭尚未正式結束,曼海姆(Mannheim)的官方公告已經發布了“我們建設家園”的號召:“我們只能暫時簡單地進行重建,因為第一步必須先清除大量的瓦礫廢墟才能露出可供建造的土地。就像一句古老的諺語說的,‘各人自掃門前雪,最好的開始就是清除堆積物。這些我們一定能夠完成。當一個幸運的返鄉者站在他原本想再次居住的屋前,而那個小屋卻早已破碎不堪時,沒有比這個更令人難受的了。我們必須用多年的經驗和能力,一錘一錘地重新建造,直到可以重新住在里面生活……擁有屋頂油毛氈和屋頂瓦片,我們才能自助。為了盡快地為更多的人提供幫助,每個擁有以前施工遺留下來的屋頂材料的人,請務必立即將這些材料交給區域重建的責任部門……由此,我們希望重建過程適度開始,一步接一步,先是封上窗戶和房頂,然后我們再來審視下一步。”
盡管不計其數的英國炸彈炸毀了曼海姆一半的房屋,但是靠著近乎完善的地下防空洞系統,只有5‰的居民喪生。這也就解釋了為何在重建的時日里,人們又錘又打忙于造房建屋的歡樂場面是那樣的充滿匠人的詩意而又不可思議。然而在曼海姆以外的其他地方,人們同樣也在戰爭結束后立刻以一種令局外人驚詫不已的熱情開始了清理。
“恢復秩序”是當時的口號,而它的字面含義為“找到立足點”。人們很快以令人驚訝的速度在瓦礫混亂中創造出了一種初始秩序。狹窄的走道被清掃,以至于人們可以舒適而匆匆地穿過亂石堆。在坍塌的城市里,被踩踏出的路徑造就了一種新的地形。在廢墟沙漠中出現了整潔的綠洲。在某些地區,人們如此認真地清理街道,讓鵝卵石就像在往日美好歲月里一樣光彩奪目,而人行道上的碎瓦磚塊,按被大小仔細排列、堆疊。巴登州的弗賴堡一向以特別愛打掃出名,約翰·彼得·黑貝爾(Johann Peter Hebel)有一句金句——“弗賴堡的街道,干凈而光滑”——人們將散落的碎片如此有愛心地堆放在廢墟的腳下,以至于原來世界末日的風景幾乎重新擁有了可以安居樂業的格調。
柏林建筑管理局和軍管委很清楚地知道,5500萬立方米的瓦礫碎片不可能單單由懲罰性強迫勞動力來清除完畢。建筑商們于是被叫來對瓦礫碎片做專業化處理。根據他們在戰時不同的政治表現,他們要么是被強制去做,要么可以按勞取酬。在所有四個被占區里,建筑工人都受雇在碎石沙漠般的瓦礫堆勞作,雖然工資很低,但他們首先為的是當時緊俏的重體力工作食物配給卡。
與此同時,“瓦礫婦女”慢慢成為戰后女神一般的人物。戰后在柏林市區外的這類婦女要比我們現在認為的少得多,然而在柏林市區最重的體力工作確實是婦女完成的。在清理工作的高峰期,有26000名婦女參與,而男性只有9000名。在數以百萬士兵被殺或被俘之后,柏林男性的短缺問題比其他任何地方更為嚴重,尤其因為柏林在戰前就已是單身女性的首都。
當年為了呼吸“汽油的芬芳”和自由的氣息,并能夠靠新生的婦女職業而獨立生活,她們從狹窄的省城逃到了大都市。然而現在,比起最低等食物配給卡所保證的讓人不死不活的每天7克脂肪,當建筑工地上的勞工是唯一相對較好的選擇。
在德國西部被占區,婦女很少被用于干這種清理瓦礫的工作。把女人送到瓦礫場干活主要是在去納粹化和實施管教措施過程中,對“無人管教的女孩和不檢點婦女”(針對“經常更換性伴侶”的女性)所采取的懲罰性行為。然而,瓦礫中的婦女們后來仍然能夠成為重建的神話英雄,主要歸功于她們在廢墟中勞動時那些令人難忘的景象。如果廢墟已經很上鏡的話,廢墟中的婦女們就更是如此。在多數印刷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她們沿著山坡站成一長排,一些人系著圍裙,有的穿著裙子,裙子下面露出笨重的工作靴。她們經常系上頭巾,像拖拉機手那樣在額前打個結。她們組成一個鐵皮桶的傳遞鏈,手手相傳地把鐵皮桶中的瓦礫從廢墟傳到馬路邊,在那里由半成年的孩子做分類和清理。
這些照片之所以深刻地烙在了人們的記憶里,是因為鐵皮桶鏈為一個已崩潰但又同時迫切需要集體意識的社會提供了一個極佳的視覺隱喻。它是一個如此鮮明的對比:一邊是搖搖欲墜的廢墟,另一邊是鐵皮桶鏈的凝聚力。重建被賦予了英雄而性感的一面,它讓人們可以心懷感恩地識別認定自己,雖然戰敗卻依然自豪。因此,那些像幽靈般頑固地留存在人們記憶圖像里的被稱為“小阿米莉”的輕浮“小姐”們,從意象上受到了清除廢墟的婦女們的挑戰。
面對攝影師,瓦礫中的一些婦女反叛性地吐舌頭,或者當面嘲諷攝影師。有些人穿著非常醒目的優雅禮服,她們的白色領口及灑花面料與這些骯臟的工作完全不相匹配,這僅是因為這身衣服是她們的最后一套了。那些前往防空襲地窖或被疏散的人們總是把最好的物品帶上,最美麗的衣服總能一直被女人保存到最后,而現在是時候拿出來穿了。
在其他情況下,那些不合時宜的優雅衣著事實上是擺拍的道具。在一些電影上映前播放的每周新聞中,婦女們優雅而準確地往瓦礫堆里扔碎磚,仿佛她們正在上體育課一樣。這看起來很棒,但其實令人難以信服,而且這種勞動也是無效的。完全虛假的還有那段由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在被炸爛的漢堡委托拍攝的錄像:那些扮演著在瓦礫堆里勞動的女人對著攝像機的鏡頭,扔磚頭時笑得如此歡快,以至于只有容易輕信的人才會認為它是真實的。事實上,她們都是女演員。
美國攝影記者瑪格麗特·伯克-懷特(Margaret Bourke-White)不帶絲毫同情地、理性地看待這些在塵土中勞作的姐妹們。她于1945年在柏林的一篇旅行報道里寫道:“這些婦女構成了為進行城市清理而組織的人力傳送帶的一部分,她們非常熟練地用慢鏡頭的速度傳遞著裝滿碎磚頭的鐵皮桶,讓我覺得她們好像確切地計算出了最低工作速度,好在以這速度完成這個工作的同時,為自己不多不少地掙得每小時72芬尼的工資。”
的確,最初的那些沒有協調好的瓦礫清除行動并不高效。在某些情況下,瓦礫中的婦女只是把碎石塊扔進附近的地鐵通道里,使得人們事后不得不再次艱難地把它們運出來。1945年8月,柏林市政府聯系了各區辦事處,命令他們制止“失去控制的鐵皮桶鏈”。那些“原始的清理工作”必須停止,即時起清理工作必須在建筑當局的監督下專業地進行。
“專業的大規模瓦礫清理”包括建立起一個有效的運輸系統,好讓市內的瓦礫可以運到城外的垃圾傾卸場。為此,人們使用了農業慣用的窄軌鐵路:在臨時鋪設的軌道上用小型火車頭拉小貨車。德累斯頓人立即設置了七條這樣的窄軌。例如T1號軌道從“城市中心清理區”通往奧斯特拉區的傾倒處。40輛全部被賦予女性名字的機車穿梭行駛。雖然由于軌道鋪設粗陋曾導致過脫軌事件,但總的來說運轉完美,有主副兩線、運營中轉站、提煉和傾倒點。近5000名員工負責這條奇特的鐵路,這條鐵路穿過德累斯頓被大火燒盡的廢墟,就像穿過幽靈般的無人島一樣。
官方宣布德累斯頓廢墟清理結束于1958年,這也是這條鐵道最后一次運行。但并非所有區域都被清理完畢。盡管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區早在1946年就已被清掃干凈,以至于埃里希·凱斯特納能夠在45分鐘之內穿過市中心卻沒有經過一棟房子,但直到1977年,即戰爭結束32年后,德累斯頓最后一支清理隊伍才停止了他們的工作。
瓦礫的量改變了城市的地貌。在柏林,戰爭導致的堆石使城市北部由大自然形成的冰磧石堆往南延長了。在長達22年的時間里,有時每天多達800輛卡車在前國防學院的空地上傾倒著瓦礫,以至于這座后來被形象地稱為魔鬼山的人工山成了西柏林的最高點。
(本文摘自《狼性時代:第三帝國余波中的德國與德國人,1945-1955》;編輯:許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