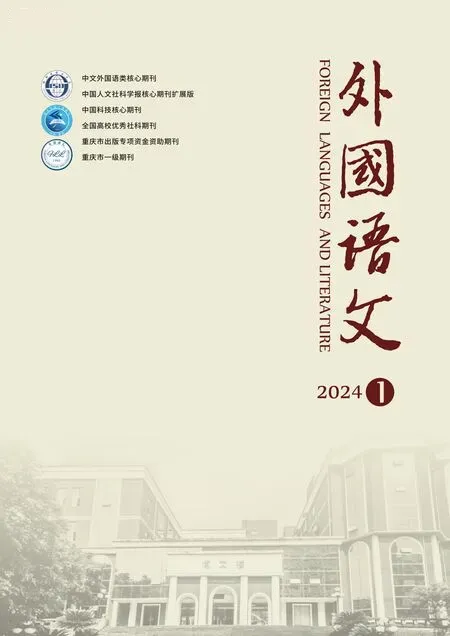論畢肖普詩歌中異化的日常生活及其救贖
馬紅旗 張羽西
(南開大學 外國語學院,天津 300071)
0 引言
伊麗莎白·畢肖普(Elizabeth Bishop,1911—1979)是美國20 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女詩人之一。其詩歌對日常生活的細微之處進行精準描摹和深入思考,展現了對異化的現代生活的洞察、批判與反思。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1985:1)稱其延續了美國詩歌傳統中的“克制的修辭、鮮明的道義感和極其簡練的形式”。以往對畢肖普詩歌中日常生活的討論多分散于較為前景化的自傳性書寫、旅行書寫和藝術形式研究中,日常生活本身則作為背景隱匿其中,鮮受重視。根據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論,日常生活是“生產方式的產物”,與作為“生產者”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交相輝映。日常生活中“意識形態的力量聯合起來形成了一個外殼……把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最深層次的或最崇高的意義隱藏了起來”(列斐伏爾,2018:52)。隨著20 世紀中葉現代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現代日常生活逐漸淪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物和現代性的附庸,喪失了潛在的差異性和創造性。日常生活中主體的個性、創造力與發展潛能受到壓抑,導致主體離開自身,淪為“對象、他者,甚至與主體相疏遠對抗”的異化狀態(韓立新,2014:8)。畢肖普對日常生活的書寫正是基于資本主義社會不斷加劇的異化進程,詩歌中呈現的同質化生活空間和單調重復的生活實踐正是對現代人異化生活的真實寫照。同時,畢肖普在詩歌中提出了可能拯救異化生活的方式,探索藝術化、審美化的生活風格和構建個人精神及情感力量,以求超越異化,恢復人的完整。
1 “浸滿滲透了油”:日常生活空間的異化
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中指出,作為日常生活的基本場所和社會的產物,空間“包含并掩蓋了社會關系”(列斐伏爾,2021:124)。被當作“物質生產的器皿和媒介”的空間已經成為“現代社會利益爭奪的焦點”(汪民安,2006:47)。在技術理性的要求下,現代資本化空間不斷擴張,擠壓本應由人自主支配的日常生活空間。同時,空間中的人也被視為物質需求下的生產工具,被迫犧牲個性化、差異化的日常生活,在異化的空間中彼此敵對疏遠。
畢肖普的許多詩歌都聚焦現代社會資本化的日常生活空間。正如詩人在《愛情躺臥入眠》(“Love Lies Sleeping”)中對城市空間的描繪:“一座巨型城市,謹慎地揭幕,/在過分雕琢中變得纖弱,/細節疊著細節,/檐口疊著外壁。”(畢肖普,2019:33-34)城市中的資本化空間經過精致打造形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邏輯鏈條服務,因此呈現出同質化、標準化的特征。《瓦里克街》(“Varick Street”)聚焦美國第一大城市紐約:“夜晚,一座座工廠/掙扎著蘇醒,/頹廢焦慮的建筑物/一身靜脈管道/試圖完成它們的工作……鼻毛是簇生的長釘/還散發這般臭氣。”(畢肖普,2019:99)詩人將城市中作為標志性建筑的工廠擬人化,夜晚的機器掙扎著蘇醒,在陣陣轟鳴中散發著臭氣。大城市工業化的高速運轉擾亂了寧靜的夜晚,也打破了人們健康安穩的日常生活秩序:“我們的床/被煤灰熏得萎縮/糟糕的氣味/將我們聚攏。”(畢肖普,2019:100)人們的居住環境和身體健康受到工業污染的嚴重侵蝕,夜空中的月亮也不再如濟慈(John Keats)《夜鶯頌》中的“月后”一樣美麗高貴,而是變得“呆板的”和“病懨懨”的,“聽隨某人的煽動而陰晴圓缺”(畢肖普,2019:100)。城市中所剩無幾的自然景觀也被卷入大規模機械生產的節奏中,這正是列斐伏爾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即“如畫的風景正隨著異常迅速的發展而消失”(列斐伏爾,2018:40)。異化的生活空間還造成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敵對與疏離,正如詩中敘述者所嘆息的:“當然會出賣你,親愛的,并且你會出賣我。”(畢肖普,2019:100)處于高度隔絕空間中的現代人難以敞開心扉,陷于精神異化的危機之中。《夜城》(“Night City”)一詩則直指異化進程帶來的毀滅性后果,描摹了一幅末日的城市景象。詩人于飛機上俯視整座城市,夜晚城市的燈光如同成堆焚燒的破碎玻璃,到處流著“灼爍的酸”和“斑斕的血液”(畢肖普,2019:219)。城市焚燒“眼淚”和“罪業”,留給人們的只有硅酸鹽河流、一池瀝青、一輪涂黑的月亮和“天空已死”的景象(畢肖普,2019:219-221)。現代城市中充斥著一種異己性、毀滅性的力量,迫使人們失去安身立命的家園。對此,人們無計可施,只能在摩天大廈上獨自啜泣。
除了對大城市生活空間進行書寫以外,畢肖普同樣關注小型家庭空間。《加油站》(“Filling Station”)一詩描繪了公路邊的家庭加油站:這個“小小加油站”臟亂不堪,到處浸滿滲透了油,形成一種“令人不安的、遍及一切、半透明的黑”(畢肖普,2019:145)。隨著20世紀以來汽車工業的迅猛發展,為汽車行駛提供保障的加油站也大量涌現。家庭加油站作為現代汽車工業與日常生活雜糅的產物,是資本化空間的縮影。這里不僅是父親與孩子們日常工作的場所,也是全家人居住生活的家園。一家人生活在局促狹小的空間中,對現代化工業生產造成的污染與破壞除了接受別無選擇。正如列斐伏爾所指出的,人們在“統治機器”和“權力藝術”的壓迫下只能犧牲曾經“輝煌”和“美麗”的生活方式(列斐伏爾,2018:40)。
畢肖普的一生輾轉漂泊,曾在巴西生活長達15 年之久,詩人對旅行空間的書寫跨越了本土與異國、熟悉與陌生的界限。正如美國著名詩評家海倫·文德勒(Helen Vendler)對畢肖普詩歌的評論:“不只有是異國的才是陌生的,也不只是本土的才是家園的。”(Vendler,1980:97)詩集《旅行的問題》(QuestionsofTravel)中的“巴西”部分收錄了畢肖普旅居巴西期間的創作,詩人以一種“接近巴西本土人的視角”(劉露溪,2018:19),深入異化的城市空間內部,真實客觀地再現了當時巴西社會的諸多矛盾。《在窗下·黑金城》(“Under the Window: Ouro Prêto”)一詩聚焦位于巴西東南部的黑金城。18 世紀的“淘金熱”使這里成為整個美洲的財富中心,吸引了大量外來移民。19 世紀以后這里金礦枯竭,人口流失,底層人民過著貧窮落后的生活。詩中帶有綠皂石雕刻的泉眼象征著黑金城鼎盛時期的美學風格,如今它已被補上石膏陳列于博物館,泉眼處只剩“一根簡單的鐵管”流著“冷得像冰”的水(畢肖普,2019:179)。這里是貧民們賴以生存的水源。穿紅衣和塑料涼鞋的女人帶著嬰兒,用臟手給他們掬水;拄拐的背麻袋老人蜿蜒而來,在水管處掏出了琺瑯茶杯。接著畫面一轉,與人們艱難取水的場景截然相反的是“一輛碩大的新卡車,梅賽德斯-奔馳/抵達,震懾了所有人”(畢肖普,2019:180)。車里的人下來依次洗了洗臉、脖子、胸膛、腳、鞋子。兩類人群的顯著對比揭示出現代資本主義城市中貧富分化的不平等現象,底層人難以擺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來的弊端與危機,只能受困于貧窮潦倒的生活,即馬克思(Karl Marx)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說的“勞動創造了宮殿,卻為勞動者創造了貧民窟”(馬克思,2000:46)。《粉紅狗》(“Pink Dog”)一詩也描寫了里約熱內盧市內邊緣人群的生存境況:“他們抓住乞丐,往漲潮的河里甩。/是咯,傻子、癱子、寄生蟲/在退潮的污水里踉蹌走動,/在沒有燈光的郊區夜色中。”(畢肖普,2019:237)底層人民生活在逼仄、骯臟、毫無尊嚴與個性的生活空間,被主流社會排除在外,卻又無可避免地受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壓迫和異化。
畢肖普對巴西生活風貌的書寫并非基于本土強勢文化的視角,而是將自身融入異國空間進行觀察與感受,這一視角顛覆了跨國地域空間中“自我”與“他者”的二元對立,凸顯了詩人對邊緣群體的關切與同情。同樣,詩人筆下的工業化場景也并非絕對化的“他者”,而是敘述者與敘述對象情感聯結的紐帶。在《加油站》中,敘述者面對加油站臟亂危險的環境,發出“哦,可是它真臟!”和“小心那根火柴!”的感嘆,并懷疑“他們住在加油站嗎?”(畢肖普,2019:145)。對于此處出現與油污臟亂格格不入的日常生活物件,敘述者也以連續三個問句表達驚訝:“這不相干的植物為什么在這里?/凳子為什么在這里?/為什么,哦,為何墊布在這里?”(畢肖普,2019:146)這樣的對話像似不經意又飽含關愛,使讀者置身其中感知空間內部的人與物,從而體會對異化生活空間從陌生到熟悉、從旁觀到觸動的情感流動。
畢肖普通過對工業發展下異化的日常生活空間的書寫,展現了資本化空間對人本應享有的穩定宜居的日常生活空間的侵占、破壞與威脅。詩人以“置身事內”的視角打破了作為旁觀者的“自我”和被注視的“他者”之間的二元對立,既以旁觀的態度觀察、評述空間,又切身體驗空間內部人的生存境況,再現并批判了現代工業文明對人們本真個性的日常生活空間和精神空間的異化。
2 “他們在夢中輾轉”:日常生活實踐的異化
畢肖普詩歌中呈現異化的另一個方面在于日常生活實踐。正如馬克思在其異化理論中所指出的:“異化勞動把自我活動、自由活動貶低為單純的手段,從而把人類的生活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馬克思,2000:51)異化勞動使日常生活不再是“具有豐富的潛在主體性的主體”,而是淪為了“社會組織中的客體”,逐步走向單一、機械(Lefebvre,1971:59)。詩人書寫了資本主義現代社會里人的日常生活實踐的異化,人們在工業化昏昏沉沉的節奏下喪失了精神價值,過著壓抑乏味、迷茫彷徨的生活。
《加油站》呈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異化勞動下的工作圖景,即馬克思所說的“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同時卻把一部分勞動者拋回到野蠻的勞動,而使另一部分勞動者變成機器”(馬克思,2000:46)。為了滿足生活需要,加油站父子每日進行著重復的工作:“父親穿一件骯臟的/被油浸透的晚禮服/在腋下扎著它”“幾個快手、粗魯/腸肥腦滿的兒子在幫忙/(這是一座家族加油站),/個個渾身臟透。”(畢肖普,2019:145)父子的衣著打扮與加油站油污臟亂的環境融為一體,一代代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此進行著機械乏味的體力勞作。可見為了滿足工業社會和家庭生活的需要,勞動者“必須遵循機械系統的節奏的必然規律”(Highmore,2002:7),去承擔功能性的勞動分工,無法自由發揮自己的肉體力量和精神力量。《去糕餅店》(“Going to the Bakery”)一詩也描繪了異化的生產活動與生活狀態,糕餅店里的商品和人無一不呈現麻木和病態。經歷了白天的營業,夜晚糕餅店里的蛋糕似乎要暈倒,“每只都翻出涂釉的白眼”;一塊塊面包橫臥在貨架上,“仿佛黃熱病人/被露天放倒在擁擠的庭院”(畢肖普,2019:183),令人毫無食欲和購買欲。與食物一樣“病懨懨”的還有工作了一天的糕點師。敘述者對此問道:“買啊,買啊,我該買什么?”(畢肖普,2019:183)。敘述者迷茫無力的情感與糕點、糕點師的“病懨懨”是共生的,人造同一的現代商品背后掩蓋著人們機械重復的工作與生活。恰如列斐伏爾對異化生活的描述:“重復性已經無所不在地打敗了別具一格,人造的與設計的東西已經將自發的與自然的東西從各個領域驅逐出去。”(列斐伏爾,2018:184)這種“千篇一律的繁殖”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意味著一種現代性與進步性的力量(Lefebvre,1971:202)。
畢肖普對異化給生活實踐帶來的未知危險也進行了細致描寫。《加油站》中敘述者發出“小心那根火柴!”(畢肖普,2019:145)的警告。火柴隱喻著現代人面臨的死亡性瞬間和現代生活潛藏的未知危險,人們只能過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生活。同樣的危險瞬間在《愛情躺臥入眠》中也有所體現。在一片虛弱而蒼白的天空中,一座因過分雕琢而纖弱的巨型城市懶洋洋地升起,如同一座小小的“化學花園”,接著“在西方,轟隆一聲,煙云蒸騰。/ ‘轟隆!’爆炸的花骨朵之球/再次怒放”(畢肖普,2019:34)。爆炸的聲音對于城市的工人來說,意味著危險和死亡。“他們在夢中輾轉,感到/短短的汗毛直立。”(畢肖普,2019:34)資本主義城市的繁榮以無數底層工人的血汗乃至生命為代價,他們即使在夢中也被無處不在的恐懼所包圍,精神與肉體都無處棲息。詩人借此指出工業化、城市化發展暴露的問題與潛在的危機。
畢肖普始終是一位具有社會關懷的詩人。《早餐奇跡》(“A Miracle for Breakfast”)一詩寫于美國大蕭條時期,作為這場危機的親身經歷者,畢肖普將個人經驗融入詩歌書寫之中,“把底層大眾的生存體驗轉換為文學的審美體驗”(顧曉輝,2023:108)。經濟大蕭條導致了大規模失業,成千上萬的失業者只能依賴社會救濟和慈善施舍生存。人們來到富人家的陽臺下等待救濟,他們對于早餐的期待并不高,只需一杯熱騰騰的咖啡和一塊面包。然而,陽臺主人姍姍來遲,期待中奇跡般的早餐原來只有“一小塊死硬的面包心”和“一滴咖啡”(畢肖普,2019:8),資本家冷漠與偽善的形象躍然紙上。對于資本家吝嗇的施舍,一些人“鄙夷地將它撣入河里”,一些人選擇繼續等待奇跡,還有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則為了溫飽而無奈放下尊嚴,“舔掉面包屑,吞下咖啡”,并安慰自己不過是“奇跡正發生在錯誤的陽臺上”(畢肖普,2019:8-9)。詩人在此揭露了資本家的虛偽面目,他們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壓榨勞動者,當危機爆發時卻冷眼旁觀,任意踐踏底層人民的尊嚴。社會貧富分化與階級矛盾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弊端,勞動者不僅無法獲得應有的成果,反而淪為發達工業文明中“作為一種工具、一種物而存在”的奴隸(馬爾庫塞,2006:32)。
與《早餐奇跡》同一時期創作的《人蛾》(“The Man-Moth”)以半人半蛾的“人蛾”形象喻指現代人怪誕異化的生活狀態,反映大蕭條引發的“思想的極度混亂和人類信仰的缺失”(李文萍,2013:155)。人蛾雖然在“向高處探測”的過程中爬得“戰戰兢兢”,卻“必須做他最恐懼的事,雖然/他必然失敗”(畢肖普,2019:31)。這暗合身處僵化生活實踐之中的現代人對于超越異化的本能渴望。人蛾住在“姑且稱為家的蒼白水泥隧道”,登上全速啟動的列車向往逃離此處,而這列列車卻以“可怖的速度”出發,沒有任何“換擋”和“漸進加速”作為緩沖,“每晚他必須/被帶入人工隧道,做循環往復的夢”(畢肖普,2019:31-32)。人蛾和人一樣,在現代城市中無法控制自己前進的方向和速度,盡管以孤注一擲的勇氣追求著純粹、崇高的精神世界,仍然被迫卷入無限循環的資本運作中無法回頭,對生活的美好愿景和艱辛拼搏只能以失敗告終。詩歌中人蛾幻想、登高、徘徊、失敗的艱難歷程映射了現代人在異化生活面前的掙扎與無力。
畢肖普敏銳地捕捉異化日常生活實踐的瞬間,現代人流水線般機械重復的工作狀態滲透進微觀的日常生活實踐,導致日常生活本應具備的趣味與活力被異化,取而代之的是日復一日的僵化與重復。人們渴望在生活中找尋內在精神的自由與獨立,靈魂與肉體卻在現代荒原的混亂與無序中消磨殆盡。
3 “有人愛我們所有人”:異化日常生活的救贖
畢肖普的詩歌多發表于20 世紀五六十年代,正值美國反文化運動的高潮時期。當時的文化聲音以“垮掉的一代”為代表,以叛逆顛覆的態度宣泄著對資本主義高壓下頹廢生活的絕望,如艾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的詩歌《嚎叫》(“Howl”)。相比之下,畢肖普的詩歌雖然同樣涉及現代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但她仍有意與主流反叛的聲音保持距離。1964 年畢肖普在書信中說:“夢境、藝術品、對超越日常生活經驗的頓悟、意料之外的共情瞬間,讓人們幻視到外部世界永遠無法一覽全貌而又極為重要的景象。”(Bishop,2008:864)相較于激烈反叛的主流聲音,畢肖普更加呼吁現代人重新審視當下瑣碎平凡的日常生活,從中發掘具有審美性、藝術性的元素,并重視生活中夢境、想象與記憶對異化的救贖作用。
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曾用“詩意的棲居”概括人類生活的理想狀態。面對異化的日常生活,列斐伏爾也提出:“生活藝術意味著異化的終結,生活藝術會推動異化的終結。”(Lefebvre,1971:184)在畢肖普的詩歌中,藝術化的生活風格是對異化的拯救。《三月末》(“The End of March”)中,畢肖普描繪了日常生活的生動樂趣:“對自己說話,并在濃霧天/觀看小水滴滑落,承載光的重負。/夜晚,喝一杯美利堅摻水烈酒。/我會以廚房里的火柴點燃它/可愛的、半透著光的藍色火苗。”(畢肖普,2019:224)在《耶羅尼莫的房子》(“Jerónimo’s House”)中,房間布置同樣精巧溫馨。屋子裝飾著“種在海綿中的蕨”和舊年剩下的“紅紅綠綠的圣誕飾品”,墻上掛著“兩把棕櫚葉扇子和一面掛歷”,桌子上放著“灑滿火辣辣的鮮紅醬汁的煎魚”以及“四朵用餐巾折的紙玫瑰”。步入其中可以發現“信紙上字里行間的光芒”和“收音機的各種聲響”(畢肖普,2019:49-52)。詩人對審美化生活的設計重拾人們對日常生活的主動參與、支配和把控,意在恢復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主體地位,正如畢肖普在書信中所說:“人們在藝術和體會藝術之中渴求的似乎是一種忘我的而完全無用的專注。”(Bishop,2008:861)這種“忘我而無用的專注”形成了對平庸僵化的日常生活的解構,為顛覆異化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可能。
相比于同時期美國“自白派”詩人對自我內心情感的肆意宣泄,畢肖普對藝術化生活與精神世界的追求則更具有一定的“明晰性”(李佩侖,2009:193),往往訴諸明確、具體的空間和物體。正如法國哲學家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指出的“任何事物都可以跨越邊界,重建審美體驗的領域”,因此詩人有責任“探究社會的幽深層面與無意識,解讀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物件上銘刻的信息,并揭示日常生活的奧秘”(Rancière,2010:126-127)。《加油站》一詩在完成對加油站日常工作狀態的描寫后,將焦點轉向家庭生活物件。不同于布滿油污和“遍及一切、半透明的黑”的工作區域,家中門廊后面還提供了唯一色彩的“幾本漫畫書”“一株碩大蓬松的秋海棠”,以及“繡著雛菊圖案”和“布滿灰色鉤花”的墊布(畢肖普,2019:146)。一系列生活物件成為詩性生活的物質載體,凸顯出家庭生活的溫馨浪漫。詩人在此處并未直接道出打理家庭瑣事的主體,而是以重復四次的“有人”代替(畢肖普,2019:147)。詩歌末尾處,“有人”把油罐放成排,“讓它們對神經緊繃的汽車/柔聲訴說/石油——油——油——油。/有人愛我們所有人”(畢肖普,2019:147)。此處主人公的缺場恰恰強調了一種無處不在的、強有力的在場。在日常生活主體“有人”的參與下,日常生活得以從異化中抽取出“生機的、新的、積極的因素”(列斐伏爾,2018:39)。詩人賦予藝術化生活以人性的詩意與溫情,喚醒現代人本能的愛與希望,呼吁個體精神的自由與解放。
由于童年的創傷記憶和長期漂泊無依的生活狀態,畢肖普的詩歌呈現出對于缺失情感的探索和彌補。夢境、想象與記憶成為循環往復的日常生活中“充滿創造性神奇性的瞬間”(任冰,2014:37)。借此,人們得以將時間空間化,突破日常生活的無盡循環,多維度審視和救贖異化生活。首先,夢境是畢肖普詩歌中多次重復的意象,夢境中“錯視”的視角提供了一個“綺麗而隱秘”的世界(畢肖普,2019:10)。在《一起醒來多么美妙》(“It’s marvellous to wake up together”)中,詩人寫道:“夜晚視角,我們平躺著/一切都可能同樣輕易地變幻……世界可能轉為一種迥然不同之物,/就如空氣變幻,或閃電轉瞬來襲。”(畢肖普,2019:268)夢境對過往與未來的經驗進行重新編碼,是一種具有革命性的瞬間體驗,人們借此實現對重復生活的破解,打開生活蘊含的無限可能。同時,想象來源于現實生活,經過人們主動創造性的加工,擺脫了異化空間和異化實踐的束縛。《早餐奇跡》中等待救濟的窮人們渴望著熱騰騰的咖啡和面包,此時奇跡出現,“我”變成了別墅陽臺上擁有面包和大廈的人,“每一天,在日光中,/在早餐時分,我坐在陽臺上/擱高腳丫,喝著一加侖一加侖的咖啡”(畢肖普,2019:9)。詩歌強調生活中人作為主體的情感體驗,彰顯了想象賦予生活的樂觀與希望,這也呼應了列斐伏爾所主張的“人類的實踐并不局限于通過重復機械的活動或生產對外部世界進行功利性的改造。它還包括愛、激情、身體、情感——即大量創造性、情感性和想象性的實踐”(Shields,1999:100)。
記憶在畢肖普的詩歌中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提出,過去和現在之間存在著一種“動態的、相互依賴的關系”“記憶的意義來源于人們如何組織和將其聯系現實”(Marks,2005:198)。畢肖普曾在大學時期的文章中寫道:“時間不是線性的,記憶也不是固定的,二者都在不斷地被重構。”(Marks,2005:199)再現記憶需要現在和過去之間的持續相互影響,畢肖普的詩歌正是當下對過往記憶的喚醒與重構。詩集《地理學Ⅲ》(GeographyⅢ)中收錄了畢肖普譯自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亞·帕斯(Octavio Paz)的《物體與幽靈》(“Objects &Apparitions”)一詩,詩中的“康奈爾影盒”是詩人曾經真實擁有過的“夢屋”,承載著童年時代的美好記憶。“夢屋”中的大理石、紐扣、頂針箍、骰子、別針、郵票、玻璃珠等物件隨著歲月的流逝成為“時間的童話”,但是他們卻“可容下夜晚,/和它所有的光”(畢肖普,2019:226-227)。詩歌中想象與記憶的時空交錯打破了平庸麻木的常規日程,為生活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不同于弗羅斯特(Robert Frost)《牧場》(“The Pasture”)一詩中“我不會去太久——你也來吧”發出的回歸鄉村生活的召喚,畢肖普對于記憶的追溯并非田園牧歌式的鄉愁或對日常生活的逃避與否定,而是直面現實,從生活本身發掘出可以救贖異化的情感價值與精神價值。法國哲學家巴什拉(2009:4)在晚年著作《空間的詩學》中提出:“家宅是一種強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憶和夢融合在一起。”畢肖普對于家宅故居“總是充滿深刻而復雜的記憶”(李莉,2019:58)。在《耶羅尼莫的房子》中,盡管詩中的房屋是“我”心中的童話宮殿,但“我”最終還是要面對當下的生活,離開時“別的不取太多”(畢肖普,2019:52),只需要取走承載著美好生活記憶的物件。詩人無意沉溺于烏托邦式的理想家園,只需要從過往的生活記憶中獲得精神力量,最終依舊要回歸現實。這種生活態度在畢肖普晚年詩作《一種藝術》(“One Art”)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面對日常生活中漸漸消失的鑰匙、旅行目的地、姓名、母親留下的手表、曾經的愛屋、熱愛的城市與風景等事物,詩人認為它們的失去“并非災禍”,而是一種“不難掌握”的藝術(畢肖普,2019:191)。這種類似頓悟的情感瞬間不僅表現了詩人直面現實的勇敢與達觀,亦是拯救僵化、異化生活的一劑良方。
畢肖普的詩歌對于如何救贖異化日常生活提出了方案:主張回歸日常生活本身,用審美化生活和來自生活的夢境、想象與記憶重建現代人真正的精神家園。詩人強調生活中情感瞬間的跨時空交匯,這也是對列斐伏爾提出的“生活藝術會推動異化的終結”這一救贖路徑的補充與超越。
4 結語
畢肖普的詩歌體現了對日常生活的觀照,透過異化的日常生活空間和生活實踐,探究現代性給人們生活帶來的矛盾與危機。現代化進程將日常生活空間納入工業生產與資本擴張中,使其失去了應有的豐富與鮮活;同時,在資本主義工業社會重復性的勞動實踐下,人淪為喪失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單向度的人”(馬爾庫塞,2006:2)。對此,畢肖普把目光轉向了具有“平庸與神奇”(吳寧,2007:174)二重性的生活本身,日常生活中依然不乏審美化、藝術化的元素,夢境、想象與記憶亦是現代人情感與精神力量的源泉。在現代化進程日益加速的今天,畢肖普的詩歌對于日常生活的批判性哲思依然警示著人們反思現代性帶來的種種異化,引發現代人深入思考列斐伏爾在半個多世紀以前提出的“我們怎樣生活”這一宏大命題。對此,畢肖普給出的答案是恢復本真詩意的日常生活,喚醒現代人主體意識與精神價值的回歸。畢肖普的詩歌不僅表達了對資本主義現代社會種種弊病的揭露與批判,同時也試圖塑造一種嶄新的理想生活秩序,讓“保持著人性”和“不平庸的幸福形式”(列斐伏爾,2018:40)在現實生活中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