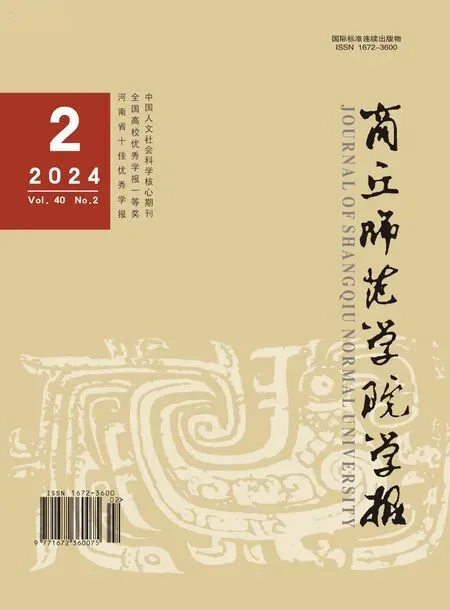本質主義普遍性的拒斥
——《莊子·齊物論》第12節解讀
郭 美 華
(上海財經大學 人文學院,上海 200433;華東師范大學 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 200241)
就其字面意義而言,“物之所同是”所追問的是事物的普遍性問題。但是,如此“物之所同是”的普遍性,是由“知”來加以呈現的。《齊物論》嚙缺之問王倪“子知物之所同是乎”“子知子之所不知邪”“物無知邪”“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應帝王》里概括為“嚙缺問于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這表明“同是”之普遍性與“知”相關聯,它意味著如此普遍性之“同是”關聯著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利害,一方面是權力政治或“帝王政治”。單純在觀念范圍內的普遍性,只有經由多樣而差異的不同觀點的自由爭論才能得以綻現。但是,如果認知與利害和權力勾連一體而給出“普遍性”,那么,其結果往往是對自然而真實的個體生命與個體自由生存的否定。因而,只有對于與利害和權力相勾連的認知加以否定,或者說明確認知的有限性與厘定權力的邊界,懸置甚至拒斥權力與認知相結合而給出普遍性“同是”,自然而真實個體生命或普遍的個體自由生存才得以可能。所以,《莊子·齊物論》中王倪對嚙缺“子知物之所同是乎”的普遍性追問,就是以“不知”作為回答。莊子對于普遍性“物之所同是”的如此拒斥與否定,實質上就是對于認知主義普遍性的拒斥與否定。認知主義普遍性的拒斥,反襯的是每一個體以及所有個體自由生存的普遍可能性。認知主義普遍性,以普遍本身作為所有個體的本質,勾銷了差異性個體自身的自然與自由,可以說是一種本質主義的普遍性;而生存論的普遍性,以每一個體以及所有個體的自然與自由生存為其本質性內容,可以相應地理解為個體主義的普遍性。就莊子拒斥與否定認知主義的普遍性“物之所同是”而言,他反對了本質主義普遍性而凸顯了個體主義普遍性。
嚙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栗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嚙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飄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云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于己,而況利害之端乎!”[1]48—50
一
從齊之為齊自身意蘊的不斷綻露而言,嚙缺追問“子知物之所同是乎”而王倪回以“不知”,就是對“知止于其所不知”之意的推進:“嚙缺同是之問,王倪不知之對,便即是知止其所不知。”[2]38知自身的懸置,敞開的是生存論的躍入可能,是“不用而寓諸庸”,是因于“滑疑”而對“天府”與“葆光”的雙重持存:“物各有適而無定論,皆滑疑也。”[3]25但每一存在者自身生存的躍入,總是牽連著天地間的相與共在者。“物之所同是”的追問,是在躍入自身生存并理解自身生存及其繼續之際,如何理解作為相與共在者的他者及其生存。
齊物之境是一個無數差異性之物共在的無限性境域。齊之為齊敞露的是每一物以及所有物的在其自身之在,不齊則是“唯知有己”[3]10,且將自身僭越為某種凌駕于他物之上的絕對普遍性——勾銷他者差異性與自在性的本質化普遍性。僭越的普遍性實質上就是一種本質主義普遍性。生存論的躍入拒斥本質主義的普遍性,但并非拒斥普遍性本身,而是凸顯個體主義的普遍性——有普遍性但此普遍性自身并非每一個體以及所有個體生存的本質,而是個體性自由生存的普遍性形式條件或秩序擔保。
因此,嚙缺“物之所同是”的追問,牽拽而出的是齊物之境的普遍性問題:“物之所同是者,此明齊一之理而故以此言而為問端也。”[4]321作為對話的雙方,嚙缺與王倪的身份具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是與堯相關的師承關系:“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嚙缺,嚙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莊子·天地》)一是與道相關的呈現樣式:“嚙缺者,道之不全也;王倪者,道之端也。莊子欲明道全與不全而與端本,所以寓言于二子也。”[4]317簡言之,與堯相關聯,嚙缺與王倪“物之所同是”的對話,由知以彰顯普遍性,內涵著權力與道兩個層面。
就道而言,它以每一物及所有物之在其自身之在為呈現,也即道以“道法自然”(《道德經》第二十五章)的方式展現為個體主義普遍性;但就權力與知的結合而言(在知識就是力量的命題中,二者甚至就是本質趨同的),二者以自身之絕對化的實現為呈現,即將自身的欲求作為無數差異性他者的普遍化強加,而表現為本質主義普遍性(僭越的普遍性)。基于權力與知糾合而有的本質主義普遍性,突出絕對性的同,即“以同為是”,一方面“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于己也”(《莊子·在宥》),一方面“同于己為是之,異于己為非之”(《莊子·寓言》)。在嚙缺“子知物之所同是乎”的追問中,潛涵著“以同為是”之意。因此,王倪“吾惡乎知之”的否定性回應,恰好就首先反對了“以同為是”與“以異為非”之論:“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故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1]48在同異與是非的關注中,每一物切近其自身之在被湮沒了。
在同異與是非的如此關系上(即以同為是,以異為非),昭示出一個基本的生存論理解,即同異是一個認知的問題,而非生存本身。在惠施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天下》)之論中,所謂小同異與大同異,都是在認知之域的界定,而無與于人自身的存在之真:“‘大同’屬于一大類,‘小同’屬于一小類,例如以動物為‘大同’,獸類則為‘小同’,這種從種屬關系來考察事物之間的同異,叫做‘小同異’。‘畢同’、‘畢異’,是說萬物都有共同之點,都有彼此相異之處,這就叫‘大同異’。惠施強調‘大同異’,按共性說,萬物都是‘物’,故‘畢同’;按個性說,每一物各具特性,故‘畢異’。他揭示了事物同異關系之間的相對性,有其合理因素;但他夸大了這種相對性,抹煞了事物的質的差別,得出了‘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莊子·天下》)的結論。意思是,要無差別地去愛一切東西,把天地萬物和自己看成血肉相連的一個整體。這里,他把抽象的‘畢同’說成實在的一體,就混淆了‘類同’與‘體同’。”[5]198以認知的歸類本質勾銷了每一物之在其自身的自然與自在之在,就是本質主義的普遍性。
二
但是,拒斥本質主義的普遍性,卻不是完全拒斥普遍性本身。認知會導致本質主義的普遍性,但認知本身卻不能被完全否定。畢竟,在有人的這個世界,假物以為用是人自身有形生命存續的一個基本維度;而有形生命的存續,需要認知相對獨立地從類或普遍性的角度來確定作為生活資料的外物。作為生活資料的外物即是財富,其占有以權力和認知作為兩翼。因而,嚙缺再進一步追問“子知子之所不知邪”——如此追問的內蘊在于敞明人必然以對物的普遍性認知作為人自身的存在的必然環節。但是,嚙缺所昧然不知的是,人之必然從認知普遍性角度視物,并不等于物自身的自然之在;而且,如此認知普遍性,不能適用于作為人的存在。因此,王倪“吾惡乎知之”的再次否定性回應,則更為深入地揭示出以“知”為問的雙重遮蔽:“以知為知則非知矣,以不知為知則深知矣。嚙缺問于知之者,是以知為知而反不知矣。”[4]321一方面,對于物的普遍性認知,是主體性的執取,而非物之自在性的呈露,不能將人類的主體性普遍認知,等同于物之自在性,如此主體性與自在性相區別之知,相較于將主體性湮滅自在性之知,是更為深刻的知;另一方面,就能知之主體而言,知不能將之視為一個知的對象,在知自身的展開中,能知的主體并非知可以知之的普遍之物,而是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將能知主體視為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相較于將作為主體的人視為認知的普遍性之物,是更為深邃之知。兩個方面結合起來看,不知與知或知與不知之間,存在著一個曲折而幽深的轉化,從而敞露出每一物相對于認知的在其自身之自在:“若以知知不知,不知還是知”,“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群才之自當”[1]48。無論將作為對象的自在之物,還是將作為主體的自在之物加以“認知化”而“有知”,每一物都會喪失在其自身之在。
但是,在有人的這個世界,人必假物以為用而必有其知。簡言之,有人的世界,畢竟有知。嚙缺再次追問“然則物無知邪”,即便物之在其自身不可被知所知,但人自身卻必有其知而以知御物,所謂物之在其自身并不能在知之中呈現,從而物只能以合于知的方式而呈現自身,“汝既無知物,豈無知者邪”[1]48。人當然不是無知無覺者,就此而言,嚙缺之問突出了人類生存的認知性維度的不可或缺。王倪依然以否定性的“吾惡乎知之”作答,“豈獨不知我,亦乃不知物”,“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1]48。因而,從類與個體之存在的過程性來看,無論是作為主體的人自身還是作為客體的物自身,總是在過程中不斷地綻現出逸出既有之知的未知可能性與新穎性,昭示出存在本身對于認知囚禁的不斷突破。
嚙缺堅執一個囊括人與物的普遍性,他力圖讓作為超絕流俗之人的王倪(“王倪即至人也”[2]39),為此作出“確定性認可”——在有人這個世界,有著概括人自身以及自身之外萬物的普遍性“同是”,以使得如此世界成其為如此世界。就齊之為齊的意蘊而言,嚙缺之所追問就是強調,齊物之境以某種普遍性“同是”為基礎。并且,嚙缺將此普遍性“同是”視為認知的普遍性,陷在認知之域的限制之中而趨向于本質主義的普遍性,從而湮沒了人自身的自然而自由的生存以及物的自在性。由此,王倪在“吾惡乎知之”的否定性回答之后,又反詰嚙缺“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以此“嘗試言之”而顯露差異性存在者之間的認知鴻溝,即不同存在者彼此之間知與不知的不可確定性:“魚游于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夫蛣蜣之知,在于轉丸。而笑蛣蜣者,乃以蘇合為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1]48如果將人與物彼此割裂相分而彼此對待是知的本質性特征,那么,知在其自身就涵著悖謬,即被知所割裂為二乃至彼此對待的不同存在者之間,知實質上無法溝通而得其普遍性“同是”。這意味著就存在之真或真的存在而言,普遍性“同是”不能得到認知的回答,從而認知的普遍性“同是”不能拘禁存在之邁向自身的真實。
就“知”而言,在認知的范圍之內,殽然雜亂之知,本身構成對知的消解。在認識論上,我們總是預設了某種普遍性的東西作為基礎。比如,從經驗主義角度看,認識的展開需要預設“生物學中感官結構本身的趨同性”,否則差異性主體經驗就無法形成普遍共同的知識;從理性主義的角度看,認識需要預設“理性的普遍性秩序或概念的先在性”,否則知識就沒有必然性,等等。但是,即使在“認知范圍”內,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二者各自所預設的內容,相互都不能確知對方所謂知是否為真知——彼此不能“真實地”知自身以及對方所預設的普遍之物。就此而言,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二者一定程度上都非真知。實質上,任何一種認知,都有作為其基礎的不可認知的預設前提。就此前提而論,特定的認知本身并不確知其自身。而且,一個具體的認知主體,其認知之真由真誠信念、普遍有效與經驗真實等各方面構成。但是,具體認知主體的認知,往往其信以為真之物實際并不普遍有效,或者普遍有效而并不為其所相信,或者經驗真實卻不被相信。在純粹的“認知之域”,認知所牽涉的真誠、真實與有效等各個方面,并不能被“確知”。“人們必須知道存在是什么,才能裁定這個那個東西是否實在(例如‘意識事實’);同樣也才能裁定什么是確信,什么是認識以及諸如此類。——但由于我們并不知道存在是什么”[6]124,所以,在認知之域,王倪的回答“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這是在“認知之域”經過知對其自身的懷疑或經由知自身的悖謬,而對于知及其普遍性執取的消解。如此懷疑與悖謬,關乎自然而自由的真實生存——“懷疑最終也反對自身:對懷疑的懷疑。而且關于真實性的合法性及其范圍的問題就在這里”[6]10。因此,莊子不得不繼續“嘗試”言之,以彰顯超越于認知主義懷疑悖謬的生存之真實。
由此,王倪再進一步反詰嚙缺“嘗試問乎汝”以豁顯認知與生存的區劃:所謂同異問題,是認知的問題,而不是生存的問題,不能以認知的普遍性消解每一物自身之在的差異性。王倪以人、泥鰍、猿猴沒有共同的“正處”,“以明萬物之異便”[1]48;以人食芻豢、麋鹿吃草、蜈蚣吃蛇、貓頭鷹吃老鼠而沒有共同的“正味”(1)對于“蝍蛆甘帶”,如成玄英、林希逸等注家大都認為是“蜈蚣嗜蛇”,鐘泰認為是“蟋蟀吃蛾子”。“‘蝍且’,蟋蟀,俗亦曰促織,皆聲之轉也。‘帶’同‘螮’。(《藝文類聚》《一切經音義》引此并作螮。)《類篇》‘螮’作‘蚳’,蟻子,《周官書·鼈人》所謂‘蚳醢’者是也。舊注以帶為蛇,蝍且為蜈公,謂蜈公喜食蛇。夫蜈公雖毒,然于蛇小大懸矣,豈能食蛇者哉!今于聲音求之,知為蟋蟀與蚳,無疑也。《淮南子·說林訓》:‘騰蛇游霧,而殆于蝍蛆。’高誘云:‘“蝍蛆”,蟋蟀,《爾雅》謂之蜻蛚。上蛇,蛇不敢動,故曰殆于蝍蛆也。’其以為蝍蛆謂蟋蟀是也。然不得據此便謂蝍蛆嗜蛇。彼上蛇而制之者,偶然之事,猶鼠入象鼻,為象所苦耳。人之于芻豢,麋鹿之于薦,鴟鴉之于鼠,皆常食也。蟋蟀豈能常食蛇哉!故吾從蟋蟀之解,而于甘帶則別釋之,求夫事理之所安而已。”(鐘泰《莊子發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頁),“以明美惡之無主”[1]49;以猵狙喜猿、麋鹿相交、鰍魚相游而恐人之所愛的毛嬙麗姬,“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1]49。居處、食味、性色等雖牽涉到認知的確定性,但是其真實的展開,卻逸出認知之域而返回到每一物的切己之在:“凡物形類不同,各不相知,雖都忘其知,而物各存焉。”[7]65不同的存在者,在知上不能相通而至于普遍之同,因而走向每一物自身差異性的獨在自存。每一物之返回自身而獨在自存,就揚棄了“以同為是以異為非”:“居處也,食味也,顏色也,各以所得為安,未可以此之是,訾彼之非也。”[8]21每一存在者切近于其自身的存在,是在其自身且自然而自覺其自身,沒有是非善惡之剖裂分別:“居之所安,食之所甘,色之所悅,皆切于身而為自然之覺,非與仁義是非后起之分辨等。”[3]25自然之覺,是區別于外在性認知的內在性領悟。悖于齊之為齊的所謂仁義是非之辯,都是個別存在者因其生死利害而扭曲自身所致:“物論之不齊,依于仁義;仁義之辯,生乎是非;是非之爭,因乎利害;利害之別,極于生死;生死者,知之生死(敔按:有知則謂之生,無知則謂之死),而非天之有生死也。”[3]25一個人為了利于一己之生,避免自身死亡之害,就以仁義是非作為流俗生存的借口,將自身的利害僭越為普遍之物,導致不同存在者之間的沖突而不齊:“夫利于彼者或害于此,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境無常”,“夫物乃眾而未嘗非我,故行仁履義,損益不同,或于我為利,于彼為害;或于彼為是,則于我為非。是以從彼我而互觀之,是非之路,仁義之緒,樊亂糾紛,若殽饌之雜亂。”[1]49生死與利害的纏縛,將內在性領悟的自然之覺扭轉為外在性的認知,造作超越的普遍性同是,反過來否定切己而近的具體性生存本身。
具體存在總是在某種特定的空間中,依賴于特定的生活資料并與一定的人結成社會關系而展開。特定時空、特定生活資料、特定社會關系等,因為人類假物以為用的生存本性,都需要認知的相對獨立的透視。就此而言,居處、美食、美色等,因“假物以為用”而呈現,需要有對于處所、食物或形體等的“認知把握”,以確定其屬性或本質。但是,物之所以為用的基礎,乃至于其所以為用之實,居處之安逸、食物之美味、色欲之美丑等,并無一個知識論上的“高懸超絕的普遍性共同標準”。而且,在居處、美食、美色等渾而為一的存在之淵深之處,對于處、食、色的認知理解,根本就不是存在之沉淪自身的內在領悟——將生存論的熾熱之愛,還原為生物化學式認知主義的多巴胺效應是多么的乏味!在純粹、深沉而熾熱的生存之愛中,生死、利害、是非、仁義等相糾合而有的“普遍性同是”,在認知范圍自身之內被懸置、被消解。
三
嚙缺的最后追問圖窮匕見:“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表面上看,對于世俗生活來說,似乎存在著普遍共同的“標準”,有著普遍共同的“秩序”,這些標準或秩序作為普遍性“同是”,體現為所謂趨利避害的普遍性本質(以及由之而有的普遍性倫理原則等)。但是,如此普遍性同是,為其背后的“力量追求”所裹挾,再以認知的方式遮掩其虛妄不實,并杜撰為對于每一具體在者及所有在者而言的強加性本質。簡言之,基于力量與認知糾合的所謂普遍性“同是”,歸根結底是一種無與于真實存在的“趨利避害”本性以及作為其矯飾的倫理規范而已。在利害取舍及其是非對錯之中,實質上,有一部分所謂有力有知的人,因其力量與知識而將自身的自私性僭越為普遍性,剝奪了另一些有著不同之知而無力量之人的生活。在嚙缺圖窮匕見的追問中,他將王倪視為悖于普遍性本質的低階生存者(子不知利害),而認為真正有智慧的至人有著對于利害本身的洞察(至人必知利害)。
王倪以“至人神矣”為答,將《逍遙游》中的神人生存樣式,與利害的考量相關而用略微不同的語詞重新渲染而顯。所謂“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飄風振海而不能驚”,在境界論的意義上,就是至人作為“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蠆介于胸中也”[1]50。如此境界論,可以轉化為生存論的領悟。所謂生存論的領悟,就是將認知的外在性普遍執取,轉化為作為內在自然之覺的領悟。如此內在性領悟,即如我們看到一朵粉紅的鮮花,我們領悟于花之粉紅與粉紅本身之無與于粉紅,或我們看到一塊方的石頭,我們領悟于石頭之方與方本身無與于方,等等。物之為紅為方的認知,拒斥其被理智造作為“如有物焉的獨立自存者”,而融于心、身、意、知、物一體之在中而為內在之領悟。在流俗之知看來,大火之炙燒、氣溫之寒冬、破山之疾雷、振海之颶風,作為極端的自然現象,都是有損于人之生存的危害。至人是否無與于這些危害?嚙缺認為,至人無論如何存在,都必須以對于這些危害的普遍認知為基礎,從而其生存以普遍的趨利避害及其普遍規范為基礎。但是,在王倪看來,嚙缺如此“必有利害”的視野,是以凝然不變的絕對化普遍性“同是”,囚禁了人自身的多樣性生存可能以及天地的多樣性呈現可能。實際上,我們坐在溫暖的屋子里,看著窗外的大雪飄零、聽著屋外的寒風凜冽,我們能“認知”寒風與飄雪的冷,但是,我們本身卻生存在無與于冷冽飄雪與寒風之境。寒熱驚悚之物作為危害而呈現,為認知所強化而成為絕對化的普遍性同是。王倪作為至人則讓認知返回到物之呈現之初而無寒熱驚悚之害:“王倪即至人也,神矣者,言其妙萬物而無跡也,不熱、不寒、不驚,即游心于物之始也。”[2]39游心于物之始,也就開啟了異于認知化流俗之境的四海之外的廣袤之境。
我們生活在世俗之中。我們對于世俗中的利害有著認識,并趨利而避害。但是,抽象的趨利避害作為普遍性同是,并非每一在者及所有在者的本質所在。流俗基于普遍性的趨利避害而展開的生活,反過來制造了更多的利害攻伐,使得每個人乃至所有人都斤斤以趨利避害為生活的本質內容乃至唯一內容。這在扭曲的基礎上,遮蔽了每一個體以及所有個體邁向無限深邃與無邊廣袤之在的通道。孟子,在倫理領域,以舜的大孝方式對害進行了某種安頓——舜的父親和弟弟幾次預謀害死舜,舜知而避之,但并不妨礙舜在倫理上依然孝其父、友其弟(《孟子·萬章上》)。孟子以為對利害的認知不妨礙孝悌的倫理踐行,它所凸顯的是倫理純粹性與圣潔性。在《莊子》這里,知曉于利害而開啟邁向廣袤與深邃的通道,它所凸顯的則是生命的自然淳樸性與生存的自由自在性。一個砸破流俗囚禁的深邃廣遠之域的開啟,使得自身之在與相與而在的萬物之間,也邁入了一個新的意境。“寄物而行,非我動也”[1]50而“乘云氣”,“有晝夜而無死生”[1]50而“騎日月”,“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1]50而“游乎四海之外”,“與變為體,故死生若一”[1]50而“死生無變于己”,最終使得利害“不足以介意”[1]50而生活于別處。換言之,我們認知某種普遍性“同是”,盡管我們的生命及其展開與如此普遍性同是相關聯,但我們并不以之為生,我們生在別處,生在超越于普遍性同是的更為廣袤淵深之處,我們生活在“無何有之鄉廣袤之野”(《莊子·逍遙游》)。
在《莊子》,與“同是”具有相似意蘊的說法還有“公是”:“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莊子·徐無鬼》)莊子并非以普遍性的“公是”來消解多樣性差異性的“各是其是”;相反,是以多樣性差異性的“各是其是”而懸置、拒斥著“公是”。與對普遍性“同是”或“公是”的拒斥與否定相應,莊子提出“玄同”的說法:“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莊子·胠篋》)德作為每一個別之物的個體性,其玄同,意味著多樣性、差異性與無數個體性的渾融。曾、史、楊、墨等,都是以一己之私僭越為普遍性,強行爚亂天下及萬物,從而使得他者的差異性與個體性喪失了可能性。每一個體都自含其明、自含其聰、自含其知、自含其德,也就是拒斥了僭越式的超越認知及其普遍性執取,而凸顯出每一個體自身的內在領悟。如此而言,差異性個體的玄同,與認知所強調的本質主義普遍性相對,也就是個體主義的普遍性。
總起來說,莊子以對“知”及其本質主義普遍性的否定來敞明自由生存的可能性,即自由生存是個體主義的普遍性,不是認知意義上的本質主義普遍性。個體主義普遍性,就是個體自由生存的普遍可能,本質主義普遍性,則是個體自由生存的普遍不可能。在政治哲學上,對無限認知的否定,或對于認知有限性的確定,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意味著“認識本身在生成中是不可能的”[6]359。不斷自我生成的自由個體,拒斥、否定認知及其普遍性,從而為他者之逸出我之認知之外的活生生的生存讓出可能,也捍衛自身逸出他者之認知之外的活生生的自由生存可能。僅就認知而言,我們不能“大膽地從純然的思維能力出發而無須一個對象被給予所憑借的一種持久的直觀就去形成一個獨立自存的存在者,而不是更好地去承認自己不知道怎樣說明一種能思維的自然的可能性”[9]277——承認在認知上不能清楚地闡明能思的存在本身的存在,這是自由的存在可能性。這實際上就是《應帝王》的主題。與莊子追問“物之所同是”有所相似的,是孟子對“心之所同然”的追問。表面上,“物之所同是”注重的是普遍性的客觀性維度,“心之所同然”注重的則是普遍性的主觀性維度。但實質上,孟子肯定“心之所同然”的本質主義普遍性而顯現出絕對客觀主義傾向,邏輯上必然導向了獨斷論與權威主義,從而必然與專制權力形成沆瀣媾和;而莊子拒斥、否定普遍性的“物之所同是”而顯現出相對主義或主觀主義的懷疑論傾向,邏輯上必然走向開放與自由,從而捍衛每一個體自由而自然之在。就此而言,莊子哲學對于本質主義普遍性的拒斥與否定所彰顯出來的政治哲學意蘊,就更加顯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