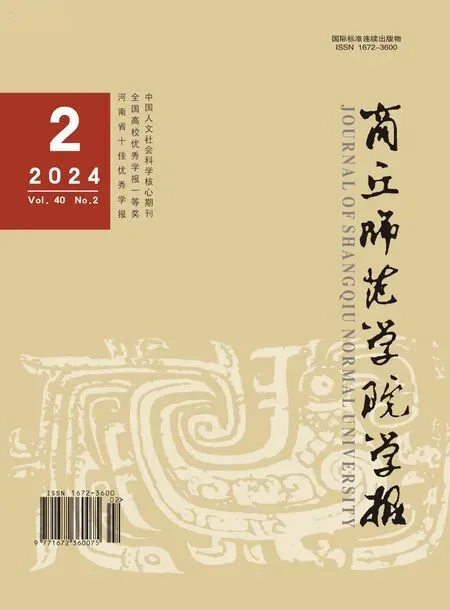激進的莊子與傳統的莊子①
任博克 (著) 黃圣平 (譯)
(1.美國芝加哥大學 宗教與哲學系,伊利諾伊州 芝加哥 60637;2.上海大學 哲學系,上海 201800)
這部三十三篇的文本有時被稱為《莊子》,有時也被稱為《南華真經》,傳統上被認為包含了古代一位名叫莊周的無名人物的思想。莊周(前369—前286),他是后來被稱為道家哲學(參見“《道德經》與老子”詞條)和漢朝以后道教中的關鍵性人物。很少有現代學者接受將整個文本都歸屬于這個人的做法,有些人完全懷疑他的存在,或者是懷疑他作為作者的存在。本條目將把這個文本視為一個組織松散的著作選集,它表達了與宗教哲學相關的一系列立場,集中在三個方面:(一)天、道觀;(二)精神修煉和神秘體驗;(三)死亡。
這些著述中的一些部分(大部分,但不是排他性的,出現在被稱為“內篇”的前七篇中)呈現出邏輯性的和懷疑主義的觀點,與一種突出的反基礎主義的神秘主義思想相互交織,這種神秘主義避開了所有形而上學的承諾(即拒絕所有關于自然事物和人類行為的來源與目的的主張,并從這種拒絕中找到了一種變革性的宗教體驗),這種方法在任何其他漢代以前的中國文本中都沒有得到驗證,盡管可以說在后來的思想史上以非常不同的形式有一些繼承者。
這些著述的其他部分貫穿了各種基礎主義的形而上學觀點(對自然事物和人類行為的來源與目的之設定),成為后來道家和其他中國思想中的更為普遍的主題。
借用李亦理(Yearley Lee,2010年)的話[1]126—136,我們將把第一類“激進的莊子”(無論在文本的什么地方發現這類材料)和第二類“傳統的莊子”中的所有作品稱為想象中的單一作者的著述。這兩個莊子都將在這里被討論,因為可以為每一個構造中的人物重建一種相對一致的設定,每一個人物都有其自身的哲學意義,但他們彼此之間也有重要的不同。此外,我們將討論第三個莊子,這個人物(真實的或虛構的)以莊子的名字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他被認為是整個三十三篇《莊子》文本的作者,在一個單一性的視野中包含了“激進的莊子”和“傳統的莊子”。
一、激進的莊子論天、道
中文的“天”字,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指字面上的天空,但這個術語在早期中國有許多不同的含義和指稱。所有這些指稱所共有的,是人類意志所不能做的事情,是超越人類力量的事情的含義,就像天空一樣。在周朝(前1046—前256)的政治宣傳中,這個詞開始被使用,可能是作為一個間接的轉喻,用來稱呼掌管政治命運的神。在公元前11世紀周朝推翻商朝(約前1600—前1046)時,它是周王朝的贊助者,表面上的原因是商朝的末代君王道德敗壞。在接下來的一千年里,這個神——“天”——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以前人們更傾向的、對帝國政治在道德上感興趣之控制者的官方稱呼——“上帝”,在上之帝。到了春秋時期(前771—前476),這種神的擬人化特征在一些知識分子中逐漸淡化。孔子(前551—前479;見詞條“儒家”)已經評論說,他希望仿效天,因為它“無言”,但仍然在某種程度上有助于所有自然事物的出生和成長。天空和季節轉換之間的聯系,以及因此與植物和動物的誕生和生長之間的聯系,已經在這種去神話化的趨勢中脫穎而出。與此同時,對孔子來說,天仍然保留了一些對正當的政治、社會和倫理革新事業的關注性贊助,比如他自己的事業。大約兩個世紀后,儒家思想家孟子(參見詞條“孟子”)保留了這種關于天的自然性和倫理性之關聯的模糊性,他將這兩種含義聯系起來,斷言在自然界中看到的自發生長過程和在人類身上的道德情感的自發萌生都是由于天的相同力量,兩者都來自人類無法控制的東西,但需要人類的照料和滋養才能達到最充分的繁榮。天可能會,也可能不會根據道德的發展來控制事件的外部結果(孟子在這一點上是模糊的),但它肯定會通過世界上一個非常特殊部分的活動——即自然的和自發的人性構成,以及在正確條件下對之予以因循的行動——來對世界進行道德干預,他對彌合自然與人類、非規范與規范之間的間距問題的特殊解決方案是,將這種非人類動因的活動正好定位于人類活動的中心(字面上的),作為某些(但不是所有)人類情感之產生和增長的自發性,最終源自天。
在這一點上,孟子自己提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定義:“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孟子·萬章上》第六節)他可能不是字面上的意思,甚至不是去否認一個神圣的動因,而是簡單地意味著沒有特定的人類動因去故意做這些事情;它們是由另一個(可能是有意的)動因——天——完成的。歷史上的莊周和孟子是同時代人,激進的莊子對天的作用提出了截然不同但又密切相關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他的出發點是認真地和從字面上理解孟子對天的定義,這個定義在當時可能已經很普遍了。孟子的意思可能是,天是任何沒有人類干預而發生之事情的非人類動因的名字,而對于激進的莊子來說,天只是所發生之根本沒有可識別動因的事情的一個名稱:這是一個替代性的空白填充詞,代表了真正無動因的自發性。發生的事情不是人之所為,也不是被稱為“天”的某人或某物之所為——這種動因的缺乏,無論是人還是神,現在都是當“天”這個詞被使用時之所指。這種情況導致了許多自我指涉的悖論和修辭的間接性,這是《莊子》所特有的。
此外,鑒于沒有一個動因如同天這樣具有可識別性,因此也沒有一個具體活動如同天的活動一樣比其他活動更具有可識別性。孟子認為某些自發事件優于其他事件——即屬于人類的心之器官的道德沖動,它優于屬于人之其他器官的那些自發功能——這種觀點已經過時;它們本身的自發性,缺乏一個可被發現的動因,現在這正是這個“天”的生產性能力之所在。這個“天”不是一個具體的存在物——也就是說,它已經成為一個表述沒有任何具體存在物的詞匯——它無所在,同樣地又無處不在。
激進的莊子通過對身份確定性(identifiability)概念本身在哲學上復雜的批判得出了這一結論,伴隨著這樣的動因,他運用了初步性邏輯話語(a nascent logical discourse)的詞匯,開始對傳統上接受的判斷、區分和意義歸屬的可靠性提出質疑。在激進的莊子中,這些問題轉向對身份的明確屬性所必然具有的視角本性(perspectival nature)的探究,而這一方式必然會導致對任何身份屬性的自我破壞。設定一個身份,就是區分什么是那個東西,什么不是。這種區分是根據一種視角進行的行動;但是這種視角自身也是具有某種身份的東西,是被設定與其他視角相對立的東西。因此,莊子認為,假設一種視角,從定義上來說,也就是假設一種替代性視角。但是,根據定義,這種替代視角會給出不同的區分,包括“此”(自身)和“彼”(另一個視角)之間的根本性區分,而這與最初設定的視角和最初設定的身份上的區分是矛盾的。因此,設定任何一種給定的視角同時也是設定了一個矛盾的視角;給任何事物賦予一種身份屬性,也就是在同一行動中為它設定了一種矛盾的身份屬性。這里所引用的結構可以通過考查某些常見的指稱詞來予以說明:說“此時”是與說“彼時”相對而言的——但如果“彼時”存在,它也必須是“此時”,這反過來使得原來的“此時”成為“彼時”。類似地,說“我”是與“你”相對而言的,但是這個“你”的存在使得他(這個“你”自身)也成為“我”,而對他(這個“你”)自身來說“我”也是“你”。說“這里”就是假設了“那里”,而“那里”本身就是“這里”,相對于“這里”,原來的“這里”變成了“那里”。對于激進的莊子來說,同樣的問題適用于任何實體,物理的或形而上學的,邏輯的或經驗的,抽象的或具體的,只要它是確定的,是一個相對于“彼”的“此”。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非由人所為之事不再被看作是由某人或某非人所為之事;更確切地說,任何試圖確定一個動因的努力都必然會假定一個替代性視角,從而使得它不再是那個動因。因此,我們自己的行為,以及自然世界的事件,根本不能歸因于任何明確的動因,甚至也不能明確地歸因于動因的缺乏,它們作為一些特定狀態和相對應的否定狀態,同樣也成為這種身份確定性批判的犧牲品。那么,對于激進的莊子來說,在同一個敲擊下,非人類(如神)的動因與人類的動因就同時消失了。第二篇,激進的莊子的零起點,開始于對自然事件(即天),以及對以情感、行動和話語的形式(即人類自我)表現出來的,人類對事件的所有劇烈變動之反應的,它們背后的動因或“真宰物”之尋求的失敗。這種“真宰物”在兩種情況下都被尋找過了,但從來沒有找到過,因為一旦任何東西被確定為符合這個要求,它的身份,作為一種視角的產物,由于該視角必然假定了破壞它的替代性視角,就被顯示為對它自身的破壞。在不斷變化的表象背后尋找一致性的身份,這種尋找及其失敗都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很明顯,在所有的經驗中都潛伏著一些“他者”,一些與自身不一致的東西,一些滑溜的和不穩定的存在,然后它們被誤認為是指向一個與自身完全一致的,不滑溜和穩定的,超越性的他者實體:天或自我。為了消除這種關于天和自我的幻覺,首先要注意的是,以所有可識別物之創生者的身份,根據假設,它們都沒有自己的特定身份;如果是有特定的身份,它們就不會是所有身份的創生者。(顯然,像神學范疇中的自因這樣的東西,不會被認真地認為是解決這種擔憂的方法。)因此,即使它們必須存在,它們也不可能有一個特定的身份,而且無法弄清楚一個沒有身份的東西與無人和無物有什么不同。但是,同樣的道理,無人和無物與一個不可識別的事物,它們之間也是無法區分的:“無物”的意思與“我們無法以任何方式識別的事物”之間沒有什么不同。天和自我的明確的缺乏也是不允許的。天或自我的存在,作為神性或是人性的動因,它們的存在與它們的不存在之間沒有區別:有或沒有它們,一切都一樣。它們不可能既是某樣東西又什么也不是,不可能既不是確定的存在又不是確定的不存在。應該指出,這不僅適用于事件的來源,也適用于事件的結果,因此也適用于事件的意義。事物既沒有任何可識別的來源和意義,也沒有來源和意義的明確的缺失。
通過上述的邏輯探究,無論是作為一個來源(天、自我)還是作為一個產物(自然事件或個人的經驗和行為),這種牽涉于被認定為無身份之物的內在混亂,一個虛無的事物和一個事物的虛無之莫比烏斯環(Mobius-strip),它們被認為與身份的本性相關:擁有一個身份并不意味著絕對擁有那個身份,因為一個身份依賴于一個視角的屬性,而一個視角也總是設定了與之不同的視角。每一個創生的來源都會產生另外一個視角,而當下的后一視角自身也會成為一個確定性的創生之源。而且,因為這些產物(特定的經驗)被視為具有不同的含義和不同的身份,這些又取決于它們的來源和結果,這甚至會破壞它們作為自己的創生來源之產物的明確身份。我們無法區分我們所稱的“天”是人的產物,還是“人”是天的產物,因為對任何一種選擇的定位都直接等同于對另一種選擇的定位。這種模式在本文第二篇結尾著名的蝴蝶之夢的故事中表現得最為優雅:莊子夢見自己變成了一只蝴蝶,但醒來后他會想,他剛才所經歷的他作為莊子的身份,在前一刻夢為一只蝴蝶,但這不僅僅只是一個夢,在夢中他剛才夢到的蝴蝶也正在做夢。這無法可說。一旦他夢見他是一只蝴蝶,那么同樣可能的是,莊子,作為夢見蝴蝶的來源,他也是蝴蝶的所夢,從而使蝴蝶成為夢見莊子的來源。這里我們又有了在指稱語中看到的相同結構:“此時”必然與“彼時”不同,但是“彼時”的這種定位使得原始的“此時”同樣是“彼時”。通過將來源與產物、夢者與所夢區分開來,莊子變得無法與產物、與夢區分開來;作為產物,所夢者,蝴蝶變得無法與源頭、與夢者區分開來。兩者的同一性被破壞了,因為每一個都是與另一個相對照的自身,但是在定位這一個的時候,另一個的視角也被定位,而從后一個視角看,自己也是一個夢中的幻象。這使得哪個是哪個背后的真正的自我,是必然不可知的。它們之間必須有一個區別,但是,同樣地,關于哪個是哪個的來源,其中必然是混淆的;關于哪個還原到哪個,哪個是真實的身份,并被欺騙性地表達為另一個,其中也必然是混淆的。這就是莊子在萬物與它們所區別的事物的關系中,以及在它們所有的相互轉化中所看到的。
從這些考慮中出現的是一種神秘的不可知論,一種類似于虔誠的消極神學與孤立的虛無主義懷疑論的融合。在這些看似對立的立場的不可區分中,我們找到了激進的莊子獨特的宗教哲學的出發點。這通常采取三步程序的形式。首先,我們證明了區別對于任何身份歸屬的必要性。然后,鑒于它們必然會自我破壞,我們對公認的區別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就像一些邏輯學家一樣,我們認為所有的區別都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我們認為所有事物都是無差別的一體。但是,在最后一步,這種同一性也成為這個同一批評的犧牲品:“一體性”和“非一體性”之間的區別在這種視角性邏輯中不再存在。這樣,無論是最初的區別,還是作為第二個的缺乏區別都站不住腳;但這個不可避免的悖論并不被認為是一個導致死胡同的反對或反駁,而是一個積極的結果:一個存在著的,或者“任何”一個存在著的,任何一個特定身份的不可忍受性,帶來了一種“忘”和“化”,或者換句話說,一種“滑”和“疑”所描述的幸福狀態。“忘”或“疑”是對區分的破壞,這種區分將使得任何身份或其缺乏變得確定。“化”或“滑”是對不可避免的他性的肯定,這種他性貫穿于任何假定的身份之中,因為每一種身份都假定了一系列無限的,它在或來或去中得到轉變之可能的交替性身份。“忘”或“疑”是對當下之身份的領悟,這種身份已經是此時此地的那些交替性身份中的任何一個,因為它可能是其中任何一個的表達或方面。正如在蝴蝶之夢中,每一個瞬間都會意識到這一個問題:這個當下的我是不是一個夢者,他把所有過去和未來的身份用作現在的自己之所夢,以及過去之夢中的身份是不是這個現在之夢中身份背后的真實身份。因此我們達到了在所有的視角中實現無障礙的轉換,從而保證了所有可能的區別之間不斷的相互轉換,以及保證了所有可能的從相互定位的視角中產生的所有可能性區別的無限系列,它們之間不斷的相互轉換。這種轉變之所以是“無障礙的”,是因為它不僅僅是從一種確定的狀態到另一種不同但同樣確定的狀態的變化;更確切地說,這些不同的狀態可能一直是從以它們作為所夢的夢者狀態之變化而來的。這就是莊子的三步曲:第一步,建立傳統的區別;第二步,從這些區別到對這些區別的質疑和對“一體性”的設定;第三步,從“一體性”到“忘”以及所有區別在它們彼此的開放性轉化中的復活。
這種多產的不穩定性現在被體驗為一種非常具備生產性的力量,這種力量以前被歸因于“天”,盡管現在總是伴隨著隨后的抹除或反諷性的后退,它仍然有時會被以那種方式予以指示。激進的莊子有時會用“命”來代替“天”,而“命”在傳統上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它讓事情按照自己的方式發展,但現在這個詞被明確地表述為當根本找不到動因——包括天(第六篇,結尾)——時使用的詞。這些事件不歸因于任何單一的來源,不被賦予任何單一的意義,不是由任何單一的動因導致的,不可簡化為任何單一的原則。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正如我們將在下面看到的,從最擬人化的到最不擬人化的,一大堆術語被用來替代“天”和“命”:造物者,造化,大塊,陰陽——但最著名的術語還是道。對“道”這一術語的使用,在激進的莊子處,正如在《道德經》中所使用的,是對這個術語先前含義的反諷性顛倒。這種顛倒完全符合于在絕對懷疑論和神秘洞察力之間的,以及在恒常在場和恒常缺失之間的,對它們之間的交互性的發現。“道”的原意是“道路”,長期以來一直被用于一種方法或手段的稍微延伸的意義上,即達到特定目的的一個培養過程或程序——例如,仁義之“道”,圣王之“道”,射箭之“道”,乃至天道(如季節的交替和輪換,農作物的產生和生長)。從字面上看,道是使事情發生的東西,是使一個人達到預先指定的結果的東西,是一個人正在尋找的任何東西,是被一個人定義為重要的、在相關意義上是真實的事實和真實的善的任何東西。然而,激進的莊子談到了“不道之道”(第二篇)——即一種非特定的讓事情發生的方式,一種沒有特定動因的方式,一種不包含以目標作為特定愿景從而追求合法結果的方式,一種在沒有自己或其他任何人(無論是人還是神)知道如何或為何的情況下得以完成的方式。矛盾的是,我們可以稱之為一種完美的無神論,這種無神論與一種徹底的無目的的生殖力的神秘愿景相融合,從而不僅是對物體的旺盛生產,而且是對價值、觀點、視角、意義的旺盛生產,以及是對物體如何被區分、分類、識別和評價之交替性定義框架的旺盛生產。激進的莊子甚至不承認事物、行動和視角的來源和結果有確定性身份的可能性,無論它們是宗教思想中的天,或者是對天的明確否定,都將等同于作為來源和結果的明確的虛無;如同在一般的無神論或者是直接的多元論中,線性因果關系在每種情況下都將單個原因歸結為單個結果,而因為無論是單個的具體原因或是普遍原因都不可能有明確的身份,從而就其本身而言不會使得它也成為同樣可能的相反身份的載體。這意味著沒有單一的意義或身份可以歸因于任何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意味著身份和價值的無窮無盡的轉換是存在的內在因素。然而,這并沒有導致虛無主義的絕望,而是對世界的一種新的開放,這種開放超出了最初通過與“天”或早期含義的“道”之明確聯系而尋求的開放;現在它是“道”本身,是在所有方向上,在每一個位置和每一個其他位置之間的互聯和開放。這就是激進的莊子所說的“道”。
二、激進《莊子》中的精神修煉與神秘體驗
在文本中的一些地方,我們發現了可能被歸類為否定神學之精神實踐的描述(見“否定神學和肯定神學”詞條)。它們并不涉及對瑜伽式姿勢或觀想的任何詳細描述,而是逐步清除頭腦里的先入之見、對具體的固定視角的執著以及對什么是真什么是對的判斷。在這里,我們再次看到懷疑論和神秘主義的融合。這些狀態和實踐被用這樣的術語來描述:“吾喪我”;“心齋”;“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忘仁義禮樂”;“外古今,外天下,外物”;“虛而待物”;“用心若鏡,應而不藏”;“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朝徹”;“見獨”;“體盡無窮,而游無朕”;“攖寧”;等等。這些似乎都指向如上所述之對事物和自我的可識別性之懷疑性洞見的應用,并保持一種不接受任何結論,不將任何特定的單一性來源和任何特定的單一性目的或意義歸因于任何經驗之上的狀態;滑移和懷疑、變化和遺忘被重新連接起來,不斷涌現的新事件和新反應相互交織,它們沒有明確的來源,也沒有任何單一的長期目標。因為通過有效原因和通過最終原因的解釋,無論是來源還是意義,都需要一些具有明確身份的術語(即有效原因或最終原因本身),但這種可能性是莊子所拒絕的。
正如鏡像隱喻所暗示的那樣,清空先入之見本身在這里被視為一種增強大腦的敏感性和反應能力的方式,允許它適應每一個涌現出來的視角之不斷變化著的微觀需求,既保護一個人免受損害,又允許各種視角自由地相互轉換而不受阻礙。這在第三篇開頭的著名故事中具有戲劇性的象征意義,這個故事講述了一個屠夫的刀穿過形成牛身體紋理的開放通道。刀刃(莊子式的人)沒有“厚度”——缺乏任何明確的可識別性,已經“無我”——它進入牛身,允許對牛的經驗發生改變:不再是一堆堅實的可識別的障礙物,而是在每一個點上都顯示為空的通道——非同一性存在——通過它們,刀子可以穿過。這既保護了刀免于磨損,也形成了通道,為通過牛的世界掃清了一條通途,一條道,一條“路”,改造它,并將它向著與世界的進一步轉化和相互聯系開放(例如,成為帶來了愉悅、消耗、消化、能量、其他動物活動的食物)。穿過牛的出乎意料的曲折和分支路線是一種道,但是這種道不是道,也就是說,這種道不能作為引導刀的一組固定道路而被預先勘測。因為莊子的新意義上的“非道之道”是一種通暢的開放,也意味著不可預見的轉換和聯系。它們不僅是在事物之間,而且是在對事物的視角之間。在刀的接觸下(當下的視角),每一條道路都轉變成其他的道路,每一個身份都轉變成其他的身份,意想不到的曲折之路展開成為新的道,因為在刀的每一個位置(即在每一視角下)它們的身份和聯系網絡都會發生變化。刀必須到達每一個接合點,以探測該走哪一條路,而正是它的存在打開了新的和不可預見的道路。從此刻之前的視角來看,當刀還沒有到達這個新的位置和它的視角時,它可能看起來完全不可通行和受阻,沒有道路(開口、通道、路徑)可用,而從此刻之后的視角來看,當刀離開時,它可能再次被封閉。牛(世界)被刀改變了,一個非結論性的、反應靈敏的、莊子式的人把他的頭腦當作一面鏡子,通過清除其呆滯的、堵塞的、先入為主的形式而創造出意想不到的通道;這種觀念被延伸開來,指向這樣一個虛無的、沒有固定身份的人,他盡管沒有帶來可識別的積極內容,沒有提供道德指導或理論結論,但卻以某種方式改變了他人,甚至可能改變了社會政治環境。另外,所有這一切都源于身份——包括定位身份之視角的同一性——的內在不穩定性,這種看似癱瘓的虛無化的懷疑主義反而變成了對自己和所有事物之轉化的生動而幸福的諧調,這種轉化是由對所有區別的擁抱和涵括所構成的。
三、死亡問題
對于激進的莊子來說,死亡也是根據這種徹底的不可知論,以及伴隨著的對于轉化的開放性來處理的。在這種處理中,我們再次看到莊子的三“步”曲。在第六篇中,我們被告知有四個朋友破除了“生”和“死”之間固定性區別的確定性,他們注意到了這些成對術語的不可分離性破壞了每個術語的簡單同一性。第一種方法是“一體化”:他們將生與死視為“一線,一體”,作為一個整體,它本身既不是生也不是死,出生前的無是頭部,生是脊柱,死是尻部。這些朋友中的一個突然生病,瀕臨死亡。他從動因的同一性的角度,用模糊的自然神論術語,探索了這種一體性:他說,實際上,“造物者使我暫時成為人,以生命為脊柱,現在將帶來另一次轉變;我不知道那會變成什么,就像不知道在變成這個人之前我是什么一樣(1)《莊子》此處的原文似乎應是“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作者作了較大的改寫。”。值得注意的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在生前或死后一直是一個實體。一個特別規定的存在之虛無,頭部;這個人,脊柱;轉化為許多其他存在,如此人之死亡,尻部:“假使化我之臂以為此,化我之腿以為彼,化我之神以為它者,化我之尻以為另一它者。”(2)《莊子》此處的原文應該是“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作者作了一定的改寫。無論如何,沒有什么可抱怨的:他接受了上天在生、死兩方面之不可避免的行動。
在這里,身份的不可知性通過時間分布被稀釋了:他知道他現在作為一個人活著,這沒有問題,但這只是一體之中的脊柱,還有未知的大量其他身份被賦予為它的多個的頭和尻。這回避了一個問題:即使是現在,他是否能正確地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因為他是這個不可知的一體中的一部分,但在這個階段,這個問題沒有被問及,而是類似于直接服從死亡的天意。但后來另一個朋友生病了,他再次談到這種一體性及其深不可測的歷程,不再那么神化,但同樣虔誠:不是“造物者”,而是“造化”,然后隨便切換到不是那么統一和擬人化的名稱,如“陰陽”和“大塊”,來作為所有變化的動因。但是,它們現在以同樣的職責成為傳統的生與死之間區別的去除者:就像一個巨大的熔爐,造化的過程讓我們時而變成一個東西,時而變成另一個東西,或者變成許多其他東西,我們既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從哪里來或去哪里——“惡乎往而不可哉!”這里對宇宙的不穩定性提出了一種信任的態度,這種態度仍然奇怪地類似于一個虔誠的有神論者的態度,仿佛植根于自然神論的信念,即宇宙是由一個仁慈的天意所統治的,它安排所有的善,但實際上是基于對所有的價值的肯定,這些價值必然與我們自己,從我們的視角來看,碰巧認為是善的(即我們自己的生命,它有自己的偏執的視角,正好認為自己作為生命,是善的)相關聯:“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但這只是三步走的開始。在下一個故事中,我們有三個不再談論一體性的朋友。現在我們被告知這些朋友們已經把一體性給遺忘了:他們“相與”于“無相與”(即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沒有設定任何“一體性”,而他們的不同身份都是這個“一體性”的一部分),“相為”于“無相為”(即沒有設定任何單一的共同目標)。我們不再被歸結為一個動因或一個整體或所有事物與階段的一個意義。不再有任何普遍性的概觀,甚至是整體性的概觀,甚至是從當下視角而觀之的整體性的概觀。剩下的只有永無止境的轉化和相忘,不僅是在彼此之間的轉化和相忘,也是我們在某個更大的身份或事業中彼此合一的轉化和相忘。
最后,在第三個故事中,我們被告知一個人把死亡簡單地視為轉化和遺忘,沒有任何關于是什么使他生存或死亡的知識(因此不再談論造物主,或過程,或熔爐,或甚至是一個無差別的大塊),沒有任何一體性,沒有任何關于某種無知或無心之相與的斷言,沒有任何關于之前或之后會發生什么的猜測,也沒有任何關于他當下是誰或是什么的確定知識:就在任何轉化的過程中,他只是簡單地拋棄了之前和之后的一切,但是隨之他對自己現在身份的確定性也消失了。他現在甚至對自己當下是什么,是活著還是死了,是脊椎還是頭部還是尻部,都不做判斷。關于他的狀態,我們被告知,“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于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夢者乎?”他不能跳出自己的外殼去達到一個之前或之后,或一個基礎或原因,或一個結果或意義,這意味著他甚至不能真正知道他現在是什么,以及是否以后的事件顯示他會成為完全是另外的東西,會成為完全是別人的一個夢。與相反狀態的同一性現在甚至破壞了所假定部分的確定的身份,并隨之破壞了將任何部分的身份歸入任何確定的“一體性”中的可能性,甚至破壞了確定的“相與于無相與以及轉化的無限性”。這種純粹的不可知論就是“天”所等同的一體性和多產性。因此,在同一篇中,我們被告知,對這樣的人來說,“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這篇文章中所使用的夢的意象又一次讓人回想起已經提到過的莊子著名的“蝴蝶之夢”,它也說明了同樣的問題。莊子不知道他現在是被他剛剛夢見的蝴蝶夢見了,還是相反。如果莊子是蝴蝶的夢,那么即使是作為莊子的這一刻,也是蝴蝶的另外一面,是作為蝴蝶之存在的經驗中的另外一個部分;莊子是蝴蝶身份的一個側面。如果蝴蝶是莊子的夢,那么即使它在周圍飛舞,也確實是莊子經驗的一部分,是作為莊子存在的一部分。僅僅是交替性的對比視角的設定,就使得以任何明確可知的方式簡單地成為一個身份或另一個身份變得不可能,哪怕只是一瞬間。然而,它們并沒有崩塌成為一個整體:它們之間必須有一個區別,即使不知道它們是什么,它們是哪一個,因為沒有區別就不可能有“哪一個”的問題。所有的身份都在它們無可辨認的無障礙的相互轉換中被保留和廢除了,文本中稱之為“滑疑之耀”。
四、傳統的莊子
這就是激進的莊子。但是從三十三篇選集的整體上看,我們發現作為傳統的基礎主義者的莊子占據了文本的大部分。在這里,莊子三“步”曲的第二步傾向占主導地位:破壞傳統的區別,優先考慮一體性,盡管這也包括在這種一體性的力量之內或通過這種一體性的力量而存在著的諸區別形式之間的連續變換。它有時仍被稱為“道”,但現在有時也稱為“氣”或生命的能量,并構成了一種轉化中的形式的連續性:一種在傳統性區分的相對面之間的,如實體與虛空、無形和有形、美與丑、生與死之間的轉化。傳統的莊子也假定一種天生的本性存在于個體事物中,它們原本是由“天”或“道”或原始的精妙之“氣”所賦予的,而這是激進的《莊子》中沒有提到的東西。這種與生俱來的本性是存在于個體身上的不可分割的道,它們還沒有被倫理性的善、惡之間的傳統區別,或是愉悅性的享樂與不愉悅的體驗之間的對立所割裂;它們是無差別之道的樸實的原初性流出。這一固有維度有時也被描述為一個基礎性的、天生的“技藝”(或美德,德——激進的莊子使用這一術語僅指“滑疑之耀”的有效的、相互聯系的力量,但是沒有任何與原始稟賦的明確關系去將它與特定的來源如“道”或“天”聯系起來)。在個體化的形式中重新與這種原始的、無差別的、轉化性力量的狀態連接起來,現在它們是一些已經描述過的否定性實踐的目標,從而把我們從一種偶生的、守舊的區別中解放出來,迄今為止這種區別一直阻礙著這種狀態中的自由的技藝性功能。(這很容易與《孟子》中“性”一詞的突出使用相混淆,但應該與它有明顯的區別,后者認為這種與生俱來的本性是人類道德情感的自發沖動。)遺忘,對區別的遺忘,這一對于激進的莊子來說的第三個步驟,其中被遺忘的區別在這里常常被狹義化為只是施加于原始未分割的性或德之上,而不是像在激進的莊子處,還包括對未分化的、生產性的、前生產的同一性本身的遺忘,包括對道的遺忘,對天的遺忘,或對天與人、自然與人為、自發與故意之間的區別的遺忘。這允許在基礎主義者的意義上與對“道”的更為傳統的使用聯系起來,正如它在后來的中國思想中被理解的那樣,即作為宇宙的來源,途徑,甚至是所有事物的原材料(這容易與更嚴格的形而上學的或絕對實體的物質概念相混淆,在其他傳統中,這種絕對實體是所有事物的來源或創造者),或者是與人工區別,以及有意的文化和社會區分相比較,而偏好于自然性、自發性和無分別性的單邊價值穩定狀態。在這種語境下,已經描述過的那種排除了先入之見和結論的否定式實踐和體驗,被解釋為是對原始的精妙之“氣”或未被扭曲的“德”或天生之“性”的原初狀態的回歸和保存。這有時與各種高度強化的藝術和技術技能聯系起來,促進了看似奇跡般的精湛技藝,而在其他時候則與一種原始的、前文化的生活方式相關,后者既避開了社會推崇的道德努力,也避開了社會鄙視的享樂奢侈(例如,在第八至第十篇中)。
但在其他部分,傳統的莊子增加了另一個轉折,將截然不同的兩個方面重新組合成一個可供選擇的綜合體。在這里,自發的和有意的、未分化的和已分化的之間的穩定關系,被視為確保人類領域——包括其社會和政治方面——本身之更好的組織和功能的一種方式,而人類領域本身是有意的和分化性質的(特別是在第十一篇至第十六篇和第三十三篇)。
《莊子》文本所包含的內容,當然遠遠超過了這個簡單的總結所能呈現的。在它的頁面上,我們還可以找到關于政治的建議,社會批判,對孔子和當時其他思想家的諷刺,對語言和思辨的形而上學結構的批評,它自己的冒險的宇宙學推測,深奧的笑話和超現實主義幻想的飛翔,等等。
五、文化的莊子
把《莊子》作為一個完整的三十三篇文本來閱讀,作為一個作者——莊周——的作品,是中國兩千年王朝歷史中占主導地位的解釋方式。就文化重要性而言,這個“莊子”比我們在文本歷史和哲學基礎上,對不同的作者來源作出推論,從而區分出來的兩個虛擬人物有更大的影響。文化的莊子顯然沒有看到激進的莊子和傳統的莊子之間的矛盾。要么是激進的莊子為傳統的莊子在實際和政治生活中的各種應用、甚至是為基礎主義的推斷創造了條件(畢竟現在所有的視角都是允許的,為什么這些不可以呢),或者反之亦然(激進的懷疑主義是一種臨時療法,旨在去除過時的區分,并回到原初的一體性和自發性;對原初的一體性的拒絕只是修辭上的炫耀)。在這兩種情況下,文化的莊子認為,任何一種表達方式都可以從任何一方直接轉入另一種表達方式,顯示了這兩種觀點之間的暢通無阻的相互聯系和轉換——這一點很容易被激進的莊子或傳統的莊子接受,盡管出于不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