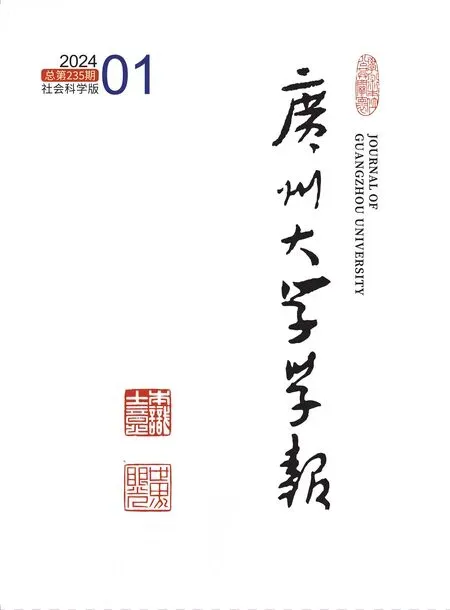新媒介文學(xué)閱讀的文化邏輯及其闡釋路徑
劉亞斌
(浙江外國語學(xué)院中國語言文化學(xué)院,浙江杭州 310023)
新媒介技術(shù)的廣泛運(yùn)用給傳統(tǒng)文學(xué)及其體制帶來諸多變化,“網(wǎng)頁擠占書頁、讀屏多于讀書、紙與筆讓位于光與電”[1],產(chǎn)生了新型的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隨后發(fā)展出博客或微博文學(xué)、手機(jī)文學(xué)以及各種自媒體文學(xué),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發(fā)展態(tài)勢,而閱讀模式則由印刷時(shí)代的紙本閱讀轉(zhuǎn)變?yōu)閿?shù)字時(shí)代的屏幕閱讀。文學(xué)的生產(chǎn)和閱讀背后都有其文化邏輯,如何看待新媒介文學(xué)閱讀的文化邏輯呢?學(xué)術(shù)界依據(jù)社會(huì)性質(zhì)、新媒介特征和文學(xué)文本表征等闡述路徑,形成了文化邏輯上的現(xiàn)代性、后現(xiàn)代和數(shù)字現(xiàn)代主義三種觀點(diǎn)。本文在對其梳理、評(píng)述與反思的基礎(chǔ)上提出,盡管新媒介文學(xué)存在多種類型,但其在技術(shù)上都有共同性,即作為人機(jī)交互中介的界面技術(shù)的運(yùn)用,界面成為新媒介文藝活動(dòng)基礎(chǔ)性、核心性的存在條件。界面并非簡單的、工具化的、作為呈現(xiàn)載體的屏幕,而是人工智能、軟件程序和數(shù)字化技術(shù)打造的具有操作、融合、呈現(xiàn)和生成特性的虛擬平臺(tái),文學(xué)閱讀是在界面上進(jìn)行的,即界面閱讀,而非僅僅是屏幕閱讀(讀屏),這樣才能較為準(zhǔn)確地把握新媒介文學(xué)閱讀在文化邏輯上的闡釋路徑,加上其具有“虛擬后現(xiàn)代”的特性,從而為新媒介文化、文學(xué)閱讀與闡釋學(xué)的關(guān)系提供了一種可能性表述。
一、現(xiàn)代社會(huì)的決定性因素及其問題所在
不僅新媒介文學(xué),還有賽博藝術(shù)、電子游戲和網(wǎng)劇、動(dòng)漫及其周邊產(chǎn)品,都是通過操作界面來創(chuàng)作和閱讀的,界面閱讀越來越成為當(dāng)代社會(huì)普遍的閱讀方式,具有劃時(shí)代的特征和意義。不過,學(xué)術(shù)界幾乎沒有使用“界面閱讀”的說法,而是將其稱為電子閱讀、電腦閱讀、數(shù)字閱讀、屏幕閱讀、視屏閱讀,甚至新媒介閱讀等等,屏幕閱讀是其中使用率較高的稱呼。無論命名如何,面對新媒介技術(shù)主導(dǎo)下的閱讀,書籍閱讀都顯得過時(shí)、保守和傳統(tǒng),其閱讀市場的占有份額呈逐年下降的趨勢。費(fèi)希爾(S.R.Fischer)預(yù)測說,“屆時(shí),‘閱讀’無一例外地在電腦屏幕上進(jìn)行,而有形圖書將成為明日黃花”,他將兩種閱讀行為進(jìn)行對比,認(rèn)為讀書是傳統(tǒng)閱讀,具有古典性,屬于印刷時(shí)代的產(chǎn)物,讀屏則是現(xiàn)代閱讀,具有現(xiàn)代性,屬于電子時(shí)代的產(chǎn)物;雖然傳統(tǒng)書籍依舊存在,但卻為“收藏者青睞,其裝幀成為人們珍愛的藝術(shù)品,外在的統(tǒng)一成為質(zhì)量與傳統(tǒng)兼顧的不朽‘印記’”,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和技術(shù)的更新,“現(xiàn)代閱讀活動(dòng)分化發(fā)展,更為引人入勝”,電子閱讀將“會(huì)成為唯一的原型”。[2]雖然費(fèi)氏沒有明言電子閱讀的文化邏輯是現(xiàn)代性,但其字里行間均表露出閱讀范式的轉(zhuǎn)換是以當(dāng)下新事物的出現(xiàn)為分界點(diǎn)。現(xiàn)代多指“現(xiàn)在”“當(dāng)下”之意,突顯當(dāng)代社會(huì)的性質(zhì)和特點(diǎn),與此相反的便屬古典或傳統(tǒng),這并非學(xué)術(shù)界對現(xiàn)代性和古典主義的嚴(yán)格定義,這種看似大眾性的口頭禪、流行語,其實(shí)是某種無意識(shí)癥候的表現(xiàn)。
“現(xiàn)在”與“現(xiàn)代”一字之差,的確容易造成混同,成為不經(jīng)意之舉,實(shí)際上還是能說明問題的。其一是有隱性的學(xué)理支撐,哈貝馬斯(J.Habermas)所稱的“未完成的現(xiàn)代性”表明,當(dāng)今社會(huì)依然是現(xiàn)代性的延續(xù),而非后現(xiàn)代社會(huì),其閱讀文化自然與當(dāng)代社會(huì)的現(xiàn)代性質(zhì)有關(guān)。其二,從閱讀媒介變遷的視角比較古典性與現(xiàn)代性,審視當(dāng)代閱讀的文化邏輯,在寫作思路上是更為常見、便捷的選擇。其三,不少走在現(xiàn)代化途中的國家和地區(qū),其社會(huì)性質(zhì)呈現(xiàn)出復(fù)雜的面向,但總體上依舊歸屬于現(xiàn)代社會(huì)。對此,國內(nèi)學(xué)界在探討讀書與讀屏的關(guān)系時(shí)便有所體現(xiàn)。研究者認(rèn)為,傳統(tǒng)讀書乃是讀者的“單向性索取”,缺乏互動(dòng)和交流;現(xiàn)代閱讀將娛樂和休閑相互交織;屏幕閱讀則是將兩者結(jié)合,更為自由包容;“現(xiàn)代電子視屏閱讀也是現(xiàn)代信息技術(shù)發(fā)展的一種閱讀必然”,其多維性“可以對傳統(tǒng)紙質(zhì)文字讀物進(jìn)行很好的補(bǔ)充”,而視屏閱讀處于現(xiàn)代視野中,是現(xiàn)代信息技術(shù)的必然。[3]有論者繼續(xù)指出,當(dāng)代中國社會(huì)仍然是現(xiàn)代性語境,與傳統(tǒng)紙質(zhì)閱讀對比,手機(jī)閱讀表現(xiàn)出文本內(nèi)容的陌生化、承載方式的微型化、接受方式的人性化和傳播方式的快捷化等文化性質(zhì),“在現(xiàn)代快節(jié)奏的社會(huì)中,以手機(jī)為載體的‘碎片化’式閱讀作為‘讀屏?xí)r代’的一種流行趨勢,其地位已然遠(yuǎn)遠(yuǎn)超過真正意義上的傳統(tǒng)紙本閱讀”,“碎片化”(fragmentation)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獻(xiàn)中”,俄羅斯形式主義者提出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后現(xiàn)代創(chuàng)作技巧,在藝術(shù)上打破常規(guī)、超越常境,“達(dá)到以‘震驚’代替‘靈韻’的獨(dú)特審美效應(yīng)”,不斷沖擊、刷新讀者的期待視野。[4]后現(xiàn)代的思想觀念被用于把握手機(jī)閱讀的特點(diǎn),集中在創(chuàng)作技巧和方式的闡明上,并沒有規(guī)定為界面閱讀的文化邏輯,而是被納入現(xiàn)代社會(huì)語境,展現(xiàn)一種現(xiàn)代性訴求。
實(shí)質(zhì)上,整個(gè)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社會(huì)與文學(xué)的糾結(jié)和錯(cuò)位,傳統(tǒng)、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的夾雜和混同,因而難以準(zhǔn)確有效把握當(dāng)下閱讀的文化邏輯。就社會(huì)形態(tài)而言,當(dāng)代中國還走在現(xiàn)代社會(huì)的道路上,其閱讀性質(zhì)歸屬于現(xiàn)代性邏輯也無可厚非;就屏幕閱讀觀之,不僅閱讀對象即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本身有后現(xiàn)代技巧和觀念的運(yùn)用,其載體媒介也使閱讀表現(xiàn)出碎片化、非線性和拼湊疊加等后現(xiàn)代特性,而界面形成的平臺(tái)空間又具有包容性和自由性,傳統(tǒng)閱讀內(nèi)容和方式都能融入進(jìn)去;從現(xiàn)代性上看,其內(nèi)涵并不明晰,現(xiàn)代閱讀或是具有電子化特征,或是具有娛樂和休閑性,或是顯示出陌生、微型、人性和快捷等文化性質(zhì),而傳統(tǒng)閱讀并不缺乏人性、休閑,尤其是娛樂表現(xiàn)。進(jìn)一步說,社會(huì)性質(zhì)能否為不同的閱讀統(tǒng)一文化基調(diào)?媒介特征是否就影響了屏幕閱讀而使其具有相同的性質(zhì)?文化邏輯里傳統(tǒng)、現(xiàn)代和后現(xiàn)代到底有什么區(qū)別和聯(lián)系?簡言之,社會(huì)形態(tài)、媒介技術(shù)和當(dāng)代閱讀及其文化邏輯具有同一性嗎?很明顯,將新媒介文學(xué)的閱讀性質(zhì)定位在現(xiàn)代性上,多半是出于對社會(huì)性質(zhì)判斷的延續(xù)之舉,其闡明路徑具有相當(dāng)?shù)哪:院兔苄裕萑氲交焱臓顟B(tài)中。
如果說上述研究者對當(dāng)下閱讀的現(xiàn)代性邏輯的論斷是出于一種社會(huì)性質(zhì)決定論,且對其要素間的關(guān)聯(lián)思慮不足的話,那么其他學(xué)者則對社會(huì)、媒介和文學(xué)閱讀有明確的、自覺的界限意識(shí),認(rèn)為三者不能混為一談。孫菲提出,后現(xiàn)代主義有其西方社會(huì)的文化背景,是后工業(yè)時(shí)代培育和發(fā)展的結(jié)果,盡管后工業(yè)因素在網(wǎng)絡(luò)里也有所體現(xiàn),但是從整體上看,“中國現(xiàn)在還是處在現(xiàn)代化的歷史潮流中”,網(wǎng)絡(luò)作品的后現(xiàn)代摹仿只是形似而已,“網(wǎng)絡(luò)的后現(xiàn)代姿態(tài)不代表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后現(xiàn)代姿態(tài)”。[5]其實(shí)質(zhì)仍然是自我欲望的情感表達(dá)、迎合市場的商業(yè)化需求和對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認(rèn)同,而對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不滿則是中國網(wǎng)絡(luò)的本土化特色。由此,不難看出論者的立場是現(xiàn)代性的,這種現(xiàn)代性由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所決定,網(wǎng)絡(luò)傳播才具有后現(xiàn)代性,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表現(xiàn)只是披了層“后現(xiàn)代外衣”的現(xiàn)代性訴求而已。崔宰溶引述了孫菲的觀點(diǎn),更傾向于從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創(chuàng)作入手,批判國內(nèi)研究界認(rèn)為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擁有后現(xiàn)代邏輯的觀點(diǎn)。他尖銳地指出,研究者們不去分析具體的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作品,是因?yàn)椤爸袊W(wǎng)絡(luò)文學(xué)作品當(dāng)中很難找到符合后現(xiàn)代理論的作品”,這些作品不存在后現(xiàn)代的零散化、碎片化和宏大敘事的消失,以及對中心、傳統(tǒng)價(jià)值的否定等標(biāo)志性特征,“我們很容易發(fā)現(xiàn)它不僅不具有后現(xiàn)代性,而且它還往往具有完全相反的特征”。讓人驚訝的是,崔宰溶隨后卻總結(jié)說,“‘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可能是后現(xiàn)代的,但它也可能是反-后現(xiàn)代的,或具有強(qiáng)烈的‘資產(chǎn)階級(jí)現(xiàn)代性’的”。對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文化邏輯判定何以如此艱難呢?恐怕他還是心存疑慮,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復(fù)雜性讓其難下最終的結(jié)論,就拿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碎片化和零散化現(xiàn)象來說,他以太監(jiān)文學(xué)為例,認(rèn)為讀者存在“統(tǒng)一性、完整性的非常強(qiáng)烈的要求”,并以此作為評(píng)價(jià)作品的標(biāo)準(zhǔn)和前提。對于作者而言,太監(jiān)文學(xué)的出現(xiàn)是其整體性能力不足導(dǎo)致的,而其瑣碎化表現(xiàn)則是出于字?jǐn)?shù)增加的利益需求。[6]可是,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確實(shí)有大量的太監(jiān)作品,不管出于何種目的,這是不爭的事實(shí),給予讀者的閱讀感受無疑是零散化的、碎片化的,具有后現(xiàn)代特征。綜上所述,探討新媒介文學(xué)閱讀的文化邏輯除了需要關(guān)注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自身情況外,還需要涉及社會(huì)形態(tài)、新媒介特性和閱讀體驗(yàn)的相互糾纏。到底采用何種有效的闡釋途徑,依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難題。
二、后現(xiàn)代媒介視角的批判
追溯媒介與閱讀的關(guān)聯(lián)史便可看出,口傳時(shí)代的文學(xué)閱讀具有明顯的在場性,受面對面交流的限制,而手稿閱讀也有具體限制,只能在手稿存放處閱讀,印刷技術(shù)的發(fā)明才拓展了文學(xué)接受的范圍,書籍被復(fù)印出來送至世界各地,滿足了讀者在更廣泛時(shí)空內(nèi)的閱讀需求。圍繞現(xiàn)代性范疇所形構(gòu)的理論觀念,如理性思維、個(gè)體化、自律性、中心性與線性觀等,都與印刷時(shí)代讀書行為有關(guān)。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講故事的人》中提到:“小說讀者卻是與世隔絕的,而且比其他藝術(shù)形式的讀者與世隔絕更深。”[7]孤獨(dú)的讀者面對以某種中心意念架構(gòu)起來的線性故事和書寫框架,不斷進(jìn)行個(gè)體的理性反思,現(xiàn)代主體性被紙本閱讀所構(gòu)建并夯實(shí),以個(gè)體自由權(quán)利為基礎(chǔ),依據(jù)平等、理性和契約規(guī)則,現(xiàn)代社會(huì)逐步確立完成。因此,紙媒閱讀才具有現(xiàn)代性,是印刷工業(yè)時(shí)代的產(chǎn)物。
到了后工業(yè)時(shí)代,數(shù)字媒介、電子化、計(jì)算機(jī)和人工智能等技術(shù)的發(fā)展,尤其是互聯(lián)網(wǎng)和虛擬世界的開發(fā),促使新媒介文藝書寫盛行,閱讀文化出現(xiàn)了歷史性轉(zhuǎn)型,超文本成為其標(biāo)志性特征。國外學(xué)者如尼爾森(Theodore Nelson)、博爾特(J.D.Bolter)、蘭道(George P.Landow)、考斯基馬(Raine Koskimaa)等人都對超文本性質(zhì)作過闡述。蘭道著眼于信息技術(shù)的可變優(yōu)勢,將超文本與后結(jié)構(gòu)主義關(guān)聯(lián),認(rèn)為“超文本模糊了作家和讀者的界限,體現(xiàn)出巴特(Roland Barthes)理想文本的另一種品質(zhì)”,即電子時(shí)代的可寫文本(writerly text);與印刷時(shí)代可讀文本(readerly text)相比,可寫文本的超文本性實(shí)現(xiàn)了巴特所說的“使讀者不再是文本的消費(fèi)者,而是文本的生產(chǎn)者”的文學(xué)目標(biāo)。[8]國內(nèi)學(xué)界關(guān)于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后現(xiàn)代文化邏輯的研究,如單小曦,他作了比較全面的概述,提到歐陽友權(quán)、安文軍、張建、賀紹俊、姚獻(xiàn)華、貢少輝和成秀萍等眾多研究者的觀點(diǎn),認(rèn)為他們受到了詹姆遜(Fredric Jameson)提出的深度模式削平、歷史意識(shí)消失、距離感消解和主體性喪失等后現(xiàn)代觀念的影響,強(qiáng)調(diào)后現(xiàn)代的邊緣姿態(tài)、平面空間性、消解中心、消費(fèi)邏輯、機(jī)械復(fù)制、無深度、交互參與、多重話語、零散碎片化、媚俗犬儒和符號(hào)幻象等具體特征。[9]總體上而言,新媒介技術(shù)本身就具有后現(xiàn)代文化品格,其打造的數(shù)字文本形態(tài)對現(xiàn)代性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沖擊,拆解了印刷時(shí)代的線性結(jié)構(gòu)模式,使語言秩序、中心性和理性邏輯等觀念都變得不再可靠。此外,借助于界面的平臺(tái)性功能,電子文本的多線發(fā)展與纏繞雜糅、超鏈接文本塊、隨機(jī)性、跨媒介閱讀等各種網(wǎng)絡(luò)化表現(xiàn),使其意義被不斷內(nèi)耗、延遲和散播以至于虛無化。而讀者呢,則被文本邀約參與其中,可寫、可操作,體會(huì)到一種新的文化精神,即不斷解構(gòu)、無中心、無深度、多元無始化、可逆性、狂歡效果、能指滑動(dòng)與星叢、意義缺場和破壞規(guī)則秩序的后現(xiàn)代精神,因此,新媒介文學(xué)閱讀就是“后現(xiàn)代的一種閱讀方式”。[10]在閱讀文化邏輯上,紙本閱讀對應(yīng)現(xiàn)代性,界面閱讀則自然對應(yīng)后現(xiàn)代主義,這樣的觀點(diǎn)似乎更符合歷史發(fā)展的事實(shí),也得到了其媒介特征和文本體驗(yàn)的印證。
然而,我們需要進(jìn)一步討論兩個(gè)問題。其一,從籠統(tǒng)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論走向網(wǎng)絡(luò)媒介的書寫效應(yīng),其闡述路徑逐漸接近文學(xué)內(nèi)部且有具體的面向,這是值得肯定的。換句話說,國內(nèi)學(xué)界主要還是集中于后現(xiàn)代社會(huì)狀況、新媒介文化特征和主體性變遷等研究維度,對文學(xué)本身及其閱讀文化邏輯的探討則顯得相對不足;而且,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發(fā)展并沒有更多地體現(xiàn)出超文本的實(shí)驗(yàn)性傾向,而是有其自身的發(fā)展特色。其二,雖然從現(xiàn)代性發(fā)展到后現(xiàn)代是歷史的必然趨勢,但并不意味著學(xué)者們對這一趨勢都持贊同和欣賞的態(tài)度,反而更多的是觀點(diǎn)上的矛盾與沖突。就界面讀寫而言,其具有的解構(gòu)權(quán)力秩序和中心性、破除理性邏輯的桎梏、保持一種自由開放的精神、具有民間狂歡化效果等特征都是眾多學(xué)者所認(rèn)同的,而其所具有的碎片化和虛無性、犬儒主義和消費(fèi)幻象等特征又是不少學(xué)人所反對的。前者多半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側(cè)重者,強(qiáng)調(diào)個(gè)體自由、創(chuàng)造與開拓性,與后現(xiàn)代精神契合;后者則以閱讀研究者居多,立足于現(xiàn)代理性的立場,在與紙本閱讀的對比中突顯當(dāng)代閱讀的負(fù)面效應(yīng)。這種負(fù)面效應(yīng)具體表現(xiàn)在如下三個(gè)方面。
首先是一種碎片化、娛樂和虛無式的閱讀。吉梅內(nèi)斯(Marc Jimenez)就談到后現(xiàn)代時(shí)期新媒介技術(shù)的廣泛運(yùn)用,使藝術(shù)門檻大大降低,無處不在、海量的閱讀資源隨時(shí)可用,導(dǎo)致種種藝術(shù)、審美和閱讀的效果“只余下空洞的回蕩”。[11]網(wǎng)絡(luò)書寫魚龍混雜、種類繁多,內(nèi)容搞笑、怪異、嘩眾取寵,讓讀者無所適從、難以承受,而那些激進(jìn)的、解構(gòu)的文本政治該“如何維持下去”[12],根本沒有任何答案,只剩下無謂的冒險(xiǎn)和破壞性的娛樂沖動(dòng);虛擬世界快速“悅讀”的性質(zhì)又容易讓人變得膚淺、缺乏耐心,“海量、快速、互動(dòng)、流通著的數(shù)字閱讀內(nèi)容適應(yīng)了城市發(fā)展的快節(jié)奏,卻消解了傳統(tǒng)閱讀中的專注、思索與深刻”[13],某種程度上折射出喧囂、浮躁、功利化和感性化的后現(xiàn)代都市時(shí)代的精神癥狀。
其次是瞬時(shí)學(xué)習(xí)的特性。學(xué)術(shù)界對新媒介文學(xué)閱讀有各種稱呼,如碎片化閱讀、簡略閱讀、搜索式閱讀、片段式閱讀、瀏覽式閱讀等等,都預(yù)示著文學(xué)接受的瞬時(shí)性,缺乏持久的專注;讀者極易受各種超文本和其他跨屏、多屏形式的干擾,宛如走馬觀花的游客,遑論對作品深刻的理解和本質(zhì)的洞察;數(shù)字技術(shù)使資料儲(chǔ)存異常豐富,知識(shí)運(yùn)用愈加便捷,但也更讓人無所適從,如數(shù)碼技術(shù)讓攝影照片海量遞增,卻“永遠(yuǎn)都存在儲(chǔ)存卡或手機(jī)里,沒有整理也沒人查看”,“更像是堆在閣樓或倉庫里的雜物”[14]133,完全沒有相機(jī)膠卷那種珍視感,以及對事物真實(shí)的關(guān)切和體會(huì)。在網(wǎng)絡(luò)世界里,海量文獻(xiàn)和資源的任意調(diào)取和嫁接,還會(huì)讓人產(chǎn)生對真理知識(shí)的誤讀和獲取途徑的曲解。
再次是塑造后現(xiàn)代式的分裂人格。隨著大數(shù)據(jù)時(shí)代的到來,互聯(lián)網(wǎng)和移動(dòng)端閱讀越來越呈現(xiàn)出產(chǎn)業(yè)化趨勢,人們崇尚消費(fèi)至上、利益優(yōu)先,各種讀物迎合大眾的個(gè)性化和感性需求,形成泛娛樂文化體系,其結(jié)果就是塑造出欲望化和分裂型的人格特性,“把人際關(guān)系中的‘我—你’關(guān)系,偷換成人機(jī)關(guān)系中的‘我—他’關(guān)系而已,人與人的真實(shí)的、活生生的交流不復(fù)存在”,用戶集中于冰冷的、毫無人性的機(jī)器上,“無異于一種新的人生囚禁”。[15]他們置身在四通八達(dá)、不斷流變的界面平臺(tái)上,為無數(shù)信息、數(shù)據(jù)所裹挾,成為數(shù)字海洋中的無根式的漂浮物,無目的、無意義和盲目沖動(dòng)隨之而來,憂郁、焦慮和絕望感應(yīng)時(shí)而生。
平心而論,虛擬世界中走心式閱讀、感性化特征,因與現(xiàn)實(shí)世界脫離而產(chǎn)生新的網(wǎng)絡(luò)禁錮的情況確實(shí)存在,有其具體表現(xiàn)。不過,就整體來說,后現(xiàn)代閱讀的負(fù)面性判斷更多是基于與印刷時(shí)代紙本閱讀的對比而作出的。馬季出版于2006年的著作《讀屏?xí)r代的寫作: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10年史》提到“傳統(tǒng)閱讀基本是面對書本,網(wǎng)絡(luò)閱讀則是對著電腦屏幕”[16],副標(biāo)題“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10年史”顯示出屏幕閱讀與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關(guān)聯(lián),在區(qū)別紙本文學(xué)的基礎(chǔ)上突出網(wǎng)絡(luò)讀寫的別樣性。美國語言學(xué)家內(nèi)奧米·巴倫(Naomi S.Baron)提到廣州大學(xué)2006年的一項(xiàng)調(diào)查結(jié)果:女性比男性更愛紙質(zhì)書,她們更認(rèn)真,而男性則偏向在線閱讀,更喜歡瀏覽、略讀和非線性閱讀,其閱讀載體就是“電腦屏幕”。[14]267她強(qiáng)調(diào)印刷時(shí)代的閱讀載體即書本所擁有的實(shí)體化、舒適性、可占具、物質(zhì)感、人性味和書香氣等感性化介質(zhì),還有其體現(xiàn)出的人類的理性智慧、知識(shí)的嚴(yán)肅性、出版的嚴(yán)謹(jǐn)性和傳承的價(jià)值性,都是電子閱讀對象即虛擬文本所不及的。我們認(rèn)為,將兩種閱讀模式進(jìn)行對比,易有一種情緒化的反應(yīng),印證某種潛藏性、基底性的懷舊情結(jié),因此,所得出的結(jié)論與其說是出于現(xiàn)代理性而對當(dāng)代文學(xué)閱讀的后現(xiàn)代性進(jìn)行嚴(yán)厲批判,還不如說是長期接受已成文化積淀的閱讀范式因電子閱讀帶來強(qiáng)大沖擊而產(chǎn)生焦慮、隱憂和悲觀論調(diào)。界面存在的短暫歷史自然無法讓人擁有那份久遠(yuǎn)的、熟悉的甚至是文化基因式的情感,而增量不增智的讀屏批評(píng),也只是將其思考集中在新媒介技術(shù)僅僅被當(dāng)作一種中介手段或載體工具的改變上,從而影響了閱讀的現(xiàn)代性效果,破壞了已有的書籍情懷。就此而言,這種觀點(diǎn)嚴(yán)重忽略了界面技術(shù)對閱讀性質(zhì)的調(diào)整、閱讀模式的變革以及新風(fēng)景的開拓。
三、數(shù)字現(xiàn)代主義的整體性局限
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社會(huì)的時(shí)代差異,紙媒閱讀的挽歌情懷和閱讀效果,以及對后現(xiàn)代的批判,其背后都有某種潛在的現(xiàn)代性立場;同時(shí),閱讀文化依托于新媒介和界面技術(shù)的發(fā)展,產(chǎn)生各種后現(xiàn)代性的征象,不同于以往的閱讀范式和效果;兩者構(gòu)成了新媒介文學(xué)文化邏輯探究的矛盾面向。艾倫·柯比(Alan Kirby)卻據(jù)此提出“數(shù)字現(xiàn)代主義”(Digimodernism)作為綜合改編的方案,并將其建立在賽博、交互的數(shù)字文本性及其主體性構(gòu)想上:一方面,強(qiáng)調(diào)界面閱讀數(shù)字化的媒介根基和后現(xiàn)代性效應(yīng);另一方面,重視現(xiàn)代性的承嬗離合,認(rèn)為后現(xiàn)代只是現(xiàn)代的未完成階段,可運(yùn)用交往理性解決后現(xiàn)代虛無主義的問題,從而給予新媒介文學(xué)閱讀數(shù)字現(xiàn)代主義的總體定位。國內(nèi)學(xué)者則沿其路向繼續(xù)思考,數(shù)字媒介文化被當(dāng)作人類生存遭遇的社會(huì)新語境,是交互性文本與現(xiàn)代性思想的某種結(jié)合。作為數(shù)字現(xiàn)代主義的文學(xué)范例,早期臺(tái)灣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通過數(shù)字文本方式體現(xiàn)出了強(qiáng)烈的主體自由、自我表達(dá)、個(gè)體意識(shí)、追求意義和反抗消費(fèi)文化邏輯的現(xiàn)代性追求”;《女孩的悸動(dòng)》(These Wares of Girls)“被譽(yù)為西方網(wǎng)絡(luò)化數(shù)字文學(xué)的典范之作”,盡管它主要得益于“采用超文本修辭、不可靠敘事、復(fù)合符號(hào)生產(chǎn)等數(shù)字網(wǎng)絡(luò)化美學(xué)形式”,但其書寫依然關(guān)注和探索“數(shù)字文化時(shí)代的人性、人生和男權(quán)文化世界中女性命運(yùn)等嚴(yán)肅主題”。[17]235尤其是進(jìn)入21世紀(jì)后,西方文學(xué)厭倦解構(gòu)主義的文化觀念,重視當(dāng)代嚴(yán)肅主題,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問題,像《冰河時(shí)代》《快樂的大腳》和《籬笆墻外》等動(dòng)漫文學(xué),還有凱魯亞克《在路上》、艾米麗·肖特《機(jī)智》、喬恩·英格德《所有的路》、唐娜·利什曼《基督徒肖的財(cái)產(chǎn)》等作品都表現(xiàn)出文學(xué)傳統(tǒng)的回歸。中國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則更具代表性,在海量作品中照舊彰顯現(xiàn)代人文精神,在眾多形式奇異的后現(xiàn)代景觀下還是延續(xù)而來的現(xiàn)代性主題。具體地說,第一階段中痞子蔡、安妮寶貝、李尋歡和寧財(cái)神等作家基本延續(xù)現(xiàn)代性風(fēng)格;資本介入后則向數(shù)字現(xiàn)代主義的深部挺近,如貓膩《朱雀記》《慶余年》《間客》和《將夜》等系列作品,而《夢回大清》《步步驚心》和《協(xié)奏、交響與獨(dú)自沉迷》等網(wǎng)絡(luò)流行作品根本沒有后現(xiàn)代特征,反而體現(xiàn)出新型現(xiàn)代主義價(jià)值觀。因此,國內(nèi)學(xué)界對新媒介文學(xué)的后現(xiàn)代性判斷還是“網(wǎng)絡(luò)后現(xiàn)代性偷換為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后現(xiàn)代性的問題”[9],網(wǎng)絡(luò)媒介和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性質(zhì)不同的問題再次得到重申和更深入具體的闡發(fā)。
數(shù)字現(xiàn)代主義的最大貢獻(xiàn)在于其文化邏輯的探討基于文學(xué)作品自身,尤其是內(nèi)容和主題表現(xiàn)出文學(xué)本位論的考量維度。新媒介文學(xué)閱讀的文化邏輯從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媒介表現(xiàn)到文學(xué)內(nèi)容的變化,是其闡釋路徑不斷改進(jìn)的結(jié)果。同時(shí),數(shù)字現(xiàn)代主義對讀屏行為的現(xiàn)代性和后現(xiàn)代性進(jìn)行折中與調(diào)和,既避免了后現(xiàn)代主義的虛無與解構(gòu),又摒棄了現(xiàn)代性無視當(dāng)代新媒介文化的過時(shí)與保守,進(jìn)而將媒介技術(shù)改變所帶來的新的文化價(jià)值與文學(xué)文本內(nèi)容的既有現(xiàn)代性訴求結(jié)合起來。在虛擬世界中,共同體社區(qū)、粉絲化和全球性倫理表明交往理性拓展的事實(shí)與可能,而文本運(yùn)作方式的后現(xiàn)代主義和文本內(nèi)容主題的現(xiàn)代性嫁接,有其客觀的文本依據(jù)。再者,數(shù)字現(xiàn)代主義在現(xiàn)代性規(guī)范和后現(xiàn)代解構(gòu)間取得某種平衡而往回走的路徑,更能反映中國當(dāng)代急劇變革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各種文化和思潮短期內(nèi)洶涌而至,從伊始的刺激與興奮,到后來的矛盾和焦慮,伴隨多元和并存,最終走向雜糅與結(jié)合,只是其現(xiàn)代性和后現(xiàn)代性的交織,難以涵蓋更多的文化性質(zhì)。
數(shù)字化讀寫語境,借助新的文本形式,表現(xiàn)新的思想性質(zhì),獲得新的審美體驗(yàn),卻延續(xù)著現(xiàn)代性主題的文化邏輯。如此,現(xiàn)代性成為一個(gè)包羅萬象的概念,甚至連后現(xiàn)代性都作為其內(nèi)在辯證要素而容納進(jìn)去。與此同時(shí),國外數(shù)字現(xiàn)代主義強(qiáng)調(diào)后現(xiàn)代文化只是未完成的現(xiàn)代性,它仍然建立在理性基礎(chǔ)上,側(cè)重交往理性而非個(gè)體理性;國內(nèi)數(shù)字現(xiàn)代主義則將網(wǎng)絡(luò)媒介和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嚴(yán)格區(qū)隔,前者是作為文本的載體、容器與運(yùn)作模式,帶有游戲性、感性美學(xué)、消解、碎片化和網(wǎng)絡(luò)交互等后現(xiàn)代文化特性,后者主要指具體內(nèi)容的表現(xiàn),依然是人性、人文、倫常命運(yùn)和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等嚴(yán)肅的現(xiàn)代性主題。它既沒有考慮到技術(shù)形式、工具載體和運(yùn)作模式的變遷而導(dǎo)致文學(xué)觀念、視角風(fēng)格和閱讀體驗(yàn)的重塑,更談不上其本體轉(zhuǎn)型帶來新文藝世界的構(gòu)建。由印刷技術(shù)、紙媒文本及其語言線性排列所造就的現(xiàn)代性文化,包括個(gè)性特征、人文關(guān)懷、社會(huì)規(guī)制下的人生命運(yùn)和生活理想等,并非因數(shù)字技術(shù)、電子文本和語言圖符化的出現(xiàn),以及閱讀的多線性、隨機(jī)性和異質(zhì)關(guān)聯(lián)性而有所改變。從邏輯上說,媒介規(guī)制在現(xiàn)代時(shí)期催生和建構(gòu)了文學(xué)的現(xiàn)代性,到后現(xiàn)代時(shí)期卻失去了效用,新的媒介規(guī)制并沒有產(chǎn)生新的文化邏輯。媒介文藝學(xué)強(qiáng)調(diào)從媒介角度審視文學(xué)的變遷,但在新媒介時(shí)期卻受到阻礙,媒介與文藝被割裂開來,其文化邏輯陷入自身所開啟的矛盾中。
至此,新媒介文學(xué)的文化邏輯及其闡釋路徑經(jīng)由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決定性、互聯(lián)網(wǎng)媒介的作用和文學(xué)主題內(nèi)容的功能表現(xiàn),最終立足于文學(xué)本體的思考和定位,體現(xiàn)出數(shù)字現(xiàn)代主義從外轉(zhuǎn)內(nèi)的研究視角,只是其中存在著悖論性;同時(shí),結(jié)合界面閱讀的現(xiàn)代性和后現(xiàn)代性進(jìn)行分析,又使數(shù)字現(xiàn)代主義的文化邏輯具有某種普遍的包容性。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數(shù)字現(xiàn)代主義的不足也代表了既有的文化邏輯研究在整體上的闡釋局限,我們將其歸納為如下三點(diǎn)。
第一,文學(xué)內(nèi)容和主題的困境。數(shù)字現(xiàn)代主義力圖從文學(xué)內(nèi)容、主題和意義等方面闡述新媒介文學(xué)既同于又異于現(xiàn)代性的文化邏輯,體現(xiàn)“新型現(xiàn)代主義”的價(jià)值觀念。[9]如《朱雀記》里所宣揚(yáng)的個(gè)體應(yīng)該捍衛(wèi)自己渺小和珍貴的生存權(quán)利和生命幸福,其生存觀既是現(xiàn)代性的,又非康德式的最高規(guī)則,但是,這與其說是普適化的現(xiàn)代性,還不如說是更具本土文化的針對性,更何況康德的最高規(guī)則本來就是以個(gè)體自由意志的存在為前提的。再如《步步驚心》里同性友誼高于男女愛情的新模式,其實(shí)在古希臘就有同性之愛的哲學(xué)闡述,而超越肉體的純粹之愛在以往文學(xué)作品中更是有較多的體現(xiàn)。在文學(xué)史上,像愛情、反抗、人生命運(yùn)和自我抉擇等諸多主題其實(shí)是整個(gè)人類面臨的主要問題,也是所有文學(xué)的書寫對象,即文學(xué)史上的通用內(nèi)容,任何時(shí)代都不乏優(yōu)秀之作,而其創(chuàng)新往往體現(xiàn)在藝術(shù)技巧、類型、視角和想象力上,以呈現(xiàn)通用主題下多樣的真實(shí)性,挖掘獨(dú)特的內(nèi)部細(xì)節(jié)與痕跡,將其存在的空間敞開來。由此,現(xiàn)代時(shí)期長篇小說、意識(shí)流小說的確立,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接龍文學(xué)、太監(jiān)文學(xué)的出現(xiàn),給予讀者別樣、細(xì)化的感受和體驗(yàn),這些新變才是閱讀文化邏輯所要關(guān)注的。
第二,媒介作為中介的片面性。就屏幕到界面的技術(shù)歷程而言,屏幕是隨著電影的誕生而逐漸進(jìn)入人們視線的,那時(shí)只是作為運(yùn)動(dòng)影像投射放映的工具性載體,即中介性運(yùn)用,白墻等光滑的、無顏色的平面物亦可替代,屏幕并非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真正讓屏幕成為傳播媒介的組成部分是因?yàn)殡娨暤陌l(fā)明,此時(shí)屏幕才具有電子化的意義。電視用戶使用遙控器調(diào)臺(tái)觀看自己喜愛的節(jié)目,但無法干預(yù)屏幕顯示的內(nèi)容,在單向傳播的基礎(chǔ)上有一定的選擇權(quán),主要烘托一種家庭倫理的氛圍。伴隨計(jì)算機(jī)技術(shù)的發(fā)展,電腦屏幕成為人機(jī)交互的平臺(tái),用戶變被動(dòng)為主動(dòng),積極參與游戲娛樂、畫圖寫作、程序設(shè)計(jì)與各種全球性的社區(qū)活動(dòng),提升了人類的感性愉悅和理性智慧,從而具有影視所沒有的讀屏意義。因此,像看待印刷紙張那樣只強(qiáng)調(diào)界面的工具性和載體性,使界面局限于中介功能,其閱讀就只能集中在文本語言上,如此,即便是后現(xiàn)代的超文本觀念,也無法將閱讀對象從語言交織化的文本替換為媒介智能性的界面,從而完成閱讀范式的真正轉(zhuǎn)型和意義開掘。
第三,語言文本的過分重視。20世紀(jì)初葉,以索緒爾理論為代表的語言學(xué)轉(zhuǎn)向側(cè)重于文學(xué)語言、文本結(jié)構(gòu)及其要素功能的關(guān)系探索,視文本的原意為編織物,認(rèn)為語言的結(jié)構(gòu)體系決定文學(xué)的意義。后現(xiàn)代理論則源于對語言的解構(gòu),進(jìn)而是對文學(xué)規(guī)則、敘事秩序和意義中心的消解,這是文學(xué)自身要素內(nèi)的延異和展開。然而,讀屏伊始,卻是立足于影視媒介藝術(shù),具有視聽綜合的傾向,其文化邏輯的真正奠基是計(jì)算機(jī)的問世和互聯(lián)網(wǎng)的到來,界面不僅開啟了異質(zhì)關(guān)聯(lián)的互動(dòng)世界,帶來人的全身心的審美體驗(yàn),還建構(gòu)了全球性的社區(qū)共同體和萬物皆聯(lián)的智能化閱讀方式,人類閱讀文化進(jìn)入新的階段。就傳播信息方式而言,人類經(jīng)歷過體態(tài)語、口頭語、書面語和數(shù)字語的變革,體態(tài)語以身體器官即眼睛“直接觀察到彼此肢體動(dòng)作和面部表情為主”;口頭語作為簡單的指示性語言,主要以聽說為主;書面語則以讀寫來規(guī)范表情達(dá)意的文字;數(shù)字語言又回到觀看為主,可是“此時(shí)的‘看’借助了讀屏模式,無論是文字、圖像、視頻,一切可視的對象都顯示在屏幕(電視、電腦、手機(jī))上”,主客體互動(dòng)和呈現(xiàn)通過界面平臺(tái)進(jìn)行。[18]從觀察肢體、聽音、讀文發(fā)展到讀圖、動(dòng)態(tài)圖像的接受,再到當(dāng)今新媒介多屏、跨屏閱讀,界面閱讀實(shí)現(xiàn)了對既有閱讀范式的解構(gòu)和新秩序的重構(gòu)。
四、“虛擬后現(xiàn)代”文化邏輯的可能性
無論是現(xiàn)代性、后現(xiàn)代還是數(shù)字現(xiàn)代主義,都分別受制于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狀況、媒介特性或文本主題表達(dá),從而存在種種不足之處,但對于當(dāng)下閱讀文化邏輯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新媒介文學(xué)閱讀是在界面技術(shù)所構(gòu)成的虛擬世界中完成的,關(guān)聯(lián)著后現(xiàn)代社會(huì)及其文化背景。也就是說,文本閱讀、媒介特征和社會(huì)文化具有某種同一性,體現(xiàn)出多元、互動(dòng)、雜糅與生成的本質(zhì)特性。因此,如要對當(dāng)代閱讀范式的轉(zhuǎn)型作出更合理的闡明,便要將界面本體性要義作為闡釋路徑,首先要廓清后現(xiàn)代的文化內(nèi)涵,然后再分析界面建構(gòu)的虛擬空間,最后總結(jié)虛擬世界文學(xué)讀寫的新變,并找出它們的具體表現(xiàn)、特質(zhì)及其關(guān)聯(lián)的統(tǒng)一性。
“后現(xiàn)代”一詞由建筑領(lǐng)域擴(kuò)展開來,且作為專門術(shù)語獲得其學(xué)術(shù)意義。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坦言,“踏入后現(xiàn)代時(shí)期,在眾多的美感生產(chǎn)形式中,作品風(fēng)格變化最顯著、最劇烈、而引起的理論探討最能一針見血道破問題癥結(jié)的,要算建筑藝術(shù)了”,他自己對后現(xiàn)代的看法“不少是從建筑設(shè)計(jì)界的有關(guān)辯論中得到啟示的”。[19]因此,要廓清后現(xiàn)代的原初含義,就要回到當(dāng)時(shí)建筑風(fēng)格的討論才行。1975年,詹克斯(Charles Jencks)開創(chuàng)性地將“后現(xiàn)代一詞轉(zhuǎn)用到建筑領(lǐng)域”,認(rèn)為現(xiàn)代建筑都是以精英階層的品味為主,后現(xiàn)代建筑并沒有放棄其主張,而是多方拓展建筑的語言,覆蓋當(dāng)時(shí)的風(fēng)格、習(xí)俗和街頭的商貿(mào)行話,“必須同時(shí)使用至少兩種建筑語言,例如傳統(tǒng)的和現(xiàn)代的、精英的與流行的、國際的與區(qū)域的代碼”,形成并置、雜糅、多重性和兼收包容的世界性風(fēng)格。[20]通俗地說,后現(xiàn)代建筑乃是“現(xiàn)代技術(shù)加別的什么東西,通常是傳統(tǒng)式的房子”,從而具有雙重譯碼(double-coding)、精神分裂癥狀和多元主義的傾向。[21]不用說,在建筑領(lǐng)域內(nèi),后現(xiàn)代精神正是以異質(zhì)性要素的互動(dòng)、嫁接和交織融合而著稱,也是其標(biāo)志性的風(fēng)格特征。換句話說,后現(xiàn)代在其原初含義里便具有包羅萬象的雜糅性、復(fù)合性和生成可能性,觀賞者在后現(xiàn)代建筑中自己去遍歷、去體驗(yàn)、去創(chuàng)造,從而開啟新的韻味空間。總之,后現(xiàn)代是一種包含傳統(tǒng)、現(xiàn)代及其他文化,注重參與者參與、擁有開放性和走向未來的總體性文化邏輯,而非僅僅是與傳統(tǒng)、現(xiàn)代文化相對立的文化觀念。
芬蘭數(shù)字文化理論家考斯基馬(Raine Koskimaa)提出“本體互滲”(Ontolepsis)的概念,用于概括新媒介時(shí)代本體(存在)融合的現(xiàn)象:“似乎不可避免的就是,在分離的領(lǐng)域之間的、數(shù)量不斷增加的界限(或曰界面),就使得這些領(lǐng)域之間的‘互滲’不斷擴(kuò)大了。”[22]“本體互滲”是通過界面來完成的,并得到了機(jī)器技術(shù)和信息技術(shù)的支撐,兩者交匯于計(jì)算機(jī)后煥發(fā)出強(qiáng)大的活力,逐步以界面技術(shù)構(gòu)建虛擬空間。機(jī)器技術(shù)沿著智能化方向來到當(dāng)下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時(shí)代,界面早已不是簡單的屏幕,其外圍主要是由顯示器、觸摸屏、鼠標(biāo)和鍵盤,進(jìn)入虛擬世界所需的電子頭盔、服飾和手套,以及驅(qū)動(dòng)程序、運(yùn)行系統(tǒng)和軟件工具等構(gòu)成;其內(nèi)部則由進(jìn)制、算法和代碼等數(shù)字化系統(tǒng),加上用戶輸入、操作并驅(qū)動(dòng)界面呈現(xiàn)的語言符號(hào)、聲圖影像以及各種超鏈接、文本塊、視窗模式組成,由此構(gòu)建出多智能主體共同參與、即時(shí)互動(dòng)的虛擬平臺(tái)。信息技術(shù)則邁向網(wǎng)絡(luò)社會(huì),歷經(jīng)局域網(wǎng)、互聯(lián)網(wǎng)、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后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和物聯(lián)網(wǎng)的變遷,最后到元宇宙(Metaverse)的開啟階段。界面由開始用于“聯(lián)接電子線路的硬件適配器插頭”,更新至作為“窺視系統(tǒng)的視頻硬件”,通過人與機(jī)器連接,“進(jìn)入一個(gè)自足的網(wǎng)絡(luò)空間”,最后指向“通過顯示屏與數(shù)據(jù)相連的人的活動(dòng)”。[23]統(tǒng)言之,由硬件經(jīng)濟(jì)學(xué)走入虛擬形而上學(xué),再到線上線下活動(dòng)的人類社會(huì)學(xué),現(xiàn)實(shí)虛擬化,虛擬現(xiàn)實(shí)化,界面聯(lián)通了整個(gè)世界。
一方面,視窗系統(tǒng)的改進(jìn)、網(wǎng)絡(luò)的全球化和移動(dòng)化使計(jì)算機(jī)、IPAD、手機(jī)和Kindle以及各式網(wǎng)站或數(shù)字工具,如網(wǎng)易新浪論壇、Zola、臉書、Goodreads、彈幕、APP、博客、微信和Librify等流行開來,借助人工智能和軟件程序,界面成為隨時(shí)隨地讀寫、互動(dòng)和創(chuàng)造的超級(jí)平臺(tái),力求打造線上社區(qū)共同體;數(shù)字化信息網(wǎng)絡(luò)“非實(shí)體的、在個(gè)人與個(gè)人之間建立的烏托邦,并且暗示那樣一個(gè)世界會(huì)讓我們回歸更自然、更親密的生活”,充滿了友愛、慰藉與合作精神,形成多媒介交合的虛擬世界,最終構(gòu)建虛擬仿生的元宇宙社會(huì)。[24]
另一方面,新型機(jī)器、軟件、應(yīng)用程序和人工智能等通過網(wǎng)絡(luò)界面全方位覆蓋,達(dá)到實(shí)現(xiàn)萬物皆媒,不僅要實(shí)現(xiàn)人-機(jī)交互、人-人互動(dòng),還要實(shí)現(xiàn)人-物相聯(lián),參與民眾的日常生活,開發(fā)智能化的藝術(shù)體驗(yàn),將社會(huì)生活智能化和互聯(lián)網(wǎng)環(huán)境化,構(gòu)建公共文化服務(wù)平臺(tái),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和虛擬世界不再斷裂和區(qū)隔,相反統(tǒng)一成整體。人們的界面閱讀已不再局限于文藝作品,不是與冰冷的機(jī)器打交道,而是理解、參與和操勞自己的生活,體驗(yàn)身心沉浸的在場美學(xué),通過結(jié)合現(xiàn)實(shí)與虛擬世界,構(gòu)建生活審美化的人類社會(huì)。
由此,發(fā)端于建筑領(lǐng)域的后現(xiàn)代精神,借助界面向整個(gè)藝術(shù)領(lǐng)域和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全面鋪開,由一種特殊領(lǐng)域的藝術(shù)特征發(fā)展為社會(huì)文化的本質(zhì)特性,建筑與界面承擔(dān)了相似的文化意義。網(wǎng)絡(luò)虛擬世界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文學(xué)愛好者的民間樂園和試驗(yàn)基地,文學(xué)用戶日益增長,藝術(shù)活動(dòng)難以計(jì)數(shù),作品存儲(chǔ)體量驚人,日更數(shù)據(jù)快速龐大,線上線下構(gòu)建藝術(shù)社區(qū),為內(nèi)容產(chǎn)業(yè)和泛娛樂文化體系源源不斷地輸送原創(chuàng)作品,開拓閱讀和審美的新境界。我們可以從書寫創(chuàng)作、閱讀文本和審美效果三方面來印證新媒介文學(xué)閱讀“虛擬后現(xiàn)代”的文化邏輯。
在新媒介文學(xué)中,人工智能標(biāo)識(shí)語言的開發(fā)、各種編程軟件的設(shè)計(jì)等都被運(yùn)用于書寫活動(dòng),出現(xiàn)了人類主體與寫作機(jī)器合作的“賽博作者”(Cyborg Author),如創(chuàng)新工場DeeCamp與陳楸帆合作小說《大有》(2021),“彩云小夢”和王元共同創(chuàng)作《他殺》(2023),《花城》雜志還特意在兩篇小說中標(biāo)出軟件機(jī)器創(chuàng)作的文字。美國小說《背叛》(1998)、俄羅斯小說《真愛》(2006)、微軟小冰的詩歌《陽光失去了玻璃窗》(2017)等都是人工智能創(chuàng)制的作品,多智能創(chuàng)作主體及其互動(dòng)寫作帶來不同的閱讀效果。互聯(lián)網(wǎng)的全球性平臺(tái)讓世界每個(gè)角落里的讀者都可能成為作家,寫作軟件的興盛更是使書寫變得輕松便利,讀者閱讀時(shí)便可與寫手即時(shí)交流,為其出謀劃策,影響其創(chuàng)作思路,甚至自己續(xù)寫接下來的章節(jié),與其他讀者共同完成接龍或同人作品(如接龍小說《網(wǎng)上跑過斑點(diǎn)狗》《城市的綠地》,同人作品《臨高啟明》等)。網(wǎng)絡(luò)寫手則利用文字處理器和版面編輯程序來從事實(shí)驗(yàn)性寫作,增加各種頁面設(shè)計(jì),實(shí)現(xiàn)多窗口呈現(xiàn)與穿叉、自由編程與排序、短暫停留與倒轉(zhuǎn),讓讀者每次閱讀都有異樣的體驗(yàn)和感受,如薩波爾塔(Marc Saporta)的《一號(hào)作品》(Composition No.1)、科塔扎爾(Julio Cortazar)的《跳房子》(Rayuela)等,都利用程序軟件讓文本內(nèi)容隨意排列或跳接,使每次閱讀都要重新洗牌,套路繁多而難以計(jì)算。總的來看,新媒介文學(xué)利用界面實(shí)現(xiàn)其創(chuàng)作、出版、銷售和評(píng)閱“一條龍”服務(wù),用戶或讀者都可主動(dòng)參與進(jìn)去,他們不僅是文學(xué)的鑒賞者、評(píng)論者和傳播者,還是創(chuàng)作上的互動(dòng)者、接續(xù)者和書寫者,也是文本秩序的操作者、編輯者和創(chuàng)制者。
新媒介技術(shù)、計(jì)算機(jī)邏輯和互聯(lián)網(wǎng)交往模式給予網(wǎng)絡(luò)寫手以“超越以往的想象空間”,如網(wǎng)絡(luò)中的“關(guān)機(jī)下線”可能給作品里的“離魂轉(zhuǎn)世”以靈感;網(wǎng)絡(luò)虛擬的液態(tài)性讓“人和世界都可重塑”,帶來穿越與重生的想象力爆發(fā);傳統(tǒng)文學(xué)中的暴君、惡魔變成“不可見、不可觸的系統(tǒng)循環(huán)”;游戲中打怪升級(jí)模式會(huì)帶來影響,等等,網(wǎng)絡(luò)媒介經(jīng)驗(yàn)給文學(xué)文本帶來了情節(jié)設(shè)置、結(jié)構(gòu)模式、人物塑造和敘事節(jié)奏等各方面的變革,也使讀者閱讀產(chǎn)生新異感、體驗(yàn)范式的轉(zhuǎn)型。[25]更重要的是,讀者可對文本任何段落章節(jié)進(jìn)行評(píng)論,形成“本章說”,即時(shí)組成粉絲社區(qū),體現(xiàn)出“社交閱讀”的特性。讀者的評(píng)論可以成為作品的組成部分,甚至單獨(dú)出版(如《凡人修仙傳》的評(píng)論集合等),而其表達(dá)媒介除了語言符號(hào)外,還有表情包、音樂和影像等,讀者甚至可用“捏臉”技術(shù)塑造文學(xué)里的人物形象來傳達(dá)自己的獨(dú)特感受。讀者、作者和軟件、硬件及其閱讀、寫作和評(píng)論互滲互融,構(gòu)建“閱-寫”“語-圖”和“人-機(jī)”交互的讀寫模式。屏幕閱讀面對的不是物質(zhì)固化的線性語言文本,而是某種需要不斷交互操作的界面,由此,文本/界面變得復(fù)雜多變,具有臨時(shí)性和隨機(jī)性,是不同要素相互碰撞、聯(lián)結(jié)而成的產(chǎn)物。
在人類歷史上,互動(dòng)性常見于人與人、人與自然的信息傳遞,印刷時(shí)代主要集中在對書寫文本的交流上,由此發(fā)展出闡釋學(xué)理論體系,以便互動(dòng)雙方更有效地加深理解,重點(diǎn)在語義學(xué)及其有關(guān)的社會(huì)、歷史和文化語境的關(guān)聯(lián)上。計(jì)算機(jī)的發(fā)明、互聯(lián)網(wǎng)的興起不僅實(shí)現(xiàn)了人類與機(jī)器之間的互動(dòng),還突破了語義理解的文本學(xué)局限,讓不同事物打破各自界限,“在不同客體和系統(tǒng)的邊界之間游走”,借助于交互生成的界面,“形式可以存在于或跨越不同的事物、客體或媒介”,[26]界面運(yùn)用數(shù)字綜合方法,容納更多的視聽材料,將音頻影視、符號(hào)圖像和歷史文本等集合成高度真實(shí)化的虛擬世界,召喚讀者全身心投入,產(chǎn)生一種與古典式“靜觀”、現(xiàn)代式“驚顫”完全不同的審美體驗(yàn),即操作性的“融入”式沉浸美學(xué)[17]224,發(fā)揮主體生成和創(chuàng)造的能動(dòng)性。就此而言,網(wǎng)絡(luò)閱讀并非流于空洞、解構(gòu)、娛樂化和虛無主義。網(wǎng)絡(luò)用戶可借助穿戴式書籍、無線思維頭盔,以及數(shù)據(jù)手套、電子服裝和感應(yīng)帽子等硬件觸摸和體驗(yàn)對象,與文藝作品人物產(chǎn)生同步的共情,體會(huì)其心理波動(dòng),感知其隱蔽跡象,進(jìn)而激發(fā)自我感悟力,擴(kuò)展文學(xué)想象的空間。接受主體在界面閱讀中并非僅僅將視覺讀取作為改變自我的感性手段,也不再局限于文本的理性反思和作品的完結(jié)性,而是在身體、技術(shù)和心靈的全方位互動(dòng)、融合和生成中,著眼于虛擬世界中文學(xué)互動(dòng)的開放性和未完成性,不斷地刷新、成長,將自我的各種潛能釋放出來。
五、結(jié) 語
與讀書的古典情懷相比,讀屏具有更多的現(xiàn)代氣息,只是這種現(xiàn)代性并非學(xué)術(shù)意義上的現(xiàn)代性,更多的是具有當(dāng)下閱讀時(shí)尚的味道。新媒介技術(shù)廣泛而深入的影響,尤其是其擁有的快速、便捷和海量存儲(chǔ)等特性,使屏幕閱讀表現(xiàn)出原子式、碎片化、感官性和消費(fèi)性模式,擁有后現(xiàn)代文化的性質(zhì)。數(shù)字文學(xué)、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等作品采取了超文本形式,并利用各種人工智能和媒介手段表現(xiàn)未完成的現(xiàn)代性主題,體現(xiàn)出數(shù)字現(xiàn)代主義的文化邏輯。以上建立在社會(huì)狀況、媒介特性和文本主題等闡釋路徑上的現(xiàn)代性、后現(xiàn)代和數(shù)字現(xiàn)代主義的文化邏輯存在著種種不足,界面閱讀立足于界面的本體互滲性,有其自身的發(fā)展史,在虛擬世界中與后現(xiàn)代社會(huì)文化、文本讀寫的真實(shí)狀況取得了統(tǒng)一性,帶來了文學(xué)話語和閱讀范式的轉(zhuǎn)型。
從讀寫主體來說,界面閱讀有人工智能、寫作機(jī)器和程序軟件的參與,產(chǎn)生人機(jī)交互的主體性模式,由讀書的主體性、影視觀看的群體性和家庭氛圍的營造,到界面讀寫的全球化倫理和粉絲化的社區(qū)共同體,基于界面閱讀的關(guān)聯(lián),主體性交往不斷擴(kuò)大范圍。從閱讀方式來看,人機(jī)交互的界面使其不再局限于文本閱讀行為,而是各種主體共同到場,人機(jī)互動(dòng)、讀寫交叉、角色互換和即時(shí)交流,讓讀者在讀屏中遍歷操作的體驗(yàn)和創(chuàng)造。就文本形式而論,界面就是新媒介閱讀的文本,它依托于媒介技術(shù)存在,在持續(xù)更新和生成的文本空間內(nèi),創(chuàng)作和批評(píng)交織,語符、音影和圖像互聯(lián),形成文本塊、超鏈接和視窗疊加,各種媒介事物甚至社會(huì)生活都被納入其中。就閱讀效果而言,用戶打破視覺閱讀的感知,通過各種設(shè)備及其運(yùn)作系統(tǒng),全身心沉浸其中,全方位體會(huì)閱讀對象,在異質(zhì)關(guān)聯(lián)中豐富自我,打開感性和心靈的新天地。新媒介文學(xué)利用界面擁有異質(zhì)關(guān)聯(lián)、互動(dòng)生成和含納創(chuàng)造的性質(zhì),形成雜陳、多元和互相交織的閱讀世界。因此,應(yīng)以界面本體論要義,而非僅用語言文本來思考當(dāng)下閱讀的文化邏輯,以突顯其虛擬后現(xiàn)代性,彰顯新時(shí)代閱讀文化的價(jià)值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