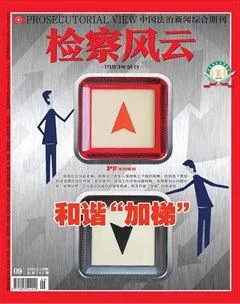劉慶邦:創作就是不斷感動和說服自己的過程

劉慶邦: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煤礦作家協會主席、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北京市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屆政協委員。
享有“短篇王”美譽的作家劉慶邦,是我國當代著名作家,其作品曾多次榮獲國內外重要文學獎項。諸如,由其小說《神木》改編的電影《盲井》獲第五十三屆柏林電影藝術節銀熊獎。近期,劉慶邦根據現實采風醞釀推出了新作《花燈調》。他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我是從剛記事的時候,就在為這部書做準備。當然,當初的準備不是文字、語言、藝術和技巧上的準備,而是饑餓的準備、生活的準備、人生的準備、生命的準備。”
潛心于鄉土文學
《檢察風云》:您近期推出的長篇小說《花燈調》被列入“2023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并入選“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和“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這究竟是一部怎樣的文學作品,您對它還有怎樣的期許?
劉慶邦:《花燈調》取材于真實人物和事件,書寫了一部天鵝女書記的播火記、丑小鴨鄉村的變形記。小說中女書記的人物原型在三山夾兩溝的深山老林,她手腳并用爬上山間小路、走訪大山里的村民,帶領村干部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在高海拔的絕壁上修建村組公路62.7公里以及水庫、水廠、山塘等基礎設施,實現了高壓電、自來水、網絡的正常使用,徹底改變了村里“人背馬馱、靠天吃飯、望天喝水”的歷史。她用7年多的時間,2700個日夜的堅守,與父老鄉親同心協力,換來了面貌一新的鄉村,也因此收獲百姓的信賴與愛戴……這部小說有著影視劇改編的豐厚潛力,我希望有識之士能早日把它搬上熒屏。
《檢察風云》:以往,您的作品中有過不少鄉土題材的作品?
劉慶邦:是的,五十多年來,趕上了能持續寫作的好時候,我已經寫了大量鄉土題材的小說。中短篇小說且不說,在寫這部《花燈調》之前,僅長篇小說就已先后出版了六部:《高高的河堤》寫的是大自然對少年兒童心靈成長的滋養,《遠方詩意》描繪了農村青年對外面世界的向往,《平原上的歌謠》記述了中國農民在三年困難時期的生存韌性,《黃泥地》揭露了國民性中的泥性,《堂叔堂》用一個個人物承載近代到當代農村的歷史滄桑。
《檢察風云》:是什么讓您產生了想寫一寫現代農村生活小說的創作沖動?
劉慶邦:我每年都回老家,對老家的變化看在眼里,動在心上。所以,一直很想寫一部記錄新農村現狀的長篇小說。可是,有了寫作的愿望和沖動,不一定就能付諸寫小說的行動。這里有一個寫作契機的問題。
《檢察風云》:是什么讓您重新燃起寫作這部作品的欲望呢?
劉慶邦:記得那是2020年的春天,《中國作家》雜志社組織全國各地的十幾位作家,到剛剛實現整體脫貧的革命老區遵義市實地采訪。在短短的三四天時間里,作家們馬不停蹄,連續走訪了不少地方,其中就有一個從深度貧困村脫貧的山村。去山村的路上,中巴車在彎彎曲曲的山道上拐來拐去,駐村第一書記不失時機,在車上就開始給我們講她的扶貧故事。她是一位女書記,她所講的為爭取扶貧項目多次流淚和哭求的經歷,讓我深受感動,留下了難忘印象。我心里一明,好,眾里尋他千百度,獲得“全國脫貧攻堅貢獻獎”的她,不正是我要尋找的駐村第一書記中的優秀代表人物嘛!
她在五姐妹中排行老二,人稱二姐。看見這個二姐,我想起我們家的二姐。我二姐也是早早入了黨,當過生產隊的婦女隊長。兩個二姐的心性有些相像,寫遵義的二姐,正好可以和我們家的二姐互相借鑒。我們只在那個山村走訪了半天,所得到的素材與一部長篇小說的容量相差甚遠,我必須再次去到那個山村,定點深入生活一段時間。于是,在兩年之后的2022年春天,剛過了端午節的第二天,我就獨自一人重返那個山村,在山村駕校的一間宿舍住下,一住就是十多天。在山村期間,二姐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差不多每天都會抽出時間跟我聊一會兒。除了在她的辦公室里聊,她還冒著連綿的細雨,帶我在山里行走。全村共四十一個村民小組,我們幾乎都走到了。她對組組戶戶的每一個村民都很熟悉,我們邊走邊聊,走到哪里都有聊不完的話題。常常是,聊到動情處,二姐滿眼都是淚水,我的眼淚也模糊了雙眼……
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
《檢察風云》:很多讀者好奇,對于作家而言,創作是一個怎樣的過程?
劉慶邦:牛想喝水,自己會喝。牛不喝水,強按頭是不行的。人做事情也是一樣,某件事情,他心甘情愿,樂此不疲,才能做得好。寫東西也是如此。寫作是手藝活兒,更是心意活兒,文思如涓涓泉水從心底流出,對自己的心意不可有半點違背。倘若逼著自己硬寫,其真誠度、含金量和質量都會大打折扣。
我們每寫一篇東西,寫什么,不寫什么,事前都有一個從感性到理性的自主選擇過程,也是說服自己的過程。不管寫長篇、中篇,還是短篇、散文,都須先把自己說服,然后方可動筆。春風不吹,花枝不搖。自己不服,何以服人?自己不感動,何以讓別人感動呢?!
《花燈調》的創作,我從夏寫到秋,從秋寫到冬,又從冬天差不多寫到來年的立春。在半年多的時間里,我每天都在寫,一天都沒停。其間我感染過“新冠”,發燒、咳嗽、嗓子疼好幾天,我照樣寫作。我常常寫得淚眼模糊,看不清稿紙上的字跡,不得不抽出一張面巾紙,搌一搌眼淚,才能繼續寫下去。將近三十萬字的寫作過程,可以說是不斷感動自己的過程,也是不斷說服自己的過程。說服自己,不是靠對自己講多少大道理,而是歷史的、現實的和自己所經歷的事實都在那里擺著,你不服都不行。
《檢察風云》:衡量一部小說的優劣,是否取決于眼淚付出的多寡?
劉慶邦:據史料記載,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巴金與朱光潛曾就作品中的眼淚問題發生過一場爭論。巴金稱贊曹禺的《雷雨》讓他流了四次眼淚,朱光潛不以為然,在《眼淚文學》中提出懷疑:“叫人流淚的多寡是否為衡量文學價值靠得住的標準?”巴金看后有些生氣,寫了數千字的《向朱光潛先生進一個忠告》,為自己的看法辯解,并批評朱光潛“少見多怪,缺乏常識”。
我認為:情感是一切文學創作的審美核心,一部作品能否打動人,首先要看他的情感是不是真誠、飽滿;而眼淚作為飽滿情感外溢的一種表現方式,它的動人力量是不容忽視的。杜甫的“人生有情淚沾臆”,還有賈島的“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花燈調》的原名為“淚為誰流”,其中的“誰”指的是誰,不言而喻。之所以最終把小說的題目改為《花燈調》,是我想來想去,覺得這個題目更有色彩,更詩意,更美,更含蓄,文學性也更強一些。花燈調是民間小調,有地方特色,更能表達民眾的心聲。
《檢察風云》:作為扎根于現實題材創作的作家,您的精神家園來自何處?您當下的創作情況可否向讀者朋友們透露一下?
劉慶邦:我有三個精神根據地,分別是故鄉、煤礦和北京。隨著精神根據地的不斷擴大,以后我可能寫北京生活的小說多一些。我今年暫時還沒有寫長篇小說的計劃,主要是寫一些短篇小說和散文。
采寫: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