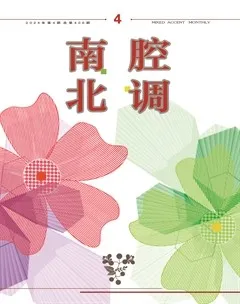鄉土女性的生存書寫和精神圖景
梁婉月 薛忠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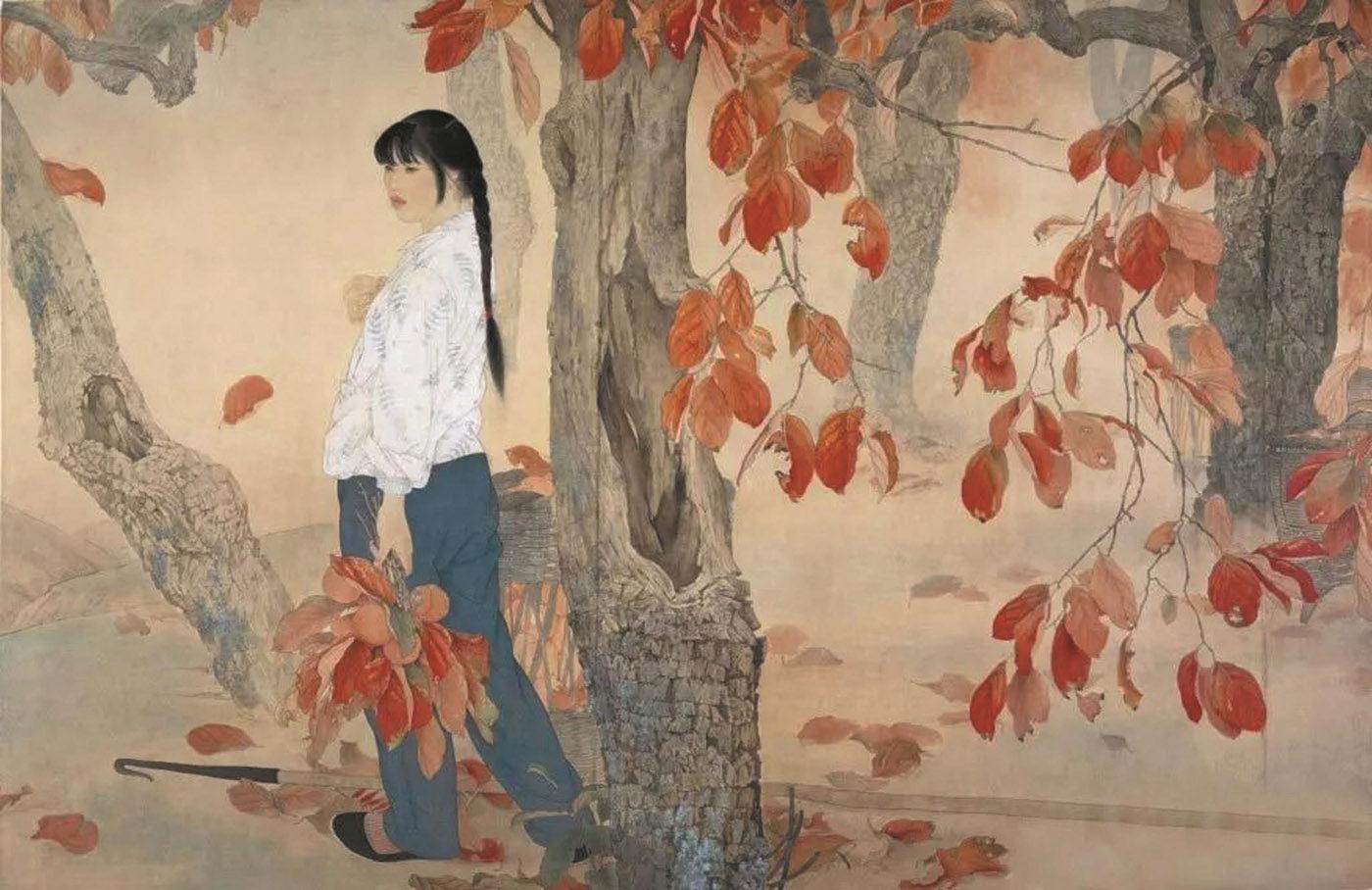
摘要:付秀瑩在長篇鄉土小說《陌上》《野望》中塑造一系列“芳村”女性,這些“芳村”女性活躍了當下的鄉土文學舞臺。她們既追求“穩定”與“親密感覺”的生命動力,又呈現出對前者的不斷叛離。她們的日常生活、潛在追求似乎存在著言語中的“第二性”與實際為行動主體的悖論,這樣的“芳村”女性成為當下再次思考“何為女性主體性”的一個典型樣本。在小說《陌上》《野望》中,付秀瑩獨特的詩性寫作,為鄉村女性書寫創造出更廣闊的想象空間,這一空間的創建為女性問題提供一個非本體論的思考方向。
關鍵詞:“芳村”女性;生命動力;主體性;詩性想象
近百年來,鄉土小說作為中國新文學的最重要組成部分,眾多作家的創作常常聚焦于“鄉村女性”,她們的形象與命運伴隨著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她們也在不同的階段呈現出不同的內在特征和價值訴求。近代以來,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女性的獨立和解放成為思想解放的重要內容,于是,以祥林嫂為代表的苦難愚鈍的鄉村女性成為迫切需要被啟蒙的對象,眾多作家也塑造一系列追求經濟獨立和精神自由、具有鮮明的女性意識的女性形象。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快速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感召下,長期囿于家庭的傳統女性終于從歷史的幕后走上前臺,在改天換地的時代擁有新的身份,拿起鋤頭、走向田地,甚或個別女性走向鄉村政治圈層,成為“能頂半邊天”的“新”女性。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思想文化的不斷嬗變及社會經濟結構的更迭,鄉村女性的形象也呈現更為復雜豐富的樣貌:她們是傷痕文學中落難的男性知識分子的靈魂撫慰者(古華《芙蓉鎮》中的胡玉音,《爬滿青藤的木屋》中的苗家阿姐,李國文《月食》中的妞妞,張賢亮《綠化樹》中的馬纓花、《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黃香久等);她們是20世紀80年代初表現鄉村變革的小說中渴求都市文明,勇于掙脫傳統禁錮的“新”女性(賈平凹《小月前本》中的小月、《雞窩洼的人家》中的煙烽,蔡測海《遠處的伐木聲》中的陽春等);另外,在 20世紀90年代“尋根”文學熱潮中,眾多女性雖然具有女性的形象特征,但作家更傾向于將其塑造為某種傳統精神文明的象征,是作者的理想寄托(莫言《豐乳肥臀》中的母親、張宇《疼痛與撫摸》中的水秀和水月、李佩甫《黑蜻蜓》中的二姐、張煒《柏慧》中的鼓額等)。
縱觀歷史上長期以來的鄉村女性敘事,鄉村女性的形象在歷史的宏大敘事中被塑造、被詮釋,雖然這與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文化思潮密切相關,但也從側面說明鄉村女性敘事一定程度上的遮蔽性。20世紀90年代以后,伴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消費主義興起,寫作出現日常化世俗化傾向,鄉村女性敘事也開始祛魅。當時的“底層文學”將關注焦點對準流入城市的鄉村女性的生活狀態及人生命運,亦有作家敏銳捕捉到進城打工潮中留守鄉村的女性,這些作品首次將鄉村女性作為敘事對象,而不是作為時代的側影來呈現。譬如孫惠芬筆下的《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中的新婚女子,作家通過大量細膩敏銳的心理描寫,展示鄉村留守女性的真實一面。但與“底層文學”敘事相伴隨的一系列爭議也一直存在,諸如作家真能代替底層發聲嗎?作家群體的城市遷移是否導致對鄉村的淺觀察、刻板記憶及主觀想象?由此可見,作家在如何深度書寫“底層女性”這條路上,仍有較大的空間。
自從作家付秀瑩于2009年發表短篇小說《愛情永流傳》,她的“芳村”敘事就在文壇掀起討論熱潮,她筆下的“芳村”女性在中國近百年來的鄉土小說發展史上,有著獨特的功能和審美價值。總結有三:一是付秀瑩正面走向“芳村”女性,關注她們的一日三餐、喜怒哀樂和人情世故,塑造出一系列能夠體現當下中國鄉村女性現狀的鮮活的生命形象;二是對“芳村”女性日常生活工筆畫式的細膩描摹背后,接續對于城市與鄉村、現代與傳統,尤其是女性主體性的深入思考,為批評家與讀者解讀當下鄉村女性提供典型樣本;三是從作家創作角度分析,付秀瑩提供一種超性別、超道德的寫作范式,并依托著個人獨特的文學敏思與鄉村經驗,表現出濃厚的地母情結,使其筆下的“芳村”女性呈現出詩性美感,這一詩性書寫背后也傳遞出更為多元、開放的女性主體觀。
一、穩定、親密的生命動力與叛離
付秀瑩筆下的“芳村”女性生活在中國最為普遍的鄉村,這樣的鄉村具有中國傳統農耕社會最基本的特征,人們維持生活日常主要依靠“禮治”原則。正如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的解釋:“所謂禮治就是對傳統規則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關系,都有著一定的規則,行為者對于這些規則從小就熟習,不問理由而認為是當然的。長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規則化成內在的習慣。維持禮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權力,而在身內的良心。”[1]這種禮治原則也是朱莉婭·克里斯蒂娃所說的“時間秩序”:“對于會說話的動物而言,就是客觀時間的鐘表:通過定義一個過去、現在和未來,它提供參照點,因而使度量成為可能。”[2]鄉村女性作為禮治文化抑或時間秩序中最典型的文學形象圖譜之一,歷來受到不同作家的關注。從作家的性別角度分析,男性作家更多傾向于將筆下的鄉村女性塑造為功能型、象征型、想象型角色。如擅長寫陜西鄉土風情的賈平凹,在其力作《秦腔》中有許多關于鄉土女性哭鬧打罵扯皮的生動描寫,作家將細膩敏銳的眼光觀察到的鄉村女性的外在行為特點轉為文字,成為其小說勾勒鄉村圖景的元素之一,同時,《秦腔》中有著完美人格的女主人公白雪,其實是作為鄉土文明的象征來塑造,具有文化尋根中的超現實意義。莫言《豐乳肥臀》里的母親,劉慶邦小說中一系列純情天真的少女,也都明顯帶有象征及想象的指向性。對比之下,女性作家更為擅長描寫鄉村女性內心的成長變化、微妙的生命體驗以及性意識等。女性作家憑借性別優勢,能夠從內傾性角度對鄉村女性展開不同的探索。對于付秀瑩來說,她的兩部“芳村”長篇小說延續女性作家書寫特長,敏銳捕捉到當下的時代背景下的鄉村女性特質,并且擅長使用大量的日常對話語言,這樣的語言網絡織就“芳村女性”的形象圖譜。
用王冰冰的話形容,“芳村”女性可以被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青衣,一類是花旦”[3]。與茅盾小說中最常出現的優雅古典的女性和時髦開放的女性代表著兩種共存的文化一樣,“青衣”代表深受傳統文化浸潤的傳統鄉村女性,“花旦”則更具時代變化新質。對于“青衣”而言,兒女的婚姻大事、婆媳相處及鄰里間的禮尚往來等是其日常生活的核心,她們通過這些日常行為來建構親密、穩定的生命動力。如在《野望》一開篇,敘述人就用大量的篇幅來寫翠臺想盡辦法勸兒媳婦愛梨回家。在《陌上》第三章,翠臺在兒媳婦愛梨不在時,自己包餃子吃,愛梨突然回家,作者細膩描摹翠臺當時的心理活動:“翠臺見了,趕忙立起來,摩挲著兩只沾滿面粉的手,問愛梨怎么回來了?話一出口,又覺得不妥,好像是不愿意人家回來似的,趕忙說,還想著你會不會在田莊住一宿呢。這話又不對。仿佛是多嫌人家的意思。”[4]這段心理描寫將婆媳之間相處的微妙展現出來,因為一個處世得體有分寸的婆婆形象對于翠臺來說非常重要,這牽涉到禮治文化對一個鄉村女性的浸潤和影響。除此以外,鄉村中常見的紅白喜事更是禮治文化的強有力表達。在這些集體事件中,“芳村”女性如何扮演合適角色、如何合理言談、如何恰當地處理問題才能更好地維持風俗禮治,是她們所依托的判斷標準,也因此形成鄉村禮治秩序中集體性的生命動力場。這在《野望》中一場紅事和一場白事的敘事中都有體現。
需要指出的是,在表面的穩定親密的秩序背后,伴隨著現代化對鄉村文明的不斷入侵,“芳村”女性表現出不同于傳統鄉村女性的某些叛離特質,這主要表現在情感關系層面,禮治更偏向于成為一種淺表的慣性秩序,雖然在家庭之外仍起著一定的行為規范作用,但實際的家庭內部卻經常處于一種崩裂的混沌狀態。婚姻中的男性不再天然享有男權中心思想下的掌控權,尤其那些難以承擔經濟責任的男性,他們僅獲得概念上的某種“中心”權力。像《陌上》《野望》中的大坡、根生、占良等,因未能在新的時代語境中經濟獲利,成為同村男性中的“弱者”,處境最是尷尬。
在總體上,“芳村”女性在環境變化中有著更為主動的行動力,但她們更多借助男性所代表的傳統“中心”話語來達成自己真正的目的。男性是她們口頭上的“一家之主”,但在實際生活中,擁有決定權的主體已悄然被置換,女性是家庭瑣碎生活的管理者,男性則更多以回避者的形象出現。所以,在經濟和意識層面,“芳村”女性在維系傳統的家庭秩序的基礎上,她們的觀念不再保守封閉,而是有著明顯的趨利心態,盡管這種趨利心態,更多是由其所維持的傳統禮治秩序受到消費主義的影響形成的,是一種無意識的心態。于是,在“芳村”的世界中,妯娌、連襟和兄弟姐妹之間的行為習慣逐漸失去傳統禮治的依托,占有經濟或權力的一方,成為潛在的話語中心,如大全、建信、中樹、香羅和小鸞等。所以,“芳村”女性在新的環境變化中表現出既保守又顛覆、既淳厚又狡黠的新特質。現代化對“芳村”的改變也體現在性意識層面,傳統禮制社會牢不可破的婚戀觀念變得含混而充滿悖論,所謂“貞節”“婦道”之類的傳統觀念,更多成為一種公共場合的修辭式話語,表面上依然傳統的當代鄉村女性,實際踐行的卻是一種開放式的性觀念。在某些情境里,性甚至會成為一種帶有目的的交換行為。如香羅的發廊、小欒飯館的經營權等,都離不開與權力相關的身體交換。
費孝通曾說:“在一個變遷很快的社會,傳統的效力是無法保證的。不管一種生活的方法在過去是怎樣有效,如果環境一改變,誰也不能再依著法子去應付新的問題了。”[5] “芳村”依靠皮革廠發家的男性成為人們口中的大老板,其他未能搭上經濟快車的人成為廠里的打工者,因此在禮治秩序形成的親疏關系基礎上,又多一層經濟利益關系,以此形成的強大衍射場使得“芳村”女性長久依歸的價值體系逐漸崩裂,置于她們面前的是難以被辨別的復雜社會。可以說,這種對于穩定、親密的生命動力的叛離是在無意識中悄然發生的,而這種叛離又有著極強的矛盾性:在欲望支配叛離行為的同時,有時是為了更好地回歸穩定和親密。《陌上》《野望》中的“花旦”香羅就是這類人物的典型。香羅作為芳村最具威望的女性,依靠與大全的曖昧關系經營著自己的“灰色”發廊,優越的經濟和豐富的資源改變她在芳村禮治秩序中的角色,成為芳村人心目中主持大局和解決問題的核心角色,翠臺兒子和兒媳的紛爭、有子的借貸麻煩和有子他娘的白事,種種事件都展露出香羅在芳村的特殊存在。而香羅本人張羅處理這些鄰里事件,既是為了彰顯自己與眾不同的身份和價值,潛在的動力更是為維護其內在一直習慣的穩定和親密關系。除香羅外,其他的“芳村”女性也產生不同程度的精神裂變,她們在傳統與現代、秩序與叛離之間不斷蛻變取舍,呈現出變革進程中復雜鮮活的生命狀態。
所以,由“芳村”女性管窺當下的鄉村女性,盡管隨著社會的發展,她們所能活動的范圍在不斷擴大,但其主體意識的形成和轉變仍然比較滯后,雖然擁有更多的角色屬性,但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和水平還比較脆弱,并容易混淆性與愛、身體與欲望、自由與放縱等概念,從而表現出看似主動,實則被動的處境。這實際上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容易出現的階段性特征,付秀瑩把握住這一階段的鄉村女性獨有的生命特質,進一步引起大眾對于當下鄉村女性生存狀態的關注與思考。
二、不被定義的“主體性”
毋庸諱言,在《陌上》《野望》中,“芳村”女性所呈現的新的生命特質更多是從文化心理層面而言,而一直以來的鄉村社會秩序依然穩固,她們如果想獲得性別建構新的可能性,仍然有著重重阻礙。她們的主體意識雖然在覺醒,但她們依然要依憑男性所代表的權威,這造成某種意義上的分裂:在日常言語層面,“芳村”女性仍然依托傳統禮治語境中的話語體系來維持穩定、親密的生命動力,但在實際生活中,她們似乎已經具有某種主體性,擁有一定自由的生命空間,雖然這種自由十分有限。不同于以性和生殖為旨歸的傳統的生理性別,當下的鄉村女性也具有越來越多的社會屬性,雖然這一社會屬性的強化仍面臨著難以把控的現狀,雖然這些現狀并未引起“芳村”女性警覺和思考,但是建構著她們的生存狀態。
20世紀上半葉,伍爾夫分別在兩所學院就“女性與小說”為題發表演講,之后其將兩篇講稿整理出版,書籍被命名為《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書中鮮明的女性意識給中國知識女性帶來深刻影響。伍爾夫采用“意識流+自傳式”的敘述方式講述外界環境帶給自己的真切感受,并尋找著屬于自己的真正“房間”,這直接影響到冰心、凌書華、丁玲等“五四”新文學作家的自傳體書寫,在《冰心自傳》《古韻》《莎菲女士的日記》等作品中,女性開始以主人公的身份表達對內心及外部世界的敏銳感知。對比之下,改革開放以來的女性寫作,更加自覺地將女性的生命意識融入當時的社會語境,在自我書寫的同時,也給予其他女性尤其是底層女性更多的體察和關注。但這種“代敘述”的寫作視角,始終充滿著“他者”意味,可能會被作家本人的個人視角和創作風格所影響。尤其隨著城鄉差異的縮小,鄉村女性的視域不斷被拓寬,出現以余秀華、姜蘭芳等為代表的農民作家,她們對個體生命的書寫開啟女性表達的新局面。余秀華在詩歌《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中大膽直白的真情流露,充滿著女性特有的張力,挑戰人們對鄉村女性的認知和想象。許多其他的作家,對于鄉土女性的敘述也不再抱持守舊心態。而付秀瑩的“芳村”小說之所以引起議論熱潮,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她的創作不再一味地探究鄉村女性到底需要建構怎樣的主體意識,而是將關注點聚焦在人性上,著重表現鄉村女性的生命張力。因此,付秀瑩找到一個有力的敘述抓手,以人性的恒常不變來書寫鄉村的巨變。這一轉向和付秀瑩本人的寫作偏好有直接關系,在《野望》新書分享會上她也表述過:“但我只負責表達和呈現,讀者自己會從中去辨認,去認清我們這個時代復雜的、豐富的、多樣的表情。”[6]在這一創作傾向下,付秀瑩的“芳村”小說采用一種日常絮絮叨叨的言語方式,展現出與眾不同的日常生活情趣,讓大家看到不斷遞變的鮮活的鄉村生態。同時,付秀瑩也并未陷入民俗風情書寫或沈從文式的人性美想象,而是通過密集的日常話語,充分凸顯語言結構的張力,以此來呈現“芳村”女性的鮮活生命特征。
從敘述特點看,《陌上》《野望》的語言具有充分的“表演性”,因為“言語不獨獨屬于身體表現,也不獨獨屬于語言,而它同時作為言語和行為的特質必然是曖昧的”[7]。言語的曖昧表現主要通過具體文本的“語境”來實現。尤其對于鄉村而言,以傳統禮治為主要生活方式的人們,在言語和行為方面都默契地依托著一定的規則,但隨著時代的變遷,規則本身不可避免地出現諸多裂隙,被作者通過文學表現出來。對于“芳村”女性而言,日常社交場合通常使用一套傳統的不易出錯的交際言語,來達到維護親密關系的目的,而私下里的種種情緒性言語,更趨向于真實的內心活動。最為典型的是小說中妯娌翠臺與香羅之間的微妙關系,經濟實力懸殊打破她們倆之間的相處方式,因此,翠臺雖然一方面看不慣香羅的種種行為,另一方面卻期望能夠通過香羅的幫助來解決家中的難題,因此在文本敘述中,她們的言語和行為表達充滿著含混和曖昧性。
付秀瑩曾說:“中國鄉村是熟人社會,盤根錯節,牽藤扯蔓,寫好這些關系,才能寫好鄉土社會。”[8]對身處復雜環境的“芳村”女性來說,夫妻之間、婆媳之間以及鄰里之間等都需要不同的相處模式,而語言的表演性使付秀瑩的敘述具有很強的藝術渲染力,能夠很好地表現“芳村”女性的生存狀態,那種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樂是她們生命力的表達。
雖然今天的中國鄉村正在經歷著激烈的變革,但鄉村女性還在延續著以前的生存狀態,付秀瑩傾向于從人性視角展開的敘述,為鄉村女性的生存書寫及精神圖景的建構提供新思路和新方向,這其實代表著后現代主義的傾向,主張“要以差異的、分散的和沖突的自我,去解構現代主義之統一的、既定的、理性的和自主的主體”[9]。在這一傾向下,作家書寫當下鄉村女性擁有更開放的視角和空間,能夠盡可能真實地呈現出當下鄉村女性的生存狀態。
三、詩性書寫潛隱的女性想象
“詩性”在中西學界的闡釋中并沒有一個明晰的定義。西方學界眼中的“詩性”意在強調作家運用個人感知及想象所創造出的某種原初本性。如海德格爾的“詩性之思”是體驗美的境界的一種方式,他認為“詩性思維是一種超功利的直觀思維,也是一種非理性思維”[10];中國古典美學中的“言意”之辨、“意境說”比較切近于“詩性”這一概念。
在女性作家的創作中,詩性敘事常常體現在她們更傾向于用平視的眼光和溫和的心態去關注普通民眾,期待和倡導“一種充滿溫厚、寬容與混沌的母愛的自然流露的社會氛圍”[11]。當這慈悲和寬容足夠深沉,就會演變為許多作品中潛在的地母情結,付秀瑩也在“芳村”系列小說中搭建出大地——母親的隱喻結構,但與其他作家擅長通過懷孕、生產的母親或女性的魔幻化來表征地母情結所不同的是,付秀瑩在自然景觀與“芳村”女性敘事之間找到很好的契合點,在情與景的巧妙遞轉融合中,這些日常生活中絮絮叨叨的普通“芳村”女性,便具有審美層面的詩性魅力。
奧野健男在《文學中的原風景》一書中提出“原風景”概念,對此,建筑理論家蘆原義信評述道:“這些作家心目中的‘原風景不是旅游者所看到的自然風土或景色,而是充滿感情色彩的風景,它常常作為文學的出發點而表現在作品當中……”[12]作為有著濃厚故鄉情結和豐富鄉村生活經驗的作家,付秀瑩對于農村的四時景致有著特殊的敏感和別樣情懷,當她調動曾經的記憶和充分的想象來建構藝術化的“故鄉”,景色就已不只具有自然屬性,而是充滿著隱喻色彩。如在《陌上》第二章“香羅是小蜜果的閨女”中,在香羅與大全發生親密關系后,付秀瑩對曖昧的具體過程輕描淡寫,戛然而止,卻把筆觸對準窗外的風景:
天色忽然就暗下來,是一片云彩,把太陽遮住了。轉眼就是芒種。這個時節,怎么說,一塊云彩飛過,指不定就是一陣子雨、一陣子風呢,說不好就又是一片云。這個時節,這種事情,誰能說得清?
麥子們已經秀了穗,正是灌漿的時候。……
正如曹文軒在評價《陌上》這部作品時說過:“在一個失去風景的時代,閱讀她的作品,我們隨時可以與風景相遇。”[13]這段描寫完美詮釋 “所有景語皆情語”。在這里,付秀瑩無意從倫理道德的角度關注香羅與大全之間的情感,而更像是一位平和的觀察者,通過人事與風景的融合書寫,給故事中的人物鍍上一層朦朧、夢幻的詩性美感,風景也似乎具有人情,“云彩”“雨”“風”都不再只具有自然屬性,也被鍍上濃厚的人情風味,同時也顯現出作者本人潛意識中的地母情結。
在大地——母親的整體隱喻結構之下,付秀瑩有著明顯的中國古典審美傾向。一方面,付秀瑩尤為擅長通過對房屋建筑、內飾風格及生活細節工筆畫式的勾勒來凸顯人物的性格特點,這其實是對“紅樓夢”式中國古典小說寫法的借鑒。如曹雪芹在《紅樓夢》第五回中,通過寶玉的視角,小說對秦可卿的臥房進行細致入微的描寫,其裝飾布置和光線氛圍都是對浪漫香艷的環境的烘托,也在巧妙暗示秦可卿的風流特征。在《野望》第一章“小寒”中,翠臺去看望妹妹素臺時,作者首先詳盡勾畫迎面看到的大影壁、高臺階和一溜排開的屋子,同時突出描寫影壁旁花池里枯敗的花草和攤在暖和舒服的屋子里已經曬干的衣物,自然而然塑造出素臺的懶散。另一方面,付秀瑩尤為擅長對夢境敘事的頻繁運用。對比《陌上》《野望》兩部作品,讀者明顯可以看出付秀瑩對夢境敘事手法運用得越來越嫻熟,在《陌上》中,夢境的敘事多顯重復、刻意,而在《野望》中已然能和整個文本的敘事悄然融為一體,有著畫龍點睛之效。夢境作為傳統敘事的常用手法,通常能夠營造出神秘夢幻的審美氛圍,亦滲透著作家或作家筆下人物所潛藏的深層意識。正如龍迪勇在《夢:時間與敘事》中這樣闡釋“夢”,“夢實質上是在潛意識中進行的一種敘事行為。與意識中的敘事一樣,夢中的敘事也是一種為了抗拒遺忘、追尋失去的時間,并確認自己身份、證知自己存在的行為。”[14]在《陌上》《野望》中,夢境經常被用來表達“芳村”女性超越現實生活的潛在欲望。如在《陌上》第四章“素臺兩口子吵架了”,吵架后氣惱煩躁的素臺昏沉睡下,就做夢夢見丈夫增志回來求和,并十分溫柔體貼的樣子。在《野望》第三章“立春”中,被兒子和媳婦之間的吵鬧和拮據的生活攪擾得心煩意亂的翠臺,在夢中走進了一個“仙氣繚繞”的世外仙境,她顧不得聆聽仙家所說的深刻教誨,只顧著撿拾遍地的金銀財寶,最后低頭一看竟然是“滿懷屎尿,臭氣熏天”……豐富多樣的夢境敘事讓我們看到“芳村”女性潛在的欲望本能,作者借助夢境很好地表現出“芳村”女性內心的復雜性,而夢境所代表的夢幻、不真實性賦予小說文本濃厚的詩性浪漫。縱觀當下的鄉村女性書寫,付秀瑩的表達方式是新穎的,這種詩性浪漫的手法,并非對鄉村女性“生存命題”的遮蔽,而是對她們精神世界的溫情凝視。
藝術家對于女性情感生活的表達和處理,歷來多種多樣:央視86版《西游記》中,導演通過一段凄美的歌曲,表現女兒國國王對唐三藏的真情流露;余秀華詩歌對于欲望勇敢赤裸的表達并不局限于欲望的書寫,而是在表達生存的困惑和精神的掙扎;“芳村”系列中的性敘事常常是詩化的,付秀瑩尤其擅長使用留白的手法,使作品有著古典含蓄之美。比如,《陌上》《野望》中香羅和大全、小鸞和中樹都屬于婚姻之外的曖昧關系,對于此種曖昧混沌的情感關系,作者在敘事中只對當時情境中人性的潛在流動作蜻蜓點水式的克制表達,不作任何傾向性評價,這種表達,使性回歸到更為自然的人性本身,也彰顯作者本人寫作時的詩性審美風格。
在當代文學中,與付秀瑩寄于“芳村”女性的詩性想象同在的,還有遲子建的“北極村”、馬金蓮的“西海固”以及李娟的“阿勒泰”等,她們從不同側面貼近當下的鄉村女性,并不急于用批判式的眼光去發現鄉村女性的閉塞,而是滿懷詩性想象,把對鄉村女性的認知導引到一個可能的新方向:不同時代的女性,她們本身都凝聚著無限的經驗和可能,她們所展現出的女性狀態都是某一階段的歷史經驗的積累,更是豐富復雜的人性的彰顯。這一書寫呈現出更為多彩的鄉村女性的精神世界,有效突破人們通常印象中鄉村女性意味的刻板和滯后,是對鄉村女性生存狀態的正面書寫和與時俱進的形象表達,而這些鮮活的形象或許更能展現她們的精神圖譜,也是對當下生活更為豐富完整的記錄。
四、結 語
付秀瑩以《陌上》《野望》為代表的“芳村”小說,是21世紀鄉土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芳村”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當下社會環境的鄉村女性生存狀態。她們追求穩定、親密又不斷叛離的精神特質是時代發展下的鄉村側影,能夠引起學者與大眾對于鄉土女性形象的不斷思考。而付秀瑩以人性角度為抓手,對鄉村女性的詩性想象和書寫,表現一種不被定義的女性主體意識,這與后現代主義的主流傾向是一致的。付秀瑩在中國本土資源中,用獨特的話語結構與審美體驗譜寫出屬于本土女性的精神圖景,這一圖景也必然會成為文學中鄉土女性書寫的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1][5]費孝通. 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82,78.
[2] [法]朱麗婭·克里斯蒂娃.中國婦女[M].趙靚,譯.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10:28.
[3]王冰冰.一場愁夢酒醒時,斜陽卻照深深院——解讀付秀瑩《陌上》[J].百家評論,2018(4).
[4]付秀瑩.陌上[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59.
[6]付小平.支撐創作的,依然是堅實的生活邏輯[N].文學報,2022-8-11.
[7][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M]. 宋素鳳,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19.
[8]舒晉瑜.付秀瑩:小說家一定要熱愛人間煙火[N].中華讀書報,2022-7-13.
[9]戴雪紅.“主體之死”與女性主體性重構 ——弗雷澤、本哈比和巴特勒之間的現代與后現代之爭[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10).
[10]王兵兵.論海德格爾的“真”與“美”[J].當代外國文學,1994(3).
[11]董之林:女性主義批評,并不奢侈的今日話題,王紅旗,主編:中國女性文化No.2[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90.
[12][日]蘆原義信.街道的美學[M]. 尹培桐,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108.
[13]曹文軒.付秀瑩長篇小說《陌上》——富有靈性的個人創造[N].文藝報,2016-11-16.
[14]龍迪勇.夢:時間與敘事[J].江西社會科學,2002(8).
作者單位:武警工程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