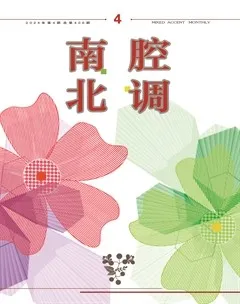“歸去來兮”:孫全鵬《幸福的種子》的新鄉土書寫
劉啟濤
摘 要:孫全鵬的新作《幸福的種子》是一部典型的新鄉土小說,作家以地處豫東南大地的將軍寺村近30年的發展變遷為背景,以麥子、河生、珍珍、小玲等青年一代將軍寺人“離鄉—返鄉”的軌跡為主線,書寫一曲新時代語境下的田園牧歌。作品充滿濃郁的鄉土意識和鮮明的時代特征,表現作家對傳統鄉土文學書寫的繼承和突破以及對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深刻思考。
關鍵詞:《幸福的種子》;“離鄉—返鄉”;新鄉土書寫;鄉村振興
長篇小說《幸福的種子》是周口新銳作家孫全鵬繼小說集《幸福的日子》之后推出的又一力作。小說的敘事背景設置在地處豫東南的將軍寺村,作家以麥子、河生、珍珍、小玲等青年一代將軍寺人“離鄉—返鄉”的軌跡為主線,講述了將軍寺村走向時代振興的故事。作家把一代農村新人的成長歷程,與鄉村振興的時代大事結合起來,于宏大的時代主題之下建構起一幅洋溢著詩性魅力的新田園景象,塑造了一群朝氣蓬勃的時代新人,講述了他們可歌可嘆的奮斗故事。可以說,《幸福的種子》是一部個人奮斗與鄉村發展的變奏曲,也是一曲新時代語境下的田園牧歌。

一、新時代語境下的鄉村講述
鄉土小說發軔于20世紀20年代,最早是一批寓居北京的青年“用筆寫出他的胸臆”[1]。在五四新文化運動背景下,這批經受現代文化洗禮的青年作家,懷著現代的眼光回望鄉村,他們的字里行間滲透了文化的悲哀和啟蒙的熱情。活躍于20世紀20年代文壇的最初一批鄉土作家多是效法魯迅,以冷峻的筆法書寫老中國鄉村的人和事。破敗的風景和愚昧的鄉民,成為早期鄉土小說的主要內容,也奠定了鄉土小說的文化批判基調。到廢名、沈從文的出現,鄉土小說有了新的轉機,牧歌式的田園風光,人情美、人性美的主題發掘,賦予鄉村以新的藝術魅力。差不多與此同時出現的左翼鄉土文學,以其階級性、革命性為核心的斗爭激情迅速引起社會關注。縱觀整個20世紀鄉土文學的變遷,我們不難發現有這樣三種主要書寫模式貫穿其中,即文化批判式、田園牧歌式和激情浪漫式。這三種書寫模式也構成“中國式鄉村”的三種典型形態,在不同的時期,作家們對鄉村的講述也表現出不同的風格特征。
進入21世紀,中國鄉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新時代以后,在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一系列國家重大方針的推動下,中國鄉村擺脫了愚昧、貧窮的標簽,以新的村容村貌見于世人。中國鄉村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而這一切變化均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幾十年間。如何表現這一歷史性進程,也成為新時代賦予作家的一項全新使命。從很大程度上說,這一使命也注定要落在孫全鵬這一代“80后”作家的身上。作為改革開放后從農村走出來的一代作家,孫全鵬的成長伴隨了中國鄉村結構性變革發生的幾十年。目前,這些作家年齡稍大的已近不惑之年,曾幾何時,他們拼命通過考學、打工等方式走出農村。可是當他們真正走出農村之后,又對農村充滿無限眷戀,農村成為他們魂牽夢縈的地方。改革開放以后幾十年中國鄉村的發展,形成農村“80后”青年一代特殊的鄉土觀念。這種鄉土情結既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根深蒂固,也不像他們的后輩那樣根性盡失。
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孫全鵬無疑是一個有著強烈文學自覺意識的作家,他從一開始就將自己的文學之根深深扎于豫東南大地,建構起將軍寺這一文學原鄉。在他的小說中,將軍寺村、將軍寺河是一套頻繁出現的地理意象。用評論家胡平先生的話說:“‘將軍寺村是全鵬小說中穩定的地理坐標,幾乎所有人物都與這座村莊相關。將軍寺也的確是個不同俗響的村名,給人帶來不少遐想。”[2]很顯然,將軍寺村并不能全然等同于孫全鵬現實生活的那個村落,而應該是“豫東南的一個縮影”[3]。它寄寓了孫全鵬深厚的鄉土情懷,以及對故鄉的全部想象,而《幸福的種子》正是作家這種情懷和想象的結晶。孫全鵬在后記中這樣寫道:“每次我回老家,走過那個叫‘將軍寺溝的地方——我已經發了一些關于將軍寺的小說,一到夜里總會有些東西跑進我的腦海中,讓我感到親切。一個個夜里,星光之下,這些可愛的人物從我‘手里跳了出來,形成這部長篇小說。”[4]
不難看出,孫全鵬并不是從一種局外人的視角出發,而是懷著深深的赤子情懷來寫這部小說的。《幸福的種子》中的將軍寺村也不是一個單純的敘事場域,其自身就是一個鮮活生動且蘊藏著豐富情感的藝術形象。小說的開篇是一段抒情性的風景描寫:“珍珍再次站在將軍寺河邊,她怎么也想不到,她還是喜歡那翻騰的將軍寺河水中漂浮著的小船。那河水清是清,白是白,圍繞著整個將軍寺村通向遠方,黃花菜依舊站在河畔,搖晃著金黃色的花朵。”[5]
在這部小說中,珍珍是作家精心設計的一個形象,她也可以稱得上是“將軍寺河的女兒”。當年,珍珍的生母桃紅愛上了來村里放電影的王新,一來二去就懷上了珍珍。后來才知道對方已有家室,桃紅不得已嫁給鄰村的男人,婚后經不住丈夫的欺侮,就跳了將軍寺河,連尸首也沒有找到。珍珍由此成了孤兒,與奶奶(其實是外婆)相依為命。孤苦的身世使珍珍對將軍寺村有著異常的眷戀,尤其在聽奶奶講完母親的故事之后,她對將軍寺河更是有一種母親般的親近。小說以離鄉多年的珍珍為視點,深情地描寫了將軍寺河以及沿岸的風景,風景的秀美也成為作家強烈赤子情懷表達的一種方式。相比于孫全鵬以往的小說而言,對豫東南鄉村風光的詩性書寫是《幸福的種子》的一個典型特征。秀美的風景描寫在小說中俯拾皆是,比如寫到秋收時的原野:“秋天的莊稼地一片金黃,有些人已經開始收秋莊稼了,大豆、芝麻、綠豆還沒有收完,螞蚱、蝗蟲‘嗡嗡亂飛,麻雀貼著莊稼棵子掠過。玉米葉子有的都發黃了,還不愿意脫落下來,風一吹搖晃著吱吱響,玉米頭上的紅纓子也干了,一撮一撮的。”[6]
不難看出,作家有意把風景描寫視為將軍寺村日常生活的另一種觀照。作為新時代周口文學的一項重要成果,《幸福的種子》在某種程度上開啟了新時代豫東南鄉土文學敘事的一個新的模式。作家花大量筆墨建構出一個富有煙火氣息的鄉村形象,并根據不同時代的特征細致描摹將軍寺村的風貌,以及村里人的生活狀況。孫全鵬有意通過一種寫實手法,全方位地呈現出一個充滿詩性且生動鮮活的鄉村。為了做到這一點,作家還引用一種民族志手法,在精心地描寫將軍寺村生活的每一處細節的同時,也對村里的婚喪嫁娶等民風民俗進行呈現,比如秋奶奶的兒子阿明的婚禮、河生奶奶的葬禮等。除此之外,作家還將豫東南農村那些廣為流傳的民間歌謠原生態地引入小說當中,比如阿霞哄著孩子一邊哼唱:“小雞嘎嘎,好吃黃瓜。黃瓜有水,好吃雞腿。雞腿有毛,好吃仙桃。仙桃有核,好吃牛犢。牛犢撒歡,撒到天邊。……”就是豫東南鄉村生活常見的一幕場景描寫,民俗元素的融入賦予《幸福的種子》一種特有的鄉土氣息。周口籍著名作家墨白在看完這部小說之后,頗為感慨地說:“全鵬文字里濃密的充滿豫東泥土的氣息勾起了我對童年與故鄉的懷想。”[7]在《幸福的種子》中,存在著一個世俗化的、生動真實的鄉村世界。
值得肯定的是,孫全鵬所建構的并不是一個傳統的鄉村故事,而是發生在當代中國尤其是近30年中國的鄉村之變。這也成為孫全鵬與他的前輩作家劉慶邦、孫方友和墨白等人最大的區別,他所面對的鄉村不是一個靜態的鄉村,而是一個正在發生著時代巨變的地理空間。同樣身處這片古老土地,孫全鵬最大的資源不在于對各類鄉間掌故、鄰里關系的深刻洞察,而是對新的時代大潮中鄉村之變的深刻認識。他的興趣點不是去建構一個個充滿傳奇的故事,而是透過個人在時代大潮中的體悟帶動新時代鄉村之變的講述。實際上,《幸福的種子》以麥子、河生、珍珍、小玲等年青年一代將軍寺人的成長軌跡為主線,講述了這個豫東南村落近30年來的發展蛻變,從而完成對新時代語境下鄉村變遷的文學講述。小說從麥子等人的童年講起,一直到當下正在發生的鄉村振興。以將軍寺人對幸福生活的追求為話題,《幸福的種子》從一個側面描繪出一個豫東南鄉村最近30余年變遷的縮影。
二、“離鄉”書寫與幸福追尋的心路
《幸福的種子》是一部有歷史厚度的作品,小說時間上跨越了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紀20年代初,這段時間是中國鄉村變革最大的幾十年。我們由此也不難看出孫全鵬的文學理想,作家試圖將近30年家鄉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以及豫東南人們在這場歷史之變中的生活狀態呈現于世人,從而賦予《幸福的種子》一種可貴的史詩品格。這種史詩品格并不體現為一種宏大的主旋律敘事,而是指向了當代農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心路歷程,就如丁帆先生所說的:“站在現實大地上向前看。”[8]胡平先生也敏銳地從孫全鵬的小說中發現,“‘幸福在全鵬的寫作中,常成為關鍵詞之一。”[9]從最初的短篇小說集《幸福的日子》到新作長篇小說《幸福的種子》,孫全鵬關注的話題始終是幸福。不過,從農村走出的孫全鵬也必然深刻意識到,幸福對農民來說很多時候是個沉重的話題。雖然《幸福的種子》表面上呈現給人的是一個歡快的主旋律故事,但是其字里行間卻透露出將軍寺人在當下社會所承受的生存壓力和精神困惑。
《幸福的種子》超過三分之二的篇幅寫的都是將軍寺人的“離鄉”故事,委婉地表達了作家對農民階層歷史悲劇和現實處境的深沉思考。在數千年的農業社會里,農民始終是與“苦難”一詞聯系在一起的,這種苦難集中體現為人與土地充滿張力的矛盾關系。一方面,農民從土地那里獲得了生存的保障,長年累月的勞作滋養了人對土地的深厚情感;另一方面,土地又是農民現實苦難的載體,成為漫無邊際的艱辛勞作和絕望精神的象征。鄉土中國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部農民的血汗史,一代又一代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地從事著艱辛勞作,同時也在窮其一生去掙脫這種令人窒息的人地關系。從魯迅的《故鄉》到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離鄉”成為20世紀中國鄉土小說的一個重要主題。通過走出祖祖輩輩生老于斯的鄉村,以《故鄉》為代表的現代文學表達的更多是走出老中國愚昧、落后的陰影,從而接受現代文明并完成對傳統鄉土社會的啟蒙。在當代文學,尤其是新時期以來的文學作品中,離開鄉村的直接目的則是為了進入城市,實現物質生活的根本性轉變,同時也涵蓋人們對實現個體價值的強烈訴求。《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的人生道路就具有極強的代表性,離開農村是以孫少平為代表的20世紀80年代農村青年的強烈渴望,也是在他看來實現自我價值的根本前提。
從某種程度上說,《幸福的種子》與《平凡的世界》有一定的互文性。小說中有一個片段,河生偶然在書攤上看到了《平凡的世界》,即便他收入微薄還是購買了一套,沒事的時候就翻翻看看,孫少平的命運讓他心疼。對于沒上完初中且不愛讀書的河生來說,他對孫少平的命運之所以會產生如此強烈的共鳴,最重要的原因無疑是其作為進城農民的特殊感受。河生這一形象與孫少平有著諸多相似之處,他的人生道路也代表了豫東南鄉村最平凡的青年一代農民在新的時代語境下的人生選擇。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結構和城鄉格局大轉型的背景下,傳統鄉土社會那種僵化的“人—地”關系很難再繼續維系,大批農民紛紛掙脫土地的束縛進入城市。小說中麥子每次回將軍寺,總會發現“村里人比以前又少了不少”。就連小說中最具古風的三老太爺也說:“人不出去走走,一輩子憋死在村里也沒人知道你。我是年紀大了,不出去了,要是年輕幾歲,我也走走。”[10]這也是孫全鵬這一代鄉土作家所面對的一個普遍的精神困境:一方面,他們對傳統鄉村有著深厚的情感;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得不去面對鄉村日漸淪為空巢的現實。對于他們來說,農民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的社會身份,還是一種浸入骨髓的文化認同,其中蘊含著諸多難以言說的生活體驗和人生記憶。雖然孫全鵬對鄉村日漸淪為空巢的事實感到痛心,但是他對當下農民的“離鄉”現象還是持積極肯定態度的。因為他很清楚,農民只有從鄉村進入一個更為廣闊的、豐裕的城市社會,才有更多機會成就自身價值,從而實現生活上的轉變。
從這一點說,《幸福的種子》延續了傳統鄉土小說的離鄉書寫,并著意建構了青年一代農民走出鄉村的兩種模式。第一種離鄉方式是“麥子式”的,這種方式也是“知識改變命運”的典型。作為整部作品的主人公,麥子的人生道路被賦予了強烈的主題價值。小時候的麥子就有異于同伴的聰明伶俐,上學之后成績優異,最后成為將軍寺村第一個大學生。得知麥子考上了大學,將軍寺人送來了雞蛋、西瓜、新衣服、新鞋子,甚至還有錢。面對這陣仗,麥子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惶恐,他來到將軍寺河邊,對三老太爺說:“他們問我這兒問我那兒的,好像我有什么本事似的,萬一以后我沒本事了,再回來咋有臉見人?”可能此時的麥子并沒有意識到,將軍寺人從他的身上看到了祖祖輩輩掙脫土地束縛這一理想的實現。無論是在重農抑商的傳統社會,還是在計劃經濟時代,通過讀書進入體制從而實現身份的轉變,才是真正意義上擺脫土地,而只要能夠擺脫土地,你就是最有本事的人。因此將軍寺人教育孩子會說:“你看看人家麥子,你就不會學學人家?那可是大學生,以后不用面朝黃土背朝天了。”麥子這一形象也代表了本世紀初從農村走出的一代大學生,他們大多數人學業優異,最終通過努力在城市擁有了體面的生活。隨著高考擴招,也有越來越多的農村孩子像麥子這樣離開農村。不過,即便如此,通過上大學走出農村的人畢竟是少數,整個將軍寺村的青年一代中,除了麥子也只有王明康做到了。
第二種離鄉模式則是“小玲式”的。相比麥子而言,小玲的離鄉之路充滿了更多的不確定因素,也更具有普遍性,這個并不討人喜歡的姑娘也更像是這個時代的“弄潮兒”。雖然相貌平平沒有特殊的學識或技能,但是小玲的內心深處卻始終涌動著一種奔放的熱情和不甘寂寞的欲望。與珍珍的文靜保守不同,小玲從一開始就對城市充滿了向往,并拼命通過努力奮斗走出農村。進入城市之后,小玲先是在工廠打工,而后與丈夫干事創業,事業剛成氣候卻遭到丈夫拋棄,一個人帶著女兒回到了將軍寺村。雖然這次變故險些將小玲擊垮,但是她并沒有被動地接受命運的安排。就在家里人為她張羅婚事的時候,小玲選擇了逃婚到南方重新開始自己的事業,還成立了玉玲瓏服裝公司。就像她對珍珍說的:“啥也不能等,啥也不能讓,我就要拼。我死也死在南方,死在城里。”[11]支撐小玲走下去的是那種“不信命”的精神,所以她不可能有麥子那樣強烈的鄉土觀念,對將軍寺也沒有過多留戀,她對麥子說:“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在北京是在家,在上海也是在家,跑到青海也是在家。”其實,也是靠著這一點,將軍寺村一批又一批青年像小玲這樣走出鄉村,在城市開辟了自己的生存空間。在小玲之前,較早離開將軍寺的是阿龍。阿龍年輕的時候就離經叛道,穿著時髦、不務正業、玩錄音機、開摩托車,在與父親爆發一場激烈的沖突后負氣出走。等他小有成就回到將軍寺時,卻失去了一條胳膊。小玲、阿龍代表了農村的大多數,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這一群體的離開,才帶來真正意義上的城鄉結構轉型。
在近百年的鄉土書寫中,“離鄉”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也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發生的一種不可逆轉的社會現象。大批農村青年離開鄉村進入城市,從而獲得了個人價值實現的更多路徑,城市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與此同時,鄉村也不復為昔日喧鬧的田園,大量社會問題也由此而生。孫全鵬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在小說中他這樣寫道:“將軍寺村這幾年有小伙子找不到媳婦的,其實不只將軍寺村,周圍其他村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哪個村子都有十幾個小伙子到了二十多歲還打著光棍。”[12]對于這一現象,孫全鵬顯然是不無困惑的。他深知農村青年一代必然是這個時代的受益者,可同時也是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承受者。當一批又一批農村的優秀青年離鄉之后,中國的農村又將何去何從,我們的故鄉還回得去嗎?這是孫全鵬的困惑,也是時代留給新一代鄉土作家的一個全新命題。
三、“返鄉”書寫與新牧歌建構
在鄉土文學發生百年之后,作家們又該如何繼續講述鄉土故事?學者張麗軍認為,新時代鄉土文學“不應一味延續以往的敘述模式,而應與時俱進,寫出新時代鄉土中國的新現實、新農民、新鄉村。”[13]如果說近百年的鄉土文學在以不同的方式講述“離鄉”的故事,那么新時代鄉土文學面對的一個核心問題則是“返鄉”書寫。“返鄉”并不是一種純粹的經濟學社會學現象,而是由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一系列國家政策推動的時代現象,同時還為一種難以割舍的鄉愁所牽動。在一系列國家大政方針的推動下,新時代鄉村并沒有淪為日漸衰敗的舊田園,而是成為洋溢著蓬勃朝氣的新農村。在麥子、河生、珍珍、小玲等人離鄉多年之后,將軍寺村又煥發出了新的生機:“將軍寺村與以前不一樣了,將軍寺河開發了,河道疏通后,水現在變清了。河堰上還種了垂柳,一排一排的。靠近將軍寺橋還建了碼頭,可以在這里坐船,暢游將軍寺河。村里的房子現在蓋得越來越高,裝修得也越來越氣派。”[14]
在麥子回村當第一書記之后,將軍寺村呈現出的是這樣一幅全新的牧歌式景象。小說在講述完將軍寺人離鄉的故事之后,并沒有戛然而止,繼而又講述起眾人“返鄉”建設將軍寺村的感人場景。至此,“返鄉”這一主題也在《幸福的種子》中清晰浮現出來。這里又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一批又一批的農民在離開鄉村成功實現自身價值之后,他們又為何返鄉,返鄉何為?要回答這一問題,也就要求作家能夠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從時代之變中重新發現鄉村、建構鄉村。正如有學者所說:“新時代文學要在鄉村振興的國家戰略實施中,發現鄉村、書寫鄉村、建構鄉村。”[15]這也正是《幸福的種子》的獨到之處。
《幸福的種子》的“返鄉”書寫其實是以麥子為中心的。作為將軍寺村的第一個大學生,麥子在周川市有著幸福安定的生活。體面的工作、漂亮的妻子、車子和房子,這一切無不意味著麥子真正完成了由農村人到城里人的轉變,因此麥子的返鄉也更能體現為一種國家意志。在駐村書記這一體制身份的支配下,以麥子為代表的從農村走出的大學生重新回到鄉村,成為新時代農村振興戰略的一線力量,承擔起從現實層面改變農村的使命。確切地說,正是麥子這一群體的歸來,才真正為傳統鄉村社會帶來了新的生機。扶貧工作的艱辛一言難盡,雖然作家在此處一掠而過,但是我們仍不難理解麥子所承受的痛苦。麥子的前任書記是一個大學生模樣的人,只在將軍寺村待了三四個月就離開了。很顯然,麥子是無法選擇離開的,因為這里是他的家鄉。扶貧工作的難度大不說,還要面對鄉親和家人的各種誤解,妻子一度要和麥子鬧離婚。即便困難重重,麥子還是有條不紊地開展著自己的工作。從村容村貌治理到幫助村民修房修院子,還幫助村里修了水泥路。將軍寺村的風貌終于煥然一新,麥子的工作不僅得到了鄉親們的認可,也贏得了妻子的理解。小說最后,麥子當著全村人飽含深情地說:“鄉親們,在我們將軍寺村,我找到了幸福的種子;在和大家一起奮斗追夢的路上,我找到了幸福的種子。”這也意味著傳統鄉土小說的“離鄉”書寫在新時代的終結,從農村走出來的優秀青年,在重新回到鄉村并將自己的人生道路與鄉村振興的時代大勢結合之后,終于找到了真正的幸福。
如果說麥子的回鄉為將軍寺帶來了新的生機,那么要真正講好新時代鄉土文學的“返鄉”故事,一個回避不了的基本問題必然是經濟問題。長期以來,鄉土文學作品中一貫存在的城鄉格局,從根本上講其實也正是經濟差異。對于這一點,從農村成長起來的孫全鵬顯然有著清醒的認識。《幸福的種子》最終呈現給人們的是一曲新時代的田園牧歌,它與傳統鄉土文學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于這部小說的落腳點在于鄉村振興。駐村書記麥子帶領大家在對將軍寺基礎設施進行改造的同時,也在思考如何為村里帶來經濟上的發展,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經濟落后的問題。他先是動員阿霞做起黃花菜的銷售直播,為村里的黃花菜打開了銷路。接著,又開發將軍寺村的漁產事業,還動員在外務工的父親老鮮回村經營集體魚塘。在麥子的努力下,珍珍的生父王新也帶著無盡的懺悔回到了將軍寺,并投資了紅薯淀粉的生產。人居環境的改善使人們對將軍寺村的發展充滿了信心,在利益和鄉愁的帶動下,越來越多的進城青年重新回到將軍寺村。小玲回鄉投資了服裝加工廠,河生建起了“河生漁業有限公司”,就連阿龍也回來了,還為村里的每條巷子安裝了路燈。在新的產業經濟的支撐下,將軍寺村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生機勃勃景象,也賦予了整部小說一種全新的牧歌情調。
“返鄉”書寫可以說是新鄉土小說區別于傳統小說的一個典型特征,它極大地彰顯了新時代國家對農村政策的優越性。在近些年涌現出來的眾多鄉土文學作品中,鄉村已經不再是藏污納垢之地,而是生態宜居、產業興旺,為個人提供充分的價值空間的全新的棲居之所。也就如孫全鵬在《幸福的種子》中所要表達的那樣,將軍寺村在時代大潮中并沒有成為一處日漸荒蕪的田園,而是一個蘊藏著無限生機的新農村,寄寓了人們對新時代美好鄉村生活的向往。很顯然,孫全鵬無意營建一個大團圓式結局,而是要正面回答那個引人深思的“故鄉”之問。新時代鄉村不僅是我們回得去的故鄉,也是我們最終的家園。
結 語
《幸福的種子》是一部表現豫東南大地新時代鄉村生活的代表性作品,它集中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時代之“新”,新鄉村、新鄉民和新牧歌構成這部小說的典型特征。通過一種“離鄉—返鄉”的故事結構,《幸福的種子》以青年一代農民個人的奮斗歷程成功地表現了將軍寺村在改革開放以后進入新時代振興的歷程。作為近些年出現的一部優秀作品,《幸福的種子》的藝術價值也應該被置于新時代文學的框架中加以考量。在這部小說中,孫全鵬表達的不僅是一種鄉愁,也是從新時代的經濟社會發展大局出發,對鄉村未來發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暢想,彰顯了鄉村的生機和活力。
參考文獻:
[1]魯迅.魯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255.
[2][9]胡平.幸福的種子·序一[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23:1,2.
[3][4]孫全鵬.幸福的種子·后記[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23:248,247.
[5][7]墨白.幸福的種子·序二[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23:7,5.
[6][10][11][12][14]孫全鵬.幸福的種子[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23:27,75,144,141, 225.
[8]丁帆.書寫新時代的鄉土文學——訪南京大學教授丁帆[N].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12-09.
[13]張麗軍.論新時代鄉土文學的現實主義創作[J].中國文學批評,2022(4).
[15]張麗軍.鄉村振興:新時代的新故事、新農民、新史詩[J].長江文藝評論,2022(1).
作者單位:昭通學院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