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祖國的喪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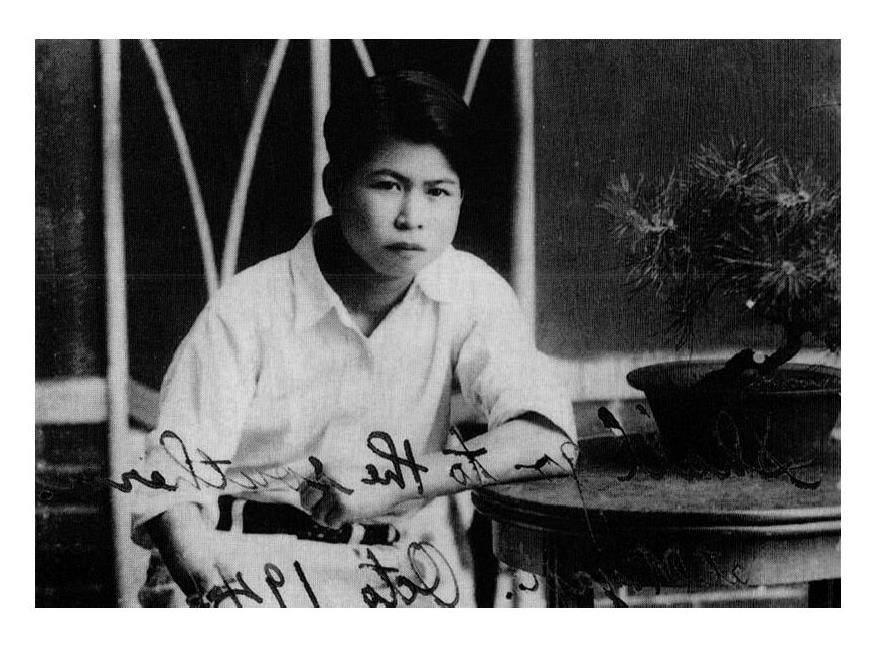
摘? 要:沖繩作家大城立裕在戰后初期創作的沖繩戰題材作品如《龜甲墓》《棒兵隊》,并未如本人所說毫無政治因素,而是作為創作時期沖繩政治狀況的一種反饋,是在復歸日本前對“日本人身份”的質疑。在早期的沖繩戰書寫中,大城立裕處處反映著戰時本應作為沖繩祖國的“日本”在戰爭中是如何一步步喪失其地位的,也有意無意間在作品中厘清沖繩與日本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大城立裕;沖繩戰書寫;《龜甲墓》;“祖國的喪失”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日本文壇上“第三代新人”登場亮相,在繼承戰后派文學的基礎上,“在文學創作中刻意表現戰后日本社會擺脫戰爭期間和戰敗后的混亂及貧困的陰霾而出現‘太平氣氛、經濟出現畸形繁榮的‘特需景氣下,人們對現實生活的不安和危機意識。”[1]1952年美軍結束對日本的軍事占領后,日本大踏步走出戰爭帶來的陰影,以戰爭為題材的作品漸漸淡出視野;被視為分水嶺的六十年代前后,“‘戰爭已經結束這一意識完全成為日常的概念”[2];然而就在沖繩文壇,戰后正醞釀著猛烈的能量,在五十年代以后噴涌而出,其中的領軍人物大城立裕在五六十年代先后寫下《棒兵隊》《龜甲墓》兩部作品,似乎是在提醒日本:對戰爭的注視與吶喊仍然回蕩在九州以南的群島之間。
一
為了對抗本土簡化、美化沖繩戰的做法,在刻意避開寫成“戰記類”小說的基礎上,大城立裕通過樸實的文字反映出戰時沖繩民眾真正的精神世界。《龜甲墓》講述的是在美軍炮轟、登陸時沖繩人善德一家在自家的龜甲墓中避難的故事;《棒兵隊》則是一個關于戰時由沖繩人組成的“防衛隊”被日本軍人歧視、猜疑的短篇小說。這兩部作品體現了大城立裕早期對邊緣的注目與對民眾的挖掘。如學者胡亞敏所言:“探討戰爭沖擊下的平民和平民眼中的戰爭,應該是戰爭文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3]1966年問世的作品《龜甲墓》就是這樣一部典型的作品,這部作品中唯一一次出現的日軍士兵甚至只是一具尸體。大城立裕在這部作品中刻畫了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沖繩普通家庭,善德一家人的群像既攜帶著共同體式的沖繩人特質,同時每個人的認知又有其自身經歷帶來的特殊之處。
《龜甲墓》的開場“如同一個黑色幽默”(本濱秀彥語):善德和妻子宇枝對即將到來的殘酷戰爭一無所知,“沖繩”“日本帝國”“美國”之類的宏大概念與“百坪院落中間那十五坪茅草房里的芝麻事”[4]85的瑣碎小事形成了巨大落差。這并非個例,而是沖繩民眾戰時的普遍反映。長久以來,被“漸進主義”一步步同化的沖繩人,“只有在送新兵出征、迎陣亡士兵遺骨歸來的日子里才會偶爾在腦袋里過一下”“什么是沖繩縣、什么是日本帝國、什么叫美國”[4]85之類的問題;滑稽的言論(例如將“打艦炮”說成“大煎包”)與可預見的悲劇結局、緊張的情節與荒謬得與之不相稱的反應(如宇枝逃難前還特意去喂豬)在開頭形成鮮明對比。小說中有這樣一段話體現這種對比之強烈:
說是要打仗了,要開戰了,可是直到走出家門前,這一家子壓根兒沒找到大戰臨頭的感覺——就像是熟睡中被人猛地踢了一下腦殼兒似的,眼下,他們只是愣頭愣腦地跳將起來,稀里糊涂地團團轉而已,要到回過神來意識到天亮了,恐怕還得等上一陣子。就這么優哉游哉地,一家人來到了村里的空地。直到這時他們才猛然發現,原來整個村子都早已沉浸在打仗的氣氛里了。[4]92
就像在熟睡中驚醒,沖繩人稀里糊涂地進入到戰爭中,似乎是在暗示無知和可悲的普通民眾在戰爭期間沒有絲毫改變。《龜甲墓》中群像整體所反映的,明面上是沖繩自戰前以來受到日本壓迫的總和與最終呈現,但同時又潛藏著對戰后重蹈覆轍的憂慮。大城試圖通過群像呈現出沖繩民眾的愚昧狀態,事實上也是對當時現實狀況的一種隱喻。誠然,相比起他的代表作小說《雞尾酒會》,大城立裕更看重這部作品的原因在于他將沖繩問題視為文化問題(關于大城立裕所說的“沖繩問題是文化問題”,大野隆之認為文化并非指如琉歌、組踴等文化遺產,而是指沖繩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及之處,包含食文化、生活習慣云云”[5])的先見之明,然而作者并未完全抹殺文字間的政治意圖。1956年大城在《沖繩文學》雜志策劃的座談會“出發之際——戰后沖繩文學的諸問題”中說過:
我們這一代人自懂人情世故以來,一直徘徊在陰暗的山谷中,無法客觀地看待自己所受的折磨,也不知道到底該往哪里走。(這一代人)對此進行(各種各樣的)摸索,對我來說,(我的方式)就是文學。[6]
大城立裕的創作是對走出皇民化教育下“陰暗山谷的摸索”,是對擺脫“祖國的喪失”所受折磨的前路之嘗試。日本學者柳井貴士說過:“《棒兵隊》《龜甲墓》等作品既不是沖繩戰的檔案,也不是悲劇的告白;可以說是含有從論爭中意識到問題的作品群。”[7]也就是說,大城立裕是通過作品本身再生產問題意識。如果將前引作品片段中打仗、開戰之類的詞語替換為“本土復歸”來看,也許就能理解大城遲至戰后20年才使用沖繩戰這一題材的良苦用心:對于盲目追求復歸日本的浪潮,大城立裕既通過沖繩戰警醒沖繩人歷史尚未遠去,又是將戰時盲目信仰“虛無的祖國”的愚昧和彼時回歸日本的熱潮形成某種互文性的聯系。在這部作品問世后,無論影響直接與否,“一直盼望‘祖國復歸的沖繩人,隨著沖繩施政權復歸開始提上具體日程,開始冷靜地看待過去記憶中所憧憬的‘祖國的現實狀態”[8],大城的作品就像一盆冷水適時地澆在盲目盼望復歸的沖繩人身上。
二
善德一家子的群像是戰時沖繩普通家庭的生動寫照,這種窘迫的處境也是時至六十年代沖繩人所處困境的一種變體。從大城立裕刻畫的群像之中的個體,如善德、榮太郎的身上不難發現,大城立裕的的確確將何為逐步喪失的“祖國”這一問題搬上沖繩文壇。這一問題的揭示路徑,是與對戰前同化教育的思考密切相關的。沖繩人“遭遇”戰爭具有無意識但又有著宿命性的意義,這是因為戰前同化教育只有在某種極端情境中才被揭開假面:需要通過戰爭中帶有悲劇色彩的死亡才得以實現。小說中大城對日本化的教育持厭惡態度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當過小學老師的堂弟善賀還是道貌岸然的議員,都是受日本戰前同化主義教育的產物。他們精致的利己主義與善德一家代表的沖繩傳統的共同體式文化格格不入,“以天皇制為中心的道德教育的淺薄”[9]99,在兵荒馬亂之下顯得面目可憎。善賀未經允許偷紅薯、議員背著一筐豬仔逃難,在善德眼里都說得上是“背信棄義行為”,背棄的無疑是沖繩民眾對于日本同化教育、日本帝國統治之信任。他們的社會地位代表著本土對沖繩物質上的拉攏,同時也象征著沖繩內部的自我殖民。當他們這批人精神崩壞的時候,也就意味著聯系沖繩與本土之間紐帶的斷裂。
小說中提到的海軍大將廣告牌也是大城立裕的精心安排:
……看來,善德已經下到豎在土堤上那塊畫著海軍大將的仁丹廣告牌腳下了。榮太郎朝那個方向趕過去,抬頭看了海軍大將一眼。這時恰好出現了一道閃光,借著光看過去,這海軍大將,戴著明治年代的帽子,好像是一個還活在太平盛世的人物似的。[4]125
明治年代的“海軍大將”似乎在提醒著讀者:正是在明治天皇在位期間,琉球王國被日本一步步吞并成為沖繩縣。“海軍大將”看似守護著沖繩這片土地,實則是一種控制與規訓。沖繩戰中的現實是日本軍隊非但沒有保護當地百姓,反而歧視、迫害甚至要求當地居民“集體自決”。固然這個廣告牌幫助榮太郎免于滾下長堤,但其作用也僅限于此,暗示著本土的產物在戰爭期間并不可靠,沖繩的命運也并非虛無的“海軍大將”所能拯救。廣告牌在結局中被炸得不見蹤影,不僅“在預示日本以失敗而告終的結局”[10],也是在昭示沖繩被殖民化的失敗,更是將本土虛構出來的“祖國”這一幻想徹頭徹尾粉碎的隱喻。
同為戰前出生、年少時經歷戰爭的沖繩知識分子伊禮孝回憶:“當時作為天皇臣民的自己,從母親懷抱中就開始被灌輸‘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的‘大日本帝國國體的偉大和自豪,這種念頭在‘國民學校中被遞予木槍時就清晰地成型。(所以戰后)彼時誰會自我反省呢?”①就是這樣的一代人,戰爭期間對“祖國”的堅定信仰與戰后的反思之間形成尖銳矛盾。更為諷刺的是,沖繩戰在尚未發生之前,被許多沖繩人視為變成“真正的”日本人的跳板。如小說中的善德,對于阿竹前夫以皇軍士兵身份戰死的結果明顯持積極態度,認可通過入伍甚至為國捐軀這種方式來同化成為日本帝國的一份子。另外,善德對于榮太郎想將那具日本士兵的尸體拋遠點的建議有過如下言論:“那可不行,會遭報應的。這當兵的,好歹也是替咱們去為國家打仗的。他家里也有爹媽不是?那么做,我們會遭報應,炮彈會一窩蜂地朝這兒飛的。”[4]118由此可見,大城筆下的善德就是戰前世代的一個象征,從中可以看出老一輩人對“祖國=日本”的觀念根深蒂固。除此之外,小一輩的榮太郎也是群像中極具代表性的人物。在中國戰場待到盧溝橋事變后回來的他,從內心深處就對戰爭、暴力抱有期許和幻想,盡管面對的是美軍艦隊的炮轟,但他“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只覺得全身有一種滋滋作響的神奇力量在膨脹——那是性欲!”[4]11這種催生出來的生理快感的根源在于年少時記憶中雄赳赳氣昂昂的日本聯合艦隊,是他以為能夠“護衛國人安全的力量的榮光”。榮太郎感受到“詭異神秘的生理機制”是對暴力的渴求之變體,而推崇戰爭暴力的源頭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戰前為沖繩灌輸的軍國主義式教育,從而強制形成對“祖國”的認同。在見到那具日本兵尸體后榮太郎仍嘴硬不愿承認日本將會戰敗:“逃是要逃的,但最后我們肯定會贏。”[4]
三
如日本學者本濱秀彥所言,《龜甲墓》是從沖繩人的角度來敘述的,而非從日本或美國軍隊的角度[11];這種邊緣的視角反而提供了極大的能量,與本土的沖繩題材小說形成鮮明對比。大城立裕通過許多細節表達出自己的立場:沖繩并不天然地應該屬于日本,日本這個“祖國”也并非是不可置疑的概念——這提醒60年代后期經歷著略顯狂熱的復歸本土運動的沖繩人:復歸的未必是理想中的“祖國”。
同樣的,《棒兵隊》雖然篇幅不長,卻也有著相似的張力。大城立裕拒絕任何“沖繩應該是什么樣”的想象,而是從真實出發,早在1958年便將戰場上日本對沖繩的歧視這一題材曝于眾目睽睽之下。與《龜甲墓》相似的是,短篇小說《棒兵隊》也是以人物群像的方式呈現,并不集中在單一的某個人物身上,其中的富村、久場乃至赤嶺都可以被視作主角。有學者因此認為,大城立裕塑造人物的重點在于幾個人物的立場(位置)和他們彼此之間的關系[9]92,而非人物本身。其特點就在于,群像既反映出沖繩人戰時的某種精神共性,又借助每一個個體發出共性中的多重聲音。“如果(沖繩人)所屬的‘共同體產生變化,(他們之間的)‘位置和‘距離也會隨之改變——如此說來個人就會在這種種‘位置和‘距離的復合之中確認自我。”[12]
《棒兵隊》這樣一部作品的故事情節非常簡明易懂,其中關于沖繩戰中本土日本人對沖繩人的奴役與歧視、懷疑與屠殺,在陳世華的《“國家意識”的徒勞——〈棒兵隊〉中沖繩人的境遇與國家認識》一文中有著詳盡的闡釋,在此不作贅述。然而對大城立裕這類作品的解讀重點“不是討論沖繩戰本身,而是討論戰后沖繩戰的討論方式,討論作為歷史的沖繩戰認識的變化”[13]。每一個人物的聲音都是一種討論方式,大城立裕復調一般地讓這幾種聲音共同重構起沖繩民眾戰時整體的精神世界,足以看出五六十年代期間大城立裕試圖扭轉沖繩方面歷史認識聲音單一的處境,也給予更多條思考“祖國”為何物的道路。這樣的創作思路在《龜甲墓》中得到成熟的體現,因此也不再贅述。而以這種路徑來理解作品的歷史意義,無疑大大豐富了文本的張力。
關于對五六十年代沖繩戰書寫的背景,沖繩史學家新崎盛暉做過這樣的總結:“對于沖繩的人們來說,沖繩戰的失敗,首先是被內化于自身的國家的崩潰,其次才是對于美軍的現實敗戰。這一雙重失敗,擁有非常大的意義。沖繩的戰爭責任問題、天皇制意識形態的批判問題、國家觀念的批判問題等等都必須從對于這一失敗的總結開始。”[14]“內化于自身的國家的崩潰”,毋寧說是“祖國的背叛”,或者說是“祖國的喪失”。從“祖國的喪失”引發的關于“祖國”和自我身份的思考,是貫穿大城立裕早期寫作的重要線索,也是他沖繩戰書寫的根源所在。沖繩戰不過是一個將“祖國”這種東西的腐朽和虛偽暴露出來的契機——正如《棒兵隊》中無數歧視和不信任最終醞釀出的結局那樣,本土的逃兵舉槍射殺了他自認為是間諜的沖繩老人赤嶺——此乃日本自從吞并沖繩以來一切暴力的集合與歸宿。由此可以窺見的是,大城立裕語焉不詳的“祖國”,因戰爭書寫的需要匆匆生成,又因為戰爭對暴力的無情揭露而匆匆瓦解。
四
正如美國學者博米克所言:“從其漫長的職業生涯伊始,大城立裕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沖繩和沖繩人身上,創造了一套與明治、大正和戰前時期的小說截然不同的文學作品。當時作者們以東京為榜樣,大多數都回避書寫他們最了解的內容——他們在沖繩的生活經歷。鑒于前幾代作家對沖繩島缺乏關注,大城對沖繩在日本中的位置的審視和質疑就更加引人注目……大城對其祖國的注視都是永恒不變的。”[9]89大城立裕對日本作為“祖國”的懷疑,正是此悖論性的展開。不管是《龜甲墓》還是《棒兵隊》,大城立裕都為沖繩人預設了一個模糊的“祖國”概念,然而殊途同歸的是,日本并不是大城立裕理想中的“祖國”,對沖繩人而言,“祖國=日本”的公式并非不證自明的。由此可見,大城立裕早期對沖繩戰的書寫,就是一個有意無意試圖厘清何為“祖國的喪失”問題之過程,它對日本作為“祖國”認同的失敗,也是一種產生新認同道路的開啟。
注釋:
①伊禮孝《從沖繩透視“祖國”》,參見http://www7b.biglobe.ne.jp/~whoyou/hondfukkinogensoh.html
參考文獻:
[1]葉琳,呂斌,汪麗影.現代日本文學批評史[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207.
[2]松原新一,等.戰后日本文學史·年表[M].羅傳開,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494.
[3]胡亞敏.戰爭文學[M].上海: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21:5.
[4]大城立裕,常芬.龜甲墓——方言風土記[J].世界文學,2020(4):85-135.
[5]大野隆之.「大城文學と沖縄の生活」[M].//黒古一夫編.大城立裕文學アルバム.東京:勉誠出版,2004:113.
[6]福間良明.焦土の記憶[M].東京:新曜社,2011:131.
[7]柳井貴士.沖縄戦をめぐる內部葛藤の物語:大城立裕「棒兵隊」論[J].沖縄文化研究,2017(44):131-157.
[8]岡本恵徳.沖縄における戦後の文學活動[J].沖縄文化研究,1975(2):191-230.
[9]Davinder L. Bhowmik, Writing Okinawa:Narrative Acts of Identity and Resistance[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8.
[10]關立丹.沖繩戰背景下的傳統敘事——讀大城立裕的《龜甲墓》[J].世界文學,2020(4):135-143.
[11]Motohama, H., Writing at the edge:Narratives of Okinawan hist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literary texts of Oshiro Tatsuhiro[D].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5.
[12]岡本恵徳.水平軸の発想ーー沖縄の「共同體意識」について[M].//谷川健一編.沖縄の思想.東京:木耳社,1970:131-192.
[13]櫻澤誠.「沖縄戦」の戦後史―「軍隊の論理」と「住民の論理」のはざま[J].立命館大學國際平和ミュージアム,2010(11):19-28.
[14]徐勇,湯重南編.琉球史論[M].北京:中華書局,2016:224.
作者簡介:忻雨帆,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沖繩文學、日本戰后文學。

